
民主新论 下卷 古典问题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37.12 5.4折 ¥ 69 全新
库存48件
作者[美]乔万尼·萨托利,冯克利 阎克文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0159
出版时间2020-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9元
货号29171300
上书时间2024-11-0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民主新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
在下卷“古典问题”中,萨托利对经典的民主议题作了全面概览,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近现代民主的区别。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等术语及其相关联系进行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关键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
作者简介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1924— )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946年取得佛罗伦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76年接任阿尔蒙德的职位任斯坦福大学专职教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特-史维泽人文科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广及民主理论、政党制度、宪政制度、治学方法等方面。除《民主新论》之外,其他代表作包括:Democratic Theory (1962),Tower of Babel (1975),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97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1984),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1997)等。
译者简介:
冯克利,1955年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翻译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译著包括勒旁《乌合之众》,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论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布坎南《立宪经济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
阎克文,1956年生,曾任职于新华社,现为自由撰稿人。重要译著包括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等,代表性的作品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经济与社会》。
目录下卷 古典问题
- 什么是民主?定义、证明和选择
9.1 定义是任意的吗?
9.2 对惯例的批判
9.3 作为经验载体的词语
9.4 求证
9.5 比较评价
- 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
10.1 同名不同系
10.2 直接民主或城邦民主
10.3 新旧个人主义和自由
10.4 近代观念和理想
10.5 认识上的颠倒
- 自由与法律
11.1 政治自由与其他自由
11.2 政治自由
11.3 自由主义的自由
11.4 卢梭的法律至上说
11.5 对自主的批判
11.6 影响递减律
11.7 从法治到立法者统治
- 平等
12.1 一种抗议性理想
12.2 公正和相同性
12.3 前民主的平等与民主的平等
12.4 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环境
12.5 平等主义的原则、对待和结果
12.6 平等的化
12.7 自由与平等
- 放任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
13.1 重合
13.2 不幸的时差
13.3 财产与占有性个人主义
13.4 自由主义的定义
13.5 自由主义民主
13.6 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
13.7 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
- 市场、资本主义、计划和专家治国论
14.1 什么是计划?
14.2 什么是市场?
14.3 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14.4 市场社会主义
14.5 民主计划
14.6 民主、权力和无能力
14.7 专家的作用
14.8 科学的统治
- 另一种民主?
15.1 卢梭和马克思的美好社会
15.2 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观
15.3 人民民主
15.4 民主专政论
15.5 民主和爱民
15.6 词语之战
- 意识形态的贫困
16.1 理想的衰竭
16.2 不可避免的与可以避免的
16.3 对观念的无端迫害
16.4 求新癖和超越癖
16.5 结语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内容摘要《民主新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
在下卷“古典问题”中,萨托利对经典的民主议题作了全面概览,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近现代民主的区别。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等术语及其相关联系进行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关键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
主编推荐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1924— )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946年取得佛罗伦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76年接任阿尔蒙德的职位任斯坦福大学专职教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特-史维泽人文科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广及民主理论、政党制度、宪政制度、治学方法等方面。除《民主新论》之外,其他代表作包括:Democratic Theory (1962),Tower of Babel (1975),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97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1984),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1997)等。
译者简介:
冯克利,1955年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翻译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译著包括勒旁《乌合之众》,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论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布坎南《立宪经济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
阎克文,1956年生,曾任职于新华社,现为自由撰稿人。重要译著包括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等,代表性的作品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经济与社会》。
精彩内容16.1 理想的衰竭
商品的欢愉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缺程度。这也适用于“好东西”。当我们的所有足够了,我们便满足了。不过一旦足够,满足便会引起不满足。一些东西的足够,唤起我们对另一些东西的欲望。西方人目前已有足够的自由,于是便追求各种福利和保障,因此“推崇”关心他的各种需要的保护性国家。但是需要会无止境地上升,后必须加以满足的已不再是需要,而是欲望。西方人的理想便是沿着这个方向在改变和衰耗着。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一书的副标题是“论政治观念的衰竭”。那么,正在衰竭的到底是什么?是意识形态,还是观念?随后发生的论战很难说澄清了这一问题。由于对意识形态这个观念缺乏一致和深入的研究,使得论战者大都是在相互谈论历史。这场论战随着校园革命一起退去,到了1960年代末,人们都心照不宣地承认,意识形态的巨浪已驳倒了那种预测。当人们踉踉跄跄地走过1980年代时,我们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衰竭了?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贮水池,那么是观念的贮水池喽?我很快就要谈到观念,但首要的事情就得先说。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紧随我们不去的衰竭过程是理想的衰竭。西方人的理想越来越不像“理想”了,也就是说,就理想的道德涵义而言,它越来越不是价值信仰了。可以说,理想危机——这是无可怀疑的事情——从本质上讲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伦理危机。
由于许许多多不完全令人信服的原因,关于人这种“道德动物”的后一种强有力的西方哲学,是康德的伦理学。也许道德离开宗教就无法自己生存,也许进步(这种理想)已经使我们改弦更张,而技术进步使我们越来越像个功利主义的自顾自的动物。虽有这些原因,事实是西方人已一代甚于一代地只有经济头脑了。光荣革命、费城会议、法国革命以及1848年革命的领袖们,很难被描绘成把政治理解为“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的人。但是当拉斯维尔把政治归结为“得到什么”的问题时,没有人对这种粗劣的观点表示惊愕。1950年代,当雷蒙·阿隆为意识形态终结的预言提供理论根据时,没有人对他完全从经济上加以论证的事实大惊小怪。阿隆写道:“在成长的经济中,分配问题已获得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意义。总的财富曾被认为是个几乎不变的量……如果有人拥有太多,这就意味着那是取自于别人。但是当集体财富每年都以一定的百分比增长时,增长的节奏和速度便比再分配问题更为重要了,即使对弱势人群也是如此。”
从本质上说,过去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有一块蛋糕,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谁来切蛋糕以及如何切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蛋糕的尺寸,政治学研究的是切蛋糕,即分配的问题。如果蛋糕尺寸和吃蛋糕的人数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如何切蛋糕的政治问题便成为主要问题,或至少是可以用不同方式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容易地提供更多的蛋糕或更大的蛋糕,制作更大蛋糕的经济问题便排挤掉了谁应多分一点的政治问题。可见,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政治,在未来的世界里是次要的。大家会慢慢认识到,重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蛋糕的尺寸。这种论点紧要的前提是,蛋糕尺寸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无限变大。但是,蛋糕能够无限而迅速地变大吗?富足的时代变得永无止境了吗?工业技术革命能够维持下去并且席卷世界,为一切人增加财富吗?这种论点的逻辑也许无懈可击(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它的事实前提已经大为动摇了。
增长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加速,尤其是有限的非再生资源。具体而言,由于工业革命接踵而至,矿物能源(煤、石油、天然气)一直在以指数级的速率被消耗着。从长远观点看,我们一直很清楚廉价能源会在几十年内消耗殆尽。无论尚未探明的深层矿物资源、核能电厂以及技术发明(即来自风力、水力和阳光的可再生能源)能否在未来提供给我们,总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过去二百年里维持着工业进步这架机器运转的廉价能源,就要变得越来越贵。且不论能源匮乏,单以成本而论,已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以过去的趋势寄望于未来。如果注意到另一些现象,这一观点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长也在糟蹋着我们的可再生资源—森林遭到毁灭,农田变成沙漠,水的供应也将日趋紧张。我们必须应付廉价能源的结束,还要支付各种生态灾难这张客观存在的数额巨大的账单。显然,这将是一张开销甚大的账单。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至少是直到石油冲击震撼了我们之前——“有组织的匮乏”已被一个富足的文明取代,或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会是如此呢?经济学家们似乎都在预言持续的增长,而不考虑长期的资源条件和增长的资源限度。今天,我们希望但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能拯救我们。既然我们只剩下希望了,就让我们这样希望吧。但这样一来,时间就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问题就成了:我们为使科学技术及时拯救我们而迫切需要的时间,会被不断加速的增长更迅速地“消耗掉”。零增长和稳态社会肯定不是令人动心的设计,而且可以说,它只有着购买时间的优点——让科学技术有时间用可再生资源取代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既然时间至关重要,那么购买时间同样重要。
如果说增长论的经济学家没眼光,说话不着调,社会科学家也好不了多少。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预言无论想表达什么,从一开始人们就不难看出——无须事后聪明——它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局限性的短期预测。它在空间上有局限,是因为只有那些经济产出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社会才会心满意足。它在时间上有局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不是后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类与属加以区分,即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范畴同它的各种历史表现——比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就此而言,在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浪潮和政治救世论有可能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贸然把一切寄托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工业民主国家中工业和平的长期持续上。富裕社会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劳动(就其奋斗、劳累和受苦的本来含义而言)——有闲暇者较不易于受到主义的袭击,这样说不无道理。但我们不应设想对富足生活的初反应也会是对富足习以为常的后代人的反应。至善论和失望情绪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是剥夺性的低级阶段)而来,闲暇时代的“大空虚”注定会导致新的反叛、新的反抗态度以及一些不可预见的难题。闲暇使我们集聚起我们不知如何消耗的精力。如果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会干些什么?
大概我们正在接近各种意识形态代用品的终结。就此而言,正在接近幻想、受代用品维持的幻想的终结。随着蛋糕不再在它的食用者的面前晃动(事实上这从未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多数地区出现过),我们会渐渐明白,非经济的病症是不能用经济疗法治好的。更一般地说,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很难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把政治行为等同于经济行为,我们告诉自己,政治说到底是个获取的问题,我们在追求着金凯德(J. Kincaid)生动比喻的“肉体政治学”,即只以“苦乐”为标准的美好生活。既然人没有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天性,而是他设想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经济动物。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卖力地干着这种事。按康德的说明,道德王国是自我奖励的“无私行为”的王国,是不以物质报酬为动机的王国。社会科学家却告诉我们,“利益”意味着“动机”,因此,所谓无私利的行为纯属无稽之谈,那等于无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动机,我们就没有行为。伦理学不是“交换”的领域,道德人的付出并不是为了交换什么。但是,据说一切都是交换。道德人的准则是,不希望他人施于己者,也不施于他人。相反,我们却想方设法把自己不愿承受的担子转嫁给别人。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主张它的成员不承担任何义务,而我们却在日甚一日地主张我们是“权利人”,有权领受这个那个,不断提高的期望就像一切革命一样,很快造成了一个权利人的社会。
道德人被推到后台,出场的是“理性人”。当然,功利主义传统提供的理由是,伦理不过是每个人开明而长远的私利。诚然,康德的伦理学也属于理性(不是宗教的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道德学说。因此可以认为,由道德动机所成就的,同样也是由理性论证所成就的。例如,假定我们需要经济增长,我们作为理性的和精于计算的动物就必须注意到,增长的放慢和趋于消失并不是由分配和消费欲望的增长造成的。同样,也可以从理性上证明,社会利益需要社会成本,因此,没有义务的权利,没有付出的获取,都是不理性的表现。的确如此,但这只能在日积月累的结果中看出,因此肯定大大超出了我们个人的处境和视野。作为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关心社会福利是不理性的;例如,把时间浪费在投票上可能是不理性的,为我们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福利付钱是不理性的。同样,组织越大,其成员就越没有理由分担它的责任和促进它的集体目标。 简言之,人人都成为社会寄生虫才是“理性的” (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剥削别人对他要有利得多。
我刚才说,我们正在接近代用品的终结,我们已走到了代用品消失的极限。我认为,这些代用品之一就是道德也符合理性这一观念。它已不起作用了。我们要求用理性人代替道德人,结果我们给两者都提出了不可企及的高标准。说出实情的时刻已拖延良久,现在终于到来了。这个真理就是,如果没有“善”,也就是说,如果把政治归结为经济,理想归结为意识形态,伦理归结为斤斤计较,就不会有善的社会。即使政治不是伦理,社会机体确实需要政治人之外的道德人。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的衰竭,是伦理政治理想的衰竭,这些理想曾养育了西方文明,随后又导致了我们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当然,技术进步本身是随着理想的衰竭而崛起的。但我不愿像普遍认为的那样,说什么“那不过是我们的文明所赖以存在的工业基础中的瑕疵”,或者“一个受机器运行支配的社会,一个依靠工厂和官场的例行公事,为个人的炫耀性消费洋洋自得的社会,终将不足以维持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的社会“受机器运行支配”,诚哉斯言。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我们受机器支配,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头脑过于发达,因为我们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伦理观念,失去使我们得以生存的忠诚。所以我要强调说,技术进步是我们理想衰竭的强大伴生物(不是其首要原因),这还有另外两层意义。首先,发达工业社会的富足造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坐享其成的”社会。其次,技术进步导致了人口过剩和过度的组织化,即一种个人变成单纯的数字,日益感到软弱和压抑的局面。我们要勇于正视它:这是些有利于滋生否定与反叛的理想、有利于导致消极而非积极理想的条件。开放社会,或达伦道夫所说的“提供机会的”社会,要以一个没有喝醉的社会为前提,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很难说是这样一个社会。
此外,历史已把我们搞得太疲劳了。我们筋疲力竭,无所适从,忧心忡忡。我们还得承认,我们也满怀恐惧。用金斯利·马丁(K. Martin)的话说,对进步的崇拜已经“变成了加速前进的福音书”。自从法国革命和次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向前冲刺,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使人无暇进行调整。另外,“高速运动令人兴奋,使他忘了……问一下自己正在朝着哪个方向狂奔。”为糟糕的是,我们被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搞得伤心欲绝。我们摆脱了真正的战争状态,竟又径直落入累人的冷战气氛。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垮掉了,我们生活在对明天的恐怖中,人类的自我毁灭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景象。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于一场血腥残酷的内战之后的1651年。对于霍布斯和他的许多同代人来说,目标似乎就是获得社会和平,为了获得它,霍布斯构想出了全能国家的学说。如果做一点适当的限制,我们也可以以此类比我们的处境。处在衰竭状态中的我们,也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取和平。加速前进的福音书带给我们的只是物质进步而非道德进步,于是我们便没命地抓住这种实在的利益。不管代价如何,我们请求生存受到保护;为了获得这种利益,我们甚至会再一次像霍布斯的同代人那样,乐于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许诺阻止世界末日大决战,并对我们示以关怀。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更不用说它的失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受着“物欲”的损害与支配,而且满怀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那些关于“真正的”民主、“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正义的狂呼乱喊,便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那不过是晚会散去的告别焰火罢了。事情的真相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自由,我们根本就不再欣赏那种自由了。我们并不看重真正的民主,我们看重的是那个分配利益、满足需要的国家。我们不关心自由和民主,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物欲熏心;我们疲劳了,说到底,not inullac upido(知者方贪),我们厌倦了过去熟悉的东西。不过,我并不十分相信这就是后的确诊。
媒体评论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 Yale University):
每个真正对民主理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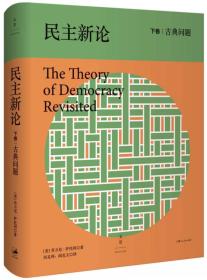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