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明风华 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57.13 5.3折 ¥ 108 全新
库存33件
作者陈宝良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9787553816463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08元
货号29494158
上书时间2024-11-0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洪武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
华夏儿女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册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英雄。
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以及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础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为旧的社会观念所容,必然会同旧的社会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具体表现为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闲暇时间渐多、旅游风尚日盛的今天,这句话已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苏州的闻名并不仅仅因人造的园林之胜,杭州的名扬天下也不只在于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这两座城市中的人。
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苏州人又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为海内所效仿。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概称为“苏样”;人们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记载,有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一时想不出如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
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地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人又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北京、南京又是如何呢?明代城市中曾流行一句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说的是出生在苏州的沈万三。这个沈万三究竟是死于元末,还是卒于明初,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即使如此,在民间传说的话语体系中,他曾因修建南京城而着实风光了一番,并因家有聚宝盆而留下了富可敌国的盛名。北京的枯树年头一定很久了,当然是虬曲的,或许还是一株折干掉枝的歪脖子老槐树,但不知在哪条胡同内,史无明载,不敢妄测。不过,南京、北京绝不是一个沈万三、一棵枯树所能代表的。他们或许一度是南京、北京的象征,但绝非这两座城市生活的全部。南京的扬名,除了六朝古都的名头、虎踞龙盘的形势,很可能与秦淮河两岸的河房、河中的桨声灯影以及旧院中的名姝有关。北京城给外方人留下的深的印象,也莫过于棋盘街的车马人声,灯市、宫市的古玩、方物,新帘子胡同的小唱、娈童,以及皇城外的“私窝子”。
扬州有“盐都”之称。盐为一日三餐所必需。徽州盐商云集于此,除了求利,恐怕也是看上了扬州是烟花粉黛聚集之地。他们心中想的是二十四桥的风月,那里曲房密户,妓女逐队倚门卖笑,是销魂的好去处。要不然,就是看上了扬州懂得琴棋书画的“瘦马”,娶回去做小妾,以尽于飞之乐。
开封城的繁盛,早已是北宋年间的旧事,大相国寺也只不过给人留下了淡淡的一点回忆。明帝国内的百姓看上开封,也许是因为城内设有“淫店”,从那里可以买到淫乐的稀奇古怪的淫具、春药。
“苏州样,广州匠。”广州工匠的产品在明代很闻名,不过,若说起知名度,还应推广州濠畔朱楼。据说在盛平年间,濠畔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倘若不信,请看孙典籍的《广州歌》:“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粉腻生活,亦可想见。
中国人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留下了现在名扬四海的“孔府菜”。清帝国的皇帝被赶下龙椅后,清宫菜满汉全席、民间菜烤鸭却被保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明帝国倒是颇有些遗憾。明宫内的名菜烹龙炮凤,大可与满汉全席媲美;从当时的风靡程度来看,杭州的烧鹅也绝不比北京的烤鸭逊色。两者的失传,实在是件憾事。否则,今天的老饕们在大饱口福之余,也可谈谈明宫掌故、杭州风情,以助雅兴。
大家都知道,城市是被一堵甚至几堵城墙围起来的空间。城墙里面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峨冠博带的士绅;有走街串巷,打着各种响器,一年四季吆喝市声不同的贩夫;有高捋袖口,攮子秤锤不离身的无赖光棍;有衣不蔽体,存身冷铺、悲田院的叫花子;有穿金戴银,一身妖气的名姬、歪妓。
不过,在明帝国的城市人中,惹眼的莫过于商人、妓女。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明代中期以后,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此不疲。张来仪《静居集》中有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如此看来,这不仅是商人生活的剖白,简直可以看作一曲“贾客乐”。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社会声誉,光耀门楣。汪道昆《太函集》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商人已不满足于掌握“贾道”,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博取科第,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商人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墨客,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他们在醉饱之余,对精神享受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
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商人的地位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据说,被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曾对一位徽州的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朋友却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王世贞无言以对,只好付之一笑。这则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他的朋友眼界更高,一言道破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而羞于言利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
曾经与士子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剧的妓女,在从良上也开始转向拜金主义。文名颇盛的状元钱福,息归田里后,听人说江都某妓动人,就整装去江都,但此妓已嫁盐商。后因贾人重状元才名,才得以与此妓一见。为此,钱福只好撰一绝句嘲讽这位妓女:“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诗句固然在嘲弄中透露出惋惜之情,但更多的还是自我解嘲。
正德至万历年间,明代城市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物价甚贱,不妨开列一张正德初年南京市面上的物价单子:
猪肉每斤好钱七文或八文;牛肉每斤四文或五文;水鸡一斤为一束,只须四五文;莲肉用抬盒盛卖,每斤四五文;干燥而大的河柴,银一两,可买三十担;鱼、虾每斤四五文。
很显然,当时的柴米油盐、鸡鸭鱼肉,诸般食用之类,无一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银子。权贵富豪乃至大贾,当然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户人家,肩挑步担之流,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也可过得一日了。到了晚上,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些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活脱脱一幅升平安乐图。
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物价骤贵。再开一张当时南京城内的物价单子:
鹅一只,钱五百余文;鸭一只,钱二百余文;鸡一只,钱二百余文;猪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羊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牛肉一斤,钱二十余文;驴肉一斤,钱二十余文;红布一尺,钱十五文;绿布一尺,钱十五文。
至崇祯年间,李自成已经起兵,烽烟四起,可绍兴城中的民众还在醉生梦死。张岱《张子诗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游春曲》,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赶到寓山(山阴祁氏名园),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轻薄少年穿梭于姑娘中间,乘机向她们挑逗,弄得她们腮红颊涩,头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阳偏西,船上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游人还在码头上流连忘返。
当李自成的军队攻打北京城的炮声一响,北京人惊醒了,他们的升平梦破碎了,顿感颠沛流离的日子离他们不远了。北京陷落以后,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是清兵大举入关,八旗兵的铁蹄践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
甲申、乙酉之际的两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感伤题材。想过去,金陵、杭州,选妓征歌,挟弹吹箫,一片繁华。看今日,时移势易,歌台舞榭,化为瓦砾。京城的繁华,转瞬成了过眼烟云;繁盛的秦淮,也已鞠为茂草;莺歌燕舞、游人不断的西湖,更是变成饮马之池,游人寥落,一片荒凉。昔日的冶游客先后埋骨青山,美人也栖身黄土;旧日的生活已经远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让人悲痛,不让人感伤!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大多怀有一种感伤情绪。当昔日繁华的秦淮河畔已化为瓦砾场的时候,有一人在破板桥边吹曲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开门出来道:“这是张魁官的箫声!”旧日之事,依稀犹在;人已作古,声却依然。
清初时明朝遗民的感伤主义作品大量涌现。余怀《板桥杂记》的基调是怀恋过去的生活,以感伤的情绪写出秦淮河的兴衰史。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借对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达了对过去风流雅致生活的留恋,其基调同样是感伤的。《如梦录》一书,记明代开封鼎盛之时的繁华景象,因李自成决河灌汴,使锦绣中原一旦付诸东流,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无非也表现了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依恋。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散文式的笔调写历史的实事,诸如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的梨园、勾栏与节日生活。
士大夫百般留恋的明代城市胜景、繁华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它不同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被发左衽”。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胡风”旧习洗刷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复确立。它也不同于满族入关以后建立的清帝国的“剃发”“顶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独具的特点,它既是汉唐以来民族传统的,却又新颖独特,对传统是一种叛逆,即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我愿以拙笔尽力描摹那些旧日的雪泥鸿爪,多取角度,用文字作一幅明代城市生活的长卷,读者诸君不妨慢慢读下去。
导语摘要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既是一部明朝生活指南,又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作者简介陈宝良,知名历史学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等作品十余部,所著作品多被知名大学列为指定参考书,学术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目录城市风景
街市行纪 002
走进胡同 019
城里人与乡巴佬 028
衣食住行
宫样与苏样 038
丰腆精食与粗茶淡饭 078
宫风士韵民用 115
船舫马房 152
礼下庶人
社交礼仪 166
家礼:冠婚丧祭 201
市井民俗
节日与仪式 218
幽默人生 235
大众传播:民谣 247
粉墨登场 260
旅游生活 275
逗闷的乐子 286
从庙堂到江湖
皇冠心态 308
天潢印象 329
太监的生活 347
士绅百态 357
市井众生相 373
人在江湖走 390
妇女面面观 401
飘摇的传统
城市风景线 416
文化变革的冲击波 427
内容摘要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既是一部明朝生活指南,又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主编推荐陈宝良,知名历史学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等作品十余部,所著作品多被知名大学列为指定参考书,学术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精彩内容幽默人生
说到幽默,不妨先引张岱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张岱(字宗子)是明末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天下闻名的“饕餮客”。当张岱六岁时,他的祖父带他到了杭州,正好遇到了当时有名的山人清客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在钱塘县里做游客。眉公对张岱祖父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应声对道:“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听后大笑,起而跃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琅嬛文集》)
张岱的对子灵巧睿智,以谐对庄,一语点破这位眉公先生钱塘之行的目的,使对子大有谐趣。而眉公先生面对这种阵势,处惊不慌,笑而不窘,这是一种容忍别人消遣的雅量,表现了一个幽默家的风度。
就其大概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幽默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它具体表现在笑话和寓言这些朴素的文学形式里。中国也不例外。笑话这种形式,虽然至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诸著录,但若追溯其源流,战国时期及以后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显然都是这些笑话的滥觞。在古代载籍中,到处隐伏着幽默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天性并非独缺幽默,中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只是将喜怒哀乐隐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自汉魏以降,尤其是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那点自古就有的快乐的心灵感受渐被压抑,幽默日渐泯灭。披上一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道袍,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正经得让人不敢亲近,这种儒者风范反而被视作中国人的典范和楷模。一至宋明理学泛滥,这一行为准则更是被理学家极为推崇,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幽默的性情反被摧残不已。物极必反,明中期以后城居士大夫与城市平民中幽默生活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的新现象。
文人:戏而不谑
明代理学是宋代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理学家们仍然将七情六欲隐藏在理智的外衣之下,通脱的性情受到理智的过分压抑,行为拘谨,生活毫无风采。明初的理学家依然恪守传统的人格修养,以矜持的态度傲视一切有趣的生活。他们遵循一种“谨言”的准则,认为“谨言”是治学的等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句句是实理”。他们又主张“慎行”,遵守一种端庄的甚至可以说是形若土偶的行为准则,以此来存心养气。他们排斥稍具实性实情的“戏谑”,认为戏谑会导致气荡心移。(薛瑄《读书录》)显然,在保守的理学家那里,行揖跪拜、饮食言动都有一定的准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也有一定的尺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这种角度而言,要从明代理学家那里找到一些幽默的心灵因子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理学家通常与幽默无缘。
幽默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应当具有宏大的雅量。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截然不同。正如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改变了明代哲学史一样,王氏心学同样也为晚明士大夫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真性实情大胆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性情从理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讲究真性情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主旨。同时,明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对一切事物好“轻遽议论”的态度,所言不乏趣味之谈。
幽默来源于生活。理学家的生活呆板严肃,生活场景极为狭隘,他们那种行若土偶的行为,在成为别人消遣、调侃的对象之外,根本无法成为消遣别人的主体,更不能自我嘲弄。而文人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从生活中追求乐趣,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明代的石中立就是这样一位能大胆自我解嘲的人。他官居员外郎之职,曾经随同僚去南御园观看皇家所畜的狮子,守园者告诉他们,这狮子每天能吃到五斤肉。同僚就戏言:“我辈日给反不如狮子?”中立笑答:“这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园外狼(谐员外郎),怎么能与园中狮子相比?”(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寥寥数语,既是自嘲,又发泄了对明代官俸极低现象的不满。
晚明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场景极为广阔,互相戏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与传统理学家的喜静恶动不同,文人士大夫好动恶静,他们互相交游,时常举行各种文宴,把盏嬉戏。吴门张献翼为人使才好奇,每天都有“闯食者”,于是他故作一谜粘贴于门上,规定“射中许入”。谜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一时没有猜中者。一天,王穉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浮白斋主人《雅谑·射谜》)张献翼听后大笑。这是士大夫在交游中以射谜互相戏谑。主人别出心裁,出谜难人,客人不但引经据典,而且还幽默风趣,将主人戏弄一番。这种既长知识又别有情趣的射谜,是士大夫幽默生活的特点之一。
人的癖性与幽默是密切相关的,其连结点在于性格,即在于性格间的喜剧性。一般说来,只有串上喜剧性的癖性才带有幽默的意味,才容易被认为幽默,除此之外的数不尽的癖性都与幽默无关。古怪癖性一旦与喜剧性相结合,一般就被称作滑稽。在晚明的城居士大夫中,行为滑稽之人比比皆是。例如,顾承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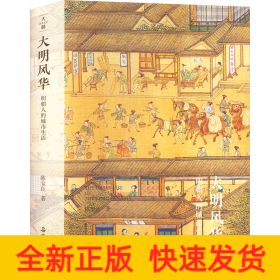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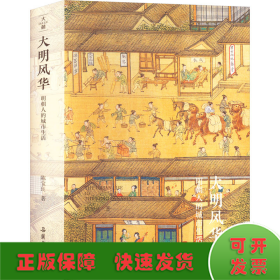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