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54.21 5.5折 ¥ 98 全新
库存14件
作者张巍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334867
出版时间2022-10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29483563
上书时间2024-11-0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序 言
近四十年来,正当西方古典学被正式引入我国,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出人意料的关注,而且也在文化公众那里掀起了小小的热潮之际,在西方,这门精致且高严的学问却已风光不再,甚至走向了衰微。现代古典学经历了18世纪后半叶以降百余年的草创、勃兴和鼎盛,进入20世纪后便开始盛极而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深层的危机感渐渐弥漫整个西方古典学界。古典学已经到了为自己的生存担忧的地步,不仅因为各种令人窘迫的现实状况,更因为这个学科面临的问题攸关其存在的理由:古典世界和当代世界有无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否需要以及能否维系下去?古典学是维系两者的有效手段么?古典学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
古典学的当代危机显露于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情形而言,古典学身处“后古典世界”,这个“后古典世界”绝不仅仅在时间上位于“古典世界”之后,更重要的是,“古典世界”已被它决定性地抛到了身后,这个时代不再跟随“古典世界”,而是摆出各种姿态,与之撇清关系。“古典世界”特别是“古典”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古典主义”饱受诟病,遭到“后古典世界”的严厉批判。根据“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思维模式,“古典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被塑造成一种理想和一个本源,由此来强调西方文明自古及今的“古典传统”(classical tradition)及其连续性:作为“理想”,古典世界的辉煌文明具有永不磨灭的内在价值,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适性以及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典范性;作为“本源”,古典世界乃西方文明纯粹的源头,具有永不枯竭的丰富性。据此,“古典主义”致力于追怀、摹仿和复活业已失落的“古典理想”,旨在承接和维护赓续不绝的“古典传统”。这样一种“古典主义”被解构为纯属虚妄的假象:诚然,古典世界在历史上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因为它的超验的内在价值和优越性,它的永不改变的完美性和典范性,而是缘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和复杂的历史条件。从认识论上说,我们关于古典世界的知识永远是片面的和不确定的,从中无法推导出任何一种普适的“古典理想”。从史实上说,“古典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本源”,并不具备纯粹性,而是受到古代近东多种文明的影响和刺激才逐步形成;纵使具备所谓的“纯粹性”,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渴慕返回其间,而无视它是如何通过与当下的交互影响被不断地构建出来的。经过此番“后古典世界”的批判性审视,“古典世界”和“古典文明”不再具有高于其他时代或其他文明的典范性,而只是众多时代和文明里的一个而已。
更有甚者,“后古典世界”的外部批评还得到了古典学界自身的普遍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古典学者们意识到,这门学科不能再像19世纪全盛时期那般,以一种高居众多人文学科之首的傲然姿态,心安理得地在其学科内部延续习以为常的研究。这些学者使出浑身解数,为古典学发掘新的研究材料和资源,寻觅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譬如20世纪下半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迅速得到重视,学者们不仅打通古典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进行交叉或综合研究,而且还引入各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来研究古典文明;60年代起,新兴的各色文学理论被先后运用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令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80年代以降的“文化转向”,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关注古代世界的底层和边缘文化,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关注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近二十年来兴起的跨文化乃至全球化古典学倡导其他文明对古典文明的主动的接受研究,以及将各种古典文明同等对待的比较研究。表面上,古典学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态,新的研究材料和资源、方法和角度拓展了研究课题和方向,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各个方面无不得到关注和探究,藉此古典学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可是,从人文学科的整体来看,古典学却不断地被边缘化,一种地位和生存的危机感如影随形,令古典学者仿佛对这个时代问心有愧。其实,当古典学者致力于翻开古希腊罗马世界的每个角落之时,恰恰是为了因应“后古典世界”的外界批评之声,远离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为核心的精英文化。结果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被日益异域化和他者化,与现代西方文明拉开无法弥合的距离。与此同时,古典学术的传统基础——古典教育也被斥为保守意识形态的温床,一个奉古典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制度化的教育机构,与精英主义、排外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典教育曾经是上流阶层的一种标志,一种文化资本,强化其种族、性别和阶层意识,维护其地位和特权;传统的古典教育往往滋生复古的意识形态,导致对现代文化及现代性的全盘否定,以及对古典文化及古典性的盲目推崇。因此,古典学术要与传统的古典教育撇清关系,成为一门纯粹的研究性
学科。
从内外两方面的危机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古典世界和当代世界没有内在关联;即便有,也无必要维系下去;即便有必要维系,这也不是古典学的任务,因为古典学乃是回避现实意义的历史性的纯学术。面对这样的结论,某些眼光不囿于古典学表面繁荣的西方古典学者认识到,这门学科正面临深层的危机,它必须清醒地反思自己的性质和任务,反思自己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一些先知先觉者提出,古典学亟待自我革新,清除任何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的“古典主义”的余孽,主动追随“后古典世界”的时代思潮,转变为多元的历史主义的古典学(参见莫利《古典学为什么重要》)或者多元的“后古典主义”的古典学(参见The Postclassicisms Collective 2020),才有可能重焕生机。言下之意就是,为了化解它面临的危机,古典学必须再次变得“合乎时宜”。
果真如此?事实上,古典学的当代危机需要从它的现代困境里找寻根源,而这一困境于现代古典学诞生之际便初露端倪。如所周知,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时代思潮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有别于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重罗马的人文主义,德国的新古典主义奉古希腊为典范,具有强烈的“亲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特征。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Winckelmann, 1717—1768)引领了这一时代风气,他发表于1755年的纲领性论文《有关绘画与雕塑艺术对希腊作品进行摹仿的思考》(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cke in der Mahlerey und Bildhauer-Kunst),率先提出“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无法摹仿的一条道路,就是去摹仿古人,尤其是古希腊人”以及“体现于希腊雕塑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同样也是好时期的希腊文学的真正特征”的著名论断。九年后,他的划时代巨著《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1764)明确主张,古希腊人的艺术作品尤其是雕塑和建筑创造了“古典理想”,处于从埃及到罗马整个古代艺术进程的。温克尔曼勾画的“古典理想”深刻影响了当时一大批文化菁英,包括莱辛、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等,他们共同开辟了现代德国文化颇具创造力的
时期。
正值高举“古典理想”旗帜的新古典主义迅速席卷整个德国文化界之际,现代古典学应运而生了。18世纪70年代,哥廷根大学的海纳(Gottlob Heyne, 1729—1812)与哈勒大学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早让古典语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趣的是,现代古典学的问世还有一个象征性的日期——1777年4月8日。那天,一位年方十八的青年学生到哥廷根大学登记入学,要求注册“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 philologiae)。校方反对说,“古典语文学”并非现有的四个系科之一,如果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应该注册研究神学(studiosus theologiae),但青年学生坚持己见,学校无奈之下只得应允。这位青年学生便是现代古典学之父沃尔夫。这则人们耳熟能详的逸闻不仅标志着现代古典学的诞生,还有其深刻的象征意味:“古典语文学”终于摆脱了神学的枷锁,不再是附庸于神学的一门技术性的辅助学问,成为独立于神学且与之媲美的一门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学问。沃尔夫创立现代古典学之举堪称从学术上对温克尔曼倡导的“新古典主义”的实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已经让罗马文学从拉丁语的教学当中脱离出来,不再为教会的神学教育服务,成为人文学者独立研究的对象,而德国的新古典主义则进一步让希腊语言和文学从拉丁语言和文学的附属地位中脱离出来,使之超越后者成为一切文明的成就。现代古典学在诞生之初将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置于首位,古罗马语言和文学置于次位,并以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对立于基督教文明,正是它原初的精神内核。也就是说,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要与基督教神学相颉颃,要使其学问的对象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峙,从而实现古典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抗衡,这正是古典学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格局所担负的精神使命。
沃尔夫把古典学的对象定义为“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有关古代的知识”,并称之为一门历史的学问,必须尽可能地在研究对象的原初历史情境中加以审视和理解。为此他发明了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词,在他所给出的定义里,Altertum(即古代)是作为整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其中希腊人的地位又高于罗马人,因为前者更完美地体现了真正的人性特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而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目标正是通过对整个古代世界的重构来寻回古希腊人的精神。可见,现代古典学在诞生之初,“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种互相制约的因素已经成为一条隐伏的线索,但古典学术初仍服务于对古典精神的追寻。然而,沃尔夫之后的德国古典学却沿着历史主义支配下的“古典古代学”(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路径发展,而整个19世纪德国古典学的鼎盛意味着古典学术对于古典精神的胜利。沃尔夫创建的古典语文学,虽然起初是复原、理解和阐释古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但作为历史科学,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对古代世界进行历史性的重构,亦即“重现过去的真实”。经过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训练出来的古典语文学者不再固守于古典文献,而要以古代文明的整体为研究对象,因此“古典语文学”转变为“古典古代学”,致力于对过去的史实(Realien)进行全面而客观的研究,藉此获致对古代文化的客观了解。这一进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古典古代学”的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身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古典学遂成为高举实证历史主义的学科,成为现代人文学术的典范而大获成功。但成功的另一面是,它早已忘却新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偏离了诞生之初的精神使命,与古典精神渐行渐远。古典学不再力争古典文明之于现代基督教文明的优先地位,也不再倡导古典精神之于基督教精神的优先地位。虽说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和耶格尔(Werner Jaeger, 1888—1961)分别致力于复兴古典学的精神使命,前者倡导“不合时宜的古典学”,后者揭橥“第三次人文主义”,但都宛如空谷跫音,难以挽回古典学对其精神使命的背弃。
综上所言,古典学的现代困境源于其诞生之初的精神使命与学科发展的历史际遇之间的两难。它在整个19世纪的空前成功使其迅速背离并彻底抛弃了诞生之初的精神使命,20世纪以来的盛极而衰更是让古典学对其原初的精神使命避之唯恐不及,“合乎时宜”几乎成为古典学的选择。为古典学术而彻底放弃古典精神,这正是现代古典学的成功之道,但同时也深化了它的困境。彻底放弃古典精神的古典学术,只能尾随其他更具现实性的学科力求“合乎时宜”,而难以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格局担负任何精神使命,这其实才是古典学所面临的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要化解古典学的当代危机,必须克服它的现代困境,重建古典学术与古典精神的真正联系,复兴古典学的精神使命。归根结蒂,古典学的精神使命就是维系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而成为维系两者的有效手段,就是古典学的现实
意义。
但问题在于,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恰恰是一种现代学术,本身便是现代精神的产物,它又如何在运用现代学术的各种方法之时,葆有古典精神?面对这一难题,首先要从更长远的时段着眼,赢获古典学术史的整体意识,以此来反观现代古典学。设若古典学的当代危机不断深化,以至于它在“后古典时代”的某一天寿终正寝了,被当作陈旧的古董而仅供赏玩,那么18世纪末以降的现代古典学究竟能为后世留下什么,什么又是其富生命力的遗产?事实上,这一假想的情形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就是希腊化时期三百年间(公元前3世纪初至前1世纪末)辉煌的古代古典学的终结,而它又为西方后世留下什么有生命力的遗产?从今日的角度来看,希腊化时期的古典学术,相比于此前的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而言,不过是一种次生的文化现象,其终价值就在于尽较大可能地保存古典作品的真面目,维护古典精神的生命力,使之具备持久的文化意义而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两百年来的现代古典学术也应作如是观。从根本上说,学术本身只是一种次生的精神活动,只有当它指向(而非遮蔽)它所依凭的原生的精神活动,才算实现它真正的价值。对于古典学术这一次生的精神活动而言,它所依凭的原生的精神活动便是古典精神,无论古代古典学还是现代古典学,莫不如此。
所以,现代古典学运用各种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古希腊罗马世界,必须以古典精神的维护与发扬为鹄的。现代学术方法只是手段,古典学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它不应满足于仅是一门历史性的学科,而只有向着古典精神进发,古典学才会成为一门现实性的学科。这就意味着从古典精神去观照并融摄现代精神,从经历时间淘洗的恒久价值来评估瞬息万变的当下价值,并从中生发出反思和批判的现实意义。这一探求“古典精神”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现实拉开距离的过程,只有拉开距离,我们才能赢获观照当下现实的批判性视野。换言之,涵泳于“古典精神”,并不意味着“返本归源”,驻守于某种奠基性的“古典时代”而流连忘返,因为如此一来,拉开距离的批判性视野便无从谈起;相反,我们必须不时从“古典精神”赢获的视距观照当下现实,使之发挥批判性的作用。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厚古薄今,用“古典精神”一味反对“现代性”,而是要从“古典精神”的视距批判性地融摄“现代性”。
再者,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其宗旨并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者本身,也就是研究者自己的人文精神。这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所在。故此,当古典学术运用现代智识工具及其精神去理解古希腊罗马世界,试图比古人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这只是学术之路的半途,我们还要反向延续这一进程,运用古代智识工具及其精神去直面现代世界,从而比今人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是一条漫长的往复之路:我们背负现代智识工具出发去往古代,到古人那里学习古代智识工具,逐步以之涵括前者,返回现代,用古典精神直面现代世界。
古典学对研究者的人文精神的抉发、培育和养成诉诸古典精神——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当中探求古典精神的本源及其演变,并通过这一向外的探求来抉发、培育和养成研究者自身的古典精神。古典学术实质上是由外入内、内外并进的探求古典精神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而言,语言和思想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古典精神虽能体现于其他各种媒质与形式,但语言和语言所传达的思想毕竟承载了古典精神恢宏博大、精深微妙之处。这便要求我们以古希腊罗马的传世经典为根本,以语文学的训练为基础,以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为辅助,来把握语言及语言对思想的传达,来体认语言所传达的
思想。
有鉴于此,本部《入门》主要围绕古典语文学,尤以传世古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展开。这一重心的选择,除本书篇幅和作者学力所限,根本的理由在于,组成古典学术的四大研究方向(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典考古学)当中,古典语文学乃是基础,而传世古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依凭这一重心,本部《入门》的目标是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为此,我们把古典学术分成“古典学养”(“学”)和“古典研究”(“术”)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本书的根本旨趣在于,经由“古典学养”(、二章)到“古典研究”(第三至五章)的古典学术之路,成为通向古典精神的养成之路。这条道路以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研习为核心,具体的操作方法有三:其一,统观古典文史哲之全局,循其学术源流的主脉而识其大体,此方法见于章“专业培养”和第二章“典籍博览”;其二,精研古典文史哲经典文本,依靠文本细读而入其精髓,此方法见于第三章“经典研读”;其三,居于古典文史哲之交汇处,从语文→历
史→思想来贯通文史哲之畛域而得其整全,此方法见于第四章“研究起步”和第五章“研究方法”。当然,如前所述,这条道路只是漫长的往复之路的前半程,返回之路才是养成了的古典精神的真正归宿。
关于本书有三点说明。,本书虽然对古典学术的整体面貌有所概览(尤见章“专业培养”和第五章“研究起步”节),古典语文学以外的其他研究方向(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典考古学),以及古典学术的辅助学科(诸如铭文学、纸草学、钱币学和图像学)都未能涉及。事实上,针对这些研究方向和辅助学科,有必要另行撰写独立的《研究入门》,并非本书作者所能代庖。第二,本书所举实例,皆来自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未能顾及希腊化时期和罗马,这当然也缘于作者自己的专业限制,不过本书所侧重的基本训练和研究方法,经适当变通以后,也能运用于其他时期的传世古典文献及基于其上的相关研究。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尽量将视野扩展到其他时期,或可弥补正文所举实例的局限。第三,本书虽放眼古典学术重要的几种学术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界的研究,但仍偏重英语学界,这固然缘于英语作为当代主导性学术语言的现实,不过作者认为,古典学术并非英语学界所能囊括,还望初习者努力拓宽自己的眼界,尽力将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学界的相关研究也纳入视野。
后,需要强调的是,本部《入门》虽属晚近四十年来将西方古典学引入我国的学术潮流,却有别于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科学化接受方式,即所谓的纯学术研究。纯学术研究者宣称,进入中国的古典学须全盘按照国际标准来移植,古典学的引入无异于某种自然科学,国际标准乃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他们有意或无意回避的问题是,古典学的“国际标准”实质上带有强烈的西方学术的当代属性,制定并奉行这一标准的主流学界往往利用古典学术来为当代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服务,进入中国的古典学不必也不可亦步亦趋。毋庸置疑,中国的古典学者需要接受国际水准的专业训练并具备国际视野,但这一国际视野不应当把中国自身的古典文明以及古典学术传统排除在外,更不应当成为自我隔绝于中国文化之外的借口。中国的古典学者要比西方古典学者更有能力反思习焉不察的西方学术话语,明辨西方古典学内部的批判暗流,结合中国文化内部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让西方古典学真正成为优质的中国学术之一部分。唯有如此,中国的古典学者方能不但作为古典学者直面当下世界,亦且作为中国学者直面自己所属的中国文化。
导语摘要本书围绕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的解读和研究,从五个方面概览古典学术的整体面貌,旨在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所承载的古典精神。
章介绍三所欧美高校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的古典学专业培养模式;第二章梳理初习者需要通盘了解的传世典籍并给出书目;第三章指导初习者使用校勘本、辑佚本及评注本,逐步深入对传世典籍的文本细读;第四章引领初习者掌握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问题的研究现状,将所涉文献分门别类地编制成工作书目;第五章讨论古典学研究常见的三类方法,引导初习者循序渐进地使用语文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思想研究法。此外,本书还收入两个附录,附录一是按“文学”“史学”“哲学”和“演说”四部分类的《娄卜古典文库》总目,附录二是与正文各章对应的古典学工具书及参考书举要。
商品简介本书围绕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的解读和研究,从五个方面概览古典学术的整体面貌,旨在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所承载的古典精神。
第一章介绍三所欧美高校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的古典学专业培养模式;第二章梳理初习者需要通盘了解的传世典籍并给出必读书目;第三章指导初习者使用校勘本、辑佚本及评注本,逐步深入对传世典籍的文本细读;第四章引领初习者掌握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问题的研究现状,将所涉文献分门别类地编制成工作书目;第五章讨论古典学研究最常见的三类方法,引导初习者循序渐进地使用语文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思想研究法。此外,本书还收入两个附录,附录一是按“文学”“史学”“哲学”和“演说”四部分类的《娄卜古典文库》总目,附录二是与正文各章对应的古典学工具书及参考书举要。
作者简介张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思想和文学、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思想形成期的比较研究,以及清末至当代中国对西方古典传统的接受。近期出版学术专著《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主编学术刊物《西方古典学辑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起)。
目录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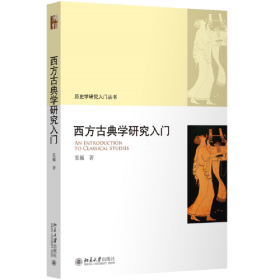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