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文插图珍藏本:战争与和平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444.72 6.4折 ¥ 698 全新
库存35件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87913
出版时间2021-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98元
货号29414244
上书时间2024-10-3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性历史小说,涵盖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和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十五年(1805—1820),以俄国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俄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为历史人物,诸如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等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并为众多虚构的人物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典型环境,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小说着重写了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俄国贵族家族,以这些家族的年轻一代安德烈公爵、玛丽亚公爵小姐、皮埃尔、娜塔莎和尼古拉·罗斯托夫等作为情节发展的贯穿始终的线索。
书中对战争以及和平生活的描写是穿插进行的,全书分为四部,情节的脉络大致如下。
部写一八○五年。开卷的场景是在首都彼得堡,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家里举行招待晚会。作家对出席晚会的来宾的性格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刻画,成为展开全书情节的一个引子。书中叙述了四个贵族家族在和平时期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俄国的社会风貌。其中写到别祖霍夫伯爵病危时瓦西里公爵谋夺遗产的不光彩的行径,老伯爵的遗嘱将全部财产和爵位传给他钟爱的私生子皮埃尔;皮埃尔与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海伦结婚;贵族家庭少男少女的初恋;鲍尔康斯基家族在童山的庄园生活。
库图佐夫在盟国奥地利的布劳瑙检阅部队。奥地利马克将军率部向法军投降,俄军处境极其危险。申格拉伯恩战役,骠骑兵士官罗斯托夫冲锋时受伤,安德烈公爵在巴格拉季翁将军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赞扬孤军奋战的炮兵连长图申。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败兵溃逃、库图佐夫负伤的危急时刻,安德烈公爵手执军旗冲在前面,身负重伤;尼古拉·罗斯托夫执行命令时在前线看到,俄国近卫重骑兵“漫山遍野”地汹涌而至,正在对相向而来的法国骑兵发动攻击。“后来罗斯托夫胆战心惊地听说,从他身旁经过的那健壮的美男子所组成的大军,所有那些光彩照人、骑着价值千金的骏马的富家子弟、青少年、军官和士官,在进攻之后只剩下了十八个人。”对一八○五年俄军在申格拉伯恩战役和史称“三皇大战”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失败和耻辱”(托尔斯泰语)的描写为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胜利做了铺垫。
第二部从一八○六年写到一八一一年。普乌图斯克和普鲁士艾劳之战在叙事中一笔带过,弗里德兰战役后宣布停战,这是一八○六至一八○七年战争中的后一次战役。重大历史事件有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的蒂尔西特会晤和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斯佩兰斯基的改革。穿插其间的情节有:皮埃尔与妻子海伦的情夫多洛霍夫决斗;安德烈公爵意外地康复,回到童山,他的妻子当夜难产而死;皮埃尔参加gongjihui,他决心解放农奴的计划和措施;皮埃尔拜访安德烈公爵,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长谈。安德烈公爵偶遇娜塔莎。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参与斯佩兰斯基的改革,对他由崇拜到失望;他在舞会上邂逅娜塔莎,不久订婚;罗斯托夫家引人入胜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娜塔莎受到阿纳托利的诱惑,解除与安德烈公爵的婚约;皮埃尔在心里指责她,“竭力想鄙视她”,但是在与她短暂的交谈之后,不觉流下了感动和幸福的眼泪。从她家里出来后,“皮埃尔一双含着泪花的眼睛快乐地遥望那颗明亮的星星(“1812年的彗星”),它仿佛以无法形容的速度沿着抛物线划过无垠的空间……”他觉得,这正是他心情陡变的真实写照。
第三部集中写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法军于六月十二日越过俄国边界,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俄军和第二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斯摩棱斯克失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波罗金诺战役,安德烈公爵的团是预备队,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他被榴弹击中腹部;俄军主动放弃莫斯科,法军占领莫斯科和莫斯科的大火。罗斯托夫伯爵一家和一批伤员撤离莫斯科,娜塔莎独自在深夜去见负伤的安德烈公爵,相爱如初;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兵荒马乱中长途跋涉,探望兄长;安德烈公爵之死和娜塔莎的绝望;皮埃尔留在沦陷的莫斯科企图行刺拿破仑,他从大火中救出一个小女孩,法军以纵火罪拘捕了皮埃尔。
波罗金诺战役是一八一二年战争的高潮。作家刻意追求历史的真实,曾于一八六七年九月乘驿车整整走了一夜,到达波罗金诺,下榻于斯帕索·博洛京修道院的旅馆,这个修道院是一八一二年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牺牲的图奇科夫将军的寡妻修建的。次日晨曦初露,“托尔斯泰就开始巡视波罗金诺战场。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那些遍布战场的纪念碑和堡垒,凝视着这场残酷战争的历史见证。”a作家在这里缅怀先烈,凭吊古战场,并就地草拟了波罗金诺战役的写作要点。
第四部,彼得堡上层的复杂斗争;伯爵夫人海伦的荒淫生活以及她的“病”和死。亚历山大一世写信责问总司令库图佐夫,为什么决定全军撤离莫斯科。俄军撤离莫斯科,退往塔鲁季诺。一个月后俄军军粮充裕,兵员得到补充,求战心切,另一方面法军在莫斯科大肆劫掠,丧失斗志,两军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强弱易势。俄军发动塔鲁季诺战役,这次打击促使法军望风而逃,俄军由退却转入进攻。尼古拉·罗斯托夫邂逅玛丽娅公爵小姐,皮埃尔与娜塔莎不期而遇。
俄国的游击战争开始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作者写道:“此类行动经常在具有人民性的战争中表现出来。”又说:“这种行动就是不以集群对抗集群,而是化整为零,击敌一部,打了就跑,以免遭到大部队的进攻,然后再待机出击。”书中详细描述了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的两支游击队袭击敌军庞大运输队的经过。他们解救了一批俘虏,皮埃尔是其中之一。托尔斯泰把游击战争形象地比喻为“人民战争的大棒”,满腔热情地肯定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他明确地指出:“拿破仑的法国军队之所以覆灭,一方面是由于进军太晚,对冬季深入俄国腹地的远征缺乏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焚烧俄国城镇、激起俄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后的战争性质”。
《尾声》写了皮埃尔和娜塔莎、尼古拉和玛丽娅公爵小姐婚后的幸福生活。皮埃尔从彼得堡回来,评论时局,谈到彼得堡的“秘密团体”和他的活动(他是该团体的创始人之一),他说:“我的全部思想就在于,既然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那么正直的人们也应当照此办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情节暗示着一八二五年俄国开明贵族旨在反对农奴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战争与和平》这部不朽的巨著再现了欧洲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气势磅礴,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风貌,而又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将万千气象熔于一炉,构成精彩纷呈的艺术整体。
娄自良
2011年3月于上海
导语摘要《战争与和平》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杰作,堪称整个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的扛鼎之作,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领域和疆界。小说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背景,围绕四个俄国贵族家庭展开叙述,五百多位纤毫毕现的人物穿插其中,全面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广阔图景。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宏大的时代背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部辉煌壮阔的史诗巨著。
本次插图珍藏本《战争与和平》公收录了一百余幅精美插图,全书采用四色印刷。封面和书脊选用两种高品质皮革手工拼接制成,书脊采用烫金起凸工艺,呈现立体的艺术字书名,封面则采用激光雕刻工艺,力求还原每一处笔锋的神韵。全书书口三面刷金,并有双向的隐藏书口图,此外还配有特制仿军礼服布面函套。
作者简介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三部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代表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将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同时,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在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俄罗斯民族毋庸置疑的精神象征,俄国著名文史学家米尔斯基将托尔斯泰称为“行走在俄国大地上的近几代人中的一位”,这里的“大”即指托尔斯泰思想之博大。或许托尔斯泰作品的现实意义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潮起潮落,但是托尔斯泰之永恒毫无疑问。
目录
《战争与和平.I》
内容摘要《战争与和平》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杰作,堪称整个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的扛鼎之作,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领域和疆界。小说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背景,围绕四个俄国贵族家庭展开叙述,五百多位纤毫毕现的人物穿插其中,全面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广阔图景。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宏大的时代背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部辉煌壮阔的史诗巨著。
本次插图珍藏本《战争与和平》公收录了一百余幅精美插图,全书采用四色印刷。封面和书脊选用两种高品质皮革手工拼接制成,书脊采用烫金起凸工艺,呈现立体的艺术字书名,封面则采用激光雕刻工艺,力求还原每一处笔锋的神韵。全书书口三面刷金,并有双向的隐藏书口图,此外还配有特制仿军礼服布面函套。
主编推荐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三部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代表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将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同时,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在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俄罗斯民族毋庸置疑的精神象征,俄国著名文史学家米尔斯基将托尔斯泰称为“行走在俄国大地上的近几代人中的一位”,这里的“大”即指托尔斯泰思想之博大。或许托尔斯泰作品的现实意义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潮起潮落,但是托尔斯泰之永恒毫无疑问。
精彩内容等了一会儿,大叔穿着后身打褶的短上衣、蓝长裤和一双小皮靴进来了。娜塔莎曾在快乐村见到过大叔的这身打扮,感到又惊讶又可笑,现在却觉得这是一套真正得体的服装,丝毫不亚于常礼服和燕尾服。大叔也很高兴;他对兄妹俩的笑声不仅不见怪(他不可能想到人家是在笑话他的生活),反而自己也和他们一起无缘无故地呵呵大笑。
“瞧这个年轻的伯爵小姐—没说的—这样的姑娘我还没有见到过!”他说,一面把一个长柄的烟斗递给罗斯托夫,又以习惯性的动作把一个截短的烟斗握在三指之间。
“整天骑在马上,男人也够呛,她却若无其事!”
大叔进来不久,听脚步声,有一个赤脚的女仆走来打开了门,随即进来一个双手捧着摆满食品的大托盘的体态丰满、面色红润的四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双下巴,嘴唇丰满而红润。她以殷勤、庄重的态度,和蔼可亲的眼神和举止环视客人,面带亲切的笑容向他们恭敬地点头致意。尽管她非常肥胖,不得不把胸脯和肚子向前突出,而头向后仰,这个女人(大叔的女管家)的行动却非常轻快。她来到桌前,放下托盘,白白胖胖的双手把酒瓶、冷盘和其他食品灵巧地拿起来摆放在桌上。然后她走开了,面带微笑站在门边。“我就是那个她呀!现在你了解大叔了吧?”她的出现向罗斯托夫透露了这个意思。怎么会不了解呢: 不仅罗斯托夫,而且娜塔莎也了解了大叔,了解了他皱着眉头幸福而得意地微笑的含义,这微笑在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进来的时候使他微微绽开了双唇。用托盘端来的是草药酒、果子露酒、蘑菇、脱脂乳汁黑面饼、鲜蜂蜜、冒泡的蜜酒、苹果、生胡桃、炒胡桃和蜜饯胡桃。随后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又送来了蜜糖果酱、火腿和新出炉的烤鸡。
这些都是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一手操办、采集和烹调的。这一切都香气扑鼻,美味可口,具有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的特色。一切都有芬芳、纯洁、洁白的气氛,有愉悦的微笑的韵味。
“吃呀,伯爵小姐。”她劝说着。一边给娜塔莎递上这个、那个。娜塔莎来者不拒,觉得这样的脱脂乳汁面饼,这样甜美的果酱、蜜饯胡桃和这样的烤鸡,她还从来没有在哪里见到过,吃到过。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出去了。罗斯托夫和大叔边吃边喝着樱桃酒,谈论着过去和今后的狩猎活动,谈论着鲁加依以及伊拉金的猎犬。娜塔莎挺直身子目光炯炯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她几次想叫醒彼佳,让他吃点儿什么,可是他含糊地叽咕几句,显然还没有清醒过来。娜塔莎在这新的环境里那么愉快、惬意,只怕接她的马车来得太快。在偶然出现的冷场之后,初次在家里接待熟人的主人往往会这样: 大叔似乎在回答客人心里的想法,说道:
“我就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了……人死了—没说的!—什么也不会留下。何必造孽!”
在这样说的时候,大叔的面容意味深长,甚至很美。这时罗斯托夫不觉想起了父亲和邻居们所谈到的大叔的种种好处。大叔是全省远近闻名的尚、无私的怪人。人们请他调解家庭纠纷,担任遗嘱执行人,向他吐露隐私,选举他担任法官和其他职务,但是他对社会工作总是坚决拒绝,春秋骑着自己的栗色骟马在田野溜达,冬天待在家里,夏天躺在草木茂盛的花园里。
“为什么您不出来工作呢,大叔?”
“工作过,放弃了。不行哪,没说的,我什么也不懂。这是你们的事情了,我脑子不够用啦。至于打猎就不同了—那可是没说的!把门打开啊,”他叫道,“怎么关上了!”走廊(大叔把门廊叫做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通往单身猎人室,这是对猎人们的下房的称呼。一双赤脚啪嗒啪嗒地走了过去,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猎人室的门。走廊里传来了巴拉莱卡a的清晰的声音,看来是一位内行的琴师在演奏。娜塔莎早就在凝神倾听了,这时她走到走廊里,想听得更清楚一些。
“那是我的车夫米季卡……我给他买了一把很好的巴拉莱卡,我爱听。”大叔说。大叔有一个规矩,他每一次打猎回来,米季卡要在单身猎人室弹奏巴拉莱卡。大叔喜欢听这种音乐。
“多好,真的,很好。”尼古拉带着一种不自觉的倨傲说道,仿佛不好意思承认,他非常欣赏这首乐曲的声音。
“什么很好?”娜塔莎感觉到了哥哥说话时的那种语气,不满地说。“不是很好,而是美妙极了!”正如她觉得大叔的蘑菇、蜂蜜和果子露酒都是世界上好的,这时她也觉得,这首乐曲是音乐美的极致。
“再弹哪,请你再弹。”巴拉莱卡的声音一停下来,娜塔莎便朝着门外说。米季卡调好琴弦,以一连串的滑音和顿音弹起了芭勒娘舞曲。大叔偏着头,面带不易觉察的微笑,坐在那里听。芭勒娘舞曲的旋律重复了一百遍。几次重新调好琴弦,于是又奏响了那些同样的音符,听众百听不厌,对他的演奏只是还想听,还想听。阿尼西娅进来了,肥胖的身躯斜倚在门框上。
“赏光听听吧,伯爵小姐,”她微笑着对娜塔莎说,这笑容和大叔的微笑非常相像,“他在我们这儿演奏得很出色。”她说。
“这一段可不该这样弹,”大叔突然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道,“这儿要奏出一个华彩段—没说的—华彩段。”
“您也会乐器吗?”娜塔莎问。大叔笑而不答。
“你去看看,阿尼西尤什卡b,琴弦坏了没有,那把吉他?好久没有玩过了,没说的!荒疏啦。”
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高兴地迈开轻快的脚步,去执行自己主人的吩咐,把吉他拿来了。
大叔谁也不看,吹掉灰尘,以瘦骨嶙峋的手指敲一下琴盖,调好琴弦,在圈椅上坐好。他握着吉他颈部稍高的地方(把左臂的臂肘张开,有点儿舞台表演的架势),朝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眨了眨眼,不是弹奏芭勒娘舞曲,而是起了个清亮、纯净的和弦,随即舒缓,悠闲,然而坚定地开始以相当缓慢的节奏演奏一首名曲《在有一座桥的大街上》。陡然,歌曲的旋律应和着节拍,以一种沉静的欢乐(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种欢乐之中)在尼古拉和娜塔莎的内心回响。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羞红了脸,以头巾掩面,笑盈盈地走出了房间。大叔继续纯净、细腻、坚定而有力度地演奏着这首歌曲,以变得充满灵感的眼神凝视着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离开的那个地方。他的脸上微微地隐含笑意,在歌曲进一步展开,节奏加快的时候,在一串连续的滑音的某些地方有点儿走神,一侧的白胡子底下更是笑意盈盈。
“妙极,妙极,大叔!再来,再来!”一曲刚完,娜塔莎便叫喊起来。她从座位上跳起身来,搂着大叔吻了吻他,“尼科连卡,尼科连卡!”她回头望着哥哥说,仿佛在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
尼古拉也很喜欢大叔的演奏。大叔第二次弹起了这首歌曲。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的笑脸又出现在门口,在她身后还簇拥着别人的笑脸。
去汲取清凉的甘泉,
他在喊,姑娘,你等一等。
大叔演奏着,又弹出一串俏皮的滑音,双肩一抖松开了手。
“再来呀,再来呀,亲爱的大叔。”娜塔莎以恳切的声音呻吟般地哀求道,仿佛不答应她的这个请求,她就活不下去了。大叔站了起来,他身上仿佛有了两个人,一个人对快活的乐天派严肃而揶揄地一笑,而这个乐天派做了一个质朴而道地的民间舞的起舞动作。
“来吧,侄女!”大叔叫道,向娜塔莎扬起刚才弹了个和弦的那只手。
娜塔莎甩开身上的披巾,跑到大叔前头,双手叉腰,做了个双肩摆动的动作,挺立在那里。
她,这个在法国女侨民的教养下长大的伯爵小姐,是何时、何地、如何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的空气中吮吸了这种精神的呢,是从哪里学到了这些早该被披巾舞排挤掉的动作的呢?然而这种精神和这些动作正是道地的不可模仿、无法研习的俄罗斯的精神和动作,完全符合大叔对她的期待。当她挺立在那里,带着傲然的狡黠而快乐的神气得意地微微一笑的时候,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初怕她做不到那么好的担心便烟消云散,于是只顾欣赏她了。
她做到了,而且恰如其分地、那么恰到好处地做到了,阿尼西娅·费多罗夫娜立刻给她递去她跳舞所需要的手绢,她望着这个苗条、优雅、如此陌生的一位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受到教养的伯爵小姐不禁含泪而笑,她竟能领会阿尼西娅、阿尼西娅的父亲、婶婶、母亲以及所有俄罗斯人的内心所蕴藏的一切。
“行哪,伯爵小姐,没说的!”跳舞后,大叔高兴地笑道。“哎哟,侄女!但愿给你物色一个好夫婿才好,没说的!”
“已经物色到了。”尼古拉微笑着说。
“哦?”大叔惊讶地说,疑问地望着娜塔莎。娜塔莎带着幸福的微笑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她说。不过她的话一出口,心里便勾起了一种新的思绪。“尼古拉说: ‘已经物色到了’,他说话时的微笑意味着什么呢?他对这件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似乎以为,鲍尔康斯基对我们的这种快乐不会赞赏,不会理解。不,他一定会理解的。现在他在哪里呢?”娜塔莎想,她的脸色突然郑重起来了。不过这仅仅持续了一秒钟。“不想这些,不许想。”她对自己说,又坐到大叔身边,请他再弹点儿什么。
大叔又弹了一首歌曲和一支华尔兹舞曲;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清清嗓子,唱起了自己心爱的猎歌:
傍晚,下了一场初雪,
纷纷扬扬,好大的雪……
大叔唱歌,像老百姓那样,天真地认为,歌曲的意思全都在歌词里,曲调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没有歌词的曲调是没有的,曲调只是要让声音动听而已。正因如此,大叔的这种像鸟鸣一样自然流露的曲调才特别悦耳。大叔的歌唱使娜塔莎如醉如痴。她决定,从此不再学竖琴了,今后只弹奏吉他。她向大叔要来吉他,立即弹了这首歌曲的几个和弦。
九点多钟,一辆敞篷马车、一辆轻便马车和三名骑手被派来接娜塔莎和彼佳了。被派来的人说,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很不放心。
彼佳像死人一样被抬着安置在敞篷马车里;娜塔莎和尼古拉坐上了轻便马车。大叔把娜塔莎裹得严严实实的,温情脉脉地同她告别。他徒步把他们送到桥头,这里要绕开桥涉水而过,因此吩咐几名骑马的猎手在前面领路。
“再见了,亲爱的侄女!”黑暗中传来了他的喊声,这不是娜塔莎原来所熟悉的声音,而是他唱着“傍晚,下了一场初雪”的声音。
他们经过的一座村庄闪着点点灯光,愉快地散发着烟味。
“这个大叔多么令人着迷啊!”他们出了村子,来到大路上时娜塔莎说。
“是呀,”尼古拉说,“你冷吗?”
“不,我很好,很好。我觉得太好了。”娜塔莎简直有点儿困惑地说道。他们久久地默然无语。
这是一个黑暗潮湿的夜晚。看不见马匹,只听到在看不见的泥泞中践踏的马蹄声。
这稚气、善感的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呢?它那么贪婪地捕捉并吸纳生活中无限纷繁的印象。她的心灵是怎样容纳这一切的呢?不过她感到非常幸福。离家不远了,她蓦地哼起了民歌的曲调:“傍晚,下了一场初雪”,她一路上都在捕捉这首民歌的曲调,终于捕捉到了。
“捕捉到了吗?”尼古拉问。
“你刚才在想什么呢,尼科连卡?”他们喜欢这样问对方。
“我吗?”尼古拉说,一边在回想,“你知道吗,起初我在想,那条红色公狗鲁加依很像大叔,假如它是人,它也会把大叔留在自己身边,即使不是因为奔跑快捷,也会因为他好而把他留下。大叔这个人多么好啊!是吧?那么你在想什么呢?”
“我?等一等,等一等。对了,我起初想,我们这样坐在马车里,以为正在回家,可是天知道我们在这黑暗中驶向何方,突然我们到了,却发现我们不是在快乐村,而是来到了仙境。后来我又想……不,没有了。”
“我知道,想必是想到他了。”尼古拉说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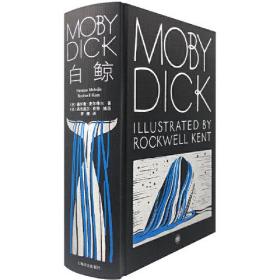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