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流行病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20.46 5.2折 ¥ 39 全新
库存41件
作者克里斯蒂安·W.麦克米伦 著,李超群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6133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9元
货号29416865
上书时间2024-10-29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序 言
张大庆
作为一本试图从宏观层面勾勒瘟疫与人类历史演进的通识读本,本书选取了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结核、流感和艾滋病等七种主要的大流行病,讲述了每种疾病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如何导致了传染病的大流行。作者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文化分析巧妙结合,还论及当代的流行病,如新发传染病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热以及禽流感等。
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传染病一直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传染病是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微生物是地球上古老的生命之一,也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大流行病的肆虐。它不仅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命,而且会造成人们的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经济和国际贸易。这次“新冠肺炎”的暴发再次证明,流行病不仅可以重塑人类的历史,同时,人类的行为也在影响着流行病的进程与转归。
回顾人类与微生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演化的历程,我们发现,自人类社会早期开始,瘟疫就是影响人类文化的关键因素。人类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因食用动物或与动物接触而被感染,导致许多人兽共患病,如旋毛虫病、非洲睡眠病、兔热病、疟疾、血吸虫病以及钩端螺旋体病等;此外,还有一些是与人类共同进化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如肠道寄生虫、体虱、沙门氏菌及密螺旋体所致的雅司病和梅毒。大约在公元前 500年前后,伴随古老文明中心的发展,天花、白喉、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迅速地在人类之间传播。传染病的流行不仅危及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同时也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古希腊由盛转衰、古罗马帝国的瓦解与流行病的肆虐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
196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消灭,剩下的部分也可以通过免疫和抗生素得到控制,医学界转向攻克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以及其他慢性退行性病变。然而,在 20世纪末,人们惊讶地发现,传染病依然还在危害人类的健康,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尚未结束。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危害人类健康严重的 48种疾病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占 40种,发病人数占病人总数的 85%。传染病依然是公共卫生不发达地区的主要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的暴发,使人们再次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任何忽视传染病控制的观点都是十分有害的。
传染病的全球化蔓延以及检疫防疫的全球化进程并非一个新问题。随着人类的迁移、贸易和殖民活动,“微生物一体化”导致了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全球性扩散。为了应付大流行病的肆虐,从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人们创建了许多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国际组织与机构,对大流行病的控制转向国际化行动。 203序? 言世纪初建立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在控制流行病蔓延、加强国际疫情通报以及协助许多国家建立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抗结核病联盟等非政府组织也促进了国际卫生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成为处理当代全球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问题影响力的组织。它展开了一系列控制疾病的全球行动:如根除天花计划,根除疟疾计划,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消灭麻风、麦地那龙线虫病计划等。 1958年,第11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根除天花决议,经过 20年的艰苦努力,人类终于在 1979年彻底地消灭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根除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计划也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在本书中,作者还讨论了国家在应对传染病流行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如检疫、隔离、旅行限制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管控。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疫苗、抗生素、化学药物等,能够有效地控制许多传染病,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传染病仍然具有破坏性。通过评估贫穷和疾病以及流行病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麦克米伦就全球各国政府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积极合作预防未来任何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了建议。
毫无疑问,在与瘟疫的较量中,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新的致命传染病还会不时地出现,例如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拉沙热、马尔堡病、裂谷热、 SARS以及近暴发的COVID—19等。面对传染病,我们要有“预防胜过治疗”的理念,要提高个人的卫生意识,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免疫力。总的来说,尽管我们依然会对突发的传染病产生恐慌,人类对于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还有待深入认识,甚至不得不接受将与传染病长期共存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为我们应对传染病提供了丰富的手段。我们相信依靠科学,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各类传染病的挑战,不断提升人类健康的水平。
导语摘要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流行性疾病的阴影始终笼罩其上,挥之不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本书简要介绍了历史上主要的大流行病——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结核、流感和艾滋病,强调了流行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人类对流行病的认识过程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特别关注大流行病之后公共卫生学的兴起和医学研究的爆炸式增长。在本书☆后,麦克米伦特别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积极合作,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流行病。
商品简介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流行性疾病的阴影始终笼罩其上,挥之不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本书简要介绍了历史上主要的大流行病——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结核、流感和艾滋病,强调了流行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人类对流行病的认识过程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特别关注大流行病之后公共卫生学的兴起和医学研究的爆炸式增长。在本书☆后,麦克米伦特别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积极合作,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流行病。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安·W. 麦克米伦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吉尼亚大学全球传染病研究所成员,研究兴趣为美国印第安历史和流行病史。著有《制定印第安法律:瓦拉派土地案和民族史的诞生》(2009)和《发现结核病:1900年至今的全球史》(2015)等作品。
目录致 谢
引 言
章 鼠 疫
第二章 天 花
第三章 疟 疾
第四章 霍 乱
第五章 结 核
第六章 流 感
第七章 艾滋病
后 记
索 引
英文原文
内容摘要回顾人类历史的进程,流行性疾病的阴影始终笼罩其上,挥之不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本书简要介绍了历史上主要的大流行病——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结核、流感和艾滋病,强调了流行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人类对流行病的认识过程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特别关注大流行病之后公共卫生学的兴起和医学研究的爆炸式增长。在本书☆后,麦克米伦特别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积极合作,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流行病。
主编推荐克里斯蒂安·W. 麦克米伦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吉尼亚大学全球传染病研究所成员,研究兴趣为美国印第安历史和流行病史。著有《制定印第安法律:瓦拉派土地案和民族史的诞生》(2009)和《发现结核病:1900年至今的全球史》(2015)等作品。
精彩内容章 鼠疫
在疾病的历史上很难找出比“鼠疫”的含义传播更广的名词了。现在我们知道它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由带病的跳蚤—跳蚤在动物宿主死亡后会寻找人类宿主—叮咬传播的疾病。“鼠疫”一词诞生于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发生的已知首次大流行病期间。它通常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名字命名。它来源不明—可能起源于中非内陆,随后传到埃塞俄比亚,再顺着贸易网传到了拜占庭帝国,但也可能起源于亚洲。人们无法确定。公元541年,埃及海港城市培琉喜阿姆首次出现了关于鼠疫的历史记录。在两年的时间里它横扫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一幸免,后抵达东边的波斯和北边的不列颠群岛。
尽管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但这次疫情中显然死亡惨重。以弗所的约翰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见闻,当时他正巧沿着疫情蔓延的路线旅行,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又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返回。他描绘了撂荒的田地、无人采摘的葡萄种植园、流浪的动物和日复一日忙着掘墓的人们。希腊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写道,公元 542年在君士坦丁堡,鼠疫一天就夺去了一万人的生命。“人类走到了灭绝的边缘。”同时代的观察员埃瓦格里估计,鼠疫造成拜占庭首都30万人丧生。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反映出疫情的惨烈。普罗柯比和其他熟知早前疫情的观察员都认为,查士丁尼鼠疫是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化之前的阿拉伯作家察觉到疫情的特殊,他们反映鼠疫对东罗马帝国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的伊斯兰作家记录了瘟疫在短期内造成伤亡无数,人们甚至放弃将死者下葬的惨状。到7世纪中期瘟疫终于播散到英国本土时,比德在自己的《教会史》中哀叹道,鼠疫“以极大的破坏力到处肆虐……夺去了无数英国人的生命”。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查士丁尼鼠疫为开端,欧洲部分地区和近东遭受了十多次鼠疫的袭击。 8世纪末鼠疫消失了,可能是因为所有人或老鼠都获得了免疫力。
鼠疫的影响因地而异。从大范围内来看,农村人口凋敝对拜占庭帝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通过对钱币学、纸草学、法律文书等相关资料的详细收集整理得出的结论—表明次鼠疫可能促成了帝国的衰亡。与此相反,鼠疫直到公元 664年才播散到英国, 23年后就消失了。它在英国造成的直接影响—许多人丧生、空荡荡的修道院、荒废的村庄—令人震惊,但长期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诺森伯兰的修道院在660年代遭受了鼠疫的惨重袭击,两代之后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鼠疫似乎无法撼动肥沃的土地、王权和巨大的财富。这些结论是从极为有限的资料中得出的, 当我们试图把目光投向修道院之外普通百姓的生活时,历史记录却无处可查。
叙利亚深受鼠疫的影响,短期和长期都是如此。载满鼠疫病人的轮船在公元 542年从埃及启航,停靠在加沙、亚实基伦、安提俄克,鼠疫从这些港口又传到大马士革,之后再传播到南方。从约翰的书中我们了解到了疫情的惨状。在那之后,公元541—749年,叙利亚几乎每七年就会暴发一次鼠疫。短期来看,鼠疫造成的死亡和大量出逃让许多地方都荒无人烟。长期来看,一再暴发的疫情给农业生产和定居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阿拉伯人四处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得疫情不容易蔓延,从而使得游牧民族的人口数量上升。始终脆弱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作物税收的减少和游牧经济的兴起。叙利亚鼠疫暴发次数如此之多,造成的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到伊斯兰早期,叙利亚成了人们口中的鼠疫之国。这一印象根深蒂固。到了中世纪,人们都知道伊斯兰叙利亚曾长期遭受鼠疫的毁灭性袭击。
关于首次鼠疫大流行我们所不知道的远远多于已知的信息。随着更先进的分析工具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转变。通过仔细研究书面资料只能得到现有的结论。历史学家必须要利用动物学、建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来揭开首次鼠疫之谜。
欧洲无鼠疫之患的时代随着鼠疫的再次暴发终结于1347年,这次疫情夺去了半数—可能还不止—欧洲人的性命。第二次大流行的冲击在1353年终于过去,之后的欧洲大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1347年鼠疫再次暴发后,它隔一段时间就会袭击欧洲和伊斯兰国家。欧洲的后一次鼠疫在1770年暴发于俄国。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不是一过性的, 而是严重程度、规模和影响范围各异的多次疫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鼠疫于14世纪中期从中亚传播到欧洲后就在当地扎下根来,这一观点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近关于中亚气候变迁和欧洲鼠疫流行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旧有的模型可能需要修正。鼠疫可能是一再播散到欧洲的。中亚的沙鼠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数量激增,它们到处游走,分布广泛,成为跳蚤的完美宿主。随后这些跳蚤跳到人类和家养动物身上,当时亚洲和欧洲的港口城市比如杜布罗夫尼克贸易往来繁忙,跳蚤随之被带到了欧洲。
几个世纪后欧洲人开始接受鼠疫的存在,甚至开始预测鼠疫的到来,并想出了应对鼠疫的办法。因此,人们对 1348年佛罗伦萨鼠疫和1665—1666年间伦敦鼠疫的反应就大不相同,两次鼠疫造成的影响也无法相提并论。前者对佛罗伦萨来说是前所未见的疫情,后者在1660年代虽然也是灾难性事件,但对伦敦来说,人们已经和它打过交道,对这种疾病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而在次大流行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疫病的暴发突如其来,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没有人见过这种病,它很特殊,能置人于死地。它是可怕的“黑死病”。
在七年的时间里,鼠疫在欧洲肆虐,对城市和农村造成破坏性影响。早关于鼠疫的历史记录出现在1346年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随后疫病无情地传播到欧洲各地。人们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丧生?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人们从几个方面对病因给出了解释: 天意、瘴气、接触传染、个人易感性等等,这些病因说互相有交集。就和霍乱流行一样,这些解释(特别是瘴气和接触传染)直到19世纪末期仍然在疾病传播理论中占统治地位。在黑死病期间—借由从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翻译成的阿拉伯语,中世纪晚期对伽林和希波克拉底著作的重新发掘正如火如荼,而臭气会致病的学说也正兴起—瘴气和接触传染这两种学说并不像日后那样水火不容。腐烂的植物释放毒气,瘴气从地面上扩散出去,人可能因此受到感染。随后这些具有传染性的人会把疾病传给他人,特别是那些容易惹病上身的人,比如有罪之人、心怀不满之人、放荡之徒和贪吃之徒。
这些对鼠疫传播路线的自然解释可以归入大众所认为的鼠疫的根源: 上帝的怒火。什鲁斯伯里的拉尔夫是巴斯和威尔斯教区主教,在感染鼠疫前,他恳求教众们祈祷。 1348年夏末,他写道:“邻国已经遭受了来自东方的疫病的袭击,我们担心除非我们诚心诚意、不眠不休地祈祷,同样的魔爪也将会伸向我们,夺人性命。”鼠疫来源于上天旨意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 1348年10月,巴黎医学院的老师在当时对鼠疫病因详尽的描述中写道:“疫病的根源在于天象……行星的会合和之前的排布,与日食以及月食一起,使得人们周围的空气受到严重污染,预示着死亡和饥荒的到来。”木星和火星相会尤其会造成“大量瘴气充斥于空气中”。木星使地气蒸发,而火星则将其引燃。不过,尽管这一科学解释基于观察之上,有理论作为支撑,并且坚信药物有助于控制疫情,但人们仍认为鼠疫的根源在于上帝。“我们不能忘记瘟疫乃天意,因此我们能给出的忠告就是怀着谦卑之心回归上帝。”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生动描述了人们对鼠疫的恐惧。《十日谈》以他在佛罗伦萨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是描绘鼠疫之下人们生活的杰出文学作品。在鼠疫病因上,薄伽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鼠疫可能是“天体的影响”,也可能是“上天的惩罚,表明上帝对人类堕落生活方式的义愤”。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突如其来的疫病面前,人类的智慧和才智毫无用处……医生和药物都帮不上忙”。
鼠疫造成的痛苦使得人们放弃了宗教和法律的约束: 没有人活着来执行它们。薄伽丘写道,住在城郊得不到治疗、没有家人也没有邻居照料的人们“像动物一样毫无尊严地”死去。人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灾难。“天降之祸(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有人祸)如此残酷,在书中提到的这一年的三月到六月带来大范围毁灭性的打击……据可靠估计,佛罗伦萨城内有10万人被夺去生命。”法国观察家写道,阿维尼翁有半数人丧生,马赛有五分之四的人死去。疫病在法国蔓延期间,“如此高的死亡率使得人们因为害怕,不敢跟任何有去世亲人的人说话,因为人们发现,家中如果有一个人去世,几乎其他所有人都会接二连三地死去”。猜疑和恐惧的情绪肆虐;人们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染病的家人;邻居们互相回避。在城市里,人们不顾殡葬习俗,将死去的人集中埋到大坟坑里,这至少表明了短期内社会秩序的崩塌。面对着可怕的疫病人们无能为力,许多人选择了逃离,然而穆斯林相信违抗神的旨意是亵渎神明。于是有人将疫病怪罪到其他人身上。在欧洲有多达 1 000个犹太社区被暴徒们摧毁。
尽管人们普遍感到无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仍然成立了卫生委员会来应对疫病。 为了保证空气的洁净,委员会下令要冲洗下水道和收集垃圾。当人们确信鼠疫正要蔓延到佛罗伦萨来时,政府下令禁止来自热那亚和比萨的人进入城内。疫病已成事实后,人们制定卫生条例,将“可能造成或引发空气污染的腐烂物和感染者”运走。这些措施大体上都无效。鼠疫仍然蔓延开来,夺去无数人的性命。要等到至少一百年后,稍微有些成效的预防措施才开始出现—不过到那时鼠疫的势头也早已减弱了。
面对鼠疫人们做出了种种不同反应: 有人试着来解释这场灾难;有人被恐惧所裹挟;有人仓皇出逃;有人怪罪于异族。而鼠疫对于人口、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宗教等的长期影响则不容易发现。短期来看,鼠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估计约有60%的欧洲人丧生。之后一个世纪人口仍然稀少,造成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并伴随着通货膨胀以及更多土地被开垦用以耕种的现象。人口减少短期内改变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某些方面,英国对此有完好的记录。 1349年,因为劳动力短缺,恩沙姆修道院的院长和庄主不得不重新与租户签订了对租户更有利的劳资协议。 1351年,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庄园里的农奴被免除了许多义务。在柴郡的德雷克洛皇家庄园,根据会计官约翰?德?沃德尔的记载,“由于疫情的影响”,房租减少了三分之一,“租户们威胁说不减租他们就离开(如此一来房屋将被空置),减租要一直持续到状况好转和房屋价值回升”。工资上涨了,但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劳动力短缺带来需求的上涨,同样意味着商品短缺。 人们要求更低的租金和更高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1349年议会通过了《劳工条例》, 1351年又通过了《劳工法令》,设定工资上限,强制人们工作,而违反者将受到惩罚。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迅速采取措施来打击任何试图从中获利之人。
媒体评论“作为一本试图从宏观层面勾勒瘟疫与人类历史演进的通识读本,作者选取了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结核、流感和艾滋病等七种主要的大流行病,讲述了每种疾病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如何导致了传染病的大流行。作者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文化分析巧妙结合,还论及当代的流行病,如新发传染病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热以及禽流感等。”
——北京大学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主任 张大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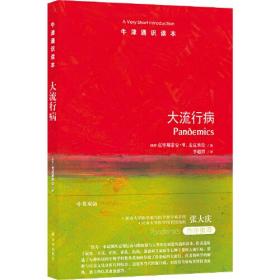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