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立足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转型背景,通过对大量档案文献的发掘与分析,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学科理论,来探寻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劳资合行”特质向国民革命时期党派政治属性演进的轨迹、特点与动因,以及隐匿于其演进过程背后的复杂面相,进而透视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诸多关联。这不仅可弥补目前学界在考察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甚少从劳资关系视角探讨的缺憾,而且还能为重新审视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问题提供典型样本和区域实证。
主编推荐
霍新宾(1972年2月——),江苏连云港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12年2月—2013年2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曾获广东省2006—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入选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七批省级培养对象。
精彩内容
结语:行会理念、阶级意识与党派政治
至少国民革命兴起前,广州劳资关系仍以“劳资合行”的社会经济属性为主,并未完全突破行会藩篱。恰如全汉升所论,“在这样工商的组织下,阶级意识是不会产生的”,“阶级意识既没有,劳资的阶级斗争自谈不到,从而政治上便可安宁无事”。然而,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党化渗透,尤其商团事件后国民政府“袒工抑商”政策的施行,其后“广州劳工运动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并迎来“澎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罢工次数很多,劳资的感情非常恶化”。广州劳资阶级斗争格局遂正式形成。至此,广州劳资关系亦由“劳资合行”的行会特质演进至盘根错节的党派政治模式。尽管这一演进的完成不过短短几年,具有剧烈易变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广州劳资关系的动态演绎中去寻觅其固有的内在变动理路。
从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党派政治属性的演进中不难发现,其始终蕴涵着“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劳资关系主题。当然,这两种主题并非固化,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波动。不过,就总的趋势来看,劳资协商合作是主要的,对抗则是次要的。如果说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和中共阶级斗争的渗透,是推进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促变”的直接诱因,那么以下“滞变”因素则使其呈现出“不变”的特点,并使传统行会“劳资合行”的协商合作主题往往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广州劳资双方的主要价值取向。
首先,劳资关系社会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协商合作主题形成的可能性。劳资关系作为一种以双方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与存在基础的社会关系,通常含有两种迥异的经济利益诉求:就劳方而言,资方若能及时提高工资待遇自是好不过,而资方当然是期望劳方尽可能减少工资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取更多利润。劳资双方这种对立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上述利益诉求的实现往往会有一艰难曲折的博弈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是劳资协商。不过,协商一旦破裂,罢工便成为工人挟制资方的杀手锏。而后,双方视罢工所产生的后果权衡利弊,或自行妥协了结,或诉诸第三方调停解决。当然,选择后一种方式对劳资双方来说实属无奈之举。因为罢工意味着停业与劳资关系的恶化,这势必危及生产的正常进行,且不说劳资双方的经济损失难以预料,就是行业内部稳定及社会秩序恐怕也成问题。其实,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劳资双方都很清楚,倘若争议中一味追求各自利益化,结果不免两败俱伤,而惟有劳资协商合作,方能实现劳资关系和社会生产正常运行。以上这种劳资协商合作主题,不仅时常呈现于广州传统行会时期,就是国民革命时期也不例外。据时人对1923—1927年广州222件劳资争议调停的分析,这些争议主要是由农工厅等第三方调处和劳资双方直接协商来解决,其结果也多是以劳方要求得到资方完全接受或部分承认而了结。须指出,这些劳资争议调解中所展现的协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共生性所决定的。尽管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党派政治属性愈益突显,但主导其变动的终因素仍是双方的自身经济利益,前述广州劳资借行会力量同盟抗税即是明证。
其次,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策导向是广州劳资关系协商合作主题生成的政治保障。综观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劳资政策之所以由“袒工抑商”至“袒商抑工”的转变,主要是其革命党与执政党一身二任的角色定位所致,也是其阶级调和理念的终使然。一方面,革命党的政治认同使其在广州选择革命群众基础时,由于商人先天政治保守的革命绝缘性,而自然更优先倾向于动员深具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国民党“袒工抑商”的政策导向则是此倾向的集中体现。而此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助长了劳资阶级斗争事件的滋生,尤其工运左倾更加剧劳资关系的紧张,并危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稳固,而这与国民党维系战时后方秩序为己任的执政党的角色认同不免相悖。此时,作为执政广州的国民党,为看重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固,自然不愿意激烈的劳资阶级斗争发生。于是,针对这种来自革命党角色定位所引发的劳资冲突有可能危及其统治秩序的危险,国民党阶级调和的执政党理念终占据主导。这就意味着其“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转向即是当然的了。其实,促使这种劳资政策转向的,还有国民党对广州商人受商民运动党化而支持革命的经济思虑,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共阶级革命所带来的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担忧。对此,深谙广东工运工作的陈公博曾这样评论道:
在广州时候,无日不看见工会分裂,工人罢工,我在农工厅时候,门口排列行打行的工人请愿,是日常司空见惯之事。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经过考虑的,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抓工人,势不能不煽动罢工,……广州既是国民政府的治下,而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那么政府维持秩序的作用已完全失掉。这样情况慢慢恶化,于是变成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不革命的了。
陈公博的上述评论,尽管带有强烈诋毁中共工人运动色彩,却也真实道出了中共阶级革命与国民党执政党角色定位的矛盾与冲突,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与协调两种劳资关系理念在国共党争中的真实显示。其实,国民革命后期中共也意识到阶级革命所带来的激烈的劳资冲突,有可能造成危及国民党统治秩序进而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后果,故也曾主张一定程度的劳资合作,试图缓和阶级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与政见的迥异,以及国民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由“慎重”向“激进”转化,国共合作的破裂亦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样,随着清党后中共势力在工人中的影响锐减,广州劳资阶级斗争态势自然也就弱化,其协商合作主题复居于常态,“广州劳工运动渐入于沉静的时期”。
此外,广州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顽强延续也是其劳资关系协商合作主题形成的要因。至少国民革命时期,广州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以传统商业、手工业为主,“是一个商业市,同时又为工业市。但所谓工业都是小规模的手工业,用机器的新工业寥寥无几”。而此种颇具传统色彩的“社会经济之形态,足以决定劳工运动之趋向”,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广州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行动始终受到来自行会制度、农业社会等传统因素的影响和支配。这里,不妨以刘尔崧的分析为例。1926年5月,时任国民党粤省党部工人部长的中共党人刘尔崧,曾对广州工人的阶级成分及阶级观念作了较切实的分析。为便于探讨,笔者根据其提供的相关信息整理成表8-1。
表8-11926年5月刘尔崧关于广州工人阶级成分及阶级观念的分析
工人类别人数占工人总数的比例阶级观念
产业工人
约17000人
8.5%真正的无产阶级,有觉悟。不过他们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职业介绍所,为其职业上之保障。因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
手工工厂工人
约25000人
12.5%工人阶级之地位比较明显,不过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农业社会之关系尚深,故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
手工业工人约11万人60%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
码头工人约13000人6.5%生活苦,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
水上工人约13000人6.5%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
店员
约12000人
6%论其生活可说甚苦,唯他们因营业关系,往往容易养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他们现在的阶级观念尚甚模糊
由上表不难得出如下基本看法:其一,传统行业工人在广州工界的社会构成中居优势。如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店员等传统行业工人占91.5%,而产业工人仅为8.5%。显然,这与广州传统社会经济形态是相适应的。其二,广州工人阶级观念模糊主要归于以下因素:(1)工人自身经济地位及营业状况。如被认为有阶级觉悟的产业工人,由于工资待遇高,其部分人易养成“工人贵族”观念,而水上工人和店员则因营业关系易生成小资产阶级思想。(2)行会制度的支配。如占广州工人总数60%的手工业工人,“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3)农业社会关系的渗透。如手工工厂工人部分因与农业社会关联而深受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码头工人“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以上因素尤以行会制度与农业社会关系对广州工人阶级意识影响。
正因行会制度和农业社会关系的长期浸染,广州工界内部纷争亦随之而加剧。尤至国民革命后期,这种“行会的恶作剧”又时常演化为激烈的武力械斗,“(民国)十五六年间广州工人械斗之事,层出不穷。每一举事,动辄数千百人,鸣枪燃炮,每次必丧数命。官厅虽加取缔,迄未停止”。广州工界的这种剧烈内争势必严重危及其整体阶级观念的生成,自然也就阻碍了其阶级觉悟的提升。诚如中共工运领导人邓中夏所分析的:
为什么广州工人没有阶级觉悟呢?因为广州新式产业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对于阶级之认识很难,他们的心理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还未脱离封建时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广东旧有械斗的风尚,他们受其熏染甚深。
如果说邓中夏所论的广州手工业工人由于“旧行会遗传性太深”,其阶级观念模糊尚可理解,那么被中共视为阶级意识的产业工人,其阶级觉悟程度在广州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广州产业工人也是深受行会制度和农业社会关系的熏染而难以自拔。在广州产业工人中居主导地位且深具行会制度渊源的机器工人堪称典型代表,“机器工人仍与小生产的农业社会有关系,即其家庭亦为农民家庭。因此农业社会之地方主义思想,仍旧存在于产业工人之脑海中,产业工人亦往往有地方之组织”。于是,地方主义观念、行会制度渊源以及自身优越的经济地位,共同造就了广州机器工人独立的“工人贵族”的身份特征。“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器]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这样,“劳资合行”的行会理念依旧在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团中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国民革命时期中共的阶级动员一直遭到这些践行劳资合作的行会型工会的冥顽抵制。
除社会传统因素阻滞广州工人阶级觉悟提升外,中共自身阶级动员能力的不足亦不容忽视。正如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所报告的:“我们的负责同志只在办公室中进行工作,没有主动地与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直至目前为止,广州的十五万工人中只有三百名党员”,可见,“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地领导工人群众”。加之国民革命后期,中共为缓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日益激化的阶级纷争,在劳资政策上进行了由激进至和缓的策略调整,这就使得其阶级斗争理念很难广泛渗透到工人中去,自然也就束缚了其阶级动员的手脚。“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足够明确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来对待工会运动和对待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成的工人群众组织。许多地方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行会组织,依然在国民党官僚,甚至是在买办阶级走狗(如广州机器工人工会)的影响之下。我们共产党却对这种状况安之若素,不去争取这些组织中的群众,也不把行会组织改造为产业工会。”曾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这番评论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工人阶级动员能力的限度。
总之,以上这些“滞变”因素共同制约着广州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劳资间的阶级意识分野,使其时常呈现出协商合作的主题。如此看来,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并未完全脱离资方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而中共对广州工人进行政治与阶级动员的难度可想而知。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对那种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工人阶级完成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传统观点予以重新审视。不可否认,就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转化而言,党派政治、社会思潮、民族主义运动等外因催化固然重要,但社会传统惯性尤其“工会中旧行会的积习甚深”的内因制约也不可轻视,而“劳资合行”理念对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便是很好的说明。事实上,至20世纪40年代,行会理念仍对中国工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国民党工运领导人马超俊有精当的观察:“虽然,行会之前途,固日趋没落,此种现象,以工商发达之各大城市,为显著,但交通闭塞之内地,工商业无若何改进,大体在职业上至今并未变更生产之形式,故其组织,仍多保留行会之固有形态与精神,丝毫无改。吾人置身内地,即可见各地之公所会馆,依然触目皆是,其数量犹多于工会。再以各大城市论,各业工人,亦有仅将公所改为工会,而其内部,并无变动。甚或因习惯已久,不能骤然废弃其传统之组织,仍沿用公所会馆之名称者亦多。”诚如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传统观点或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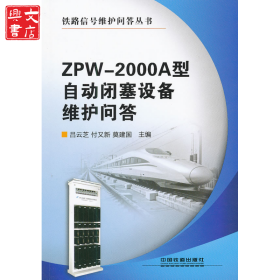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