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33.48 5.8折 ¥ 58 全新
库存281件
作者[英]沃尔特·厄尔曼 著,夏洞奇 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8032
出版时间2024-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29743532
上书时间2024-10-2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从5世纪到12世纪,当欧洲大片地区仍然无人居住时,一个社会已经成长了起来。这个社会必须学习如何组织公共生活秩序。今天西方的许多基本政治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及稍后一段时间形成的。
在这本写于1960年代的小册子里,作者追溯了西欧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例如主权、议会、公民权、法治和国家等我们熟悉的观念。在他看来,中世纪有两条意识形态的主轴影响着一系列观念、制度以及历史进程的发展。以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理论在欧洲重现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主导历史进程的是神权——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前者则逐步让位于自然法——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作者展示了这两种政府观念的冲突过程,以及它们的罗马或日耳曼根源,并解释了中世纪社会中教会权力的主导地位,以此诠释了整个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
作者简介作者:沃尔特·厄尔曼(Walter Ullmann,1910—1983),生于奥地利,先后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教会法与民法的“双法学”博士学位。1949—1978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一生著述颇丰,在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和法律理论等领域有着显赫地位,因将“政治概念历史化”而影响了多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一定时期内公认的学术权威。
译者:夏洞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专长为奥古斯丁研究。除《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还参与翻译过《新罗马帝国衰亡史》(詹姆斯·奥唐奈著)、《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彼得·布朗著)。
目录前 言
1970年版前言
佩里格林版前言
导 论
第一章 奠基:罗马与《圣经》的背景
Ⅰ罗马帝国中的罗马教会
Ⅱ罗马皇权政治思想
Ⅲ罗马-《圣经》观念的成长
第二章 西方的趋向
Ⅰ帝国的恺撒教宗主义
Ⅱ上帝恩典所立之国王
Ⅲ罗马与法兰克观念的融合
Ⅳ欧洲的概念
第三章 加洛林以降之发展
Ⅰ政治思想的教会化
Ⅱ大伪造
Ⅲ国王加冕礼中的政治理念
Ⅳ西方帝国的意识形态
第四章 成熟期的教权理论
Ⅰ主要特点
Ⅱ政治文献的出现
第五章 神权王权与封建王权
Ⅰ君权神授的实质
Ⅱ对该论点的维护
Ⅲ英格兰的王权与宪政主义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的复兴及其背景
Ⅰ自下而上论的实际表现
Ⅱ初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
Ⅲ亚里士多德的原则
第七章 新的趋向
Ⅰ托马斯主义
Ⅱ普世性国家
Ⅲ地域性主权
第八章 人民的主权
Ⅰ统治者权力的民众基础
Ⅱ作为主权立法者的人民
Ⅲ城邦国家
Ⅳ宗教会议至上论
Ⅴ保守主义与传统
第九章 结语
附录 对第三章的补充注释
原书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译者整理)
中世纪教宗年表(440—1500)(译者整理)
君主世系图(译者整理)
部分专有名词与术语索引
译后记
三联版译后记
内容摘要从5世纪到12世纪,当欧洲大片地区仍然无人居住时,一个社会已经成长了起来。这个社会必须学习如何组织公共生活秩序。今天西方的许多基本政治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及稍后一段时间形成的。
在这本写于1960年代的小册子里,作者追溯了西欧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例如主权、议会、公民权、法治和国家等我们熟悉的观念。在他看来,中世纪有两条意识形态的主轴影响着一系列观念、制度以及历史进程的发展。以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理论在欧洲重现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主导历史进程的是神权——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前者则逐步让位于自然法——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作者展示了这两种政府观念的冲突过程,以及它们的罗马或日耳曼根源,并解释了中世纪社会中教会权力的主导地位,以此诠释了整个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
主编推荐作者:沃尔特·厄尔曼(Walter Ullmann,1910—1983),生于奥地利,先后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教会法与民法的“双法学”博士学位。1949—1978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一生著述颇丰,在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和法律理论等领域有着显赫地位,因将“政治概念历史化”而影响了多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一定时期内公认的学术权威。
译者:夏洞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专长为奥古斯丁研究。除《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还参与翻译过《新罗马帝国衰亡史》(詹姆斯·奥唐奈著)、《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彼得·布朗著)。
精彩内容第三章(节选)
Ⅰ政治思想的教会化
在9世纪以前,教宗制可能从未显出过这么强烈的进取心。我们还记得,在为查理曼加冕时,教宗利奥三世的意图尚未得到实现。作为法兰克人,查理曼并没有接受那一套罗马-教宗派的理念。除了这一点,加冕礼本身也缺乏任何的宗教仪式或教会的性质。虽然它是在一座教堂(圣彼得教堂)中举行的,却没有为国王-皇帝举行膏立礼,没有进行祈祷,没有做任何具有特定的宗教仪式意味的事情。它只不过是一种在教堂里举行的、人为编导出来的行为而已。利奥三世的继位者最清楚地看出了其中的不足。为了达到教宗派创造“罗马人皇帝”的目的,教宗斯德望四世(816—817年在位)再次访问了法兰克王国。当时查理曼的儿子路易一世已经即位,他的父皇在生前就已经模仿拜占庭的做法,使他成为共治的皇帝了。基于两个原因,816年斯德望四世和路易一世在兰斯的会晤是很有历史意义的。第一,这时教宗拿出了一顶据说是君士坦丁戴过的皇冠,并用它来为路易一世加冕。没有什么比拿出君士坦丁的皇冠更有意义、更有说服力的事情了——在800年时没有用它,这无疑是一个必须马上得到补救的缺陷。第二,与此同时,教宗膏立了路易一世,这样膏立和加冕就在同一场宗教仪式中结合了起来。在以后的任何加冕礼中,二者都构成了最基本的因素。虽然膏立是起源于法兰克人的(也有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西哥特人的),加冕礼的观念却是拜占庭的。
816年的加冕以易于理解的象征手法表现了公共治理方面的基本概念。此刻膏立的象征意义被理解为,由于基督的恩典注入了国王,这样国王就变成了“基督的范型”(Type of Christ)或者说“基督的形象”(Figure of Christ)。实际上,在膏立主教和膏立国王之间只有一点根本性的差异,就是说国王(和皇帝)的膏立礼并不给予所谓的“不可消除性”,不需要按手,国王(和皇帝)并不会得到“灵魂治疗”的能力。在两种情况下,施行膏立仪式的恰当位置都是象征首领地位的头部。下文将会讲到皇帝的膏立是怎么施行的,它不是膏在头上,而是涂在两肩之间的后背上。
在816年,为了完成800年所未及之事,是教宗来到了法国。但七年以后,教宗就不必亲自跋涉了。那时路易一世的儿子罗塔尔一世在意大利,他应邀在复活节访问罗马,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罗塔尔一世也被父皇立为共治皇帝了。教宗又一次掌握了主动。加冕礼是在圣彼得的主祭坛举行的,今后那里就成了皇帝加冕的规定地点。在这次加冕中又增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皇帝从教宗手中接受了一把剑。在8世纪也有类似的先例。在758年,教宗保罗一世(在前一年继承了斯德望二世)就赠给丕平一把剑。这把剑一直被理解为物质力量的象征,教宗授予剑不仅象征着皇帝已经从教宗那里得到了“力量”,还代表着皇帝有责任来保护教宗。所以这种象征很自然地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后来皇帝被说成是从教宗那里得到了实际权力。那样它的实际意义就与圣保罗所谓的“君王不是徒劳地佩剑”联系了起来。在这种语境中,可以说“他佩剑的理由”就是“施怒于作恶者”。至于何为恶者,何者当受惩治,这都由那些在基督教社会中有权决定的人说了算。这样皇帝的辅佐职责就得到了清楚的说明——在823年还没什么希望来实现这种观念,但教宗派的政治理念时常遥遥领先于实际的运用。剑的仪式清楚地传达了皇帝在惩恶的方面辅佐教宗的观念。后来,从11世纪开始,剑是从圣彼得的祭坛上(也就是放教宗披肩的地方)取下来的,意思明显就是剑(和教宗披肩一样)都直接来自圣彼得。按那时的人里昂的阿戈巴德的说法,剑在9世纪的具体含义是“顺服诸蛮族,使其皈依信仰,为信众之王国开疆拓土”。(阿戈巴德认为古老的5世纪耶稣受难节祷词指的就是世俗统治者的剑。)
在823年,是教宗邀请了国王;而在850年,就是父皇来请求教宗将他的儿子(路易二世)加冕为罗马人皇帝了。这次加冕和膏立是确立路易二世为皇帝的唯一一次宪制性行为,因为此前路易二世并没有被立为共治皇帝。和“君士坦丁的赠礼”很相似,皇帝(在加冕之前)在前面驭马,让教宗坐在马上行进了一箭之地。虽然这三次加冕都为加冕礼增添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但查理曼加冕75年之后的那次加冕更有力地说明了教宗的主动地位。毋需发出任何邀请,毋需提出任何请求,教宗约翰八世传召了秃头查理——正如教宗所表明的那样,他是由教宗亲自传召、选立和确定的,是“凭着使徒宗座的特权”而成为罗马人皇帝的。约翰八世宣称,天上的启示指点了这一选择;另一次他又说,皇帝“是吾等所求所愿,是上帝所召叫的”。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以不寻常的方式,抽象的政治思想被转变成现实,而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查理曼的继承者们接受了教宗派的政治观点。9世纪教宗制的矢志不移和进取之心,在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相似者的。可以看到,对一个政治机构来说,具有一份蓝图或者说是纲领是多么有利的事,只要该纲领的承担者能够坚定地追求它,只要它能够符合时代的情绪。只要我们想到教宗制的巧妙手腕——它总是能以神的命令、神的法律和传统来为每个步骤提供理由,并想到那时候的一切以基督为中心的情景,教宗制的前进就很容易理解了。
查理曼当作一项原则所坚定地拒绝的东西,亦即任何意义上的“罗马”皇帝位,在9世纪当中逐步变成了他的继承者们的政策。这样,他们就接受了教宗制的思想和立场。在后者看来,真正的“罗马”皇帝位只能来自教宗,而东方的皇帝只是希腊人的统治者而已——治理和统治的普世性归于真正的罗马人皇帝,而他是由教宗来加冕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查理曼的继承者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教宗派的论点。在这许多例子中,只要举一个就够了。路易二世在871年写给拜占庭皇帝的信,经典地反映了潜藏在教宗派和西方皇权理念背后的意识形态。这封信不承认拜占庭人能被合法地称为罗马人皇帝,因为他并不是教宗所造就的;教宗不能立他为罗马人皇帝,这是由于他就不算罗马人,因为唯有承认教宗首位职责的人才是罗马人。拜占庭人只不过是希腊人的君王而已。进一步说,众所周知的是,希腊人都接受了错误的教义。这封信认为,真正的教义[与异端(这封信所用的词是“伪教义”)相对的正统]只存在于西方;作为正统的维护者,教宗制有权授予最高的实际统治权,从而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捍卫。路易二世毫不踌躇地告诉那位东方的竞争者,他已经从使徒宗座那里得到了统治的权威。这封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教宗派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现实。在8世纪中叶,教宗还只是一位恳求者——不过一个多世纪以后,教宗的意识形态已经改变了欧洲的基本性质,那时的欧洲已经由教宗所创造的罗马人皇帝来统治了。
在从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变为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对政府学说具有直接影响的文字表述。例如,对有学问的“藏书家”阿纳斯塔修斯来说(约860年),教宗就是上帝的代牧,有权分配地上的权力,因为他就是天国的守门人。他非常清楚地论述了圣彼得的捆绑与束缚权力的全面性:教宗所封闭的,没有人可以重新开启。换言之,在基督教社会中,最高的管辖权亦即最高统治权是属于教宗的。尽管这种论述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于《圣经》的(如果没有断章取义的话),但重要的事实仍然在于,《圣经》的论述被直接运用到教宗身上了。这被恰当地称为教宗制对《圣经》的垄断(见E.坎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根据《诗篇》45:17—18,尼古拉一世认为,教宗被立为全地的君王。尼古拉一世还认为,教会所有的一切都在罗马教会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罗马教会是一切教会权力的典范。他重申了原来的教义,认为在地上没有人能够裁判教宗,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宗的臣民,他们的所有权力都是来自教宗的。最高的管辖权只归教宗所有,教宗的教令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约束力。全体基督徒的有形联合体是以教宗为首的,服从于教宗的政府。它被尼古拉称为“全体信众的社会”,是由教宗所给予的法律来引导的,因为只有教宗才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这位尼古拉一世还主张,在加冕礼上皇帝的统治权得到了“承认”,因为他被给予了使用剑的权利。职责的目的论立刻就显现出来了。皇帝之所以得到剑,是“为了他的母亲,为了这个神圣的、使徒传承的教会的荣耀与和平”。至此,教宗决定了统治者拥有剑的理由。尼古拉在一封写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问道,拜占庭人只懂得希腊文,根本就不识拉丁文,他们怎能成为罗马人皇帝呢!
对尼古拉一世来说,作为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的共同体,“全体信众的社会”就是一个单凭基督信仰结合起来的联合体。他说,如果允许这个信仰的纽带在某种情况下断裂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根据这样的考虑,他给予君王们以详细的指导,论述了他们的责任。消除异端就是其中之一。国王们是教宗的臣民:他们不能裁判自己的主人,正如《圣经》所说,徒弟不能高过师傅(《马太福音》6:24,《路加福音》16:13)。尼古拉想要表达的原则,是神职人员免于世俗的、王权的裁判的权利,因为这条原则是从教宗制的功能论思路当中产生的。在“全体信众的社会”当中,教会的法律应当优先于君王的法律;世俗的法律被认为具有辅助性的性质,只要教会的法令没有特殊的规定,只要它们和教会法的原则没有任何矛盾。一言以蔽之,国王的法律必须与整个社会之所以存在的目的相符合,必须与罗马教会所阐发的信仰相一致。正如尼古拉一世所说,一切法律的功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性”。如果国王颁布了超出其管辖范围,甚至违背基督教社会之目的的法律,国王就不应当被服从——但这不算是真正的抵抗权,因为不服从的行为必须由那些有资格做决定的人来批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完全符合国王加冕礼的宗旨。事实上,按尼古拉的观点,国王的暴政在性质上就像异端一样。对他来说(对他的许多继承者也一样),如果国王不尊重教宗的法律和教令,就等于是异端了,就是国王一方要背叛的明显信号。对于尼古拉,教宗就是最高统治者,因为他的教令是终极性的,是以“全能上帝的权威”而发出的。
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阿德里安二世(867—872年在位)也强调了这种理念。他专门论述了教宗的圣彼得地位,认为既然圣彼得是基督选立的,其继承人的教令也就具有和基督亲自发出的命令相等同的效力。阿德里安二世认为,既然正义是法律的基础,教宗的教令就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正义的理念。在格列高利七世那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观念的成熟形态。教宗管辖权的全面性显然来自圣彼得的托付,教宗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一切”的托付就等于“一切”。他认为自己有权命令贵族们在绝罚的压力下拿起武器,准备实施军事行为。阿德里安还认为,教宗有权将任何基督徒(包括国王在内)从“全体信众的社会”中排除出去,因为王国的稳定有赖于国王对基督教君王责任的履行。
只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两位9世纪教宗的观点,教宗派政治意识形态得到具体实施的原因就很清楚了。他们的语言用了发号施令的统治者(gubernator)的口气,其命令被视为正义的体现。对教宗制来说很明显的是,只有那些有资格的人才能判断正义的具体内容。正如8世纪的教宗格列高利二世所说,只有那些具有“基督的判断和心灵”的人才能下这种判断。最根本性的是分工的原则。按这种原则,每一种职责的承担者,不论他是国王、皇帝还是主教,都必须遵循交托给他的职责范围。在这个问题上,阿德里安二世和格列高利一世都坚持,“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职位的要求”。应该说,这种观点也反映了社会的静态性。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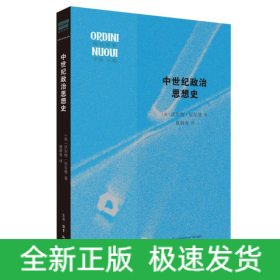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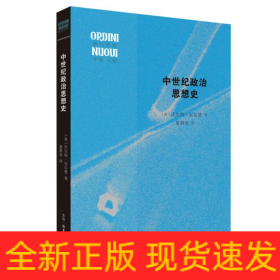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