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噪音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可开发票
¥ 35.21 5.2折 ¥ 68 全新
库存10件
作者唐?德里罗 著 朱叶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8309
出版时间2013-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29502008
上书时间2024-10-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杰克?格拉迪尼的大家庭过着平凡典型的现代生活,固定的超市购物之旅和周五的电视晚餐是他们“幸福”的基石。然而,一场化学品泄漏事故将致命毒雾送上天空,向他宣告“死亡已经到来,它就在你的体内”。恐惧已入侵心灵每个角落,它就像白噪音,始终如一,无处不在。
《白噪音》为德里罗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出版以来始终被誉为文学经典,也是后现代文学的代表。它描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伤害,呈现了人在死亡、信仰、灾难和暴力面前的惊恐,对现代人的困境作了先知般的预言。
作者简介唐?德里罗 Don DeLillo
出生于1936年,美国当代文学巨擘,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美国当代蕞重要的四位作家之一"。著有《名字》《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零K》《寂静》等。
德里罗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极限状态:超现实、消费文化、媒体权力、集体狂热、恐怖主义直到世界末日……他以先知般的笔触,刻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魔力与恐惧,预言人类命运的终点。
唐?德里罗以"代表美国文学蕞高水准"的创作,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终身成就奖、美国笔会/索尔?贝娄文学终身成就奖、耶路撒冷奖等十多种重量级文学奖项。
目录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译序)/朱叶
一 波与辐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二 空中毒雾事件
21
三 “戴乐儿”闹剧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内容摘要杰克?格拉迪尼的大家庭过着平凡典型的现代生活,固定的超市购物之旅和周五的电视晚餐是他们“幸福”的基石。然而,一场化学品泄漏事故将致命毒雾送上天空,向他宣告“死亡已经到来,它就在你的体内”。恐惧已入侵心灵每个角落,它就像白噪音,始终如一,无处不在。
《白噪音》为德里罗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出版以来始终被誉为文学经典,也是后现代文学的代表。它描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伤害,呈现了人在死亡、信仰、灾难和暴力面前的惊恐,对现代人的困境作了先知般的预言。
主编推荐唐?德里罗 Don DeLillo
出生于1936年,美国当代文学巨擘,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美国当代蕞重要的四位作家之一"。著有《名字》《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零K》《寂静》等。
德里罗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极限状态:超现实、消费文化、媒体权力、集体狂热、恐怖主义直到世界末日……他以先知般的笔触,刻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魔力与恐惧,预言人类命运的终点。
唐?德里罗以"代表美国文学蕞高水准"的创作,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终身成就奖、美国笔会/索尔?贝娄文学终身成就奖、耶路撒冷奖等十多种重量级文学奖项。
精彩内容空中毒雾事件
21
昨夜大雪伴我入梦,清早空气清新,而且一片寂静。一月份的晨光里有一种严厉凄凉的特性,强硬和自信。靴子踩踏雪地发出一阵阵吱嘎声,高远的天空中飞机划出一道道白色尾流。气候至关紧要,虽然我一开始还未意识到。
我转弯走进我家所在的大街,穿过车行道上口喷白气、手持铁锹铲雪的人们。一只松鼠顺着树枝滑行——这个动作的连续性,使它看起来好像具有自身的自然规律,而不同于我们现在相信的那些规律。当我走完半条街时,我抬头看见海因利希蹲在家中阁楼窗户外面的窗台上。他穿戴着他的迷彩服和帽子,这套服装对于他具有复杂的意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拼命想长大的同时,又不想让人注意—这点儿秘密其实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他端着望远镜向东方瞭望。
我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回到厨房。门厅里的洗碗机和烘干机运转良好。我从芭比特说话的声音中听出来,她正在与她父亲通电话。不耐烦中夹杂着内疚和担忧。我站到她身后,把冰冷的双手放到她两颊上—这是我爱做的一桩小淘气事儿。她挂断了电话。
“他为什么到房顶上去?”
“海因利希吗?火车调车场出了什么事儿,”她说,“收音机里刚报道过。”
“我应该把他叫下来吗?”
“为什么?”
“他会摔下来的。”
“别对他那样说。”
“为什么不可以?”
“他会认为你低估了他。”
“他蹲在一个外窗台上。”我说,“我总应该做点儿什么事吧。”
“你越露出焦急不安,他就会越往房顶边缘靠近。”
“我知道,但是我仍然必须把他弄下房顶。”
“哄他回房里来。”她说,“要考虑细致和显得关心。让他谈谈他自己,不要做出鲁莽的动作。”
当我上到阁楼时,他已经进了房,站在打开的窗户边上,仍然端着望远镜在看。到处是废弃物,在暴露的梁柱和玻璃纤维绝缘垫之中自有一种特别的情状,令人窒息和不安。
“发生了什么事?”
“收音机里说一辆罐车出了轨。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从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出的轨。我认为它是被什么东西撞出了一个窟窿。现在那边烟雾腾腾,我可不喜欢那样子。”
“它看起来什么样子?”
他把望远镜给了我,自己朝边上走了一步。我没有爬到房顶的外窗台上去,所以看不见火车调车场和出轨的罐车。但是,烟雾看得很清楚,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浓密黑团在河对岸的空中悬挂着。
“你见到消防车了吗?”
“那地方到处都是消防车。”他说,“但是我看它们好像没有靠得很近,一定是那东西太毒,或者易爆,或者既毒又易爆。”
“它不会向这里飘过来。”
“你怎么知道呢?”
“它就是不会嘛。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再站在结冰的房顶外窗台上,这让芭贝担心。”
“你认为,如果你告诉我这事让芭贝担心,我就会感到歉疚而不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对我说你为此而担心的话,我还会这样做。”
“把窗户关上。”我对他说。
我们一起下楼到厨房去。斯泰菲正在翻检大红大绿的邮件,寻找优惠券、奖券和有奖竞赛题。今天是中小学后一天假。山上学院一星期后恢复上课。我让海因利希去把人行道上的雪扫了。我看着他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脑袋微侧,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倾听河对岸的警报声。
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到阁楼上,但是这一次拿了收音机和公路图。我爬上狭窄的楼梯,向他借了望远镜再一次观察。那团烟雾还在那儿,比以前大了一点儿,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直冲天空的一个大团,或许更浓黑一些。
“收音机里称它为羽状烟雾。”他说,“不过它不是羽状烟雾。”
“它是什么呢?”
“像一个形状不定、逐渐增大的东西。一个散发浓黑烟雾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叫它羽状烟雾呢?”
“广播时间宝贵,他们不可能不厌其烦地做连篇累牍的描述。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什么样的化学品?”
“它称为尼奥丁衍生物或尼奥丁—D。我们在学校里看过的一部关于有毒废物的电影介绍过。还有被录像的耗子。”
“它会造成什么后果?”
“那部电影不能肯定它对人类有什么影响。电影主要是说耗子长出了致命的肿块。”
“那是电影中所说的。收音机里说什么来着?”
“开始他们说会引起皮肤瘙痒和掌心出汗。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是恶心、呕吐和气喘。”
“我们谈的是人感到恶心,不是耗子。”
“不是耗子。”他说。
我把望远镜还给他。
“它不会朝这里飘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呢?”他说。
“我就是知道。它今天完全是不活动和静止的。每年这时候有风的时候,都是朝那边而不是朝这边吹的。”
“万一风朝这儿吹怎么办呢?”
“不会的。”
“就这一次是这样。”
“不会的。为什么会那样呢?”
他顿了一下,然后用平淡的口气说:“他们刚刚关闭了部分州际公路。”
“他们当然会想到那样做。”
“为什么?”
“他们就是会那样。明智的预防措施。这是给公用交通等提供便利的一种做法。有很多需要这样做的理由,但是都与风或风向无关。”
芭比特的脑袋出现在楼梯口。她说一位邻居告诉她,罐车的泄漏量达到三万五千加仑。人们正在被告知离开该地区。泄漏现场的上空有一团羽状烟雾。她还说,女孩们正在诉说手心冒汗。
“有一个克服的办法。”海因利希对她说,“告诉她们应该呕吐干净。”
一架直升飞机朝着事故现场飞去。收音机里的声音说:“只供可选容量硬盘使用一段有限时间。”
芭比特的脑袋缩下去不见了。我看着海因利希把公路图用胶带粘在两根柱子上。然后,我下楼到厨房去开支票付账单。这时,我意识到有一些彩色的光点在我右边和身后快速地转来转去。
斯泰菲说:“你从阁楼窗子能看见羽状烟雾吗?”
“那不是羽状烟雾。”
“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家吗?”
“当然不必。”
“你怎么知道呢?”
“我就是知道。”
“记得那次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上学吗?”
“那是在室内。这是在室外。”
我们听见警报声响起来了。我看着斯泰菲的嘴唇做出一串喔嗷、喔嗷、喔嗷、喔嗷的口形。当她看到我在注视她时,便诡谲地一笑,好像从某种心不在焉的快乐中被轻轻地惊醒过来。
丹妮斯走了进来,双手在牛仔裤上摩挲着。
“他们正在用吹雪机向泄漏物喷射东西。”她说。
“什么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但是它应该是用来使泄漏物变得无害,这并没有解释他们正在对于那羽状烟雾做什么。”
“他们正在设法使它不再变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我说不准,但是如果它再变大的话,有风没风它都会到达这儿的。”
“它不会到达这儿。”我说。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它不会。”
她看了一下自己双手的掌心,就上楼去了。电话铃声响起,芭比特走进厨房,拿起话筒。她边听电话边看着我。我开了两张支票,其间,我隔一段时间抬起头瞄一眼,看看她是不是还在看着我。她似乎想从我脸上的表情弄明白她从电话中听到的话所蕴含的意思。我把嘴唇撅成我知道她讨厌的样子。
“那是斯托弗家的人。”她说,“他们直接与玻璃镇郊外的气象中心通了电话。他们不再称它为羽状烟雾。”
“他们现在叫它什么?”
“一团滚动的黑色烟雾。”
“这名称更准确一点儿,这说明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解决问题。真好。”
“还有呢。”她说,“预料有某种气团正在从加拿大向这里移动。”
“从加拿大总有一个气团向这里移动。”
“那倒是真的。”她说,“这事儿肯定没有什么新鲜。既然加拿大在北面,那么,如果滚动的烟雾向正南方吹的话,它就会隔得相当远地离我们而去。”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我说。
我们又听到警报声,这一次是另外一种信号,声音也更大—不是警车、救火车、救护车发出的警报。我明白那是空袭警报声,好像是东北方向一个叫锯手镇的小集镇那边发出来的。
斯泰菲在厨房水池里洗好手就上了楼。芭比特开始从冰箱里取东西。她走过桌子时,我抓住了她大腿的内侧。她手里拿着一盒冻玉米,优美地扭动身体。
“或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那团滚动的烟雾。”她说,“我们是因为孩子们才坚持说不会有事的。我们不想吓着他们。”
“没有事将要发生。”
“我知道没有事将要发生,你知道没有事将要发生。但是,在某个层次上我们总是应该考虑它一下,仅仅以防万一。”
“穷人居住的暴露地区才会发生这些事情。社会以特殊的方式构成,其结果是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成为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低洼地区的住户遭受水灾。棚户区居民遭受飓风和龙卷风之害。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在电视上的水灾镜头中,见到过一个大学教授在他所住的街上划着一条小船吗?我们住在一座整洁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小城里。附近还有一所名称古怪的学院。这些事在铁匠镇这样的地方不会发生。“
她现在坐在我的膝上,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支票、账单、有奖竞赛表格和优惠券。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吃晚饭?”她挑逗地对我耳语。
“我没吃午饭。”
“要不要我做点儿油炸辣味鸡?”
“好极了。”
“怀尔德在哪儿?”她口齿不清地说。我的两只手在她乳房上抚摩,同时我试图用牙齿隔着她的上衣解开她的胸罩扣。
“我不知道。也许默里把他偷走了。”
“我熨好了你的睡衣。”她说。
“太好了,太好了。”
“你付电话账单了吗?”
“找不到账单啊。”
这会儿我俩的声音都含混不清了。她的两臂交叉,压在我的两臂上,使我正好看得清她左手里的玉米棒尖盒子上的食用说明。
“让我们想想那滚动的烟雾吧。就想一会儿,行吗?它可能是危险的。”
“罐车里装的东西都是危险的。但是其效果都是远期的,我们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开它。”
“我们千万要把这事放在心上留意着。”她说,一边站起身来,将一只冰盘在水池边上反复敲打,三三两两的冰块被打了出来。
我向她撅起了嘴。然后我再一次爬上阁楼。怀尔德与海因利希在一起,后者向我迅速一瞥,带着责备的眼光。
“他们不再称它为羽状烟雾了。”他说此话时目光不与我对视,似乎为了使他自己免受见到我的窘态。
“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现在叫它滚动的黑色烟雾。”
“好。”
“为什么这样就好?”
“这说明他们现在大致在正视这件事了。他们是完全掌握情况的人。”
我摆出了一副厌烦而果断的神气,打开窗,端起望远镜,爬到房顶的外窗台上。我穿着厚厚的套头衫,在冷空气中感觉够舒服了;但是我设法保证自己的身体重心侧向房子,我儿子还伸出手臂抓住我的裤腰带。我感觉到了他对我这小小使命的支持,他甚至满怀希望地相信,我能够把我成熟和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分量加在他正确的观察上,从而使其站得住脚。这样做毕竟是父母的职责。
我举起望远镜,穿过越来越沉的暮色张望。在化学品的烟雾下,是一片紧张和混乱的情景。探照灯光在调车场里扫来扫去。军用直升机在不同的点上往下面的出事现场发射一道道光束。警察巡逻车的彩色灯光与这些宽阔的光束交相辉映。罐车死死地躺在铁轨上,雾气好像从它一头的窟窿中升腾。显然是第二辆车上的连接装置戳破了罐车。消防车停在一段距离之外,救护车和警车停得更远。我能够听到警报声、手提扩音器里的呼叫声,一股无线电静电在冷空气中使之略略变调。人们从一辆车子奔向另一辆车子,卸下仪器设备,抬着空担架。另外一些人穿戴着黄色米莱克斯服和防毒面具,拿着死亡测量仪器,在亮闪闪的烟雾中缓慢地移动。吹雪机向罐车及其四周喷射一种粉色的物质,它在空中形成一道弧状的浓雾,看起来好像爱国节音乐会上巨大的装饰物。吹雪机是用于机场跑道的那种,警车则是运输暴乱中伤亡者的那种。烟雾从红色的光束里飘进黑暗,然后又从探照灯的白光中飘出。穿米莱克斯服的人像登月者似的小心行进,跨出的每一步都是令人焦虑的举动,而非出于人的本能。着火和爆炸在此已算不得什么危险。这种死亡将会渗透,渗入人的基因,在尚未出生的人体内显示出来。他们陷入了关于时间性质概念的困境,行进时好像在穿越无垠的、飘动着月球尘土的荒滩。
我有点吃力地爬回房里。
“你觉得怎样?”他说。
“它仍然悬挂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扎根那地方了。”
“所以你是在说,你认为它不会到这里来。”
“我从你的话里听得出来,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认为它会到这儿来,还是不会?”
“你要我说它一百万年后也不会到这里来。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一小堆数据来攻击。说吧,在我爬到外面去的时候,收音机里说了些什么。”
“不像他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它不会引起恶心、呕吐、气喘。”
“那它会引起什么?”
“心悸和幻觉。”
“幻觉?”
“它引起人类记忆的虚假成分或者什么的。还不光是这一点。他们现在不再称它为滚动的黑色烟雾了。”
“他们现在称它为什么?”
他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下。
“空中毒雾事件。”
他用一种预示凶兆的干脆腔调,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几个字,好像他意识到了这个特殊情景产生的术语所包含的威胁。他继续仔细地端详我,企图从我脸上寻找某种没有真的危险可能性的保证—对于这种保证他会立即加以否定并斥为虚假,这是他惯于玩弄的一种手法。
“这些事情并不重要。至关紧要的是位置。它在那儿,我们在这儿。”
“一个巨大的气团正从加拿大向这儿移动。”他平静地说。
“我已经知道这一点。”
“那并不说明它不重要。”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要根据情况而定。”
“气候马上要变了。”他简直是对我在喊叫了,他的嗓音中带着他生命中特殊时刻的悲鸣。
“我不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我还是一个系主任。我不能在一场空中毒雾事件中逃跑。那是住在穷乡僻壤的养鱼场附近活动房里的人干的事儿。”
我们看着怀尔德倒退着下了阁楼楼梯,那是整幢房子里的楼梯。吃晚饭时,丹妮斯几次三番站起身来,一只手捂着嘴巴,急急地小跑步到过道外面的盥洗间去。我们在咀嚼和往食物上撒盐时,尴尬地停下来听她断断续续呕吐。海因利希对她说,她表现出过了日期的症状。她眯着眼瞪了他一下。这个时代盛行使眼色和说不尽的心领神会,我一般来说赞赏这种传递感觉的方式。体温、吵闹声、灯光、脸色、言辞、手势、个性、器械。频繁的对话使得家庭生活成为感性认识的一种媒介,其中包含了惯常的心灵的震撼。
我看着姑娘们半闭着眼睛交谈。
“我们今晚是不是吃饭早了一点儿?”丹妮斯说。
“什么时间叫早?”她妈妈说。
丹妮斯看了一眼斯泰菲。
“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躲避它?”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斯泰菲说。
“会发生什么呢?”芭比特说。
姑娘们再次互相对视,严肃和长久地交换眼神,表明某种不祥的猜测正在被证实。空袭警报又一次响起,这一次离我们非常近,以至我们都感到不安,甚至设法避开对方的目光,以此来否认某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声响来自我们自己的红砖房消防站,这些警报声十多年没有使用过了。它们汇聚而成的噪音像是某种来自中生代的动物保卫自己领地时发出的粗厉叫声。一只具有大如D-9运输飞机翼展的食肉鹦鹉。野蛮侵扰的巨大喧嚣充斥了整座房子,使它的四面墙似乎都要崩裂。这声音怪物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如此确实无疑地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简直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多年来一直躲在我们附近。
我们继续吃饭,动作安静、利索,每一口吃的食物越来越少,请求传递东西时客气礼貌。我们变得小心翼翼和寡言少语,缩小自己动作的幅度,在面包上涂黄油的样子就像是专家在修复壁画。恐怖的粗厉声还在响着。我们仍然避免目光相对,小心地不让餐具发出声响。我相信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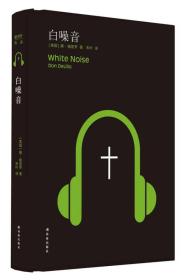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