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当正版 我以翅膀触碰你 李都格 9787522500386 九州出版社
新华书店直发 全新正版 急速发货 开票联系客服
¥ 12.6 2.6折 ¥ 49 全新
库存4件
作者李都格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22500386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29278753
上书时间2024-10-2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1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心理系新生金冬冬入学不久即被敏感阴郁的医学生季晓辉吸引,在碰到晓辉舍友,冷硬坚定、怀抱英雄主义的奚江后,又与之萌发新的火花,三人的关系因晓辉突染重病,嘎然止步。护理系学生心心在一次探病之后,以奋不顾身的热情投入对晓辉的爱恋,四人由此开始一段夹杂着苦涩、泪水和甜蜜的爱之旅途。晓辉死后,心心在奚江、金冬冬的陪伴下,爬出谷底,到晓辉住过的那家医院工作,其后在一场烈性传染病的救治工作中殉职。至友接连去世的打击下,奚江和金冬冬踏上各自寻求救赎的路。他们再未见面,而那个关于心灵的秘密也许藏在他后给她的那封信里……
本书探讨心灵之爱的敞开性和神圣意味,通过四个青年学生之间的情感,找寻爱在其自身内实现完善的可能性,打造一条经由爱实现精神不断上升的通道。
商品简介心理系新生金冬冬入学不久即被敏感阴郁的医学生季晓辉吸引,在碰到晓辉舍友,冷硬坚定、怀抱英雄主义的奚江后,又与之萌发新的火花,三人的关系因晓辉突染重病,嘎然止步。护理系学生心心在一次探病之后,以奋不顾身的热情投入对晓辉的爱恋,四人由此开始一段夹杂着苦涩、泪水和甜蜜的爱之旅途。晓辉死后,心心在奚江、金冬冬的陪伴下,爬出谷底,到晓辉住过的那家医院工作,其后在一场烈性传染病的救治工作中殉职。至友接连去世的打击下,奚江和金冬冬踏上各自寻求救赎的路。他们再未见面,而那个关于心灵的秘密也许藏在他后给她的那封信里……
本书探讨心灵之爱的敞开性和神圣意味,通过四个青年学生之间的情感,找寻爱在其自身内实现完善的可能性,打造一条经由爱实现精神不断上升的通道。
作者简介李都格,苏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士,同济大学外国哲学硕士,现居常州,小说《石榴子》获评为“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入围作品”。
目录目录
引 001
童年 003
熔化 023
结晶 039
心心 061
礼物 097
锻铸 112
强盗 141
秘密 159
魔法 179
重生 201
尾声 225
他的来信 244
(代后记)
内容摘要心理系新生金冬冬入学不久即被敏感阴郁的医学生季晓辉吸引,在碰到晓辉舍友,冷硬坚定、怀抱英雄主义的奚江后,又与之萌发新的火花,三人的关系因晓辉突染重病,嘎然止步。护理系学生心心在一次探病之后,以奋不顾身的热情投入对晓辉的爱恋,四人由此开始一段夹杂着苦涩、泪水和甜蜜的爱之旅途。晓辉死后,心心在奚江、金冬冬的陪伴下,爬出谷底,到晓辉住过的那家医院工作,其后在一场烈性传染病的救治工作中殉职。至友接连去世的打击下,奚江和金冬冬踏上各自寻求救赎的路。他们再未见面,而那个关于心灵的秘密也许藏在他后给她的那封信里……
本书探讨心灵之爱的敞开性和神圣意味,通过四个青年学生之间的情感,找寻爱在其自身内实现完善的可能性,打造一条经由爱实现精神不断上升的通道。
主编推荐李都格,苏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士,同济大学外国哲学硕士,现居常州,小说《石榴子》获评为“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入围作品”。
精彩内容童年
他从不跟我谈论悲伤,喜悦,以及任何情感,所有不确定的、羸弱的、会由外力揉捏成其他形状的事物,他都不屑,冷静像一块铁,却又是经熊熊烈火炙烤过的一块坚硬的铁。次见面,在晓辉的宿舍。那时候,晓辉还是个健康的,因为沉思,一双眼珠总是亮闪闪的青年,而他,我惊异的是,他那样苍白,不,不是苍白,是透明,于是,浑身上下透出一种温热的血液的淡红色。
(谁还愿意阅读这冗长的诗篇?)
那时候,我是晓辉的小跟班——九月的天,这个瘦弱、寡言的青年,骑一辆高高的脚踏车从我身旁经过,跟他一般纤细的轮子扭出去一个犹豫的弧,折回来,穿黑色皮鞋的一只脚踮着地,露出一截同样黑色的袜管:金同学,你这期稿子……不错,可那首词……平仄完全错误。我撑着一双沉重的、单薄的眼皮,灰绿格子纸上,细长的笔迹,带着太阳的光晕,辉煌,无与伦比。
我难以追溯确切的源头,但一种迷恋似的生活方式大约就是这么开始的。那首仿照南宋辛稼轩一时兴起填就的《菩萨蛮》,经晓辉数易其稿,终于得以附在一篇以怀念高中生活为主题、略带忧伤和矫揉之作的结尾,刊登于由其主编的校刊。
格林童话里,丑陋的女巫把她的镜子递给男人,告诉他,看看吧,里面才是真正的那个我。镜子里出现的是在这世上的美丽女子。我相信这个故事,不仅相信,更躬身践行,为锻造这样一面显示出真实自我的镜子,我预备耗费一生光阴。如今,有人在帮助我打磨这面镜子——一个能够修饰我的文章的人,必定也能矫正我的灵魂,既然我已把大部分的自己存放于此。我幼稚而热烈的生命急需要这一位驯导者。
此后,有晓辉在的地方总有我,到哪儿都有,无论多么遥远、迂回、晦暗,费尽周折,我总能适时出现在他面前。借书是经常的方式,一个礼拜必定一趟,还有他常去的午餐厅二楼、图书馆、梧桐园后面的自习室和林荫道。但晓辉住的那栋5号宿舍楼,我此前并没踏入过。5-433室,数字这样朗朗上口,每天可以在心里滚几遍,以至于我次踏进那里,觉得是异乡人终于踏进传说中有美人居住的幽深宫殿。
而宫殿深处——美人不止一位。
晓辉说:“奚江,我的舍友兼好友。”越过一屋子脸盆、晾衣架、热水壶,他遥遥朝我裂开笑容,两排牙齿占据了大半张脸,也是透明的,析出阳光的一种颜色。
“你好!晓辉常常说到你。”
“晓辉也说起过你。”
“他肯定说了我很多坏话。”
“我的糗事也不少。”
“彼此彼此,你俩都很适合做话题。”
“完了,完了,看来我已经不需要重塑形象了。”
空气陡然燃烧起来,每个人的声音都像熊熊的火,有好一会儿,我意识不到这其中哪些是我的,哪些是晓辉或者他的,某些东西在大大小小的衣袜、盆、架间流窜,好像被敲打的钟鼓,或是,每一丛火焰底下顽固的星子,噼里啪啦,一刻不停。
变化只在于多了一个人,不知道是我和晓辉多了个他,还是他和晓辉多了个我。总之,两个人和三个人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聚合,前者严肃、狭窄、寂寥,而后者,热情、辽阔、结实,此种变化,令人想大声赞美。
他说话慢条斯理,声调一扬一抑,爬上高山顶又缓缓地、小心翼翼下去,像技巧高超的驾驭者,始终让船舶在浪尖上颠簸,甲板上不沾一滴水。他的声音也如此笼住情感,密不透风,你嗅不出一丝儿味道,可不由得跟着起伏、荡漾,后,以全部身心呈现其中的奇崛与低回。一个人的心灵完整映照另一个,这是我从不敢想象之事,因为它是过去才有的,或者,传奇和故事里的。现在我知道,这种事,今天和以后还会有,因为,眼下,就在这里,这间狭窄的,前后不足十平,窗框生锈,北风呼呼从缺了一角的窗钻进来,酒精灯、萃取杯、烧瓶和滴管如交响乐般碰撞不停的5-433,真的发生了。人们彼此照耀,如粼粼水波,留住印刻其上的每一寸风,还把一直以来搅拌均匀、秘不示人的心重新揉捏、雕琢,成为新的、锃光发亮、与四周融为一体的奇妙之物。
我在5-433一坐,便久未离开。本来,只是去还一本借了晓辉两个礼拜的书而已。直到日落黄昏,暮色降临,月上柳梢,星移漏转……我还坐在进门时的那个牛皮转凳上,纹丝不动。这一晚的对话,我全记得,这里,只需说其中一节。
我再一次地,小声地追问:
“世界这样完美,为什么人们还不满足?”
他们中的一位回应:
“因为幸福。人们因为幸福而满世界追逐他们的理想。”
于是,我迫切,但小心翼翼地说:
“你们觉得,就我们现在所做的……可不可以称之为……呃……理想?”
另一位,更加小心翼翼地回答:
“可能……也就是……还没被遗忘的童年。”
每个礼拜至少有两天是三人固定的聚会日——不到二十人的心理系小班被分插到几个大临床班一块儿做实验,我自然被安排跟他俩一个组。为什么说自然?因为,一切必得如此,否则,我们的故事没法往下说,毕竟,5-433只是偶尔可以去一趟的地方。
常做的实验是关于兔子的:打开兔子胸腔,插一根管子进它的心脏,或者切开腹部,扎掉里面一段血管或神经。实验开始前,先要给兔子做麻醉,利多卡因或巴比妥或乙醚。我害怕这个,麻醉后的兔子没有哪个还会醒来,实验结束,就推进更多的致死剂量的麻药。每个都一样,麻醉,一旦启动,就进入死亡——不,在我们手里,麻醉就是死亡,是缓慢的,为一既定目的(实验操作、数据或其他更大的什么),拖延至特定时刻的死亡。
行刑者永远是他。干净,利落,凛然,以及仁慈——像一位烈士。刽子手和被刑杀的,同受其难。我下不了手,晓辉有时也犹豫,我们都爱惜自己,等着他动手。
于是,由我捧着操作册,口里念念有词,他持针,抽药,摸索至受刑者耳后那枚柔软的血管,不等发号施令,不等摇旗呐喊,他已沉默地,坚定不移地,推进了一枚同样细弱的针尖,注射量通常达至参考给药量的上限。
邻桌有人过来,捏了捏操作台上耷拉的腿,吹一记口哨:“麻翻了,这速度!”我们避无可避地,相视一笑。这当然算一种胜利,及不上攻城略地,也近乎手刃仇敌。
余下的事便可交给晓辉。晓辉有一双纤长而精确的手,可以在不到一厘米的切口里完整分离肌肉、筋膜、血管、神经,血管壁上剪出漂亮的“V”字,插入比血管粗一倍的管子,再打上一个同样漂亮的结。
我是无足轻重的那个,但作为观众,我想我是出色的。凝神屏息,腰杆笔直,站定不动,如一座雕像,没有哪个演出能拥有比我更虔诚的观看者,我也再未以同样的虔诚观看过其他剧目。死亡、牺牲和拯救、理性、进步一起,也和我们无辜的、欣欣向荣的青春一起,除了观看,我不置一词,心里也一样。
因为眼泪,在那之前,已经淌过了。
堂课,不是现场,一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录像,新西兰大耳白兔气管切开、颈动脉插管和迷走神经分离,隔着一层薄灰的屏幕,我已偷偷地、羞耻地淌下过眼泪。
现在,观看是我重新参与他们的方式,或者,也是他们塑造自己的方式。
“你离那么远?相信我,没那么容易割到大动脉。”
他把我拉到前面,肌肉底下一丛丛眦目偾张的血管,米诺斯宫殿纵横交错的腥味。
“我晕血……而且……插管太长,也会晕……”我开始渴望有那团线和一柄魔剑。
“哦,我希望现在仍是遥远的过去,女人不必强行遵循男人的法则。”晓辉的嘴角浮起他一贯的弧度,手指已探至心脏深部,穿过根导管。
我汗如雨下,咬紧牙关,摇摇欲坠,但还是不动声色地维持住一名观众的体面——没让自己晕倒。而且,手里没忘了记下眼睛看到的每一步,连一个小数点也不放过。
“你这双手,只要不是针或者刀,随便握一支笔,哪怕一支烟,都这样合适。”他俩有时候夸我。也许,只是安慰,免得我每每为一场实验心碎神伤。但我宁愿相信。因我并不耻于承认,我在以此为自己赋予价值,以此为一名沉默难言的观众拓展其边界,以此面对永远正确的晓辉,以及后来那个冷静、克制的他——我们一起的时间,所有翻江倒海,火烧火燎,都转瞬即逝,唯有我亲手画于记录册上的,数字、线条、瘦骨嶙峋的笔迹,把一切揉成细沙,也赋予它们永恒。
金冬冬,你听过米诺陶洛斯的故事吗?
是那个被关在迷宫深处,每年要吃七对童男童女的牛头怪吗?杀掉那头怪兽可要容易得多,只要你想得到用线团,沿路做标记,后总能碰上它,然后举起魔剑,手起刀落……
你看,你不就是所有人里擅长标记事物的那个吗?你缺的,不过是后那一下——手起刀落,直击要害。
可我并没有魔剑!
知道魔剑的秘密吗?它所有的魔力,不过是让你看不见米诺陶洛斯作为人的身体,在你眼里,它将不再像一个人,而只是一头牛,一头可以砍下头颅,贡上祭坛,献给海神波塞冬的牺牲——就这么简单。
哦,别再说了,米诺陶洛斯……你忘了,它会成为地狱入口的审判者,用它的尾巴缠上你,缠几圈,你就被安置在它之下第几层。
你相信地狱吗?或者天堂?
喔,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有,那也蛮好的。
我也这么想,因为这样,人世大概就永远不会结束。所以,你还是别逼我了。既然一切都会继续下去。
好吧……其实,你只是胆小。
兔子们阖上眼,像一堆抹布,被送去处置室。我继续握紧我的笔,奋笔疾书,“米诺陶洛斯和一把可以隐身的剑”,为我的下一篇小说决定了题目。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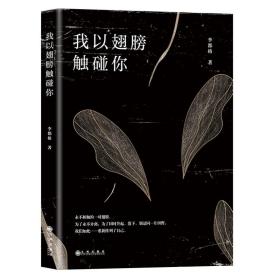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