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正版 新书--不安之夜(精装) (荷兰) 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 译者:于是 978753217969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华书店直发 全新正版 急速发货 开票联系客服
¥ 27.19 4.3折 ¥ 63 全新
库存8件
作者(荷兰) 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 译者:于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79695
出版时间2021-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3元
货号29283895
上书时间2024-10-1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雅斯问上帝:非要带走我的兔子吗?不可以我哥哥马蒂斯去换吗?
十岁的雅斯拥有独特的体验宇宙的方式:在皮肤上涂乳膏来抵御严冬;迁徙的蟾蜍身上绿色的疣状物是斗篷……
然而,马蒂斯真的死了。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她的好奇心开始扭曲,形成越来越不安的幻想漩涡,一家人或许就此偏离人生轨道,堕入黑暗……信仰的禁忌被突破,欲望的尺度被超越,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雅斯对黑暗充满恐惧,不断诘问自己:爸爸妈妈是不断蚕食我们的害虫吗……
作者简介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1991— )
诗人、小说家。世界文坛90后的佼佼者,国际布克奖年轻得主,亦是首位获得该奖的荷兰作家。
出生于荷兰北布拉邦特省的一个乡村家庭。20岁大学肄业,22岁从创意写作学校辍学。
开启写作生涯的《小牛羊毛》获2015年C.巴丁格诗集首作奖。长篇小说处女作《不安之夜》不仅登上荷兰年度畅销小说榜首,还先后斩获ANV首作奖和2020年的国际布克奖。后出版诗集《幻想》和长篇小说《天选之人》。
目录
《》无目录
内容摘要雅斯问上帝:非要带走我的兔子吗?不可以我哥哥马蒂斯去换吗?
十岁的雅斯拥有独特的体验宇宙的方式:在皮肤上涂乳膏来抵御严冬;迁徙的蟾蜍身上绿色的疣状物是斗篷……
然而,马蒂斯真的死了。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她的好奇心开始扭曲,形成越来越不安的幻想漩涡,一家人或许就此偏离人生轨道,堕入黑暗……信仰的禁忌被突破,欲望的尺度被超越,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雅斯对黑暗充满恐惧,不断诘问自己:爸爸妈妈是不断蚕食我们的害虫吗……
主编推荐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1991— )
诗人、小说家。世界文坛90后的佼佼者,国际布克奖年轻得主,亦是首位获得该奖的荷兰作家。
出生于荷兰北布拉邦特省的一个乡村家庭。20岁大学肄业,22岁从创意写作学校辍学。
开启写作生涯的《小牛羊毛》获2015年C.巴丁格诗集首作奖。长篇小说处女作《不安之夜》不仅登上荷兰年度畅销小说榜首,还先后斩获ANV首作奖和2020年的国际布克奖。后出版诗集《幻想》和长篇小说《天选之人》。
精彩内容我在餐盘里把西蓝花的小花捣碎。西蓝花就像迷你圣诞树,让我想起了马蒂斯没有回家的那个夜晚,我在窗台上坐了几小时,脖子上挂着爸爸的望远镜。它们本来是用于寻找大斑啄木鸟的。我没有看到大斑啄木鸟,也没有看到我哥哥。望远镜的挂绳在我的后脖颈留下了一条红色的勒痕。如果我只需从大视镜那端望出去,反转视线,就能把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东西拉近,那该多好啊。我经常用望远镜在天空中搜寻——想在树上找到天使们的踪影。哥哥死后一星期,我和奥贝把小天使们从阁楼的盒子里偷偷拿出来,用力地让它们互相摩擦(“我鲜嫩的小天使”,奥贝假惺惺地呻吟着,而我应道“我亲爱的小瓷人儿”),然后,让它们从他房间的天窗掉进排水沟。天气变化,让它们变成了绿色。有些天使被埋在了橡树叶下。每次去检查它们是否还在那里,我们都会失望。如果这里的天使在轻微的挫折后就失去了飞行能力,那他们怎么能飞去天堂陪伴马蒂斯呢?他们怎么能保护他和我们呢?
后,我扣上望远镜的镜头盖,放回盒子里。我再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就算大斑啄木鸟真的回来了,我也没有再用——望远镜的视野将永远是漆黑一片。
我吃下一大口西蓝花。我们的午餐总是热乎的。入夜后,这里的一切就都冷冰冰了:庭院,爸爸妈妈之间的沉默,我们的心,铺满俄罗斯沙拉的面包。我不知道怎样坐在椅子上才好。我左右挪动身子,尽量避开屁眼的灼热感,那让我想起奥贝的手指。我决不能透露半个字,否则我哥哥会让我的兔子像夜晚一样冰凉。我自己也肯定不想说出去,不是吗?让公牛看到你的屁股,就能让它们安定下来,如果你是奶牛的话。
我的视线没法离开听诊器,它就摆在餐桌上,紧挨着兽医的餐盘。这是我第二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诊器。我在荷兰1台的节目里看过一次,但你是看不到尸体的,因为那样就会有太多裸露镜头。我幻想了一下:听诊器放在我裸露的胸前,兽医把耳朵贴在金属上,对妈妈说:“我认为她的心破裂了。这是家族遗传,还是次发生这种现象?也许她该去空气清新的海边。所有那些稀粪肥都会渗进你们的干净衣服,心脏就会更快地被感染。”在我的想象中,他从裤袋里摸出一把史丹利工具刀,就是爸爸割青贮草包装袋用的那种刀——嚓、嚓、嚓,直到包装袋散开。然后,他会用毡头墨水笔在我的前胸画线。我想起了吃掉七只小山羊的大灰狼被开胸剖肚,以便活生生地取出小山羊——也许,从我的身体里会取出一个高个儿女孩,她不会再有恐惧,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会被看到的人,那个女孩被遮掩在皮肤和外套的层层覆盖下已然太久。听诊器从我的皮肤上移开后,他就不得不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我只需吸气呼气,就能让他的头上下起伏,表示他懂我。我会说自己浑身都疼,并指出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从我的脚趾到我的头顶,以及这二者之间的每一处。我们可以在雀斑间画出辅助线,确立我们的界限,或剪切出我的身影,就像那些用点组成的画。但如果他听不到我的呼救声,我就得扯下胸前的金属块,尽可能把嘴张大,再把那块圆形的金属塞进喉咙,尽量往下塞。那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听了。哽噎历来都不是好兆头。
奥贝的胳膊肘戳了戳我的肋间。
“在吗?地球呼叫雅斯,把肉汁递过来,好吗?”
妈妈把汤罐递给我。罐子的把手已经断了。有些小油球漂浮在肉汁中。趁奥贝还没扫兴地问我在想什么,我赶忙把它递给他。他正在说学校里的所有男生,一个一个说过来,而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男孩却在他一直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有块纪念碑。现在牛都没了,各方面的情势都不太喜人,兽医也在说口蹄疫对村里所有农民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不想谈这件事,他说,那些人恰恰是危险的,有可能颓丧至极,乃至做出一些傻事。
“很难理解,”爸爸没有看任何人,说道,“你终究还有自己的孩子吧。”
我看了一眼奥贝,他的头都快凑到盘子上了,好像在研究西蓝花的结构,看看那些小朵的绿花能不能当伞用,好让我们躲在下面。他的拳头握成一团,我看得出来,爸爸说的话,或者说,爸爸没有说出的话让他很生气。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也可以当吊锤,就是用来让窗帘垂坠、不让它们飘起来的那种小坠子。我一直看着兽医。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舌头去舔银色的金属餐刀。帅气的舌头——深红色的。我想起爸爸温室里的植物,想他怎样用刀划开一条叶茎,再把这根插枝种进盆土里,叶子朝上,再用篱笆钉固定。我想象着兽医的舌头触碰我的舌头。我终将舒展开来吗?不久前,汉娜把舌头伸进我嘴里时,我尝出来她吃掉了后一滴蜂蜜。我问自己,兽医的舌头会不会有蜂蜜的味道,那能不能让肚子里让我痒痒的小虫子消停下来?
爸爸坐在桌边,抱着脑袋。他已经不在听兽医说话了。兽医突然神秘兮兮地倾身向前,压低声音说道:“我觉得这件外套穿在你身上很可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压低声音,因为大家都能听到,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做,好像他们希望大家能靠拢一点,竖起耳朵,像被磁铁吸过来那样,乖乖地听话。这和权力有关。汉娜今天住在朋友家,我觉得很可惜,否则她就能亲耳听到: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得救了。也许,我应当忘记奶酪铲勺的事。那确实让我对他失去了一点信念,就像那次爸爸把我叫到桌边——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次也是后一次在餐桌边进行了不以奶牛为主题的谈话。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时,爸爸这样说,我的手指摸索着刀叉,只想抓点什么在手里,但那时离吃饭时间还早,餐具都还没铺好。
“世上不存在圣诞老人。”
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而是把杯子斜着拿,盯着杯底的咖啡渣。爸爸又清了清嗓子。“学校里的圣诞老人是常来买我们牛奶的提埃尔,那个光头。”我记得提埃尔,他常开玩笑地用指关节敲敲自己的头,舌头弹出空空的声响。我们都很喜欢,每一次都喜欢。我无法想象他有胡子、戴红帽子的样子。我想说点什么,但嗓子眼就像花园里的雨量计一样满满的,后溢出来,我就开始抽噎。我想到那一切都是谎言:坐在火炉前,唱着圣诞歌,希望圣诞老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其实,顶多只有一只煤山雀听到了我们;我们把鞋子留在炉边,收到的柑橘礼物让袜子闻起来都有点酸味。也许迪沃恰·波洛克也是假的。真相是我们必须乖乖听话,否则就会被装进圣诞老人的空袋子里送去西班牙。
“那迪沃恰·波洛克呢?”
“她是真的,但电视里的圣诞老人是演员扮的。”
我看了看妈妈放在咖啡过滤杯里的胡椒小饼干,那是给我的。我们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被仔细称量过,连这些指尖大的香料小饼干也不例外。我没去碰,让它们留在桌上好了,眼泪一直在流。后来,爸爸从桌边站起身,取来茶巾,粗糙地抹了抹我的眼泪。哪怕我已经不再哭了,他还在不停地擦,好像我的脸上沾满了鞋油——助长幻觉的鞋油,圣诞老人的助手们蹭到的烟囱灰。我想捶打他的胸口,就像他多年来捶门的样子,然后跑进夜晚,不再回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撒谎。然而,随后的那几年里,我努力地去相信圣诞老人,就像坚定地相信上帝那样——只要我能想象出他们的模样,或是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只要我心有愿望,想要对谁祈祷,他们就是存在的。
兽医把盘里后一朵西蓝花放进了嘴里,再次向前倾身,把刀叉在盘子里摆成十字,以示他吃完了。
“你多大了?”他问。
“十二岁。”
“那你差不多算长成了。”
“你是说,长成疯子了吧。”奥贝说。
兽医没有理会他。我差不多长成,并为某人作好了准备,这想法让我挺骄傲的,哪怕实际上我好像瓦解成了越来越多的碎片——但我知道,完整的状态总是个好兆头。我收集的牛奶瓶盖就快集齐了,只剩三个塑料格子还是空的,所以,假以时日,当我回想自己赢过的、输过的所有游戏时,我将会有同样的感受。虽然检阅自己肯定会更难,但你大概必须是个成年人才行,身高要保持在门柱上的某一根线上,不能再擦去以前的高度。长发公主被关在塔里,又被王子救出来时就是十二岁。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的原意是德语中的“羊生菜”。
兽医看了我很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的脸开始发烫,跟肉汤罐的外壁一样烫。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差距:为什么他十二岁就知道该怎么做,但成了和我爸同代的成年人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大人不是应该什么都懂吗?
“明天可能下雨。”爸爸突然说道。桌上的任何谈话他都没听进去。妈妈一直在厨台和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在自然课本上读到过,蚂蚁有两个胃:一个装自己吃的,另一个可以用来喂养别的蚂蚁。我觉得这很感人。我也想有两个胃,那样就可以单独用一个胃让我妈妈的体重维持在正常水平。
兽医对我眨眨眼。我决定明天跟贝莱说说他。终于有个人可以让我悄悄地谈论一下了。我不会告诉她他有很多皱纹,比没烫过的桌布还多;也不会说他咳嗽起来像一头得了猪瘟的小牛;也不会说他可能比我爸爸还老,而且鼻孔很宽,至少可以塞进三根薯条。我会告诉她,他比鲍德温·代·格罗特还要帅。这样说就意味深长了。放学后,我和贝莱经常在我的阁楼卧室里听他的歌。我们感觉非常悲伤的时候——贝莱有时会非常沮丧,就因为汤姆没在短消息末尾给她发一个大写的X,只有一个小写的x,其实,你打完一个句号后,X就会自动出现,所以他是不嫌费事,特意把X换成了x——就会对对方说一句歌词:“我心里有一只溺水的蝴蝶。”然后就只是点点头,非常明了对方的感受。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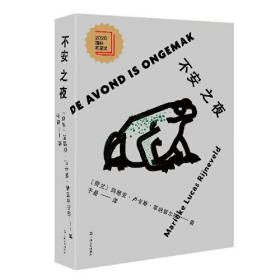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