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正版 金匠一号 魏枫 97875171321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新华书店直发 全新正版 急速发货 开票联系客服
¥ 21.32 4.4折 ¥ 48 全新
库存8件
作者魏枫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ISBN9787517132165
出版时间2021-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29277207
上书时间2024-10-1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9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湘中一个叫打鼓垄的地方,金匠辈出,在改革开放之初,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排名老二的金匠,在规矩、良知与金子的博弈间,引来杀身之祸,家人随即踏上漫漫寻凶之路。其间经历的阵痛、迷茫、焦虑跟执着,在现实的火炉里备受煎熬。凶手是谁?为何要下此毒手?家人在茫茫人海中能否找到真凶?一切都那么惊心动魄,迷雾重重,让人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魏枫,原名魏仁安,1970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市老粮仓镇,2015年起至今供职于宁乡市融媒体中心,担任记者,不少新闻稿件被人民网、新华网、学习强国等转载。曾出版长篇小说《回不去的月娥》。
目录金匠二号 / 1
黑 伢 / 14
翠 鸟 / 21
金匠一号 / 25
翠 鸟 / 29
黑 伢 / 32
翠 鸟 / 42
黑 伢 / 53
赶猪匠 / 63
猴 子 / 67
哑 巴 / 71
水 仙 / 74
翠 鸟 / 79
李文俊 / 81
哈利油 / 84
阿 兰 / 88
翠 鸟 / 92
李桂花 / 98
乘 客 / 104
阿 兰 / 111
李桂花 / 114
裤 子 / 118
翠 鸟 / 122
赶猪匠 / 130
黑 伢 / 134
翠 鸟 / 138
黑 伢 / 147
李桂花 / 154
黑 伢 / 161
李桂花 / 167
黑 伢 / 170
金匠一号 / 175
金匠二号 / 179
李桂花 / 183
翠 鸟 / 186
黑 伢 / 197
李桂花 / 206
黑 伢 / 211
翠 鸟 / 216
黑 伢 / 221
金匠一号 / 226
翠 鸟 / 230
黑 伢 / 247
水 仙 / 257
翠 鸟 / 260
李桂花 / 263
翠 鸟 / 265
黑 伢 / 268
翠 鸟 / 270
黑 伢 / 273
黑 伢 / 275
李桂花 / 277
赶猪匠 / 279
内容摘要湘中一个叫打鼓垄的地方,金匠辈出,在改革开放之初,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排名老二的金匠,在规矩、良知与金子的博弈间,引来杀身之祸,家人随即踏上漫漫寻凶之路。其间经历的阵痛、迷茫、焦虑跟执着,在现实的火炉里备受煎熬。凶手是谁?为何要下此毒手?家人在茫茫人海中能否找到真凶?一切都那么惊心动魄,迷雾重重,让人欲罢不能。
主编推荐魏枫,原名魏仁安,1970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市老粮仓镇,2015年起至今供职于宁乡市融媒体中心,担任记者,不少新闻稿件被人民网、新华网、学习强国等转载。曾出版长篇小说《回不去的月娥》。
精彩内容金匠二号
我听见掘土的声音从棺顶往下一点点地掘进,一点点地清晰,不慌不忙。没多久,就传来一阵子嘈杂声,棺连同我的尸骨一起被几根铁棍撬动后,被几根绳索稳稳当当地吊出土眼,悬在空中,那感觉就像是浮在水面,浪花不时拍打着棺,棺在水面荡漾,我在水面荡漾。这个过程很慢很慢,当然我晓得我不是浮在水面上,而是浮在前不久那十六个男人或老或嫩的肩膀上,是他们把我抬进土眼的。
地仙给我堪舆的土眼沙石累累,尽管八个开山的乡亲汗得一身透湿,皮肤晒得墨黑,手掌磨出血泡,沙子溅进眼睛里,也像我们金匠一门心思镶嵌一枚漂亮的绿宝石,焊接一条精美的金项!链,想方设法挖一坨金子一样,在我下葬的时间点前小心翼翼地将土眼打造得方方正正,所花费的工夫超过打鼓垄以往任何一个土眼的几倍。
我记得那时在路上歇了三回,虽然路程并不远,也就一两里,但是他们满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两脚几乎就要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跪倒在地。都是赶猪匠做的好事,给我挑选这么一副水泥棺,连同我的尸骨、陪葬品一起,起码上千斤。打鼓垄历史上没埋过上千斤的棺,这我晓得的,尽管这些年我走遍全国各地,待在家里的时间少之又少,但至少也抬过上百副棺。
说实话,抬棺都是有套路的,八个人的步子要是不一致的话,棺就会摇晃,扁担会从肩膀上滑下来,砸在脚上掉到田坎下或者阴沟里。当然,还有一件顶重要的事,就是给寿杠套索子,这可是技术活,套不好的话,抬到半路上棺会掉到地上,这是孝家的大忌,因为棺在没进土眼前,是不可落地的。在半路上歇气,棺要搁在两条长凳上,因为棺掉在半路上,亡灵回不了家,变成孤魂野鬼,夜夜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游荡喊叫,让活着的人心惊胆寒。虽说是鬼话,但老祖宗几千年来从不怀疑,在打鼓垄像赶猪匠这号上了年纪的人,这是忌讳的。遗憾的是,那些满哥或者说读书人,不单单嗤之以鼻,还一口咬定是迷信。就说我的崽黑伢跟翠鸟吧,我曾经一次次对他俩说,大人的话往往是很灵验的,不单单要听,还要记在脑壳里。我给他俩举了个例子,我亲身经历的。话说分田到户那一年那一个抓阄的夜里,我情绪非常激动,“终于要分田了,要是抓阄能抓到家对门那连着的三丘肥肉田,就好啦!反过来,要是抓到弯头冲的沁水田,或者磐基滩的干旱田,不但要抬扮桶、掮犂耙、担谷爬垄过坳,付出比做家门口田几倍的劳力,亩产还很低。怎么办呢?”我沐浴更衣,跪在堂屋神龛下冥纸香烛燃烧出的缕缕烟雾里,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随后右手朝空中一挥,两条桃花鱼似的竹卦飞出指尖,在空中划出两条好看的弧线,在泥地上活蹦几下后,发出清脆响亮的“吧嗒”声,像是绽放出两朵好看的花。我接连打了三卦,卦卦激荡心弦。我二话没说,转身离开了家,来到生产队保管室。明亮的灯火悬在大桌子上空,悬在黑压压的头顶,悬在激荡沸腾的心上,叶子烟、汗臭、口水、鼻涕、煤油的混合气味弥漫在空中,牛卵大的眼珠,钢针尖的眼光,穿不透青花瓷的质地,猜不透纸团的密码,戳不破古老的法则。梦寐以求的肥肉田,三十年不换主的肥肉田,全凭神灵的点拨,在伸手之间。当队长喊“下一个,金匠二号”时,我锉刀般粗糙的手,伸到碗边,我看见阿爸的眼睛,就隐藏在青花瓷边,隐藏在青花瓷底,隐藏在纸白的皮面,“崽呀,看见冇?那三丘肥肉田,就在那个闪光的纸团里,那是我的眼睛在眨”!我笨拙的指尖,捻起那个纸团,像捻一坨沉甸甸的金子。“啊,阿爸,崽终于抓到屋门口三丘肥肉田了!”我至今回想起当年抓阄的情景,仍止不住激动的情绪,可惜我的两个崽,除了深信五满丘六满丘七满丘是我家的田外,对于阿爸那夜是如何打卦求助死去的公公,死去的公公是如何显灵的故事情节半信半疑,要是把讲述者换作别人,他们简直会嗤之以鼻,甚至嘲笑这纯粹是骗细家伙的把戏。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不信乱弹。
不晓得棺在空中摇晃了多久,就突然不动了。倏忽间,我看见棺盖被撬开抬走了,眼上方顿时一片明亮温暖,我又回家了,回到跟堂客困觉的房了,嗅到了被子枕头蚊帐跟她身上的香味,当然还有我的汗臭味。我堂客粗糙的手掌拍打着棺框边,尖尖的指甲鲜红,薄薄的嘴唇朱红,圆鼓鼓的眼睛血红,两行泪水从棺上方坠落到我的丧服上,痛不欲生,被几个乡邻架开。我在感动的同时,内心却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她是打鼓垄一朵金花,我在外地奔波想着她,打鼓垄在家游手好闲的畜生暗地里撩她,还有,唉。我看见一双双熟悉的、惊愕的、悲伤的、怜悯的眼光,从棺盖腾出的地方,齐刷刷地朝我扑来,我眼泪长流,乡亲啊,尘世啊,从此与我无缘。我的不舍,我的留恋,从此向谁诉说。
我的陪葬品,是一枚白得耀眼的银章,上面篆刻着我跟打鼓垄的名字,我在世时精心打磨的杰作,就像一颗珍珠,含在嘴里,百年以后,我的子孙后代,会记得一个叫洪石奎的先人,曾经背着箱子拿着锤子,跟打鼓垄一帮金匠,走遍千山万水,传播打鼓垄璀璨的青铜文明。
且说1936 年,时值惊蛰。我叔公洪田凹到家对门菜地挖土,一锄挖下去,“哐当”一声,手震得发麻,锄头歪倒一边。他以为挖到了石头,没放在心上。第二年惊蛰那天,叔公又去挖土,一锄挖下去,又是“哐当”一声,手震得发麻。叔公终于下定决心,要把它挖出来,免得年年碍事。就这样一点点地挖,一点点地刨,不想,挖出的并不是石头,而是一个又笨又重的怪物,他性急回家喊来伯公,把怪物悄悄地抬回家,用清水洗掉泥巴,用盐酸去除锈迹,于是,五牛鼎尊贵的容颜在埋藏三千多年后横空出世,熠熠生辉,那细若游丝的金线,那天衣无缝的焊接,那一气呵成的锤路,那花样百出的纹饰,美得让人心醉,仿佛不仅仅是一件青铜器,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注定被载入打鼓垄史册。叔公由衷地感叹,对鼎的铸造工艺之谜及三千多年前的打鼓垄不停地追问。可是,在伯公的煽风点火下,叔公以三百块大洋的价钱,把五牛鼎卖给了街上一个古董商,古董商又以三千块大洋的价钱卖给了长沙城的几个皮革商,当皮革商准备以五万块大洋的价钱卖给一个英国古董商时,哪知走漏了风声,被县府抓获并没收归公。抗战期间,五牛鼎被日本鬼子投下的炸弹炸成二十七块,躺在一家银行的库房里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专家找到五牛鼎,历时数月予以修复,终于再现了它的尊容。经文物专家考证,被认定为稀世国宝,珍藏于国家博物馆。一时间,打鼓垄名震全国,当地政府邀请省里的专家,在我叔公那块菜地周围又发掘出上百件的铙、鼎、卣、觚等(均为青铜器,其中尤以青铜铙多),并在打鼓垄集镇建起了一座青铜博物馆。现在,我叔公跟伯公,还有我阿爸,早就归于尘土,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每每来采访,就要采访我,因为我阿爸在世时,常常跟我讲起叔公当年挖国宝的那档子事,说得眉飞色舞口沫横飞,满脸的嘚瑟跟骄傲,三千多年间,无数次电闪雷鸣没劈出她,无数次地动山摇没崩塌她,无数铁蹄没踩出她,无数战轮没碾出她,唯独被我叔公用锄头挖出,真神奇啊!我阿爸怎能不嘚瑟跟骄傲?
考古专家试图破译刻在鼎内侧的“犰”字,以及她为何地人所造,有人说她来自数千里外的中原大地,随军队的征战流落于此,但更多的人(包括我叔公伯公)说,她无疑是打鼓垄金匠的杰作。
我常常站在叔公家当年的那块菜地上,像一位智者沉思冥想,恍惚间看见,三千多年前,在打鼓垄盆地,先人们修筑了高大的城池,国王犰的旌旗在城楼上迎风飘扬,猎猎作响。犰命令作坊里的十八个工匠,从盆地的泥土沙砾岩石间,提炼出一种坚韧耐腐蚀的金属物质——金铜。他们精挑细拣,冒着风寒顶着酷暑,一点点地积攒,到开工时,犰赐予十八名工匠每人一根又尖又长的鱼刺,命令工匠们刺瞎自己的眼睛。工匠们在痛苦绝望间领悟了犰的良苦用心,因为精湛至尊的金鼎只有双目失明的匠人才能打造出来。
双目失明的工匠在人称驼子大师的带领下,在与外界隔绝的作坊里,在黑暗中,挥舞锉子、錾子、锛、凿、斧、锤、磨石,凭着娴熟的手法深刻的记忆,精心构思,将牛头、牛角、牛腹、牛脚的形状、色泽、纹理移植到鼎上,在鼎的躯体上精雕细琢出云雷纹、饕餮纹、鱼鳞甲、蛇鳞甲、羽毛,集线雕、浮雕、圆雕技法于一身,将平面图像、立体架构和动物形状巧妙地融合起来,如狂风扫落叶,似山洪冲决堤坝,流畅刚劲有力的圆点、弧线、直线,乌青发亮的色泽,栩栩如生的造型,磅礴的气势,至尊的地位,深刻的寓意,无与伦比。十八名工匠,前前后后耗费十八年心血,经历十八次浇铸、雕刻跟打磨。驼子大师,精湛的技艺达到永恒,成就了鼎的至尊。遗憾的是,为了让后人铭记自己的功勋,驼子大师偷偷地在鼎外一头牛的眼皮下刻上了他的签名,那几乎是用肉眼无法辨识的名字,却被一名嫉妒他的工匠告发,愤怒的犰于是赐予大师一杯毒酒。剩下的十七名工匠在大功告成之日,家人收到了犰赏赐的牛羊跟谷物,同时也收到了亲人的尸体。从此,五牛鼎成了千古之谜。
时至清朝末年,名震天下的湘军在全国各地战场上所向披靡,一路上攻城略地,除保卫了边境、国土的安宁外,还携带着或缴获或受到朝廷赏赐的无数金银财宝,回到了家乡。就说当年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那阵子,湘军将士的铁镐掘遍了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别说金银财宝,就连城墙上的一根根木方也被吊到船上,顺长江而下,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再用竹筏、骡马、土车等运回了打鼓垄,可谓捞得盆满钵满(哈,我的祖先)。于是,打鼓垄金匠被将军们请去为大婆子、细婆子、爷娘制作犹如皇帝头戴的皇冠,后宫妃子头戴的金簪金针,金手镯般的金器。于是,“叮咣叮咣”的捶揲声,宛如一支支曲子,在将军们豪华的大屋里荡起,飘到打鼓垄悠远的天际。
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就很少打金了,转而打章子,我们在章子上打出的是篆字,是花鸟虫鱼,起先打木章子,后来打铝章、铜章、银章、银首饰,用银圆(又叫花边)、散碎银子为细家伙打制脚圈、项圈、手圈,脚圈上吊着的铃铛,项圈上吊着的百家锁,手圈上爬着的两条龙,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充满了金匠的灵气、思想跟泥土的香味。金匠嘴里含着一根细长的铜管,将木炭或成捆的蜡烛燃烧出的火焰吹到银坯上,大自然的气流被源源不断地从鼻孔里吸进去,从铜管里喷出来,将银坯熔化成坨,手起锤落,银坨被捶揲成薄薄的银片,再在铜模具上压制出两片百家锁的外壳,用錾子在外壳上雕刻出“双龙戏珠”的图纹,把写好百家姓氏、细家伙出生年月的红绸子,放进被焊接起来的两片百家锁内壳里。然后,在铜模的圆孔里压制出铃铛的外壳,做成一个个铃铛,焊接在百家锁外壳下方。后,通过拉丝、编织、焊接出银链条,将百家锁连接起来,挂在细家伙的脖颈上,百家锁宣告制成。所谓“写好百家姓氏的红绸子”,指爷娘为了防止细家伙走丢,或者家门口有池塘以防被淹死,或者前头生的崽因种种不幸而夭折,就根据老人们的教诲,在细家伙可以下地走路时,背着袋子,拿着红绸子,一边讨米,一边请施主在红绸子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直到写满一百个为止。讨到的米,无论多少,都要交给金匠作手工钱。据说,戴了百家锁的细家伙,上天在冥冥之中会保佑他一生平安。
我家数代都是金匠,阿爸告诉我,在我们洪氏族谱上刻印着一幅画:在一栋低矮的木屋前,摆着一个五十厘米高的木箱,箱子贴着白纸的一方正对着街,白纸顶格写着“洪记”两个大字,一个寡瘦的男人,头戴盆帽,身穿浅绿色的长袍马褂,脚穿黑布鞋,伏在箱子边,右手扬起铁锤,左手不知抓着什么工具,全神贯注,温暖的阳光洒在他身上,盆帽遮住了他的脸。阿爸说,那是我公公的公公。可惜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洪氏族谱被一把大火焚烧,化为灰烬。
我阿爸一生讨了三个堂客,个堂客生了个妹子,第二个堂客又生了个妹子,第三个堂客直到四十岁才生了我,前头生个崽夭折了,阿爸生怕我再夭折,就打制了一把百家锁,让我一直戴到七岁。
我很小就随阿爸到集镇打章子,后来发现流动的生意更好做,就跟着阿爸用帆布袋装着工具、打章子的原材料,到外地的大街小巷摆摊。直到把沉甸甸的原材料用完、荷包里的票子鼓起来,才满心欢喜地踏上归途。改革开放后,一切都变了,打鼓垄的木匠、漆匠、师公、泥水匠、农民,背着箱子,握着锤子,坐班车,搭火车,天南地北打章子,打金银首饰。打鼓垄,被冠以“青铜之乡”的美名。
我想,为什么一回到打鼓垄,就遭此毒手,我究竟得罪了哪个?当刀子捅进我胸脯的瞬间,我整个思绪飘到了成都,眼光紧紧地盯着新龙门客栈的金匠,浓妆艳抹的藏族女人,腰间挎着藏刀的藏族汉子,细皮嫩肉的小姐,细声细气的婆婆,我努力回想与他们打交道时的细枝末节,我承认,每次从成都回来,我总是把打金的秘密捂得紧紧的。我胆战心惊,焦虑难熬,夜里梦见有人拿刀子追杀,我慌不择路,逃到江边,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我纵身一跃跳进江里,接连呛了几口水,我游啊游,游啊游,肚皮下,是深不见底的吸人的江水,我手臂又酸又疼,力气一点点地耗尽,我就要死了,我年纪轻轻,拖家带口,连福还没享啊。我要活下去,我要游到江对岸去,可是我的手臂像没了骨头一样,一点力气也没了,身子在慢慢下沉,大口大口江水涌进肚里,把肚皮撑得像个皮球。我就要沉入江底,被大鱼一口一口撕碎,被水鬼拖入滚滚洪流。我听到了我的呐喊声:“我不能死,要活!要活!”我醒来了。我看见自己躺在床上,一身汗得透湿。堂客问我,我没作声,后怕得发抖。闭门躲客三天。三天后,我时刻观察周边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就见机行事。凡是从成都回来的金匠,只要没结仇,就去打听那边的消息。这次,我又在家躲客,后来粑粑回了,他悄悄地告诉我,说在我离开新龙门客栈后,一个藏族女人来找过我,声称要打一副金项链,谁打都不行,非要我。她深褐色的皮肤,藏袍上嵌着珍珠跟玛瑙,浑身散发出牦牛气味,一双眼睛眨个不停。头一回,我老老实实给她打了一副空心大耳环,连加工费也没收。当时客房就我跟她,趁帮她戴耳环的机会,我摸了她的耳根跟头发,又斗胆去摸她奶子,她居然把我的手按在胸脯上,然后猛地一拉,把我死死地搂在怀里,力气之大,足以让我窒息。
第二回,第三回,我拿着她黄澄澄沉甸甸的金子,一瞬间怦然心动,恨不得拿到嘴边舔,亲。可是,我的手,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抖了,就像头一回对顾客的金子下手那样抖。作为金匠,让人耻笑的莫过于抖这个字,它是懦弱、胆小、惧怕、窝囊的代名词。曾经,金匠粑粑就一度因为抖,竟然将挖到的金子抖到顾客的眼皮下,遭一阵死打,以至于一拿金子,就害怕得哆嗦,被金匠们茶余饭后一次次地嘲笑。我在内心告诫自己,不能抖,不能抖,我是个老手,挖金的绝技就是我创造发明的。我内心趋于平静,一狠心,挖了一坨金子。后来她又来了一回,就是这次回打鼓垄之前,蠢得要命的藏族女人,还蒙在鼓里。然而,粑粑说,那天她神色惊慌,形迹可疑,叫我近不要去。嘿,她总算发现了,要是栽在她手上,说不定连命都没了。我要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不到万不得已,成都是去不得的,即使去了,新龙门客栈、华天街也去不得,悦来客栈、文殊院倒是可以去。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死了,我不晓得是藏族人,还是别的客人,或者跟我有仇的金匠害死的,总之,不外乎这些人,都是金子这家伙闯的祸。金子啊金子,为了得到你,有多少金匠被客人追杀,有多少金匠被警方通缉。哦,我想起了金匠一号那个蠢货的警告,后悔当初没听他的话,才落到这个下场。也许你认为我的死,是罪有应得,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试问,如果我们只拿加工费的话,哪有钱交房租?哪有钱养家糊口?金匠越来越多,福建的莆田,广东的潮汕,与我们湖南打鼓垄金匠,像三张巨网,撒向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为了打金的营生,为了抢占地盘,不惜火拼,生意越来越少,靠加工费连房租都交不起。也许你们又会问,那你们何必出来打金?你们可以到建筑工地担灰桶,可以进厂打工,可以到街上开店,可以到工业园开厂当老板,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说,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试问,难道我们世代打金的荣光就这样消失?打金的技艺就这样荒废?不能,我们绝不能失去金匠的身份跟荣光,绝不能就此金盆洗手,不但要延续千百年来的打金传统,还要做大做强。
你们至今也不晓得我是怎么死的。就在我前几天刚刚从成都打金回来,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有人从背后突然袭击我,一刀将我捅倒在地,在我的脑壳、胸脯、肚子、腿把子、手臂上一顿乱捅。后来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七刀,刀刀要命。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仅仅叫了两声,就再没吭声了,那个该千刀万剐的家伙,在我大腿跟肚子上踢了几脚后,又搬大石头砸我脑壳,然后拖到刺蓬里,扔进其间一个隐秘的枯井里。那里的一窝蜈蚣像蚂蚁一样爬满我的身躯,像饿狼一样撕扯吞噬我的皮肉。当我看到血从刀口涌出时,我感觉身体分量在一点点地减轻,在一点点地被掏空,而思绪却变得越来越飘逸轻灵,几乎感觉不到一点点痛苦。在我肉体就要变成干树枝时,灵魂像一缕青烟,迅速与肉体剥离,升到空中,像一只鸟在旷野飞翔。我看见法医用酒精棉球将那十七道刀口上的血痕一点点吸收干净,用尺子仔细测量后,相机“咔嚓咔嚓”响。锋利的手术刀麻利地剖开胸腔,像剖开青蛙的肚皮。我的内脏被迅速摘除,浸泡在容器里。随后,法医飞针走线,就像去世的阿妈在缝补一件衣衫,麻利地把剖开的皮面缝合。锣鼓叫,鞭子响,师公摇曳引魂幡,吟唱声长长短短高高低低。黑伢、翠鸟、水仙身穿孝服,手拄哭丧棒,围着我尸体拜了又拜,喉咙嘶哑。我躺在土眼里的日子,无时不在诅咒那个该千刀万剐的家伙,愿他到阴间后,阎王爷将他丢在油锅里慢慢地煎熬,在蜈蚣、毒蜘蛛、恶蛇盘踞的洞穴里,被一点点地撕咬,在结束生命的过程中,他遭受的疼痛至少超过我疼痛的百倍千倍,那样我就能像挽联上写的“驾鹤西去”了。
媒体评论《金匠一号》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触,作者的文字犹如一把手术刀,犀利、无情地剖开那个坐绿皮火车的年代,那个BB机的年代,人们或许至今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的东西,那是一团无法在心间抹去的阴影,疼痛,忏悔,渴望,给人无尽的思索……
——阎真
《金匠一号》是一部复调小说,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在深刻剖析当代人物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nbs
相关推荐
-

正版现货新书 金匠一号::: 9787517132165 魏枫著
全新北京
¥ 28.30
-

全新正版 金匠一号 魏枫 97875171321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新北京
¥ 20.04
-

金匠一号魏枫中国言实出版社9787517132165全新正版
全新平顶山
¥ 32.88
-

金匠 民间工艺 王晓昕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473.69
-

另一张面孔 图像中的明代社会 历史古籍 金匠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46.89
-

另一张面孔 图像中的明代社会 历史古籍 金匠 新华正版
全新长沙
¥ 46.4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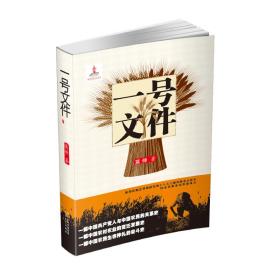
一号文件 杂文 莫伸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12.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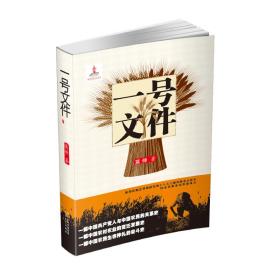
一号文件 杂文 莫伸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35.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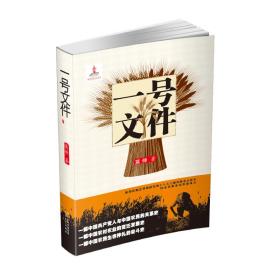
一号文件 杂文 莫伸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35.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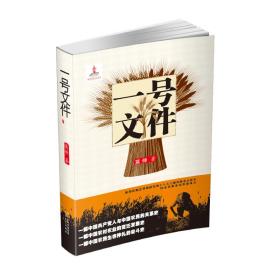
一号文件 杂文 莫伸 新华正版
全新保定
¥ 34.80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