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女儿书
¥ 8.47 5.6折 ¥ 15 九五品
仅1件
作者王朔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062768
出版时间2007-09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129页
字数82000千字
定价15元
上书时间2024-05-29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
基本信息
书名:致女儿书
定价:15.00元
作者:王朔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9-01
ISBN:9787020062768
字数:82000
页码:129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商品重量:
编辑推荐
“很多心思对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流畅,几次停下来想把这本书变成给你的长言。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是你。” “最后一次离开你们,你妈妈一边哭一边喊你的名字,你不应声,悄悄坐在自己屋里哭,我进你屋你抬头看我一眼,你的个子已是大姑娘了,可那一眼里充满孩子的惊谎。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 ” 《致女儿书》是王朔为自己女儿写的一部书,也是王朔的自传。书中以身在美国成长的女儿为倾诉对象,叙述了王氏家族的血脉渊源、历史遗传以及自我成长经历。书中无时不体现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挚爱深情。在书里,他细致体贴地告诉女儿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和人的本质,以益于她确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应对生活的态度和能力。和他以往的全部作品相区别,这是王朔的第一次“真人秀”,面对女儿他坦诚地打开了真实的内心和情感世界。作品情感真挚,尤以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独树一帜。既有一个作家的创作野心,还有一个父亲因对女儿的成长不在场而产生的深深自责与忏悔,更有一个人时时面临的孤独与脆弱,他对生命敏锐而独特的体验。读者正可以从中找出形成王朔复杂而特殊的个性的原因。 离你越远,越觉得有话要跟你说,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想,等她大一点,再大一点。2000年开始我给自己写一本小说,本来是当给自己的遗书,用那样的态度写作,把重要的人想说的话那些重要的时刻尽量记录在里面,当然写到了你,写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写到你时闸门开了,发现对你有说不完的话,很多心思对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流畅,几次停下来想把这本书变成给你的长信。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是你。 王朔的关键词(责任编辑的话) 有关王朔的一个关键词一直被我忽略,那就是:讲真话。其实它从头到尾或隐或显地贯穿在王朔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和他本人的处世态度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朔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作为“反讽”、“调侃”的王朔的语言风格,表明了他嘲弄虚假崇高的精神姿态。这些其实都与他求“真”的心理相关。 当他反对的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以后,王朔的求“真”便开始转向了对自我精神世界、个人内心生活的探究。这便是“现在就开始回忆”的结果: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写作。它是要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质命题。因此有读者称王朔老了,已经开始回忆了,不是知人论世的恳切评语,至少它不贴切。 我们说十九世纪马克思他们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道路是伟大的求真精神,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寻求和谐共同发展的今天,从自身出发、从个人出发,探究个体生命的真谛也是一种诚实和诚恳的求真精神。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从来是人类社会进化并行不悖的两个支点。 从王朔个人的创作看,《看上去很美》以后直到今年以前的这一段沉寂,正是他不断“求真”的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他打破了很多藩篱:许多固有的小说观念、文体模式、体裁限制…力图做到不违背生活的规律和内心的感受。当他遵循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写作的真实情状时,他的求“真”让他达到了自由的状态。《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等作品俱让人感受到他写作的自由无羁状态。当灵魂袒露无遗时,你便可看到它本质的皎洁和美好。 因此,王朔的写作成为今天的样子是自然而然的。求“真”的理念使他的创作向内转,寻求一种最自我最个人的表达。因为人不能对自己讲假话这是最低限度。《致女儿书》的出版与“隐私”无关与炒作无关。王朔克服了他内心极大的矛盾和犹豫,这是因为他深知“讲真话”在今天依然很难。他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做一个人类的标本,一样样拣出那些自私、唯我、暴虐、阴暗、欲念以后,剩下的让我们对自己还有信心。 求真的结果,是王朔不惜把自己拿出来论断是非。因为大家都是人,要错都有错。他起初是想在女儿面前为己辩白,说说爸爸的理由,但结果所有的理由对别人都说得通,惟独对女儿说不通。在女儿这里,他成了一桩原罪的肇因。 而王朔就敢把这桩原罪放大在众人面前。我敬佩他的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禾佳 王朔答编辑问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你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时候,结构特别麻烦,根本没可能一个视角讲到底,中间不换角度就有视野狭窄症的感觉。《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假装真挚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原来我想的是对女儿讲呢就有所讲有所不讲,有些话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讲,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因为写作的时候老觉得不太自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对写作有太多要求以后,自己就有很多束缚,你挣脱束缚的过程特别难受,结果后来《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像就跳过很多叙事直接抒情了,太浓了就叙事而言,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并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十六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会接受以后反正我也觉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就造成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那段写的东西全都是写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叙事调子以后,叙事到一定程度后就叙事不下去了。最后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写作痕迹就有写作痕迹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作为小说来说,再自由的心态和方式恐怕也没法穷尽生活,我那时候也有个不太对的想法,也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穷尽在一个结构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说写性,我想我现在写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可以都写了,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自己心情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肯定,我发现我还是挺道德化的一个人,自己开始审查自己,以一个老古板的眼光,就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譬如说,这里头全没有性描写,但我在另外一个小说里头写过。 问: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吗? 答:不是,那个我就没敢拿出来,我就认为不能拿出来,就我现在也认为不能拿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我老觉得是个社会禁忌。其实社会禁忌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当时写,当遗书写,也是一个姿态而已,就是不发表,或死后才发表。这么想你能放开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全部放开,也仍然受限制,所谓的道德观念或是什么的。 问:这是私人化叙事范畴里的? 答:当然是,就是不想做宏大叙事或者是观念性的东西做是非判断,做道德化的判断我都不愿意。依据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真实是第一的,道德判断根本就不是应该作者来下的,当然我认为读者也没有权力来下道德判断。但我们特别习惯于道德判断,这特别影响叙事,当然我自己不认为小说中谁虚构过什么,都是存在过的东西,不管是在你脑子里还是在生活里存在过。那因此真实描述是第一位的,因为有道德判断在前面之后肯定会做一些隐瞒在里头,或曲笔在里头,我觉得那个都会妨碍别人的观感的,或者自己的,写写就不诚实了。真正把性写真实了又特别难,实际上就是你不习惯讲真话的时候甚至讲真话的方式都找不到了,老实说我碰到的就是这个,因为讲假话的一堆,我们所有的文学技巧其实都是在讲假话,方便讲假话。烘托也好,比兴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遮蔽真实,或者把真实美化了,把丑陋的东西写得不那么丑陋了。讲真话想坦白地讲的时候特别困难,它就变成了只有直抒胸臆那么一个直接表达,但是这种简单的表达又不太适合表达复杂的东西,譬如说出现平行的这种心理感受的时候,它在一个叙事中要中断叙事来铺陈心情,讲一层层心情,把叙事节奏就打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接不上叙事,出现技术上的好多问题。 问: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写自己的。私人化写作可能是观感问题吧,譬如说,(问:是内容问题吧?)我觉得不是内容的问题,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因为写亲情,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吧,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所以你得从效果上来看它是社会化写作还是从题材上看,当然从题材看我从来认为我是有故事的。当然我认为我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不只我有代表性,每个人都有代表性,其实越个性越共性,我认为有好多作品不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它个性化不够,它概念化了,概念化是不可能引起共鸣的。要避免概念化没有别的,只能真实和极端真实,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不可能替代的,同样的故事不管亲情还是爱情,每个人经历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必须把最真实的那部分写出来才可能避免概念化,否则真的会掉入概念化,当然道德化也会掉入概念化。 问: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这本书也可叫“忏悔录”、“思痛书”。 答:你说的是自私的原则,是吧?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也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 但是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这是跟别人自私时没有产生过的,差别在这儿了。这个我觉得当然中国人不讲究什么罪恶感,咱们认为自己从来都很无辜,包括我过去也这么认为:错,永远是别人的。我只是在主张权利或更恶劣的:显示公平。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特别重要——有没有罪恶感,对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假如你永远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天经地义也有可能不对。我们讲自私是人的本性,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评价就放到一边去了,讲利他主义也是在确保自私——生存的前提下讲的,要先活着才能利益他人嘛,一般人都这么说。有一段提倡大公无私,牺牲自己——放弃生存,这个底线算拉高了还是拉低了,分从哪头说。我倒认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里头可能比传统儒家价值观先进就先进在这儿了,但显然不合人情没有实施下去,也确实不合人情造成了很大伤害,所以你看现在价值观复辟呼声特别高。但是我就觉得中国一场革命死了这么多人,大家一点进步也不接受,都回到老路上去了,真是血都白流了,回到老路上并不太平我认为。当然不讲缘由无条件牺牲自己,一般人也做不到;硬要别人做,强制别人做,用高压手段压别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集体互相翻脸。价值观本身是先进的,操作过程太猛了,当然这是其他的话题了。但之前谁觉得过自己有罪过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是生活的受害者,这个当然使我自己觉得,因为没有罪恶感,你会把好多廉价的行为称之为爱,给别人点钱就叫做爱,叫博爱,才不叫呢!就造成满街险象,抓起来一问都是弱者——好人?这种怪事。说实在的,我认为价值观颠倒是造成人无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为例。 问: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答:我觉得,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但实际上不是,是迁徙来的,而且迁徙之远简直是,在这书里我才上溯到炎黄那儿,其实我得上溯到非洲去,炎黄不是周口店下来的北京猿人,我在书里追根儿追到北京猿人实际上是个错误,炎黄不是北京猿人是非洲直立人来的。我们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特殊,不过“性相近,习相远”而已,只是环境造成了一些差异,把差异当了文化。我们强调文化上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没有生物上的根据的,环境变了你可以随着环境变异,与时俱进么。你不必坚持你所谓的独特性,您不特殊,您很一般, 您坚持的所有的跟别人反着的价值观都是无源之水,当初也是权宜之计,笨笨地承认残酷现实,给现象命名。老实说普世价值在我们身上是适用的,儒家和普世对立的这套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挺原始的,一点不高明。坚持这一套一有空就拿出来招魂的骨子里这是一种种族主义我以为,暗示我们的种族是独有的,具有不可调和性,且不说是不是优越,中国人太多都是种族主义者我们这里自己人人知道。这妄想恐怕都进入基因了,可惜它不建立在一个历史真实上面,是建立在一个假象上。最近复旦大学搞的DNA调查我们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洲来人,跟北京猿人混血的一个都没采到,我们强调自己是龙的传人——爬行动物传人?要不要考证一下个别恐龙和猴子杂交的可能?说给谁听呢彰显自己的无知么?跟这世上所有人一样很没面子么?黄是中间色,肯定是黑白混的别不好意思承认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是非洲,祖宗之法、祖宗的规矩是:真相与和解。你还法哪儿啊?道法自然——岂是君君臣臣所能扮演的?失去了生物狭隘性,我觉得我作为父亲——复制生命接力赛的上一位传手也没有了优越的必要。我可不想当一个野蛮的儒家父亲,愚昧地认为位置靠前判断力就一定准确。孝,实在是弱者之间可怜的互相拴对儿的口头承诺。我的全部经验告诉我,正确的生活态度实在和年龄没关,非和年龄挂钩也一定呈反比关系。父亲所能做的、大发慈悲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恶习传染给孩子,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发问时就学会对他说:不知道,我不懂。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堵住这只自上而下索取的脏手,并且随时准备揭发上一代乃至上上无数代的伪善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人失去本质了觉得特别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原来就没有什么本质,就是一系列的文过饰非这古老史,所有这些画地为牢以为纯粹的描述都是不合时宜的。我希望我女儿将来是个天性解放的不背历史包袱的,也不因为她的肤色她的来历使她到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有什么障碍。还是说到那句,就是说我们在精神上实际上是无产者,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没有一个精神特质失去了你就不能称之为人,或者不能称之为中国人这回事。我想跟她说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她后来到国外去念书,她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实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认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让你逾越。不让出身成为孩子成长的累赘我觉得这是我做父亲的义务,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好多格言都是错觉。 问:噢,原来这个根是这么写出来的。 答:当然写起来,就是往前,是从果往因那儿,你就必须到猿人那儿去。当然我这本书也有很多东西搞错了,因为当时有好多最新DNA测试结果不知道,加上是三年前写的东西后来没看,前面说的那个最近刚做的对中国人一万两千份的调查,复旦大学做的,上星期才公布。原来的历史只聊到我们是炎黄子孙,再往前就不聊了,周口店发现猿人化石就想当然地把它们和我们联系到一块,也是一笔糊涂账我就不说是认石作父了。 问:你是一个懂得推己及人的现代父亲。书里有一句话,“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 答:那都是很感性的话。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儒家伦常是保护老人的,是保护落后的,是反自然法则的。你看野生动物有养老的么?老动物们都自觉着呢。实际上养老是个国家福利问题,不是个人的生物义务,生物义务是养孩子,把DNA 往下复制, 你让他倒行逆施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反自然行为能力的,你把它规定为法律责任,你因此让他在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上产生罪恶感是不道德的。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丧尽安全感,下意识不自觉——个别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其实都破裂了但还拿铁丝箍在一起假装完好。老实说,我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破裂家庭关系的影响,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其实已经疯了很多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往昔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并没有在中年以上人群中的心理上真正平息。中国的事情很镜相,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文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譬如说家庭暴力大量的是父母打孩子,这何止是不道德,纯粹是犯罪,弱者的残忍。但是在我们的电视上随便一对父母谈到打孩子都不怕承认——坦承,口口声声为孩子好,我谢你了真不知道寒碜特别是父亲;心理学家的规劝都极尽温婉生怕惊扰、磕、碰、贬损了他这权力。善良民俗就认为这是可以的,他拥有这个权力,他终身拥有,不管他走到哪儿,丑恶到什么样,你都要对他尽义务。而且你要强调这个,你就让世代中国小孩这一生得不到他拥有的权利,实际上从一出生就剥夺了他免受屈辱、疼痛的权利。人是条件反射动物,哺乳动物都是。你打次猫试试,狗是奴才,狗能不反抗,猫反抗不了也跟你玩阴的——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小孩组成的国家将来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党建军之初就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不打骂士兵,连队实行民主管理实际是官兵平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罗荣桓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优良传统哟。不打仗了,打孩子——什么情况?一家子老是打来打去也是会伤感情的哟。在我们这儿,孩子对长辈不敬的事与长辈对下一代的虐待相比是不成比例的,父母普遍虐待孩子或虐待过孩子,而子女反过来虐待父母的屈指可数最多是不爱搭理,因为父母的权力大得多,父母打孩子社会不认为是不正常的,国家也不干涉,但是孩子不体谅父母,社会就一片哗然,我认为这是不公平。这体会我自己有了孩子更深感到所谓父母之恩之虚幻,是旌表包裹自私举到云端的欺世。赡养老人当然是一个义务,我的意思也不是就不要赡养老人,但那种东西是国家的义务,不能转嫁到公民身上去,国家不许逃避责任!独生子女他们也没有能力这么管呀,一家四个老人、八个老人就是所谓亲情慰藉——走面儿,他都走不过来净剩落埋怨了,包括老人最后的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垂危火葬入土。一个孝子正经一点我以为每个月至少要去医院一趟陪护扫墓什么的——将来。你看现在这社会仍然在或明或暗地给孩子们施加压力,常回家看看呀如何如何呀,多陪陪老人呀,这东西会变本加厉的,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上:你不这么做就是犯罪。那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做父母的都是成年人了,至少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父母应该懂事、自尊,应该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人必须经历的,我作为成年人得自己去扛这个事,国家当然应该统筹一下,在我能挣钱的时候就把后事安排好,这实际上是一个服务的问题,反过来要求孩子不太好。我觉得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不太正常,孩子承担这么多的义务,父母拼命来要求孩子,说什么赢在起跑线上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赚钱机器,这就叫成功,表面是为孩子好,其实是想自己将来有个靠山,无情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这是一种颠倒,颠倒的人性,这不是爱孩子,所以就会出现那样奇怪的逻辑,就是我为你好我可以打你,我爱你我打你。我靠,不带这么聊天的。(笑)你说你爱我,其实我很清楚你骨子里是脏心眼,是叫我将来在你老了失去劳动能力后保障你——你不肯学习意味着你将来不打算为我的衰老负责任。你看这么多父母都快——已经——把孩子打死了。我靠,您这不是爱,爱是不能交换的,无条件付出,不要回报,想都不想,起这念已是罪恶了,付出中已经达成次级回报——快乐奖赏了;跟牺牲肉体放弃清白遗臭万年享受痛苦那种境界又怎么聊呢——听都没听说过吧?我国人群的基本价值观是混乱的,混沌不明的,越老越不懂事。 问:这本书你女儿看过吗? 答:没有。 问:从目录看你只写了计划的前两章,没有完成它。 答:因为后来老实说,我的那点勇气也已经耗尽了,这里头其实涉及到点隐私。这些人都还在,再往下写,我觉得涉及的人再多的话,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我认为我女儿不会说什么她不满最重的口头语就是:太过分了。但涉及到的成年人未必会如孩子般谅解我,年龄越大的人面儿越薄你没发现么?自我往上年代的人都特小心眼,越没什么越盼什么,对什么越敏感 ……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是最激烈的,因为大家之间没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好像聊这个是把它视为家丑,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丑,这证明中国人是有情感的,在家庭里头才能显示情感,当然大家可能认为情感就是互相容忍,但我认为那不是情感是客气,真正的情感只有在冲突中才表现出互相的情感深度。其实大家都很没面子老实讲,谁有什么面子啊我都不知道,但大家都维持一个默契好像不说就都有面子。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天天有勇气,所以我不再往下写了。我现在什么心理啊,挺矛盾的,比发表别的小说不安,反正我就想看看大家有多正经就想看看,等着看别人说我如何地不顾别人感受呀,等有人认为我涉及到其他家庭成员不懂尊
-

【封面】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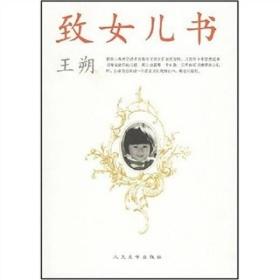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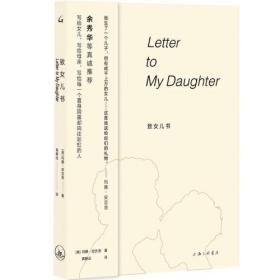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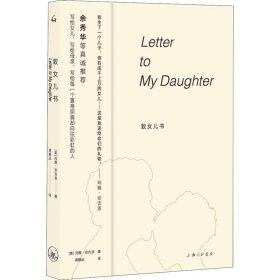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