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烧的城堡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大河 新华正版
¥ 16.9 2.5折 ¥ 68 全新
库存3件
作者赵大河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5913115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其他
开本16
定价68元
货号702_9787555913115
上书时间2024-06-3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5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目录:
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启示录》
章 漫长的/1
第2章 黑羊/16
第3章 寸绍锡和张问德/26
第4章 噩梦/35
第5章 大刀/48
第6章 七杀简史/60
第7章 穿越/73
第8章 梦及其他/82
第9章 天使/88
0章 父亲/96
1章 病/100
2章 田岛与瞿莹莹/120
3章 母亲/136
4章 爱与蛊/152
5章 答田岛书/163
6章 与死神的三次照面/180
7章 蛇影/189
8章 家宴/201
9章 救县长/209
第20章 李代桃僵/220
第21章 悲怆/233
第22章 空白/241
第23章 拯救/255
第24章 田岛夜访/262
第25章 寸绍锡与刀玲子/270
插入的一章 赋格/276
第26章 诊所/306
第27章 情报与计策/318
第28章 炮火下/326
第29章 战争的背面/334
第30章 出城记/345
第31章 废墟奇遇/357
第32章 邂逅与重逢/365
第33章 尾声/378
致谢/393
内容简介:
一部腾冲浴血奋战反抗军侵略的抗争史,一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涅槃重生的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军侵略云南腾冲。踩在生死悬崖上的羔羊们,开始了向死而生。而这座多山多雨多骨头的城市,终将在熊熊火焰中涅槃。鲜明的主题:残酷的战争造成一个苍茫的时代困局,国破家亡的痛楚,生死存亡的处境,情与欲的人挣扎,使我们仿佛在地狱中行走了一趟。小说史诗般地表现了战争中所遭受的可怕苦难,他们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深沉的哲理思: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始终隐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透过层层乌云依然照亮。作者将人物置身于复杂险绝的生死之境,拷问灵魂的质地,彰显人的复杂。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正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决定着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时他要为这份选择承担责任。是遵从民族大义奋起反抗,还是卑怯偷生忍辱负重,每个人都在艰难中做出决策,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小说注重展示人物在复杂险绝之境的抉择,以及各自的抉择所带来的命运。高超的艺术手法:作家赵大河是一个具有诗的手艺、编剧的构思、与小说家讲故事的本领的作家。小说故事戏剧强,人物鲜活,情感饱满,视野开阔,切入点独到,画面感强,适宜于电影表达。目前的抗题材很多,但是这个小说角度独特,艺术手法高超,超现实主义手法的部分使用,使小说具有透视功能,打开小说叙事的多维空间,使叙事维度得以扩展,具有极强的艺术震撼力。20世纪40年代,军铁蹄入侵云南腾冲这座小城时,父亲方渡正在忙乱地迎接“我”的诞生。踩在生死悬崖上的羔羊们,从此开始了向死而生——在血与火中,他们或苟且偷生,或抑郁悲怆,或不屈不挠地展开英勇的抗争而这座多山多雨多骨头的城市,也终将在熊熊火焰中涅槃。小说以孩子的全知视角,用大量真实可信的细节来呈现陷落之城的生活,沦陷区人们的生活遭际及奋勇抗争,创造地再现了以县长张问德、医生方渡等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讴歌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坚强、不屈、抗争、奋斗、拼搏精神,谱写了一部腾冲浴血奋战反抗军侵略的抗争史,一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涅槃重生的交响乐。
作者简介:
赵大河,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文学刊物编辑。现供职于河南省文学院。作品见于文学十月花城中国作家山花美文等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手记北风呼啸的下午六月来临,长篇小说侏儒与国王等。话剧作品有“开心麻花”系列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等,以及大魔术师霍迪尼的后遁逃等。影视剧有湖光山乐活家庭四妹子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奖、“曹禺杯”戏剧奖、莽原文学奖、金质文学奖等奖项。
精彩内容:
街上景象像一幅卷轴画在我面前打开,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我好像亲眼看到过。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父亲走过街道时,我还没出生呢。我不可能看到。那么,这些景象由何而来?是父亲讲的,哥哥讲的,还是别人讲的,抑或我从哪儿读到的?我不确定。还有,父亲那天的活动我好像都知道。你会说,这不奇怪,也许你父亲给你讲过无数次。可是,父亲心里如何想的,我好像也知道,这很奇怪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清楚的是,我不是在虚构,我是在记下我头脑里出现的画面和声音。回到街上。这条街父亲走过无数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是去找寸绍锡,和寸绍锡谈古论今,每次走的都是这条街。诊所有急诊病人,如果父亲不在,母亲会打发哥哥到学校去喊父亲,父亲在那里。对父亲来说,多么熟悉的街道啊,现在竟如此陌生。光线、气味、尘埃、声音、天空,都是陌生的。甚至脚下的石板也有些陌生了。常的热闹、笑声、吆喝、讨价还价、一团和气等等都不见了,好像那是梦境,现在一觉醒来,这种混乱、惊慌、叫喊、咒骂、紧闭的大门、冰冷的铁锁、可怕的阴影等等,才是现实,才是真实世界。描写这些让人心里发堵。这个世界我应该不愿意来才是,我为什么急着要来呢?母亲说她受了惊吓,动了胎气。受什么惊吓?原来院里有一大缸,哥哥搬东西时将靠在墙上的梯子碰倒,梯子砸到大缸,“哐”的一声。然后,他们眼睁睁看着大缸裂开一道纹,裂纹从上到下,慢慢延伸,到缸底时突然崩开,分为两瓣,缸里的水“哗啦”泻一地。母亲正好看到这一幕,心头一惊,便感觉肚子里有反应。次阵痛持续了十几分钟。母亲咬牙忍着,不叫出声。哥哥看在眼里,他要去叫父亲回来,母亲制止他:别去。哥哥听母亲的话,没去。他以为母亲希望他陪着,其实是母亲知道从次阵痛到分娩还会有相当长时间。这期间,唯有忍受,谁也帮不上忙。父亲回来也没用。母亲坐到凳子上,看着打包好的东西,骂我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添乱。哥哥看着院子里的水,想把裂成两瓣的缸挪到墙边,试了试,挪不动。母亲说,等你爸回来挪吧。过一会儿,阵痛结束,母亲起来继续收拾东西。哪些带上,哪些留下,不好取舍。父亲交待,所有药材器械都带上。好吧,母亲说,都带上,都带上。她知道那些东西对父亲有多重要。可是,这是逃亡,不是搬家。能不带吃的吗,能不带穿的吗,能不带用的吗。女人虑事情和男人不一样。人要活着,得有吃有穿。可是,单靠父亲,哪能带那么多东西。雇人?这时候到哪儿去雇人。父亲去找寸绍锡,商量往哪里逃亡是其一,其二是结伴好有个照应,重要的是想让寸绍锡帮着拿一些东西,运气好的话,还能叫上一两个过来帮忙。趁父亲还没回到家,重大问题还没到来,我来说说母亲吧。这时候我和母亲关系亲密。母亲的子宫,我的天堂,这狭小的黑暗的温暖的海洋啊,我徜徉其中多么惬意。似有不同。静的海洋先是一阵悸动,叫我害怕。接下来,归于静。但这静却叫人不安,似乎有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某处积聚,随时准备掀起惊涛骇浪。我能怎么办,想叫喊,发不出声音。踢腿打拳,只会叫母亲疼痛。祈祷吗?也只有祈祷了。我蜷曲的适合祈祷,再虔诚也莫过于此。神啊,我吧,我的母亲。母亲远涉重洋,在上海还与外公外婆书信往来,到腾冲后,书信一概断绝。在这儿,她听不到一句熟悉的母语,吃不到一熟悉的什锦汤面。母亲已经中国化了,腾冲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本人。她在本学的是护理,跟随父亲来中国后,她一直帮父亲打理诊所。嫁鸡随鸡,嫁随,她早打定主意,一辈子跟着父亲,是福是祸,在所不计。父亲回来。满院子的水已渗入地下,他没看到。但地皮是湿的,他不可能看不到。裂为两瓣的大缸那么醒目,他不可能看不到。但他是没看到。他只看到那些打包好的东西。母亲正在和一包干的山野菜搏斗,她想把山野菜塞进包里,山野菜是不屈服,不肯往里面钻。父亲来到母亲身边,接过山野菜放一边,扶母亲坐到凳子上。他说不走了。这句话来得如此突然,母亲愣住了。为什么?父亲说不为什么,留下来是了。因为我吗?母亲说,不用管我,我能行。说这话她自己都不相信,可她要这样说。她没说刚才阵痛的事。不是因为你,父亲抚摸着母亲的大肚子说,是因为她。我猜想,父亲决定留下来,至少有这几方面的虑:一、妻子的预产期马上要到了,这么笨重的身体能翻越高黎贡山吗?二、孩子若生在终年积雪的山上,能活下来吗?三、逃亡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活命,留下来活命的机会可能更大些。母亲说,你要想好。父亲说,我想好了。这时候母亲才告诉父亲她有反应,她说,我疼了一阵,可能要提前。她说话的气带着歉意,好像这是她的错一样。差不多,只是错几天而已,父亲说,这也算正常,别怕,没事的。来的不是时候,母亲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他(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没错,父亲说,这是命。我感到母亲放松下来。留下,是她希望的,但她不会主动提出。父亲提出正合她意。来中国后,她感到本的强势,这种强势对中国是一种威胁,所以在家庭中她不能再强势,要让丈夫强势。父母和哥哥将打好的包又拆开,东西放回原处。整个腾冲城,如此反常的景象不会有第二家。寸绍锡来的时候,这项工作还没完成。寸绍锡带来两个强壮的,这是要帮忙搬家的架势。他虽然没和父亲交流,但领会了父亲去找他的意图。他看到父母和哥哥拆包很吃惊:这是干吗?我们留下,父亲说。寸绍锡说,你想搬的东西都可以搬走,人手不够,我还可以再叫。他以为我父亲怕搬家麻烦才不想走。我要留下,父亲说得很坚决。寸绍锡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方晴雪,晓得了我父亲的顾虑。他将我父亲叫到东厢房,那儿是他们下棋的地方,比较僻静。他说,别人可以留下,我们不能留下。你认为我会做汉奸吗?不会,寸绍锡说,正因为这样,留下凶多吉少。你是说,鬼子会杀一个医生?我敢肯定,鬼子对一个拒绝合作的人不会手软。一阵难耐的沉默横在他们中间。寸绍锡后拍拍父亲的肩膀,要父亲保重。他带着两个走了,此别过。父亲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怅惘了好一会儿。下午。腾冲城陷入可怕的寂静。棺材铺老板躲在棺材里,他巧妙地为棺材留了一条缝,以便呼吸和听外面的动静。裁缝铺老板的老娘没有走,她从容地为自己缝着寿衣,嘴里嘟嘟囔囔,好像在与死神拉家常。杂货铺一家没逃亡,老板是个守财奴,铺子是他的命,他才不会扔下铺子呢,那比要他的命还难受,他不走,也不让家人走,他说,世道越乱越要看好家业几个商人在江西会馆开会,商量着下步如何做生意,不管谁统治这儿,只要不耽误他们发财行,他们不怕当汉奸,但他们不会当汉奸,那样不划算,他们会找个代理人,出面欢迎本鬼子,可是,这会儿到哪儿去找代理人还有,英国领事馆大楼静静伫立,火山岩石条墙体和镀锌瓦屋顶漂亮得无以复加,可以和来凤山上的白塔媲美突然一声响,划破腾冲的寂静。鬼子进城了。此时,母亲迎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在狭小的海洋中遭遇惊涛骇浪,大海仿佛要翻过来,将我倒扣在下面。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父亲让哥哥去烧水,抓紧了,快去,他说。他的声音都变了,陌生得可怕。哥哥赶紧跑去生火烧水,他浑身发抖,好半天才将火点着。会不会难产?母亲问,她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你放松,放松,有我呢,没事,没事的,父亲强作镇定地说。父亲让母亲躺,他要调整胎位。父亲的手像钳子一样有劲,碰到我,我的骨头都要碎了。母亲大声叫喊。母亲的叫声冲出房门和院子,像疯狂的野兽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父亲、母亲和我,纠缠在这场生死中。如果母子之间只能保一个,父亲会毫不犹豫地保母亲,牺牲我。我不怪父亲。你无法要求一个男人舍弃同甘共苦的爱人去自私地保存自己的一点骨血。母亲也没说让父亲保孩子。孩子没了,她还可以。再者,她要活着陪伴和照顾这个男人。我也不怪母亲。时间是怎么到黄昏的,我们都不知道。母亲声嘶力竭地叫喊一阵,喊不动了,停下来歇歇,积攒力量,再喊,如此反复,直到气若游丝。父亲无视母亲的痛苦。他更在意的是两条命,妻子和胎儿,他都想保住。他绝望地努力着。妻子的叫喊让他心烦。他快要崩溃了。他跑到门深吸一新鲜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他又跑到厨房,冲哥哥喊:水烧好没?不等哥哥回答,他揭开锅盖,看到水正在锅里沸腾,他跑去拿来一些闪闪发光的器械,手术刀、镊子、夹子、剪刀等,丢进锅里。继续烧火!他冲哥哥吼道。厨房蒸汽弥漫,什么都看不真切。父亲点上汽灯和蜡烛。他把煮过的器械用消毒,准备给母亲动手术。七岁的哥哥给他打下手。我,此时既是那个等待剖腹产的胎儿,又是一个旁观者。我的灵魂大概随着母亲的叫喊又跑到了外边。我亲眼目睹了自己恐怖的出生过程。我诞生在昏暗的灯光和黏糊糊的血泊中。我被父亲从血泊中托出,已经窒息了,对外界没有任何感觉。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腕,将我倒提起来,用力地拍打我的背写到这里,我突然写不下去了。那天我(确切地说是我的灵魂)冷漠地旁观自己的出生过程,甚至看到自己窒息也没什么感觉,现在写下这个故事却让我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这是为什么?我想不明白。诸位请原谅,在此我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吧,如实写下去,也许写的过程会有灵感。父亲正在拍打我的背,鬼子来了。哥哥先看到鬼子,他喊父亲,父亲没听到。也不知哥哥哪来的勇气,他张开手臂拦住鬼子,不让鬼子进门。两个鬼子。头戴钢盔,端着,寒光闪闪,背上背着一大疙瘩东西,怪模怪样,像妖怪。哥哥说,不许进!两个鬼子停下来,呜里哇啦说一通。哥哥三岁前学过语,到腾冲后不但不再学了,还被禁止说语,几年过去,他的语差不多全忘光了。再次听到语,不知激起了他什么样的反应,他嘴里竟然又蹦出了一个语单词:パパ。他用语喊父亲。很多年后,我这件事求证过哥哥,哥哥说不可能,他不可能说语。他说他从前没学过,后来也没学过语。他学过英语,学过俄语,但没学过语。如果哥哥所说属实,如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呢?我想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哥哥喊“爸爸”,鬼子听成了“パパ”。两个鬼子,乍看上去,一样,只是一个年龄大些,一个年龄小些。我叫他们大鬼子和小鬼子吧。其实他们区别大着呢,大鬼子狡猾,小鬼子生猛。他们从缅甸一路打过来,经历多少硝烟炮火,杀过多少人,说也说不清,岂能让一个小孩给拦住。大鬼子逗我哥哥说,为什么不让进去,屋里藏着宝贝吗?哥哥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摇头。大鬼子说,噢,没有宝贝,那为什么不让进去?哥哥还是摇头。小鬼子将架到我哥哥脖子上,你不怕死吗?大鬼子让小鬼子别吓唬小孩。他继续逗哥哥,你爸妈呢?哥哥不说话。小鬼子说,他听不懂,杀了算了。这时候屋里静悄悄,母亲没声息,我还在窒息,父亲倒提着我,见我没动静,将我放到一块白布上。如果我后来没活过来,父亲大概会将我的尸体包在这块白布中埋掉。父亲准备给母亲缝合的时候,听到外边的动静。一边是妻子剖开的肚子需要缝合,婴儿需要救,一边是儿子面临危险。父亲走出去。突然冒出一个满身血污的人,两个鬼子吓一跳。他们举起对着父亲,喝道:站住,举起手来!父亲站住,将手举起来。举过头顶。是。大鬼子问,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医生(私は医者です)。停顿。两个鬼子意识到父亲说的是语,父亲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父亲让哥哥回屋里。哥哥回到屋里,躲门后,朝外面看。以下鬼子和父亲的对话自然是语。大鬼子问父亲在哪儿学的语,父亲说他在长崎上过学。父亲不想和鬼子多说话,他说,我在做手术。父亲说完要回屋,小鬼子突然扣动扳机,叭!声响得厉害,子弹擦过父亲的耳边呼啸着钉进门板。父亲站住。不知小鬼子是打偏了,还是恫吓他。大鬼子将小鬼子的压下去,别乱杀人。他问父亲,给什么人动手术?父亲说,我太太。小鬼子说,肯定是远征军战士。大鬼子说,是吗?父亲说,我妻子难产,我给她动手术。两个鬼子半信半疑。父亲为了摆脱他们,尽快去给母亲缝合,说道:我太太是本人。父亲说罢不管不顾进屋给母亲缝合。两个鬼子没有离开,在门外商量。他们没遇到过这么傲慢的中国男人,这个中国男人还娶了一个本太太。这两件事都刺激他们。按照以往的逻辑,很简单,杀!这次因为兵不血刃占领腾冲,他们还没杀人,猛然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还有些不惯。大鬼子说,他很傲慢。小鬼子说,他娶本女人。大鬼子说,贱女人,给我们丢脸。小鬼子说,睡我们姐妹。大鬼子说,该死的女人。小鬼子说,统统杀了吧。大鬼子说,也许他在给敌人包扎。小鬼子说,我看也是。他们杀人不用找借,但找个借下手显得理直气壮。大鬼子说,用。小鬼子从腰里掏出,正要拉弦,屋里传来嘹亮的婴儿哭声。父亲在给母亲缝合前又抽空给我一巴掌。我嘴里吐出一团污物,“哇”的一声哭出来。因为憋得太久,哭声格外高亢。两个鬼子听到哭声吓了一跳。他们杀人的借没了。小鬼子有些犹豫,要不要扔进去。大鬼子说,这是个孽种。小鬼子说,!大鬼子说,大本帝国不该有这么贱的女人。小鬼子说,该死!两个鬼子这时候想杀人,不是兽发作,也不是为了战争目的,而是思想钻进了牛角尖,认为中国男人娶本女人是对整个大和民族的侮辱,难以容忍。投出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投,不是他们心软了,发慈悲,而是因为紧急集合号响了。集合号是军令,听到后必须立即停止行动前去集合。大鬼子说,明天吧。小鬼子说,便宜他们,让他们多活。他们心有不甘地离开了。我的嘹亮哭声像旗帜一样飘扬在腾冲城上空。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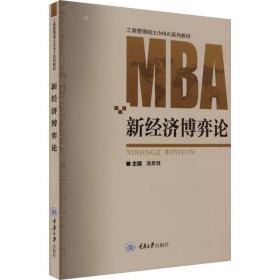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