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到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公路之旅 成功学 (美)大卫·利普斯基|译者:林晓筱 新华正版
¥ 12.1 1.8折 ¥ 69 全新
库存3件
河北保定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大卫·利普斯基|译者:林晓筱
出版社北京联合
ISBN9787559626707
出版时间2018-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337页
定价69元
货号411_9787559626707
上书时间2024-06-16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目录:
"
尽管到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 1
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同行 1
前言 2
序 5
编后记 6"
内容简介:
"although of coure you end up being yourelf: a road trip with david foter wallace
讲述了书无尽的玩笑作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滚石杂志记者一同踏上新书宣传之旅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在为期五天的公路旅行中,华莱士讨论了从孤独到哲学,从电视到现代诗歌到爱情,当然还有写作的。
滚石记者和大卫?华莱士的公路之旅,这本是两个作家的对话,却接近不掉书袋,从很普通人的角度入手,慢慢深入。
"
作者简介:
"
david liky是滚石的特约编辑。他的小说和非小说出现在“纽约客”,“哈珀”,“很好美国短篇小说集”,“美国很好杂志写作”,“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等等。他为npr的所有事情做出了贡献,并获得了朗博奖学金,glaad的媒体奖和杂志奖。的非小说类作品“美国”(尽管到后,你还是成为你自己),获得了时代杂志年度很好图书。"
精彩内容:
"译序
1996年3月5,滚石杂志的记者大卫利普斯基主动请缨,前往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住所,并与他一起参与了后者为小说无尽的玩笑举办的巡回宣传活动。期间利普斯基用录音机和本记录下的访谈内容一度被搁置,直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去世后两年,以尽管到后,你终会成为你自己为名整理出版。时代周刊的利夫格罗斯曼说,这是一部由“四只手以二重奏的方式在打字机上打出的作品。”
两者除了有共同的名“大卫”之外,年龄也相仿,彼时利普斯基30岁,华莱士34岁,这使得两者在对谈时没有年龄上的隔阂感。此外,两人都是出版了作品的作者,只不过华莱士比利普斯基的名声要大许多。利普斯基清醒地意识到,除去这几个相似点之外,两人优选的不同在于:“他憧憬比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好的事物。而我想要的恰恰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同时,我也想要让他认识到,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需改变。”访谈在这种“共同”和“差异”之间展开。
不过,利普斯基在走进华莱士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展现出仰望的姿态,想要真诚告诉华莱士“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需改变”的愿望既拉了对谈的姿态,又使得两人得以忘却“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偶像和拥趸”,乃至“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以朋友间的方式进行沟通。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沟通是双向敞开自我的过程。
无论是华莱士所宣传的书籍无尽的玩笑的主题,还是他长年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抑或是利普斯基造访时的现状,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孤独”。这是利普斯基凭借其敏锐的记者嗅觉和
专业写作者的素养迅速捕捉到的信息,它构成了访谈的主题。这个主题使得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也让这场访谈具有可持续下去的可能。
有关“孤独”的主题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并不陌生。华莱士的好友乔纳森弗兰岑在其散文集如何独处中对其有过全面的展示。而从利普斯基对华莱士的访谈中不难看出,弗兰岑对于华莱士的孤独,除了出于友情的关怀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描写关系。仿佛华莱士更像是乔纳森笔下的一个人物。而对于华莱士本人而言,孤独是始终伴随在他身上的“症状”,像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有时在身后,有时在脚下,更可怕的是,它也会落在前方,永不缺席,算迟到也会及时补位。利普斯基在企图捕捉这种“孤独”时所遇到的问题接近于保罗奥斯特在其频繁出版的各本回忆录中揭示的困惑:孤独一旦被言说,是否还算是孤独?
具备专业素养的利普斯在访谈伊始,的确为了保障被采访内容的客观,做到了尽可能地不去干预被采访者华莱士的。但随着访谈的进行,读者可以发现对这种“不干预”感到不适应的恰恰是华莱士本人。两人往往在独处时,华莱士显得较为和,但一旦到了公开场合,有第三者或者更多的人在场时,敏感的华莱士会迅速意识到有利普斯基的存在。无论在华莱士的课堂,还是在书店宣传现场、朋友的家中,华莱士是刻意地在寻找利普斯基存在的痕迹,并时不时地会提醒利普斯基尽其记者的“本分”。这使得整个对话显现出一种古怪的反讽:孤独并不是诞生于独处之时,后知后觉式的伤感,而是他人在场时,即时即刻的敏感。这种对孤独的自省乃至自嘲,不仅构成了华莱士撰写游记、时独特的风格,也构成了华莱士独特的幽默感,读者可以借助这部采访录,寻找到阅读华莱士一系列作品的视角。
在利普斯基的访谈中,这种对孤独的自我体认首先是一种“自我聆听”。利普斯基时常会对着磁带复述华莱士说的话,这种间接引语式地重复,一度让华莱士感到有趣。这种聆听他人述说自己的感受,本质上与华莱士在谈话中揭示出的对糖果、大众娱乐的迷恋密切相关。糖果和大众娱乐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不是一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主要营养来源,但却能让人上瘾。瘾源在于两者都会通过强烈的感官刺激,营造出一场幻觉,华莱士认为:“这是短暂地抽离自我,给自己放一个的方式。”然而,其孤独而言,华莱士借助幻觉并非是对孤独的克服,而是短暂的抽离,这意味着,终他又会回到这种孤独之中,继而怀着对幻觉的期待,开始新的循环。本质上来说,华莱士并没有因为哪个人的介入打破这种循环,而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只不过这种封闭过于喧嚣。
这本该是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幸运的是华莱士身上有使得孤独这种瘾症得以传播开来的社交魅力。之所以称其为社交魅力,是因为随着访谈的进行,作为译者,我发现利普斯基的发音惯,用词方式,乃至言说模式,开始不自觉地朝华莱士靠拢。更为重要的是,利普斯基也加入了“华莱士波段”之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普斯基才真正走进了华莱士。
如果说孤独如瘾,那么一次次的公路旅行、航空飞行本质上成了对这种瘾症的扩散与传播。这部访谈录如同利普斯基所言具有公路片的特质,只不过“在路上”的体验并非是冒险,也非致命的邂逅,而是一次对自我抽离式的幻景体验。旅途中风景的变换和分出不同地点的感受,不仅让华莱士和利普斯基的对话具有了无数“变奏”的可能,也使得华莱士对自我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往事的揭示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
无疑,这是适合采访华莱士的方式,也是华莱士得以展开自我的很好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大卫,两位作者,两个孤独的人,才能构成两个独特的声部,合奏起有关孤独的二重奏,读者才能在这种合奏方式中聆听到独特的音符。
本书得以面世需感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张其鑫,正是他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这本书,也因为他对我译文的信任,使得这本书具有了与读者见面的可能。此外,还需感谢本书的编辑丛龙艳,她为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
作为译者,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此书的首批中文读者之一,但正如利普斯基自己所说,书在遇到读者之前,首先会与一群朋友相遇。以上两位是在读者之前遇到的朋友。此外,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多次向身边的人提起这本书,这本书能够顺利翻译完成,离不开他们对此书的关注和对我翻译工作的鼓励。
我设想这本书适合在旅途中被人阅读,因为读者在旅途中,可以在窗外变换的风景之外,看到书中另一番“流动着的”风景,而正是在这两种变换的风景之中,他们或许才能意识到自己被另一种已被言说的孤独所击中,才能激发出对自己的关注。别忘了本书的书名还包含着这样的信息:你终会成为你自己。
编后记(调至正文后面)
大卫身高6英尺2英寸[ 1英尺=12英寸≈0.305米,1英寸=2.54厘米。],身体健康时体重达200磅[ 1磅≈0.454千克。]。他长着一对深的眼睛,声音轻柔,下巴上留着胡楂儿,一张可爱、嘴唇上翘的嘴是他显著的特征。他走起路来像退役的运动员那样闲散——裤腿管卷到脚踝处,仿佛身体任一部位都是令人愉悦的。他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叙述所有人的生活,进行写作——这些都是你不曾细想的事物,是你在超市和上下班的途中匆匆瞥过的背景中的举动——而读者会蜷伏在彰显他个人风格的角落和空间里。他这一生是一张止于错误终点的地图。他曾是一名全优高中生,打过美式橄榄球和网球。在从阿默斯特学院之前,他写过一篇哲学和一部小说。他上过写作学校,随后发表过小说,全市那些惊声尖叫、言词激烈、睚眦必报的编辑和作者全都陶醉般地爱上了他。随后,他出版了一本长达一千页的小说,获得了专享用来表彰天才的奖项。之后他又创作了许多随笔,这些随笔传递的感受不分区域,至今依旧鲜活。他曾接受加州某所学院颁发的特殊教席,在那里教授写作课,结婚,出版另一部书,46岁时自缢身亡。
是一种力量强大的结局,它回到过去,并搅乱根源。它具有一种重力效应:终,每一份记忆和印象都会受到其拉拽。曾有人让我写写有关大卫的死,我将此事告知朋友(他们都是作家,听后无不感到震惊,劝我不要写)和他的家人(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但几乎不可能和她谈起此事)。他们所顾虑的其中一点在于,我该如何将大卫富有活力、讨人喜欢的一面展现出来。我曾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交谈过,他用一些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的术语回答我,仿佛种种事实都是中的,如果拿捏过久会变质。那位教授做了许多专家都会做的事。他提醒我,他不会带着个人彩看待大卫,但是可以列举一些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喜欢服药。“我的意思是说,我表示同情,”那位医生说,“我自己不会去服任何药。”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自1989年起,大卫一直在服用一种药效极强的代抗抑郁药——苯乙肼。这种药会带来一车厢的1950年代的副作用,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有引发高血压的潜在风险。到了2007年,他决定弃用这种药。医生听后在电话里一时没有说话,相当于点头默许了。“其中有一种模式。当一种作用因素收效显著时,人们或许会误以为自己不再抑郁了。所以,这是一种虚的安全感。他们感觉他们已经没事了,已经痊愈了,算停药也不会有事。不幸的是,人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经常会经历症状的反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随后,他们或许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先前卓有成效的了。”
对于大卫来说,情况是如此。苯乙肼出现在一长串禁食食品目录中——巧克力、腌制肉类、某些芝士,以及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吃的过熟的香蕉。于是,他的餐盘中会放着一些目录之外的配餐,相互搭配和优化。所有人都认为,大卫的前半生是他度过的快乐的时光。婚姻,宁静,加州——落,终老的海岸。2007年晚春,大卫、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的父母——吉姆和莎莉,一起坐在一家波斯餐厅里用餐。其中某种食物让他感到不对劲。他的胃剧痛了数。当医生们听说他曾长时间地服用苯乙肼——一种尚在使用含铅、观看天线电视的年代的一剂猛药——之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建议他别再碰这种药了,试试别的新药。
“于是,在那一刻,”他的妹妹艾米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感伤,“已经注定。‘哦,好吧,上帝啊,我们的制药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我肯定我们可以找到别的药物,将那烦人的抑郁症连同所有这些副作用一起剔除。’他们其实不知道,这是专享能保他命的东西。”
大卫随后的生活轨迹可以用惨败来形容,大卫本该慢慢戒掉先前服用的药物,然后慢慢服用新的药物。“他知道过程会很艰难。”乔纳森弗兰岑告诉我。弗兰岑的小说纠正获得了图书奖,他是大卫成年后第二阶段优选的朋友。“但是他曾认为他或许可以花一年时间去适应。他曾设想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至少是暂时为之。他是一个主义者,你知道吗?他想要成为一个的人,而服用苯乙肼算不上。”
这是弗兰岑想要强调的事情。(接受采访的弗兰岑,具有一个作家对自己职业当仁不让的品质,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把我推开,自己来讲述这则故事。)大卫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层面,有时这一点会让他变成一个无法与别人欢处一室的人,而现在他很开心。他爱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这是主干叙事,是诸多原因中重要的原因。正是处于乐观、和坚强的起点,他才能试着迈出下一步。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正因为诸事皆顺,他才觉得自己处于足够稳固的位置,可以做出一些根本的改变。但是他运气不佳,这些没有起作用。”
医生们开始为他开具其他药,但每种尝试都失败了。到了10月,大卫的症状加重了,不得不住回医院。他的体重开始下降。那年秋天,他看上去像又变回了大的样子:长长的头发,紧张的眼神,仿佛重拾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青涩。
当艾米打电话和他交谈时,他时常会展现出先前的那个自我。她说:“去年,你不该向大卫提出的问题是‘你过得怎么样?’,但是若不这么问,你几乎无法与一个不常见面的人展开交谈。”大卫非常诚实。他会回答说:“我过得并不好。我尽力了,但我过得不好。”
那一年的状况时好时坏,时间开始过得很快,随后放缓,情况稳定却又遇到突如其来的低谷,头上的天空看起来是那么遥远。5月初,他和他写作班上的高年级们一起坐在咖啡馆里。他们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未来该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他逐一解答。临近结束,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哽咽了。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有些人笑了,这份记忆后将令人痛苦。大卫抽噎起来。“继续笑吧,尽管此刻我正在哭泣,但是我真的会想念你们所有人的。”
所有的药都没奏效。6月,大卫企图。随后,他又回到了医院里。医生们给予了十二次电击疗法,这种方案一直让大卫感到害怕。“十二次。”他的母亲一再提起。“如此残忍的方案。”他父亲说。“历经对大卫来说宛若地狱的这几年,”他母亲说,“他们决定再度启用苯乙肼。”
弗兰岑感到担忧,于7月坐飞机赶来,在大卫身边陪伴了一个星期。大卫的体重在那一年一共掉了70磅。“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瘦。他眼中透露着一种神情:恐惧,靠前悲伤且空洞。但是,与他相处依旧令人开怀,即便他只有百分之十的力气了。”大卫现在或许会拿他自己开涮,他之前还从未意识到,他说:“电击室里的某些椅子其实坐着挺硬的。”弗兰岑会和大卫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同他的两条玩耍,当大卫点烟的时候,这两只会去屋外。“我们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他用他惯常的语句说:‘的嘴如此干净,简直可以当消毒剂来使。的唾液也不像人的唾液,而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当他要离开时,大卫对他的来访表示感谢。“我很感激他能让我去陪他。”弗兰岑对我说。
六周后,大卫让他的父母坐飞到西部。苯乙肼并没有起效,这是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优选的风险。病人出院,再次住院,药物却不再起效。大卫无法入睡。他害怕离开这栋房子。他问:“我要是遇见我的可怎么办?”他父亲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我确信,如果哪个看见他,肯定会伸出胳膊抱住他的。”
华莱士一家在一起相处了十天。大卫和他的父母会在早上6点起床,随后出门遛。他们一起观看dvd影片,聊天。萨利给大卫做了他爱吃的饭菜,都是些能宽慰人心的大餐——菜肉馅饼、焙盘菜、奶油草莓。“我们一直对他说,只要他活着,我们开心。”他的母亲说,“即便在那时,我也能感觉到,他马上要离开这个星球了。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离开前的下午,大卫表现得非常沮丧。他的母亲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我摸了摸他的手臂。他说,有我这么一位母亲,他感到欣慰。我对他说,那是我的荣幸。”
9月中旬,卡伦出去了几个小时,留下大卫和两条待在一起。当她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已自缢身亡。“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的妹妹告诉我——她还对我说起了另一件令她感到难过、亲切、难受的事情:“大卫和他的那两条,很压抑。我肯定他吻过它们的嘴,并且向它们表达了歉意。”
作家们通常会写两大主题——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疾病,这两个主题虽是他们内心的惊涛骇浪,说起来却波澜不惊。曾有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詹姆斯乔伊斯去一个聚会上拜会马塞尔普鲁斯特。你期待那是一场级别的相互打趣。乔伊斯说:“我的眼睛糟透了。”普鲁斯特说:“我可怜的胃啊,我该拿它怎么办?说实在的,我得马上离开。”(乔伊斯过话锋,说:“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能找个人搀着我的胳膊好了。”)大卫可不会那样。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他从未把自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告诉过别人;另一方面,他长得不像你们想象中的作家的样子,他看起来像一个瘾君子、一名矫健的运动员。(马克科斯特洛是大卫成年后阶段优选的朋友,他说,大卫曾教给他一个伊利诺伊的土话,叫作“土”。“有些坚韧,也有些像废材废物的网球运动员形象。”科斯特洛说。)大卫看上去像某个大学代表队里的队员,是那种用不了多久会脱颖而出,逐渐与队友拉开档次的人。他是一个大个子,头上缠着头巾,头发披散着,像某个会邀请你去玩沙包游戏的人,如果你拒绝,他很有可能会揍你一顿。
这样打扮是有意为之。当大卫还是个时,曾因为长得像一个学院作家——细腻的眼神,敏感的洞察力——而感到困扰。他把这些人称为“愣头青。老兄,我记得,我依旧不喜欢称自己为作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不想被别人误认为是那类人”。
这一点并不便于你与他人相处——与人相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需要极强的亲和力、幽默感以及饱满的情绪。这说得通了。书籍是社交的替代物,某种层面来说,你读到的是你乐意与之结伴出行的人。章节、片段、小说和文章,这些都是接近的东西。即便遇到的仅仅是一个善于描写事实的作家,你也还是会想缠着他们讨要事实,这像试时,你坐在一个头脑聪明的孩子身边,偷偷抄他们的一样。大卫笔下的自己——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中尤其明显——是你迄今为止优选的朋友,他袒露,悄悄说着笑话,用文雅的风格扫除那些逼你发怒、令你感到乏味或不快的东西。
马克科斯特洛与大卫结识于阿默斯特学院。他们是通过分配寝室成为朋友的。“戴夫[ 戴夫是大卫的昵称。]曾为了选到很好的房间,研透了其中的数学因素,用一种很好的游戏理论来处理这事儿。他想要添加一个人。他申请了一个双人间,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随后,我们抽到了马萨诸塞州西部糟糕的一个住址。我们住在一个强行改装成双人间的单人间里,这间屋子紧挨着大个儿的垃圾桶。”这对室友走在校园里,交换抽着,此番经历变成了一场戴夫秀。他会捕捉并模仿别人走路、说话的神态以及歪头的角度,描绘他们的生活。“不是一板一眼地模仿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取其神韵。我无法想象,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里,有谁会像他那样做,”科斯特洛说,“他模仿别人的速度之快、效果之有趣,令人难以置信。戴夫具有这种钻进别人表皮的能力。”
作家玛丽卡尔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与大卫约会,当时他正从此生为艰难的阶段走出来。经过康复期,他的依然不太稳定——但他是大卫,率而为,将抛诸脑后,是那样,善于猎取信息。“数据进入他的头脑之后,马上会迸出火花来,有趣到令人癫狂,电量极大。他对所处的世界怀抱极大的兴趣与好奇。每过一秒,他都会比我们其余的人多获得数帧画面,他从未停止过。他在一刻不停地吞噬宇宙。”
在那段时间里,大卫开始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他写的文章。当一篇文章寄来之后,编辑们“会在走廊上商定词句”,斯康恩对我说。“或者,如果有人和他聊过文章中的任何一部分,他们都会相互转告。这是这位作家带给他们的兴奋感——他所写的,他所说的。”康恩是哈泼斯杂志的一名编辑和撰稿人,是他把大卫拉入这本杂志的,大卫造访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转了转,他以全屏的视角见识到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大卫。“him in new york city—that wa a how on it own.他对周遭呼啸而过的都备感惊讶,对万事万物都惊奇不已。他比任何人都敏锐,包括你,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大多数时间里,只要与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他不会在意自己待在什么地方。他会对感到惊奇与好奇。如果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观察万物,他怎么能够写出那些文字来呢?而你需要进入他的感官,才能看到更多东西。他能同时调动六个半的感官,这会让你发疯。但是他会与我们分享这一点,这是他善解人意的地方。与他交谈是一次令人愉悦的社交体验,也是一次文学体验。”
一旦你意识到他将带你进入某些有趣的点,他会把整个世界变成华莱士式的样貌——尴尬,令人惊奇,鲜活。完成无尽的玩笑之后,大卫和康恩一起加入了一个小团体:这是一群产品试用者,是一个专门研读文学作品的团体,他曾把手稿寄给这个团体。她在上班的地铁上来回地读。在她的座位旁放着一摞书,是一堆叠放的小说。乘客们会看着这些书,看着她笑。“蔚为壮观,滑稽可笑。人们以为这很滑稽。而我以此为傲,我爱这么做。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很好。”
大卫是乔恩弗兰岑的读者和,他是用这种为常见的方式与后者认识的。他给弗兰岑寄去过一封称赞其处女作的信件,弗兰岑回信,安排两人见面。然而大卫没有赴约。彼时正值那段阴郁时光的中期,哪怕是简单地在历上做出安排也变得颇具挑战。“他精疲力竭,”乔恩回忆道,“他没有出现。那是他这一生中饱受药物折磨的一段时光。”到了90年代中期,弗兰岑找到了一个能轻松预估与大卫见面的方法:“我会抓住机会与大卫见面。”1995年,弗兰岑因为一部大部头作品中写作和阅读的问题,与大卫产生了争执,于是他登上了火车,去康涅狄格州见大卫。“我们在一座停车场见了面,我们一起待了大概三个小时,只是坐在停车场边上。我一直在说:‘这篇东西需要引文,这篇东西需要引文。’”想象一下这两个未来会写出有名作品的作家竟数小时待在熟睡的汽车和水泥隔断物之间对谈,这画面真好看。他们达成的共识——这是大卫提出的——是:书籍存在的目的是与孤独做斗争。
在纽约为书做巡回宣传的过程中,大卫与弗兰岑共处一室。那正好是几近成名之时,费用都还须作家自掏腰包。“我只能说,他过去与我待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在他把饮食进行分类之前——他靠那种从熟食店买的用玻璃纸包装的金黄蛋糕和嚼烟过活。他回到公寓后做的件事是从我的废物回收袋里挑出一罐优选的番茄罐头,然后吃掉。你知道,他会对着罐头吐痰,这一点非常好。他还会认认真真地把罐头洗干净,并把它放回废物回收袋里,这一点也很好。这样一来,他离开后,整间公寓里是弥漫着从罐头里散出的一股淡淡的冬青的味道。”
有一次,弗兰岑曾试着拉大卫参加一场文学聚会。他们一起随众人从前门进入,等到弗兰岑到厨房时,大卫不见了。“我折回去,整个屋子都找遍了,结果发现他为了摆脱我,刻意躲进了浴室,随后迅速掉头,径直回到前门。他回到了我的公寓。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公寓,发现他编撰了让我和我当时的女友都 感到难堪的故事。”
相遇和离别都令人不快。一方面,大卫在对话时能听出弦外之音。大卫曾在一篇有关英语语的散文中对离别做过详尽的展示——一半在文本中,一半散落在脚注里。他去世四年后,我又找出这本书,在电话里读给一个朋友听,以此来展现大卫是多么清醒、有趣。读到一半时,我想起我曾打算不再去烦他,这是多么缺乏热情,这么说倒是与我无关,但是像拍照时吸紧腮帮子、收起下巴一样,令人不自在。“设你我是熟人,”他写道,“我们正在公寓里交谈,随后到了某个时刻,我打算结束对话,并且不打算让你再待在公寓里。这是个非常微妙的社交时刻。我想了所有我可能试着去表达的不同说法:‘哇,时间不早了。’‘我们能否以后再谈?’‘请你现在离开好吗?’‘走吧。’‘离开这里。’‘滚出去。’‘你刚刚不是说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是该踏上沙石路了,我的朋友。’‘你该动身离开了,亲爱的。’或者是那些狡猾的挂电话的伎俩,比如‘好了,我要挂电话了’于我而言,结束对话或者求人离开是那么艰难,有时告别时刻会因为社交的复杂变得如此微妙且令人不快,以至于我不知所措干脆直截了当地打断——‘我不想再聊下去了,不想再让你待在我的公寓里了’——此举显然会显得我非常粗鲁、唐突,或者有些以自我为中心我确实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
在写作时,他会变得犀利且谦虚,对想要精心架构的类型,他有一种建筑师般的战略意识。立志当作家的人,该像运动员或者想要加入梦想的棒球联盟的人那样勤学苦练,积累职业经验。只不过那些数字和棒球场更加私人化:次出书的年纪,次获奖的年纪,次结婚的年纪,次危机来临的年纪,以及有时次、第二次、第三次离婚的年纪。(大卫会笑话我回忆这些东西的。你们可自行体会。)我们相遇时,大卫刚刚出版无尽的玩笑,显得非常自信,因为他知道,他对已不放在心上,他也尽力完成了这份差事。这是一种善意的自信。我一直在想海明威笔下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是在他们坐火车去鲁昂取车之前。菲茨杰拉德那时刚刚写完他优选的小说,海明威说: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随后和我说起有关作家、出版商、经纪人、批评家的事,还谈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所遭受的流言蜚语和经济状况。他愤世嫉俗,言谈风趣,兴致勃勃,又是如此迷人,讨人喜欢,即便你会对那些变得讨人喜欢的人格外留心。他轻蔑地谈起他所写的,但不带挖苦之意,而我知道他这本新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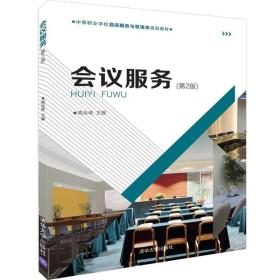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