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器之辨:告诉你文化的真相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18.5 6.6折 ¥ 2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陈远著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1243857
出版时间2008-0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8元
货号4523239
上书时间2023-12-25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内容摘要
第一辑 所读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和许倬云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做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存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以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一位是史学界领军式人物,固守着历史的疆界,内心却渴望冲破这一藩篱。这两种姿态,我想会是将来学术史上最具典型的两种姿态。
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
1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起胡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没有哪个人像胡适这样大名鼎鼎:自1917年与陈独秀一起倡导白话文暴得大名,胡博士就一直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誉也随之,谤也随之。如果按照时间表把世人对于胡适的评价梳理一下,会发现,世人的口风也如同李零先生在《丧家狗》中提及的人们对于《论语》的评价一样,像是“翻烙饼”,一会翻过来,一会调过去。盛名之时,举世咸道:“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字适之)”;遭厄之际,“举国上下共讨之”。胡适本人对此大概是有所预感,所以在生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相很难画”。这样一个人,想让人不议论,都难。
我还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邵建。邵建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篇文章中得以定格的,一篇是《事出刘文典》,另一篇是《勇于不敢》。凭着这两篇文章我把邵建定义为中国当代学者中运用历史学方式将个人主义表达得最清晰的表述者。《事出刘文典》被认为是厘清围绕着胡适和鲁迅发生的种种误解的最好的文字。 《勇于不敢》说的是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这是胡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说句带点感情色彩的话,听多了学界陈义甚高的声音,邵建对于“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考究,我喜欢。但是这种基于底线的叙述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招致“同一战壕”里的人的不满。
现在,邵建和胡适联系在了一起,他写了一本胡适的传记《瞧,这人》,副题是《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
关于胡适的各种传记,是在我的书架中所占比例最重的一类图书之一,所以当我知道邵建开始写胡适传的时候,我多少抱有几分的幸灾乐祸:那么多的胡适研究摆在前面,邵建,你要想推陈出新,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不过,读完之后,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落空了。在胡适研究上,邵建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不是在做关于胡适的学术研究,而是关于胡适的再阐释。此胡适传非学术的胡适传,而是思想的胡适传。
依托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邵建把胡适抽离出来,抽离成一个文化符号,邵建所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符号的言论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文化遗产。在这里,胡适的酒杯里,装满的其实是邵建的块垒。譬如书中第二部分《负笈北美》的第三小节《“民有、民治、民享”》,事出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一次演说,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句话被梁任公视为不可翻译的名句,也深为胡适所折服,不过翻译了两次,都不满意,及至孙中山,这句话才被传神地定格为“民有、民治、民享”,也即“三民主义”的发端。邵建关注的显然不是胡适翻译两次而不满的经历,而是由“民治”所引申出来的“程序正义”和“目的正义”的问题。在同一部分的第七小节《民权政治的“初步”》中,邵建再次谈到了程序正义,不过,这一次他的笔尖一荡,转而又荡到“技术理性”上面去了。翻开邵氏胡适传,此类叙述比比皆是。从文化理念上讲,我与邵建一脉相通,对于这些理念也十分赞同。不过,我也有迷惑,那就是胡适的酒杯,究竟能否装得下邵建的块垒?负笈北美时期的少年胡适,在心灵上到底有几分与现在人过中年的邵建相通?面对“程序正义”、“目的正义”以及“技术理性”这些现代学术术语,留胡适是否会一脸茫然?这大概是我的苛求了,因为邵建的块垒,不是他个人的块垒,而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所面对的块垒,邵建的这番话,也不是说给胡适听的,而是说给我们这些活在当下这个世界的人们听的。这块垒,浇得痛快!
2
忽然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人间鲁迅》,那时我年纪尚小,得知这本引得一时纸贵的书,已经是后来的事情。后来读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林贤治的笔法,笔尖随鲁迅的是非荡来荡去,“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若说邵建此书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邵建大概是不同意的。确实,书中对于胡适的指摘并不少,例子不用多举,有心人阅读时很容易就会发现。
不过,读完此书,我还是有此感觉。且听我说上一二。
书中对于胡适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其二是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而有自己的判断。这两种情况又可以做一番分析,每当邵建回到历史的情境时,其是非标准是按照胡适的是非来划分的,比如书中第三部分第十小节《枕上炸弹诗》中,提及胡适的“炸弹诗”以及革命诗,邵建虽然认为“这是胡适一生中的稀奇”,但同时又说:“也是30岁的他未泯的血性”。这样饱含情感的文字,似曾相识,没错,就是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历史多么意味深长和摇曳多姿,胡适和鲁迅这一对“冤家”,在多半个世纪之后,分别有了这样的一本传记。
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者,也为数不少,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十小节《世界公民》中,关于胡适对于世界公民的认识的反复,邵建论道:“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胡适自己认为不对的,邵建却认为是对的。考察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错,只不过,时空不同了而已。在90年前,胡适有那样的认识,已经难得,他显然没有置身于“国家主义”这一类的语境当中。放眼今天,邵建所言当然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品评历史人物,最好还是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好,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更认同胡适自己的说法。
说到胡适的是非,顺便说说胡适的选择。对于胡适,我曾经说过一段这样大不敬的话:“就学术水平来讲,胡适在其同时代人当中是极其一般的。胡适的伟大,在于其人,在于他在激变时代每每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在我看来,胡适早年的暴得大名,不过是因缘际会,而在其成就大名之后的中年之际,每一次的选择对于我们如今的警示意义更大。可惜的是,我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中少有看到对于胡适的选择用浓墨重笔的,即使有,也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不疼不痒地说上几句。
媒体评论
第一辑 所读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和许倬云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做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存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以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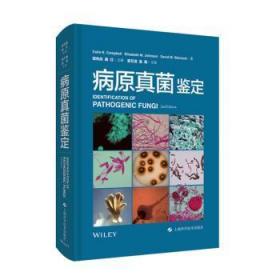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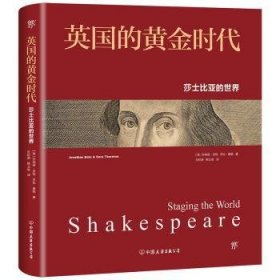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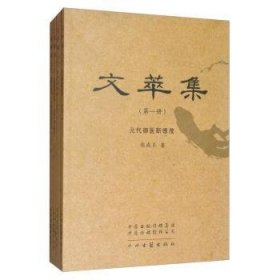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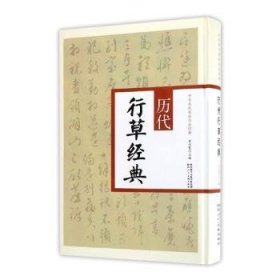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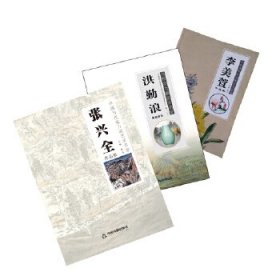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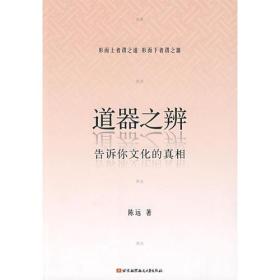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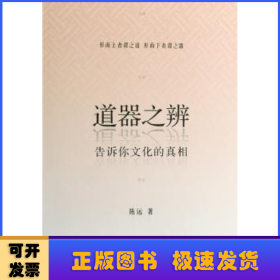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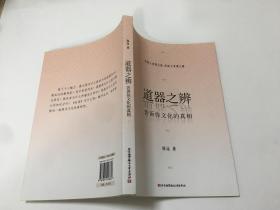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