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仿佛
正版全新
¥ 31.14 7.4折 ¥ 42 全新
库存7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孙甘露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5915591
出版时间2022-12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42元
货号4378484
上书时间2024-06-3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0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书 名】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仿佛
【书 号】 9787555915591
【出 版 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 者】 孙甘露
【出版日期】 2024-06-01
【开 本】 32开
【定 价】 42.00元
【编辑推荐】
★著名作家孙甘露小说代表作四篇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精彩点评
★作家生活照片多帧
★精致小开本,好看好带
【内容简介】
《仿佛》是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收录了孙甘露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及《仿佛》。
《访问梦境》发表于1986年,是孙甘露的成名作、开启中国先锋派的重要小说作品之一,叙述了一个人进入一座梦幻般的城市寻找一个叫“剪纸院落”的地方。小说以诗化的语言写成,含有大量抽象的意象,探讨了人们内心诗意的层面。
《请女人猜谜》发表于1988年第6期《收获》,讲述了“我”车祸入院后为打发护士,谎称自己写了一篇《眺望时间消逝》的小说,为了圆谎,“我”开始构思写作,并进入小说文本之中。该作品也被视为先锋派小说的重要作品。
《信使之函》是作者的一次“梦游”,创造了一个远离世俗且否定生活世界常规秩序的语言幻想世界。该小说使其成为典型的“先锋派”作家。
《仿佛》中有一部可以从里外同时阅读的小说《米酒之乡》,男人从书页中潜入米酒之乡开启神秘之旅,而女人则守着顶楼房间的书籍《米酒之乡》等待男人归来。*终,男人以否定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精神的回归,以此拷问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孙甘露的作品广受关注,并有多种译本,其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化的故事,其个性化的叙事拓展了汉语的表达空间。
【目录】
请女人猜谜
仿佛
访问梦境
信使之函
优雅的语言事件
——作为事件哲学的小说艺术
陈晓明
【前言】
优雅的语言事件
——作为事件哲学的小说艺术
陈晓明
这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有机会重读孙甘露早期的小说,仿佛重回三十多年前的文学语境中。历经世事变化,似乎还持存着当年文学的余韵。
孙甘露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优雅。不要认为这种优雅很容易做到。我觉得要达成这种风格很有困难,汉语小说缺乏这种优雅,特别是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在这种美学风格上,在这种艺术品质上,是有所欠缺的。格非、苏童和孙甘露他们小说中的那种优雅,让人们深感意外,尤其是格非和孙甘露,在优雅这一点上特别鲜明。当然他们二者的风格并不一样,后来更有非常鲜明的变化,但是当年,孙甘露在优雅这一路上确实是做到了极致。
怎么去理解优雅?其实中国古典文学是有一种优雅的,特别是唐诗宋词;当然,人们会说这是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经典。《红楼梦》有一种优雅,并非说像《金瓶梅》的那种粗野就不好,《金瓶梅》是另一种路数。我这里强调优雅并不是以此来排斥其他,我觉得另一类小说的那种磅礴大气、那种粗蛮朴拙同样是一种价值,文学需要的是多样化。孙甘露的小说有非常独到的地方,因中国小说的优雅风格非常之少,因此有其非常独特的存在意义。
1987年,孙甘露在《人民文学》第1、2期合刊发表《我是少年酒坛子》,当时这本刊物非常著名,但孙甘露这篇小说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当时来看,这种写法离经叛道(那一组小说都是现代派,都属于离经叛道),只能称为一种“亚小说”,它是散文、诗、哲学、寓言等等的混合物,这标志着后来孙甘露一贯的风格。1986年,孙甘露在《上海文学》发表了《访问梦境》,这是一篇把梦境与现实混为一谈的小说,想象奇异怪诞,结构流畅自如,语言瑰丽奇崛。孙甘露是*早用“梦境”来介入小说的,或者说把梦境挪进小说里,在这点上他与众不同。小说当然大量涉及梦境,通常里面的人物会做梦,电影里面也会,但是孙甘露的小说是一种仿梦的结构、一种仿梦的叙述。他能做到非常流畅,把一种语言和梦境结合在一起。这就不容易。
《访问梦境》的开头所引的题词来自所谓卡塔菲卢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位作家或诗人、哲人,这个名字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不死的人》中出现。博氏这篇小说开篇写道:“1929年6月初,在伦敦,伊兹密尔的古董收藏家约瑟夫·卡塔菲卢斯,把一部蒲柏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年出版)赠送给卢辛热公主。公主接受了,在赠书的时候,跟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一个瘦弱而脸带土色的人,灰眼睛,灰胡子,面貌特别模糊不清。他毫不自知地交替使用好几种语言。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从法语变成英语,又从英语变成谜一样的萨洛尼加西班牙语和澳门葡萄牙语的混合语。”《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外国文艺》编辑部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显然,《访问梦境》在某种意义也可以看成叙述回忆,小说的普遍经验当然都可以说是叙述回忆,但孙甘露沿着回忆的边缘一点一点用语言渗透进去。小说开篇就写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似乎是一个假设,是一个虚拟。小说接着写了“我趴在窗前”,“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孙甘露的叙述带入了一种情境,这种情境通常会把它说成是一种诗性的。但是我宁可把它表述为带有某种优雅,就是一种气氛,仿佛一种手势,一种姿势,人物的一举一动,有一种作派(绅士派?),或者说法式浪漫主义的那样一种情调,那种感觉,那种姿势。显然他还有这样一种回忆,以及他伏在窗前,看着外面,这是他的思绪或是他的想象,所以他把回忆、梦境、想象这些都混为一谈。他的叙述显然不是原本的世界,小说写道“这些目光游移的人骑马来到海边”,这里制造的一种氛围和一种情境,是我们的日常经验所不能达到的。费兹杰拉德说,小说要去写撕心裂肺的生活,这是一种说法。纳博科夫说,小说,它除了闪闪发光的生活,什么都不是。孙甘露的小说并没有撕心裂肺,甚至也不是闪闪发光的,但是非常独特,有韵味。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低音部,或者说是低调性的,他的人物都是逃避性质的,落落寡合,有某种孤独感,有某种拒世的态度,他们仿佛和现存世界隔得非常遥远,都像是梦中的人物。语言追踪着他们,缓慢行进,多年后,孙甘露说起“比缓慢更缓慢”的感觉,那是他的小说语言的艺术。他似乎总是在回忆,在辨认,在接近。
孙甘露的想象、回忆、梦境被混在一起,描写的都是些梦中的事物、梦中的情景。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英文名为Inception,其原意表示某个事物或概念的起源、开始或形成的初期阶段。诺兰的原意大概是指人的意识在*初的活动状态,即对一个事物规划意图还未完全成形的*初状态,这时被其他意识侵入进去,或者说其他意识侵入另一个意识在构想、回忆或造梦时刻的状态。而孙甘露小说题名为《访问梦境》,大约也是处于这个状态。孙甘露在1986年就试图接近人的意识的那种状态,他是用文字这个*没有图像能力的表意符号试图去激发人的想象。感觉诺兰的《盗梦空间》可以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对照来观看阅读,会非常有意思。孙甘露的小说毕竟早了24年,这是很了不起的。
小说写道:“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种透视的方式向深处延伸。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孙甘露又把书写引到书里面,书在孙甘露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里书就是一个梦境,读书就是进入一个梦境,读书就是访问梦境,或者说读小说——更准确地说读孙甘露的小说,就是访问梦境。小说接下去写道:“在页与页之间,或者说在两种建筑之间……”这里的想象力过渡非常自然,尽管内含的跳跃那么大,书页,还有页与页之间,他马上把它们变换、再变换。又像音乐,据说孙甘露会弹钢琴,对古典音乐非常熟悉,他显然有那种对位的结构意识,所以他用建筑调换了书页。然后他说:我读到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他是这么来表达的,可以看到他那阅读梦一般的内心,以此守候他的奇异的苏醒。孙甘露的小说叙述非常富有诗意,这一切都因为这种诗意的表述使其能够成立,它越过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越过了逻辑的障碍,依赖诗性的语言修辞,诗性的转换。支撑它的是一种想象力。
显然很难去概括《访问梦境》的故事,孙甘露其他小说也都是这样,像《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仿佛》都是这样。他都是以这种语言、这种叙述、这种诗性来推动小说。小说里总是有某一本书,他写道:“我手中的这本记载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小说,是一本连环画。书名叫作《审慎入门》……它由十三位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伟人的事迹片段所组成。”孙甘露的小说中随时会出现这么一种异想天开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诞生于一夜之间,所以这种纯粹虚构的故事里经常也会涉及一些日常性。他有时候又非常突然地把现实的经验拉扯进去,小说往前推移,几乎突然出现“我丝毫也不怀疑我的妹妹有什么不清白的可为我们家族所指责之处。她交上了你这么个丑陋的小伙子”。这种现实的态度中,人物又保持一种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或许很轻微,或许很严重,他来自对妹妹择偶事件的不满,又有某种亲情以及对这种亲情的暧昧,这个妹妹可以说泛指女性。颇为奇怪的是,读孙甘露的小说总是包含有一种对女人的怜爱。他并没有大量描写那些女性,《请女人猜谜》有一些关于女性的描写,但也是很抽象的,写得很有诗意。《请女人猜谜》里面写到我的女友丰收神,很难想象这样的女人能被现实化。《访问梦境》里不只是出现妹妹,还有姐姐。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想象,这种现实经验的介入非常突然,依然沉醉于一种诗意的想象,始终是梦境似的一种呓语。小说叙述仿佛是在梦中挣扎,然后想清醒过来进入现实。他的叙述也一直想在这样一种诗意的语言里突围出来,在这种梦境般的语言中挣扎出来,想让它现实化,想让它突然间闪现出一种现实的真实感,他用“妹妹”或“姐姐”去唤起现实感和确实性。他在梦境的不确定性中寻找一种可能性。
作为小说,《信使之函》(1987)显得更加激进,通篇用几十个“信是……”的句式作为叙述提纲,也可以看成段落起承转合的引导句式。这篇被称为“小说”的东西,既没有明确的人物,也没有时间、地点,更谈不上故事,它把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与东方智者的沉思默想相结合,把一些日常行为与超越性生存的形而上的阐发混为一体,把修改语言规则的行径改变为神秘莫测的优雅理趣。如果把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称为小说的话,那么这几乎是迄今为止当代汉语文学中*放肆的一次小说写作。彼时,孙甘露的作品并不算多,却让文坛大惊失色,无数批评家理屈词穷,面对他的写作无从下手。《信使之函》作为当代第*篇极端的小说,表明当代小说没有任何规范不可逾越。
《信使之函》把信看成内心的一次“例行独白”,小说里下了一些类似的定义:信是一次悖理的复活,也是夫妇间对等守护的秘密,信是信使的一次并不存在的任意放纵,等等,这些想法都奇特奇妙而有才华。据说孙甘露早年当过邮递员,信使即邮递员的雅称。大约是在“文革”期间或“文革”后几年,孙甘露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在城市街道游走,那也是很幸福很逍遥的。邮递员的经验激发了孙甘露很多的想象,可以想象他拿着那些信件又是如何体味着写信人的那种心境和读信人的那种喜悦或悲痛、希望或失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所承载的内涵有多重。《信使之函》把信看成一种耳语,信使是穿行在耳语城的。信使送这些信件,仿佛听到了信在言语,用一种耳语在说话。从经验的角度来说,看信会读出声来,有时候读出声来仿佛对方在与你说话,又仿佛在耳边喃喃细语。孙甘露引导我们一步步进入耳语城里,那里面有着梦一般的故事,也如同访问梦境。孙甘露的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在访问梦境。孙甘露总是涉猎这些非常另类奇异的想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让我们惊异于汉语小说怎么能够抵达这样的地方。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寻求艺术变革的年代,一批年轻的作家更加大胆地越过边界。《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先生敢于把它标榜为中篇小说,这也是非常大胆的命名,也可以说是非常杰出和有变革性的,所以先锋小说的革命也应该记上这些编辑的作为。程永新和孙甘露合谋,把《信使之函》定义为中篇小说,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这是当代小说的革命。经历过这一道坎,当代中国小说便无所不能了。小说的世界突然间被拓展得无边无际了,甚至可以说小说的定义被完全改写了,小说就是小说本身,任何书写都有可能成为小说。
《请女人猜谜》同样非常令人意外,男主打开门,门外的女人自我介绍是因为读了男主写的小说来找他的,男主看不清在暗中的她的脸,然后问她读过哪些小说,女人说全部,男主问读过《眺望时间消逝》吗,女人在思考是不是在诈她,停顿了好一阵才说没有。男主说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其实我还没写这本书。这些场景和对话,都有一种陌生性,又有一种奇怪的悄悄潜伏的欲望激情,被延搁的情欲和可能要发生的无限可能的故事被隐瞒了,只留下那种暧昧和优雅。这篇称为《请女人猜谜》的小说,文中男主又声称在写作一篇《眺望时间消逝》的小说,也可能是一部书,就是说有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能是一篇短篇小说。小说里写到医院。孙甘露的小说场景经常固定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时空里,要么是一个封闭阴暗的小屋子里,他独居的小房间;要么是医院。医院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从福柯的观点来看,医院也是一个被监禁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对你有无比的权威,可以宣告你的一切。病人其实是失去了自主性的,他的肉体已经交付出去了,交付给医生和护士。在医院里,身体的主权已经让渡给医生和护士,只剩下灵魂在轻盈地飞翔。很有意思的是,人们都把医生和护士想象成白衣天使,因为病人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生命主权的全能支配,只有寄望于医生和护士来拯救——病人只能相信他们是行善的,而且他们确实有一种对善的承诺。但是医院里也经常发生一些很恐怖的事情,中国也有很多医患之争。但在孙甘露的笔下,在那里,特别是男性病人愿意把女性护士想象得生命饱满而美妙,病人几乎是没有保留地把身体交付给他们。面对女医生和女护士,男人会有羞涩感,心里隐含着对她们温情脉脉的一种想象,一种非常温情的依恋,孙甘露乐于去捕捉这种心理和情绪。他的讲述中甚至会把她们想象成某种爱人。当然,在孙甘露的笔下,这些医生护士都是怪怪的,所以这所医院让人疑心是一所精神病医院。小说写到的士是一个男医生,他原来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偷吃实验室里的蛇而遭指控。孙甘露单写了这么一个细节,士是怎么偷吃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么一句话却使小说露出狰狞的面目。原来在梦的轻盈中,还有狰狞的一面。
蛇是使人感到害怕的动物,它属于阴性的恐怖的动物。在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中,你疑心医生逐步放弃医院/医学转向巫术,在孙甘露的笔下,医学和巫术非常接近。孙甘露的小说,可以说有巴洛克的风格,近乎一种巫语,也像巫术一样。只是孙甘露把它写得很优雅,是优雅的巫术。你可以看到这种优雅的巫术又是优雅的诗意,这种书写十分神奇,或者说是离奇。小说叙述《眺望时间消逝》又是一部戏剧,本来说是一部小说,现在又变成戏剧,叙述者是这么设想的:“人们总是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站一会儿,他们总是隔着窗子对话,他们的嗓音喑哑并且语焉不详,似乎在等待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战胜某种闲适的心态。他们在院子的阴影中穿梭往返是为了利用这一片刻时光搜寻自己的影子……”孙甘露小说中的人物都跟影子一样,他们在墙上、在空间里、在地上晃动,当然,他们也许是在梦境里。在回忆性的叙述中,他们总是显得那么不真实,但是又让你感觉到一种触感,所以孙甘露的小说的描写能力也是很强的。孙甘露有时候会写到让你感到痛楚的那种经验,他小说里面的人物会改变叙述者。然后他又会把里面的人物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主导的牵引小说的叙述视点的人物。《请女人猜谜》写到的士本来是一个很远距离地去描写的人物,突然间,士变成一个主角。他引导了一种小说的视点,他“看见骑着脚踏车的邮差将一封信投进花园门口的信箱,他顺着思路怜悯起这个信差来。他没去设想一个噩耗正被塞进了信箱,塞进了行将烟消云散的好运气”。士随后主导了小说,他的经验引导阅读者的目光。小说接着写到一些场景,既美丽又令人恐惧。他写到当他经过一个巨大的水泥花坛时,一道刺目的阳光令他晕眩了片刻,一位丰满而轻佻的女护士推着一具尸体,笑盈盈地打他身旁经过,士忽然产生了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中自如飘移的感觉。然后他淡淡一笑,他认识到自古以来他就绕着花坛行走,他从记事起就在这里读书。这样一种叙述,看上去很美,里面却夹杂着恐惧。在饱满的生命之侧就是一具死尸,生与死咫尺之隔。这样一种情境,仿佛是梦境,仿佛是现实的想象,仿佛是曾经事物的一种夸张和变形。
孙甘露的小说总是描写一些非常奇异的经验,用他非常奇异的语言,非常规的句式,让我们去经验一种生活的不可能性,给我们呈现一种不可能的世界,让它变成语言的事件。孙甘露小说的根本意义在于制造了语言的事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高事件,以此推论,可以说,语言是小说存在的*高事件。在80年代,孙甘露的小说虽然不多,但是它具有事件性,他的一次一次“访问梦境”的书写,酿就了类似行为艺术的小说事件。若把80年代先锋小说看成一次事件,或看成一次行为艺术,它在中国现代主义的进程当中是一次悄无声息的语言突破,又是一次强行的穿越,如风穿过墙一般,风推倒了墙,推倒了那些禁忌、那些禁锢和那些樊篱,使当代小说进入无边的旷野,也使先锋小说自身像一阵风吹过无边的旷野。当然它们并非无影无踪,它们吹去了种子,像王德威所说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它们长出了麦子,长成一片又一片的稻田。当然它们落下的种子也有成为树的,它们长成了一片森林。这就是先锋小说,今天中国小说在语言这个层面或多或少包含当年先锋小说的经验。这是孙甘露的这些作为语言事件的小说存在的一种意义,这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阅读它们、怀念那样的时代、向那种事件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2024年3月27日
改定于北京万柳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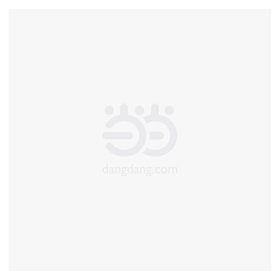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