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行小字中央
正版全新
¥ 26.12 4.7折 ¥ 55 全新
库存4件
上海浦东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江弱水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99988
出版时间2020-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纯质纸
页数252页
定价55元
货号957485
上书时间2023-10-07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0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书 名】 十三行小字中央
【书 号】 9787308199988
【出 版 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 者】 江弱水
【出版日期】 2020-04-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页 码】 252
【定 价】 55.00元
【内容简介】
从一件不惹眼的拍卖品,引出中国古代一段令人热眼的风怀诗案:十三行小字中央,竟隐藏着如此细微而又惊心动魄的情感密码!从曹植到王羲之,再到朱彝尊,从诗歌到书法,再到历史,作者用细腻而体贴的文笔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一种情爱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目录】
目录
独孤求败的罗隐
《水浒》里的人情
《聊斋》小样儿
末世的伦理学:从《蜀碧》到《黑洞》
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
附逆者的逆耳忠言
——读《花随人圣庵摭忆》
文心提气骨,花光艳红绮:潘天寿与倪元璐诗学因缘
为山作传,为水作诔
——读《两宋萧山渔浦考》
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杜甫为什么说马的瞳孔是方的?
栀子花茉莉花
善歌如贯珠赋
文学研究中的诗意
顾随先生的讲堂
一惊一乍又一精一诈:论小学语文
下不为例:也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学、史的大手笔
——论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从麻雀山到樱草丘:关于赫尔岑的随想
波德莱尔与永井荷风
纳博科夫的细节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
——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大历史与小时代
——读奥利维埃•罗兰《纸老虎》
后记
【文摘】
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节选)
(一)
2008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出示了一件编号为1284的藏品,“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底价三万五千人民币。*后成交了没有,成交价多少,我没去查,因为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件拍卖品本身。
所谓“十三行”,是晋王献之所书曹植《洛神赋》,残帖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这十三行小字历代被认为是“小楷极则”,在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它有两个传本,晋麻笺本和唐硬黄纸本。唐硬黄纸本上有柳公权的两行题跋,被认为是他临写的本子。晋麻笺本北宋时入内府,徽宗曾刻石,拓赐近臣。靖康之后,这麻笺本及其刻石的下落,众说纷纭。龚自珍《重摹宋刻洛神赋九行跋尾》说:
天下知有《洛神赋》,言《洛神》称十三行,言十三行称两派:一柳派,一玉版派。柳派以唐荆川藏玄晏斋刻者第*,文氏本次之,玉版则雍正中浚西湖得之,入内府,拓本遍杭州,杭人言有篙痕者善,鉴赏家言尽于此矣。靖康后不百载,金亡,元室不崇图书,无秘府。赵子昂仕元,知九行在北方,辗转迹北人获之,阅丧乱,卒藏宗匠之庭,岂非神物能自呵护,大照耀一世欤?
内文试读
这段话,说《洛神赋》十三行分两派是不错的,其余的就不大靠得住了。从北方辗转找到九行的,都说是南宋权臣贾似道,而非赵孟頫。“玉版”又称“碧玉版”,为约一尺见方的水苍色河南石,现藏首都博物馆,其失而复得,不是清雍正年间疏浚西湖时从水里捞上来的,而是明万历年间在西湖葛岭上贾似道的半闲堂旧址从地下挖出来的。但这“碧玉版“究竟是贾似道所刻呢,还是宋徽宗原刻?麻笺本真迹已经零落到只剩十三行了,怎么还继续支离成九行和四行?而且,又有一说是宋高宗得到九行,米友仁题跋为真迹。但熊克的《中兴小记》,记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九月丁巳,“上曰……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这一条资料似乎更可信,因为熊克做过孝宗的起居郎,精熟高宗一朝典故。然而麻笺不是竹简,这十三行却又生生给分成九行、六行、四行不等,实在匪夷所思。更何况“碧玉版”之外,还弄出了一个估计是翻刻的“白玉版”来,越发添乱了。
总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地位既高,身世又奇,其拓本自然珍秘十分。杨守敬曾经从天津古玩肆上购得一幅,视若拱璧,却被诗人陈三立看中,跪请相让,杨痛惜不已,自比李后主的“垂泪对宫娥”。龚自珍一想到自家的藏本二百年间四易其主,便格外宝重,打算劳烦篆刻家于铿也来刻那么一块石:“抱孤本,担愿力。乞于铿,伐乐石。祈此石,寿千亿。见予石,勿妨毁。隔麻笺,一重尔。”
我们来看这件盖有“竹垞审定”朱文印的“南宋拓本”十三行拍卖品。其拖尾的跋文第*则,便是钱大昕女婿瞿中溶所录的竹垞跋语:
此玉版十三行有十二意外巧妙。袁仲长云幽深无际,古雅有余。其楷法纯是隶体,后人妍媚纤秀,去之日远矣。此本结构端严,精彩完*,定为南宋初拓手无疑矣。余得自济宁王氏,重付装池,因跋数语于后。金风亭长朱彝尊。
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十岁起自号竹垞,七十岁后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叟,诗词均为大家,经学史学都有很高成就,又性嗜金石书画。十三行拓本既然如此难得,竹垞拂拭吹嘘一番,十分正常。
问题是,这《洛神赋》十三行事实上却有二十一行,上面也没有龚自珍说的“篙痕”(其实应该是原迹所在麻笺上的粗麻筋)。这是什么回事呢?要给个正常的解释倒是不难。据道咸之际的收藏家蒋光煦说:“十三行帖,潢者每多割裂,求整拓者已不多见。”也就是说,装潢者往往将拓片裁剪一番后重新拼接装裱,十三行就这样变成了二十一行。果然,目前所见的十三行拓本,既有整拓的,也有割裂成十八行的(无锡博物馆藏),或者割裂成二十六行的(上海博物馆藏)。这回也不过剪裱成二十一行而已。但既然是竹垞“重付装池”,就不会是装潢者的擅作主张,而是主人的想法吧。可是竹垞会这么想吗?如果他这么想,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原因我们后面慢慢会谈到。
细看这幅小字《洛神赋》,肥润多肉,与“碧玉版”十三行精拓对照,远逊其秀挺劲拔,明显感觉经过了翻刻,隔麻笺何止一重。难道竹垞没有别的拓本过眼,所以精鉴不了?更何况他题跋中转引元人袁仲长的八个字评语“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竟是袭用唐人张怀瓘《书断》里评钟繇的话:“(元常)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再说,竹垞既然题跋于后,为何不见他的亲笔,却要百年后由别人转录?转录又录自何处?凡此种种,真是疑窦丛生。
(二)
对于朱彝尊来说,王献之《洛神赋》小字十三行具有极为特殊的情感价值,其中分明有他*深沉的一段恋情的密码,可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这故事说来话长,我还是从曹植的《洛神赋》说起。子建此赋写于黄初三年(222),他朝罢京师洛阳回封地鄄城,途中渡洛水,见洛水之神宓妃,于是两情相悦,却终因人神道殊而永绝。作者虚构了一场人神之恋,所恋的对象托为洛神,但自从初唐李善注《文选》以后,大家都认为其实是写甄氏,即曹丕的妃子,也就是曹植的嫂子,故《洛神赋》又名《感甄赋》。《文选》李善注引《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无论后世有多少学者为这场不伦之恋辩诬,说曹植如何不可能爱上自己的嫂子,诗人们却都当了真,宁愿相信这个凄美的传说。故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云“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李商隐《无题》云“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郭沫若《论曹植》一文也拿它当真,认为魏晋时代的新人物对于男女关系看得不那么严重,而子建爱慕大自己十岁的美丽嫂子不会是无中生有——他说这话倒是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再说,在《洛神赋》中,这是一场发乎情止乎礼、只开花不结果的爱情。王献之所书《洛神赋》残存的十三行,正是一篇之关节: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当子建表达了爱慕,宓妃也做出应答之后,子建却疑惧起来,“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这两句话,可以高度概括两汉魏晋一个系列诗赋的主题,不过我们且留待下回分解。
与曹植与甄氏的叔嫂恋性质相似,朱彝尊也有一段惊世骇俗而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便是与自己的妻妹。此即有清一代著名的“风怀诗案”。
浙江秀水(嘉兴)朱氏累世为诗礼传家的望族。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万历十一年与汤显祖同科进士且擢为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竹垞父辈已家道中落。竹垞自幼被过继给伯父,十七岁时入赘归安(今属湖州)教谕冯镇鼎家,妻为冯家长女,名福贞,字海媛,小竹垞两岁;三妹冯寿贞,字山嫦,小竹垞六岁。此时正值乙酉之变(1645),南明倾覆,江南兵连祸结,竹垞经常与妻族合家四处避难,所以与姨妹迹密情亲。寿贞渐长,慧而有色,安居时常得竹垞教习诗书,两人于是暗生情愫。寿贞十九岁时,嫁与吴中一土豪人家,夫婿伧俗,不免抑郁。竹垞与她互通款曲,至成幽媾,应在顺治十五年(1658)竹垞家居而寿贞归宁时。但竹垞贫窭如旧,生计无非坐馆入幕,所以近客山阴、永嘉,远游岭南、山西,两人离多而会少。康熙六年(1667),三十三岁的冯寿贞病逝,待竹垞自北地归来,见到的只是坟头的宿草。
这有悖于礼教伦常的爱情,本不可告人,但朱彝尊不仅在冯寿贞去世当年就情不可遏地写成一卷《静志居琴趣》,以一连八十三首词细叙两人情史之始末与曲折,两年后又惨淡经营了《风怀二百韵》这一史上*长的五言排律。这不免让卫道之士戟指,冬烘先生痛心。故竹垞晚年手订《曝书亭集》时,就有人劝其将《风怀》诗删去,如此才可望以三百卷《经义考》配享文庙。竹垞“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后决然说:宁可不食孔庙两庑冷猪肉,也不删此诗。好一个不管不顾,敢作敢当!
……
(五)
朱彝尊与其姨妹的这段恋情,世人或艳称其风流韵事,或痛砭为人格污点,皆属皮相。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庶几能够反映他们二人的关系之实质,能够说明这位情人与这段情事何以对竹垞如此重要。想当初他孤寒一身,入赘冯家,仰事俯畜,一无所能,且不习举子业,功名已然无分,除了饱读万卷,将自己读成一个高度近视眼。姨妹不嫌不弃,无惧无悔,而以身相许,非唯情深似海,亦且恩重如山。当她死后,竹垞用了二百韵长诗,上百阙小词,将两人二十年间的情事做了浓墨重彩的全记录,“盖酬知己之深,不禁长言之也”,其风怀固然可慕,而风义尤为可感。冒广生《风怀诗案》说得好:
书生受恩,粉身图报,至报无可报之日,乃思托之文字,以志吾过,且传其人。虽堕马腹中入泥犁地狱,方且不顾,何暇顾悠悠之口耶。
值得欣慰的是,朱彝尊死后大概并没有入泥犁地狱,反倒是侧身进了文庙,至少我看见他进去过一次。数年前在台湾宜兰,我谒拜当地的孔庙,大成殿左侧东庑供奉着儒门先贤的牌位,从董仲舒、郑康成起凡百十数,就中我居然看到了朱彝尊的名字,当即替他高兴了一回。不过转念一想,如今都什么时代了,配享文庙算哪门子了不得的事呢?何况冷猪肉也早就没的吃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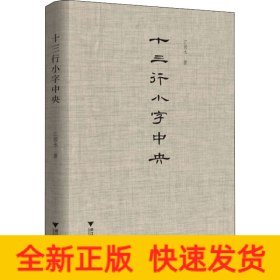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