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梦魇(域外故事会神秘小说系列)
全新正版 急速发货
¥ 12.8 3.7折 ¥ 35 全新
库存9件
作者[美]安布罗斯·比尔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79992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29378492
上书时间2024-12-16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名家导读
爱情:名词,短暂的疯狂,结婚可愈。
漂亮:名词,女人用来吸引情人、要挟丈夫的威力。
礼貌:名词,可以接受的虚伪。
祝贺:名词,文明的妒忌。
魔鬼:名词,表现内心恐惧的可见的外在表象。
叉子:名词,主要用于把死去的动物送入嘴中的工具。
玩世不恭者:名词,视觉有问题的摸黑者,往往实然地而不是应然地看事情。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1842-1914)是美国著名记者和恐怖、灵异小说家。他的《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被列入“100部美国文学名著”,他的《猫头鹰桥上的恐怖故事》(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被看作“美国文学中列入选集次数多的、著名的故事”,他的《士兵和百姓的故事》(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被认为是1900年前出版的100本有影响力的书之一。有人认为,他的恐怖小说可以比肩埃德加·艾伦·坡和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他描写战争的故事对斯蒂芬·克莱恩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闻名的《魔鬼词典》的初版为《愤世嫉俗者的词典》(The Cynic’s Word Book)。上文的七句名言皆出自这本奇书,充满哲理,但又玩世不恭。这次出版的故事集,包含了《猫头鹰桥上的恐怖故事》等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842年6月24日,安布罗斯·比尔斯出生在俄亥俄州梅格斯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几岁时他随全家搬迁至北印第安纳,一家十余口人依靠在小农场耕种为生。因为穷,他只上了一年中学,但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从小受到了文学熏陶。南北战争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联邦军队,在威廉·哈森将军麾下当地形测量军官。枪林弹雨的战场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旧金山,并依靠自学当上了《新闻通讯》(News Letter)的编辑。从此,他开始了编辑兼作家的忙碌生涯。1872年,他和一个有钱矿主的女儿结了婚。婚后同她一道去英格兰,先后在几家报刊任职。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三本作品集。1875年,他回到美国,出任《旧金山淘金者》(San Francisco Argonaut)副编辑,之后又加盟《旧金山观察者》(San Francisco Examiner),任专栏作家。自1888年起,他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与妻子分居,接着大儿子情场受挫而自杀,小儿子死于酗酒和疾病。他逐渐变得悲观,对人生陷于失望。他的大部分与死亡有关的恐怖小说都是在这之后创作的。1913年,比尔斯已经厌恶美国式的文明,他决定退休。于同年10月,他购置了一套马车,并驱车前往饱经战争创伤的墨西哥心脏,去寻找“真、善、美”。但没有人知道他后的下落如何。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后的结局更是文学史上的解不开的谜。多部小说将比尔斯作为主人公来描写,还有电影将他的生平搬上银幕。读他的恐怖小说,让人心惊肉跳;了解他的生平,看到的都是冒险和传奇。
从1866年进入《新闻通讯》到1914年神秘失踪,安布罗斯·比尔斯写的作品非常可观,但流传至今并且为人们熟悉的主要为《军人和百姓的故事》和《这些事可能吗?》(Can Such Things Be?)这两本书。这两本书的精华是十多篇超自然恐怖小说。这些故事重要的主题之一便是复仇,描述的是死人变成幽灵、鬼魂来对曾经造成伤害或死亡的人复仇、索命。《复仇冤魂》、《闹鬼的山谷》、《鬼屋之夜》等作品都描述了被谋杀者向刽子手复仇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鬼屋之夜》的主角是一个冤死的中国移民的鬼魂。故事的描写非常形象生动,让人毛骨悚然。以下就是一段精彩的描绘:“地板中央方孔里冒出了那个已经死去的中国人的头颅。他的眼窝干瘪,一双玻璃眼骨碌碌地盯着那条摇晃的辫子,脸上露出极度渴望的表情。比森先生惊恐地叫了一声,
再次伸手捂住脸。房间里充满了大烟味。那鬼魅只披了一件蓝色丝面夹袄,夹袄铺着一层厚厚的霉。如同一个慢慢推起的弹簧,它站了起来,待到两膝齐地,像跳跃的火苗似的猛然上冲。那鬼魅双手抓住辫子,挺起身,用黄得可怕的牙齿咬住辫梢,可怕地来回晃动着。接着它用力解下横梁上原属自己的东西,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个场景非常惊悚,让读者心惊肉跳。
恐怖故事的场景往往为鬼屋,如古堡、教堂、旧屋等,描写的是可怕的内部空间。上文提到的《鬼屋之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鬼魅共舞》与《幽灵店主》等也把鬼屋描写得活灵活现。所谓的鬼屋是指废弃的房子,通常经历过谋杀或者其他类似的恐怖事件,并且经常闹鬼。明知闹鬼,人们却还要有意或者无意地去靠近或进入这闹鬼的屋子,结果导致悲剧再次发生。这种内部空间往往机关重重、幽暗可怕,让人感到压抑,逃无可逃,甚是恐惧。相比之下,外在空间一般没有那么可怕,并非恐怖故事的。但有些外在空间,如峡谷、荒野、森林等,也可以作为恐怖小说的场景。比尔斯的《闹鬼的山谷》与《林中活尸》等把外在空间也描绘得让人不寒而栗。
阅读比尔斯的《魔鬼词典》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者。一个敢于怀疑一切的人真的会相信鬼魅吗?分析一下他的名篇《与鬼魅共舞》,应该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叫贾里特的人,长着黑黑的皮肤,嗜赌如命。他和别人打赌的内容是:把自己和一具尸体一起锁在一栋废弃宅子的黑屋子里,不许用被单罩布之类蒙住眼睛,看看是否能够坚持一个晚上,并且不会发疯。从他踏进房间一直到后,他都在经历着非常人所能想象的煎熬和恐惧。我们读一读下面的描述,可以体会到作者的高明的笔法:“与此同时,房间的大门倏地被推开。一个人走了进来,一步一步挪向尸体。他刚进来,门便啪的一声扣上。接着,外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有人正在吃力地转动发涩的锁孔。只听得啪的一声,锁栓扣进了锁眼。随即走廊上响起了七零八落的脚步声……这个人踱到长条桌旁,站了一会,端详了一番尸体,随后耸耸肩,走到窗子跟前,拨开百叶窗,眺望黑魅魅的夜景。窗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他用手试了试,才发现窗子嵌在雕花的石板里,外面装了结实的铁护栏。他又跑去查看另一扇窗子,情形也是如此。”但富有刺意味的是,贾里特并不知道,那个尸体是由真人曼切尔扮的。后他被这个活人假装的尸体吓死。故事虽然非常恐怖,但并未涉及真正的鬼怪。从比尔斯的玩世不恭的人生观来看,他未必相信鬼怪的存在,恐怖感也许只是体现了他的创作艺术。
幽灵、死亡必然给人带来恐惧感,在现实当中,属于痛苦的感觉,人们都尽量设法避免。而这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在小说当中还深受欢迎呢?法国修道院长杜博曾经做过有意义的解释。他认为,对于心灵有害的莫过于老是处在那种懒洋洋的毫无生气的状态里,它会毁掉一切热情和事业。为了摆脱令人厌倦的状态,人们就到处寻找能吸引他兴趣和值得追求的东西,如各种事务、游戏等。不论引起的激情是什么,即使它是使人不快的,苦恼的,悲伤的,混乱的,总比枯燥乏味、有气无力的状态更好。悲痛的故事的确可以帮助读者摆脱无精打采的状态,使精神高度兴奋,但杜博并未对现实中的不愉快和文学中的不愉快进行区分。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作家的所作所为与玩耍中的孩子的作为一样。他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地对待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同现实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就是说,痛苦的故事可以使人兴奋,但读者又能够把它和现实分开,视之为游戏。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人们逃避痛苦而在小说中却喜欢痛苦的重要原因。恐怖是不愉快的感受之一,是人们首先应当回避的,但小说的虚构性,使它变得受欢迎。
导语摘要本书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世间究竟有没有鬼怪?他们为何深夜徘徊于古堡老宅之中?是蓄谋已久的复仇,还是夙愿未偿的执念,亦或是活人装神弄鬼,借灵魂之口诉说世态炎凉?恐惧如影随形,跟随超自然力的召唤,踏上通往未知的旅行。随着真相的逼近,重重梦魇即将冲破你的底线,扼住你的咽喉……
商品简介本书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世间究竟有没有鬼怪?他们为何深夜徘徊于古堡老宅之中?是蓄谋已久的复仇,还是夙愿未偿的执念,亦或是活人装神弄鬼,借灵魂之口诉说世态炎凉?恐惧如影随形,跟随超自然力的召唤,踏上通往未知的旅行。随着真相的逼近,重重梦魇即将冲破你的底线,扼住你的咽喉……
作者简介安布罗斯• 比尔斯(1842-1913),美国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先驱,其作品故事离奇、结构精巧、语言犀利,代表作有《军人和百姓的故事》《这些事可能吗》等短篇小说集。
目录鬼屋之夜
古宅惊魂
邪恶的鬼魂
诊断死亡
卡可索的永恒魂灵
闹鬼的山谷
犬魂
行尸游荡
鬼谷谜云
恐怖的葬礼
盗尸者
孪生兄弟
幽灵返乡
转世灵魂
林中活尸
复仇冤魂
不速鬼客
幽灵情思
鬼魅世界
海上梦魇
猫头鹰桥上的恐怖故事
内容摘要本书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世间究竟有没有鬼怪?他们为何深夜徘徊于古堡老宅之中?是蓄谋已久的复仇,还是夙愿未偿的执念,亦或是活人装神弄鬼,借灵魂之口诉说世态炎凉?恐惧如影随形,跟随超自然力的召唤,踏上通往未知的旅行。随着真相的逼近,重重梦魇即将冲破你的底线,扼住你的咽喉……
主编推荐安布罗斯• 比尔斯(1842-1913),美国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先驱,其作品故事离奇、结构精巧、语言犀利,代表作有《军人和百姓的故事》《这些事可能吗》等短篇小说集。
精彩内容这是一个奇冷无比的夜晚。天气晴朗,空中清澈得就像一块钻石的中心。晴朗的天空往往寒意更浓。虽说在黑夜,就是冷也未必觉得,可当你能悟出冷时就觉得受不了。这晚的天空异常清澈,因此气候也就显得更冷了,仿佛一个人挨了蛇咬,简直痛入骨髓。月亮在南山顶高大的松树后面神秘地挪动。已经冻硬了的雪地上,辉映着清冷的白光。西方黑乎乎的天幕下,隐隐现出鬼魅般的海岸山脉轮廓。山脉那边是太平洋。雪沿着峡谷底部开阔地伸展,有的堆成长长的山脊,高低起伏;有的堆成小丘,像是四处飞溅的浪花,那浪花其实是月亮投射到雪面之后辉映出来的白光。
矿山营房的废墟中,许多破旧的小屋都被雪湮没了(水手们会说它们沉没了)。偶尔,连那曾经架起水渠的高大的栈桥也都盖满了雪。栈桥上是一条叫做作“弗鲁姆”的水渠。“弗鲁姆”就是拉丁语“弗鲁门”的同义语。生活在大山中的淘金者自有其生活的优越感,其中大山不能从他们身上剥夺的就是他们说拉丁语的权利。人们谈起死了的邻居时说“他到渠上去了”,比说“他命归黄泉”更委婉一些。
大雪穿上铠甲抵御寒风肆虐的同时紧紧抓住每一处有利地势。它像是被风驱赶的俨然撤退的大军,在开阔的地方摆开阵势:能立足的地方立足,能藏身的地方藏身。偶尔也能看见整片整片的白雪躲在断壁残垣之后。山腰上凿出的那条崎岖的废弃山路也堆满了白雪,那白雪一队接着一队地争先恐后从这条道上逃去。冬天的子夜里,人们再也想不出比“死人谷”更凄凉、更阴森的地方了。可是希拉姆·比森偏选中这里,成为这里的居民。
他的松木小屋就在北山的山腰上。一束微光穿透小屋仅有的一块玻璃,整个小屋看上去宛若一个用崭新发亮的别针别在山腰上的甲壳虫。屋内,比森先生独自坐在熊熊的炉火前。他出神地盯着红通通的炉内,好像平生从没见过那种东西似的。他长得并不好看,头发灰白,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脸色苍白憔悴,两眼炯炯发光。至于他的年龄,人们可能先是猜四十七岁,随即纠正说七十四岁,而实际上他才二十八岁。他形容枯槁,也许马上就能见本特利洼地那位拮据的殡葬员以及索诺拉那位满腔热情的新任验尸官了。贫困和热情就像上下两块磨石,在这种三明治中充当夹心真是危险。
比森先生坐在那里,双肘撑在膝盖上。肘关节和膝关节处的衣服都已破烂不堪,干瘦的双手捧着干瘪的下巴。他还没打算上床。此时,他看起来好像只要稍微挪动便会绊倒,摔得粉身碎骨。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他的眼睛还是眨了不止三次。
突然,屋外响起了刺耳的敲门声。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天气里的敲门声,对一个在峡谷中住了两年都没见过一张人脸,又很清楚这一地区道路不通的人来说,准会大吃一惊。然而,比森先生只是抬眼看了看,甚至在门推开时,他也不过耸了耸肩,缩了缩身子而已,犹如人们在等待什么东西却又不愿看到,又好像殡仪馆里的妇人,等着棺材从身后走道上抬来时才露出无奈的样子。
走进门来的是一个瘦高的老头。他身穿绒毛外衣,头上裹着面巾,脸上蒙着面罩,眼珠发绿,露在外面的脸煞白煞白的。他进来时,迈着阔步,却没有一丝响声。老头将自己戴着手套的僵硬的手放在比森先生的肩上,比森先生不由自主地仰起头,脸上失去了血色。不管他在等谁,很显然,他没料到自己迎来的会是这样的人。然而,见到这位不速之客,比森先生百感交集:惊诧,感激,后是深深的祝福。他站起身,从肩上抓起那只青筋突出的手,热情地和老头握了两下。那股热情真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就老头的外表而言,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没有,有的倒是令人厌恶。然而相对厌恶,魅力总是无处不在;而厌恶尽管无处不在,但不为人重视。世界上有魅力的东西要算我们在脸上本能地蒙上遮羞布,若想再注目一点或者更迷人一点,就再在上面堆上七英尺厚的泥土。
“先生好,”比森先生说着,松开了老头的手。那手自然垂下,轻轻地落在他的腿上。“天气太糟糕了,请坐,见到您真高兴。”
人们怎么也难以想到比森的话竟会那么随和,那么文雅。真的,他的外表和言行反差太大了,谁也不相信这会是矿上为普通的一种交际现象。老头朝炉火前走上一步,深陷的绿眼珠闪着亮光。比森先生接着说:“我真的很高兴!”
其实,比森先生的话还不算十分文雅。那话早已降低了标准,带有当地的味道了。他停了片刻,目光从来客的面罩向下,掠过那排发霉的紧扣着的大衣纽扣,后落在那双发绿的牛皮鞋上。鞋上沾着的雪泥已开始融化,一股股地流到地上。他审视完自己的来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谁都会满意的。然后,他接着说:“真不巧,我只能照现有的一切来招待你了。不过,你若不嫌委屈,愿意跟我在一起,而不想到本特利洼地寻找更好的住处的话,我感到十分荣幸。”
比森先生的话既殷勤好客,又谦卑讲究,好像在说老头在这样的冰天雪地走上十四英里,来到他的温暖小屋,简直是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作为回应,老头解开外套。主人在火上又加了块煤,用一只狼尾巴掸着炉床,接着道:“但是我又想,你好快点离开这里。”
老头在炉边坐了下来,把那双宽大的鞋底伸向炉火,没有摘下帽子。在矿上,人们很少脱帽,除非脱掉鞋子。比森先生没有再说话,也在一个椅子上坐下。这椅子原来是一只桶,还保留着它原来的特征,好像是为了收藏他的骨灰而设计的,倘若能使他粉身碎骨的话。霎时间,小屋又沉静下来。这时,远处松林里传来一只恶狼的嚎叫声,门框嘎嘎作响。两者的相连意味着狼厌恶风暴,而风却越刮越紧了。然而两者之间似乎又有一种诡谲的巧合。比森先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打了个寒颤。他很快又定了定神,再次对他的客人说道:“今晚这儿有些蹊跷,我将一切都告诉你吧。当然,如果你决定要走,我可以送你走过那段可怕的路,一直送到鲍迪·彼得森枪杀本·哈克的地方。我想你知道那个地方。”
老头用力地点了点头,像是暗示他不仅知道,而且非常熟悉那个地方。
“两年前,”比森先生开始说道,“我,还有两位同伴,住进了这间房子。在人们都涌向洼地时,我和其他人也一道离开这里。不到十小时,整个峡谷里的人都走光了。可是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落下了一只珍贵的手枪(就是那只),便赶回来取。结果我独自一人在这里过了一夜,从此每夜都在这里度过。我得说明一下,就在我们还没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们的中国佣人死了。那时天寒地冻,很难像平常那样给他挖个坟墓。于是我们匆匆离去的那天,只好把地板挖开,草草地安葬了他,但人还没入土。我十分没趣地剪去他的辫子,把它钉在坟上的横梁上。那地方你这会儿就能看见,不过好等你暖和了再慢慢看。我有没有说那个中国人是老死的?当然不管他怎么死,都与我无关。我回来,既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无法抵制的诱惑,也不是鬼迷心窍,只是因为我把手枪忘在这里。这你很清楚,对吗,先生?”
老头神情严肃地点了头。他看上去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即使有话,也不多。
比森先生继续道:“根据中国人的信仰,人就像风筝,没了辫子尾巴就上不了天。哎,长话短说吧——可是我认为还是说一下好——那晚我独自一个人在这儿,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中国人回来要他的辫子。他没有拿到。”
说到这里比森先生再度陷入沉默,茫然若失。也许因为他不太习惯说那么多话,也许他突然想起什么,不能分神。这时风声四起,山坡上的松树被风刮得格格作响,声音异常清晰。
媒体评论
比尔斯被誉为美国百年文坛怪杰,可与爱伦?坡比肩,更对海明威影响深远。他一生富有传奇性,成名之后却又神秘消失,不知所终。其生平被拍成电影,与他的小说一样,被喜欢恐怖小说的读者追随。比尔斯的作品以离奇怪诞的题材闻名,敢于挑战人性中隐秘的弱点和阴影,讽刺辛辣,一针见血,可谓后世西方一切黑色幽默的开山鼻祖。《海上梦魇》将现实主义与超自然元素相融合,一流的悬疑,极致的惊悚,惊险的故事,给读者带来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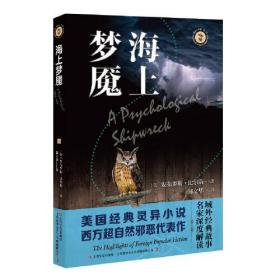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