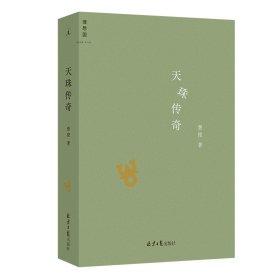
天珠传奇
新华集团 直发
¥ 38.15 6.8折 ¥ 56 全新
库存11件
浙江杭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费滢
出版社北京日报
ISBN9787547746011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6元
货号31760868
上书时间2023-12-2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费滢,1986年生于江苏,历史系学生,法国索邦大学毕业,高等社会科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高等实践学院博士在读,专业方向为佛教文献与医学史,作品散见于《钟山》《山花》等,出版有小说集《东课楼经变》、翻译作品《历史的逻辑》。中学时期征文作品《平台》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曾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联合文学报短篇小说奖大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
内容摘要
一个“小小的古玩商”,一个“身份纸”已经过期、混迹于巴黎十三区中国城、靠赌博赚金边粿条吃的“无纸人”,一个被导师称作“失踪人口”的文献学博士生,一个年少屡获文学奖、近十年却无新作的不务正业小说家,一个“捡垃圾的人”,正在“收集世界的边角料”。
一座从未有人这样书写过的中国城,一份不仅限于一国一民族一文化身份叙事的“移民文学”样本,一部用中文写就的世界文学。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地摊文学,以其惊悚、香艳、八卦、猎奇红极一时,作者“由心羡到心动”,誓要写出一本堪比《“正大光明”的秘密》《戴笠和他的情人们》的地摊文学,“天珠传奇”由此得名。
然而,不知是出于古玩商的劣习,还是作者笔力不逮,“地摊文学”不可避免地变成“逛地摊的文学”。作者笃信汪曾祺笔下的“跑警报”理论: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地摊和地窖里一定有漏儿等着人去捡,那里散落着世界的碎片,或曰边角料;或许还有一些真实,因为真实就是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各处的嘛。历史系学生总难免被碎片化的事实吸引,有意无意地收集各种流落边角的知识体系,不然本雅明干嘛自称拾荒者呢?他也相信边角料中蕴含着总体性的秘密,事物的痕迹诉说着它全部的经验。
作者手握半只天珠,也学着运用起蒙太奇视角,只是拼凑而来的并非已然失落的意义,而是整个天珠产业链的大秘密:如今市价十万到千万一颗的所谓千年藏传“至纯天珠”,大概率是现代制品。历史系学生又要讲了,但凡给它一代人的时间,也不至于从无出土记录不是?与此同时,在台湾“珠子科学家的研究所”里,有两位青年,正借助最原始的玛瑙珠、印度饴糖和坩埚,进行着第四代天珠的研创。故事线索千头万绪、旁逸斜出,堪比历史考证;推理过程高能刺激、异彩纷呈,如同侦探小说。但这也只是最为边缘的知识,与世界的运转无关。
满世界地晃膀子,除了真真假假的器物,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各色移民、泰国巴基斯坦混血的珠子猎人、失去居留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勤勤恳恳学习劳动还是以赌博抢垃圾为生,同样与世界的运转无关,莫名出现莫名消失,偶然获得偶然失去,微不足道,毫无意义,俱是徒劳。
仿佛仍有一个巨大的中心在缓缓旋转,它裹挟一切,又不断崩解、失落,人与事物无不处于“离去的倾向”之中,全部的文字线条纹路颜色终于混为一谈。
——小说便由此而来。
除同名篇外,本书还收录了归游之作《行则涣》,一个小小的古玩商,厌倦了不断地跑动和换手,回到家乡里下河地区,托了一个熟朋友介绍住进庙里,本想着混一日算一日,孰料不是被眼睛绑架,就是被手势出卖——一上手便知有没有,太过熟练的手势、总是在追寻人生活痕迹的目光,难免流露出老吃老做的神态。职业习惯使然,眼睛过处,无有情绪,无有疑问,痕迹学研究便是全部。朱彝尊的砚台、徐渭的印章、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南京洪水过后的风筝……最终还是只有它们让人不困倦。
以及颇具幻想色彩的“民国风”实验小说《反景》,在一个无文字的世界里,一人无意识地行经唐鲁孙的民国游乐场、废名的桥、鲁迅的社戏、脉望故事、骷髅幻戏等文学现场,在一句“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牵引下,反身跃入不断流动的梦境,亦可视作一场“赛博拾荒”惊奇之旅。对大量现代文学片段、文献材料、文体形式及传统意象的移用和戏仿,令人置身于一座文字游戏场,乐而忘返。
三篇小说看似风格迥异,实则互为谜面与谜底,作者设置诸多机关(埋下无数烂梗),只待各位读者前来一探究竟。
精彩内容
我住过两回中国城。第一回,五洲超市尚未歇业,有个潮州打工妹每次都与我搭话。讲她一位朋友叫小梅,专门上门理发,其他不规矩的事情不做,单纯理发,五欧一次。潮州打工妹现在KOK做工。KOK是中国城唯一一家卖牛肉粉的,汤头不甜,无论谁坐下来,先送盘煨得极烂的牛腩,这也是企鹅273最常去的pho店。潮州打工妹仍然爱搭话:今天喝什么?三色冰?清补凉?咖啡奶冰?KOK吧台做饮品大体胡混,虽说pho一定要配三色,我们还是只要瓶自来水。玻璃瓶口积了水垢,不干不净的,水杯也是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擦干的。KOK就这样,污秽的红色桌布,堆在吧台上一叠叠盘子里摆着豆芽薄荷叶金不换泰国芫荽,水滴滴答答流到地上;放了大半天表面已风干的腌洋葱、柠檬、小米辣、蘸酱,随意取用,可能是北越的作风。我找小梅理过发,小广告贴在五洲超市门口,与陪同看病、办居留卡、黄色按摩、走私香烟之类的挤在一起,确实规规矩矩。名叫小梅,然而已是个中年的妇人,进了门,先由小推车里取出一叠旧报纸铺开,指示我站在中间低下脑袋,又变出只喷壶朝头发上喷了喷,十分钟剪出个狗啃似的发型。几年后,我听说小梅练熟了刀法,给人开起双眼皮了,都是人家上门找她做,也在中国城。她还兼职外卖热菜,一番结合,开双眼皮送地三鲜。中国城这种地方,住过一回的便不想再住,尤其对于在伊夫里(Ivry)和舒瓦西(Choisy)那两处高楼里生活过的人:一个公寓分隔成六个隔间,公用浴室洗手间洗衣机,垃圾通道屡屡爬出蟑螂,隔壁室友总在换,甚至有一间是四个铺位的临时旅馆,洗盘子的斯里兰卡人、西藏人、泰国僧侣、南国背包客来来去去,一晚十欧。我在中国城街上真正认得些人,已是第二回居住时,伊夫里高楼之间的公园空地上开了赌场,赌泰国骰子,花花绿绿一张纸,押点数。小梅居然也赌。潮州打工妹在脏兮兮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和庄家的家眷们唱南国歌谣,吃腌螃蟹木瓜沙拉,喝狮牌啤酒,看到我,热情搭起话来,讲泰国流行歌曲很好听,录音机里正在播的是国民歌星滑病(Illslick),堪比周杰伦。我打开YouTube,果然每一首的播放量都好几千万。这是二〇一六年的夏天,赌摊上的每个面孔都对我微笑着,像认识我很久了,只有小梅记不得她曾帮我理发,专心于三颗骰子每一次的跳动。他们就是用那种放腌洋葱的小碗倒扣在放豆芽薄荷叶金不换的盘子上摇着骰子,塑料碗盘克啷啷地直响,上头印着五福捧寿花纹。一开,小梅押着四六点的五欧元就被收走了。她又押一次三六点,仍是不中,便抬起头来,略有些尴尬地看向四周,好似围观者中有人要嘲笑她连续输了两次小钱。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滑过去,并未停留,也对,我现在都找越南阿姨理发啦,而且,我一直是极单的单眼皮。
我都是在早晨十点去找越南阿姨理发。那个钟点理发店地上的淡绿色方砖格外清爽,洗发池里也没有上一个顾客留下的碎发。仅越南阿姨一人在,她涂了涂指甲油,坐在高高理发凳上,脚踩着方砖,配合着九十年代金曲,缓慢地转来转去。十点开始播放的是黄乙玲的《忧愁》,之后一首赛一首苦闷,不提也罢。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月去一次,偶尔我会问,阿姐,能不能换个歌单。越南阿姨说,别唤阿姐,叫我阿曼。她帮我理发时也会照照镜子,叹道,每回照一下便一吓,我好老。我又问,阿曼,你在托比亚克(Tolbiac)做了多久事?她带我去洗头池,放水,挤了一手心经久不换的杏仁味洗发膏,长长的指甲避开,用指腹揉起我的头发。我知道有人就是爱洗头,头发越长越喜欢在理发店里洗头,约会到早了,便要洗个头吹个头发打发时间。但只要别人用手在我头顶心招呼,我便会脚底发痒,浑身不自在。阿曼还问,水热不热,冷不冷?我遂回她,没事,快点洗完就好了。烧燃气热水出得慢,一股半冷不温的水浇上来,人就清醒。我盯着天花板,总想问阿曼一些十三区传说,比如亮哥亮哥的事。似乎我也问了,她也答了,每次零零碎碎,阿曼的中文我有点不懂,她讲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越南话、法国话和一点点普通话。大体开头是这样的:亮哥亮哥,厉害吼,砰砰砰砰。我也配合她,学了点黄乙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啦。往往还没听完,头就理完了。阿曼告诉我,她做了三十年工。有空我们去小锌咖啡喝一杯,吃一块清心糕,慢慢说。我要一张纸巾,擦擦耳朵里的头发,站起来掸掸衣领,讲,好哦。阿曼又夸我是个干净学生,怎想会赌博?清心糕是广南泰饼家做的,广南泰,BanhTanTan,让人很有些费解,我学过一些南洋拼音,知道“陈”拼做“Tan”,故而陈氏兄弟超市写成“Tangfrères”。BanhTanTan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我熟小锌咖啡馆,它就夹在法国巨人超市(Géant)和巴黎冻品店之间,斜对面是潮州城大酒楼挂满烧鸭的玻璃橱窗。开始赌博后,我老看到赌摊上的几个熟脸在那儿喝咖啡,其中有一个白发胡子飘飘的白天赌马,晚上赌骰子。他们瞧见我,也略略点头。——总之,我与阿曼从来没有约过,也不晓得怎么约。等我现在又想起十三区诸事,再去理发店找她,别的理发师告诉我,她已休工不做了。好吧,既然来了,还是理个发吧,洗发膏味道没变,杏仁的,只是音响里换成了法国电台“老歌大联播”(Nostalgie)。
2十三区的气味一日多变。十点二刻理发毕,广南泰头批糕点出炉,火腿面包、蛋挞、清心糕、杏仁饼;烧腊店挂出鹌鹑烧肉烧鸭;一百多家餐厅齐炸红葱酥。由小陈氏超级市场门口的电扶梯可上至潮州会馆(须注意入口处的下水沟,脏水漫溢,不小心就溅一腿)。会馆连着混合小庙,前厅上供奉黄大仙,进了里殿,则为释迦牟尼与十八罗汉了。大香炉中散漫地插了几炷香,应是买菜妇人与赌马的已先行拜拜。我脱了鞋,跪蒲团,磕了头,捐五欧元,祈愿早日拿到长居。所谓长居,就是一张一年更新一次的学生居留卡,我加入无纸人(sans-papiers)行列已有大半年,连学校也很少去,只时不时到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BNF)装模作样找东找西。里殿放了些折叠椅,信众们周三周五晚上要念的经就搁在椅垫上。地上也铺了地毯,每天居士出来用大吸尘器将人落下的各色灰尘同香灰香烛味一道吸走。这会儿香炉中又开始冒出今日的檀香味。释迦牟尼旁边不知谁摆了个长生娃娃,脸上也贴了金箔,与佛一大一小地闪着光,一刻晦暗一刻亮。没旁人,只有最顶头的椅子坐着黑大哥,可能累得狠了,光着的脑袋顶着墙这么睡着,一个大块头,以头为支点,双脚踏地,卡在折叠椅里,保持着奇怪的平衡。很快到十一点,餐厅便纷纷开门,他要去后厨上工洗碗盘,放李锦记海鲜酱和是拉差辣酱的小碟最麻烦。不过,对面香香餐厅的才哥不会刁难人,洗快洗慢没那么紧要。才哥是个胖胖的财主样子,三个儿子分管吧台、收账、上菜,他乐得轻松,前两个月刚在小公园草地上办过六十岁生日会,铺一张大草席,找了乐团吹小号萨克斯,开了几十瓶红酒,在场大家无论赌徒还是在路边摊就餐的,都跑来喝一杯。小公园空前热闹,傍晚时分,日落高楼,有一片玻璃窗反射红彤彤的日光,反而照得枯草地、垃圾堆、破床垫和污水等历历分明。几个塑料袋在高楼风中好似永不会坠下,飘飘荡荡,随着音乐起伏。就连仓库后门处的道友也从光照不进的地界中挪动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上前,讨要一欧元硬币。几个白人又喝酒又打针,才哥不想过问,给每人倒一塑料杯勃艮第打发了去。老娄姨来得比较慢,由于在腿上打针,两条腿都坏了,两块草皮走了十多分钟。她还担心家当被人夺了去,拖着小车来了,小车上捆着数个大购物袋的杂物。才哥给她一张红色十欧元票子,讲,马头将军吃K仔好好的,打针人便坏掉。老娄姨回,是喏。拿上钱,并不喝酒,更不吃东西,着急去买今日的药了。才哥望望她,来不及叹气,又有熟人来敬。我也敬了一杯。边喝边用几个硬币单押一个点数,赢了十几欧,所以闲下心来,买串香茅烤鸡肉,听了会儿生日歌。
阿辉迎我,让我坐在外卖打包位,才哥要稍后到,目前不知在伊夫里还是舒瓦西或是马塞纳(Masséna)上溜达。我说,阿文,先来壶茶。阿辉和我说,我是阿辉啊,带客人的。为了区分,他留了两撇小胡子,可我总忘。才哥亦觉得儿子多得有点乱,一眼冒出一个仔,往往并不理他们,专门溜溜地转着与客人讲话。自从认得才哥,我便不再去隔壁清心小馆吃饭,不然他要走出来,转到清心的桌台边与我说,好吗?他知我是无纸人,便问我被警察抓住怎么办。我说,我又不做工,警察才懒得查。他更担忧,不做工怎么办呢?我手一摊。他遂指示我去潮州会馆香炉旁拿白条。白条是张警察局放的白纸,专门给无纸人的临时做工许可。潮州兄弟会在局子里有人,其实十三区市长也是讲潮州话的华人啦,月头拿十五张白条来,先到先得。每日早晨五点招工的也来,我望过一次,陈氏门口扶手梯入口锁了,得从托比亚克大街上爬上高楼之间的天台。天仍是黑的,密密麻麻的窗户仅有数个点亮,空气飘来隔壁94省工厂两只大烟囱的灰味,果然,抬头看,烟囱已吐出两条灰白龙,堆入黎明的厚云中。喷气式飞机飞过,划了一条更直更长的线,不一会儿天亮,这条线也变亮,又变透明,一天中少有的振奋时刻。已聚着几十个等工的人,大部分穿着灰色工装,裤腿上沾着白色泥灰——工地上招人最多。其余是临时洗碗工,多半是斯里兰卡人在做,如果手快亦可以一试;极少文书类,这一次正巧发到:中华圣母堂本周寻代课书法老师。我没有拿白条,遇到检查可能会被遣返。做力气活儿的已散了,剩数人立着,与我一般踟蹰。一个臃肿的影子过来,我在黎明些微的光中看到她的侧脸,认出她了。有段时间,在KOK食pho,她常来桌边拉一段小提琴,不知是哪一支曲子,偶尔有人给一两个硬币。她不开口说话,我以为是聋哑艺人,但某天她抬手拿琴弓,碰翻斯里兰卡人兜售茉莉花的铜盘子,两个人吵起来,一齐被潮汕妹赶出了店子,她又回头骂了句极为恶毒的脏话。店外下着小雪,正是过年时分,马路两边挂上了中国城才会有红灯笼,咏春团由文华酒家出发走上舒瓦西大街排演舞狮子,嚣嚣闹闹,我本想追过去给她一个两欧硬币,那脏话实在让人震惊,我一愣神,她已随着狮子混入人群。眼下初夏,她仍穿着几年前的灰色大衣,头发很久未洗,眼神定定讲,我会书法。招工目光由我身上扫过去,问,有没有其他人做?我赶紧望向远处去,喷气飞机的轨迹已涣散,掺到其他的云里了。
3小公园赌场,其实是一个个桌。天暗折叠桌撑开,每一个放一只装电池的白灯,铺上赌纸,一人摇骰子,一人算赌账。由外面马路往里看去,似白水母漂浮,本该透明的白水母又伸出一些黑色的触手,是围住桌的赌客。又似高楼间的亮蘑菇,吸引一群大蚂蚁,包裹住它吮吸汁液。大蘑菇发射菌丝,笼罩巨人超市红蓝霓虹与日式烧肉绿色自助餐广告牌的射线,大家忽而在海底,忽而在林中,赌到晕头。突然地,白水母亮蘑菇花花赌纸骰子声硬币响人的喊叫瞬时消失,众人立于昏暗,头顶数千户密密灯光如星星复又显现,是警察来了。警察摸黑在小公园中巡察,一个个桌早已折叠藏在草中,遂装样喝问,你等这许多人在做咩事?赌摊老板答,晚餐后散步啦。赌客答,练咏春啦。警察拿警棍拨弄一下白灯与五福捧寿塑料碗盘,再喝问,这是何物?赌摊老板答,晚餐后散步又聚餐啦。十分钟后,警车开走。闪出放哨小童,要二十欧报酬。二十欧去舒瓦西路桥下的废弃铁轨处可买两副偷来的雷朋墨镜。怕警察杀回头,大家仍要站立片刻,却已没那么紧张,相互聊起天来。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用手肘捣捣我,喂,我见过你。我正欲辨认,白灯亮,骰子声一响,“开”,他便再也无心交谈,拿刚刚还没来得及押的十欧,摆在十一点(也就是三个骰子点数加起来为十一,一赔十一),只十秒,钱便被收走了。
他随即掏一张五十欧,仍押十一点,又输。我和他讲,十一点概率太低,四五十开之后才会碰一两次,但凡庄家手一偏就归零。现已有十次没有出现两点,不如单押两点,胜算大。他没回头,只答,太慢,我凭预感。我预感这把就中。遂摸摸夹克内袋,再掏出一张五十欧。我问,今日工钱?他不置可否,唯眼睛紧紧盯着“开”的手。我们看庄家的手便知赢面——这双手凶险,右手断了中指,按住碗时,使人错以为中指透入其中,抚摸着正跳跃的三粒骰子,如此轻轻弹拨一下,我们大大小小的硬币钞票便被收去了。可赌徒不爱挪步,怕跑了运气,选一摊便站定着赌。也有像我这样凭概率的,换摊得从头再赌十多把。其实,再凶险也不过一双手,它既然老练,必然稳定,即使摇动间有细微调整,也须服从于概率。庄家根据台面上的赌注分布来作弊,也并非无迹可循。赌纸上有大小、十一点、单数、双数、三数,押单独一个数总归有得赢。我默默计算,等待着手来揭示。所有人都在等。庄家故弄玄虚,再三以残手抚住碗底,每每又放开,弄得嘘声一片。终于叫“开”,人群尚未反应,他忽地也大叫了,十一点十一点,中了!庄家表情不变,旁边算账人数出十二张五十欧递给他。众人啧啧羡慕,他嗯嗯出声,有了活人的神色,连黑夹克都闪闪发光,明星一般对左右皆笑,将钱揣入怀中后,又瞥了我一眼,拖长嗓子,今——天,收工。三步并作两步,隐入高楼去了。两点亦中,却没有这么大的传奇性,我收起只赢一倍的十欧元,正欲离开,迎面走来四楼生命之粮的陈牧师。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