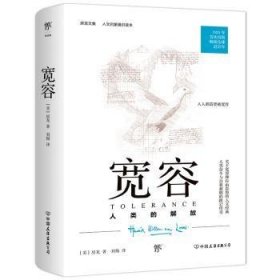
宽容:人类的解放9787505732506 房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正版图书保证质量 七天无理由退货让您购物无忧
¥ 18.7 4.7折 ¥ 39.8 全新
库存172件
山东泰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房龙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SBN9787505732506
出版时间2013-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9.8元
货号R_11203407
上书时间2024-01-3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全新正版
- 商品描述
- 第二十章 布鲁诺 有一种颇为可靠的消息说,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是一群没有军衔的士兵的战争,那些将军、上校及三星战略家整天坐在一个废弃的别墅里,受着寂寞的折磨,伴着单调的光亮,沉迷于几英里长的地图,冥思苦想之后,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那是用三千人的生命为代价,使他们能够获得半英里的领土。而在这个时候,一些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干着所谓的“黑活”——也是不为人知的的勾然了,边防的陷落是必然的结果。 即便是为了精神独立行的大规模战斗,形也大同小异。 几乎没有出现过几十万人的正攻。 也不可能出现那种破釜沉舟似的盲目冲锋,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士兵当成活靶子交给敌人宰割。 可以这么说,很多时候,绝大部分人自始终都不知道战争已爆发了,他们只会好奇地关心一下谁死于清早的火刑,谁又将在明天下午的绞刑架上丧命。然后,他们或许有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不顾自身性命的人还在继续原则而战斗,但是,天主和新并不赞同自由原则。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小道消息只会引起人们轻微的惋惜而已。但是,假如遭受这种灾难的人是他们的叔叔或者什么亲戚的话,他们会痛不欲生。 况似乎如出一辙。我们不能单纯地用几个数学公式将者以生命为代价换回的事业概括了,算安培和马力也不能表示他们为事业做出的努力和。 乔达诺·布鲁诺的著作是每个在读博士生的书籍,他们精心地收集了他作品中精辟的语句,诸如 “人们可以自由的思想,不受国家干涉”或“国家不能用武器(比如剑)来处罚那些反对公认教条的人”。这样他们能够轻松地写出人们喜欢的博士论文来,题目为《乔达诺·布鲁诺(1549—1600年)和自由的原则》。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那些不研究这种重要课题的年轻人,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那么一批忠诚无比的人,看到当时的狂热和人们身上沉重的枷锁,老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于是乎,他们站出行反抗。他们实在是太过贫穷了,只有一件破衣烂衫而已,并且毫无安身之处,但是,他们的心中有一团圣火激励着他们,他们整日穿梭在大街小巷,不停地演讲、写作,还庄严的大学,找到那些学问渊博的教授,并与之不停地争论高深的问题,即使在普通的乡间小酒吧里,他们也会同村行口沫四溅的争吵。他们不知疲倦地宣传着善意、理解、宽容和仁慈的待人之道。他们顾不上破烂,提着书,拿着小册子,从东到西,走南闯北,不停地奔波。后,他们中一些人患上了肺炎,死在了伯美拉尼亚偏僻的小村庄里,一些人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汉私刑处死,还有一些横尸在的大街上,被车轮轧得粉碎。 乔达诺·布鲁诺,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可是像他一样的人不计其数。不过,他对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对自认为正确的事的那份执着、那份坚持、那种熄灭的热,值得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例子提出来讨论。 布鲁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像很多孩子一样,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资,按部班入修道院,后来也成了多明我会的一个僧人。这是个支持迫害行为的团体,与布鲁诺的思想半点都不相符,那个时候的多明我会也被称为“正统信仰的爪牙”。这样的称呼说明教会里的人都很机敏,那些异教者不必将他们的观点写成白底黑字,只要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者一个举止,他们能分辨出来,然后把他们统统抓到法庭的面前。 布鲁诺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服从的声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叛逆者的呢?是什么让他丢下《》,而拿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这一点,我也弄不明白,不过,格格不入的布鲁诺还没来得及学完那些必修课被赶出来了,从此他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他像许多前辈那样翻过了老的阿尔卑斯山。他们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希望在罗讷河和阿尔夫河交汇处的那片森林里有他们企盼的自由和美好。 可是,他们发现改变教义并不代表可以动摇人们的内心,而人们的行为恰恰是受内心指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带着失望的绪离开了。 布鲁诺在日内瓦居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的难民充斥了这座城市,通过同乡的帮助,他得到了一套新,并且找了份校对员的工作。他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行文学创作,当他看到了一本德·拉·拉米的书的时候,像找到了知己一样的惊喜。德·拉·拉米同他一样都坚持世界的步伐被中世纪教科书中宣扬的阻碍了。跟他的老师相比,布鲁诺走得并没有那么遥远,他认为不能对希腊人的理论全盘否定。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了公元16世纪,人们还在受到早在出生前四个多世纪的时候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 信仰正统的人告诉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而年轻的叛逆者却这样回答他:“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死去的人应该永远地死去。” 没有多久,警察找上了他。警察建议他收拾行李,到别的地方交好运去。 从此,布鲁诺踏上了寻找自由居住地的旅程,他努力地去寻找,可是这条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他先去了日内瓦,又来到里昂,然后又去到图卢兹。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涉足天文学,并对哥白尼的学说表示赞同,不过这样做会让他走入一个危险的境地,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在大声叫喊着:“这个世界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世界只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一颗普通的星星?见鬼去吧!真是可笑极,谁会听说这样的呢?” 即便是在图卢兹他也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他便横穿,徒步到达了巴黎,后又去到英国,成了一个大使的私人秘书。但是,他只是再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英国的神学家跟大陆的神学家简直是半斤八两,可能他们更实际一些,例如,在牛津大学,对于违反了亚里士多德教诲的年轻学生,他们用的不是处分,而是处罚,每次罚款十先令。 历了很多事后,布鲁诺开始变得喜欢挖苦别人,喜欢讽刺人。他开始写一些很精彩却带有危险性的短篇散文和对话,内容大多以、哲学、政治为主。在对话中,整个现实社会的制度被他弄得颠三倒四,被剖析得细致入微,一点面都不留。 同时,他还教授自己感兴趣的天文学。 虽然布鲁诺的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校方却不喜欢他。学校向他下达了逐客令,他只能又回到,然后来到路德和茨温利刚刚待过的马尔堡,这两个人曾在这里交流匈牙利伊丽莎白的城堡里辩论变体说的本质。 他的“自由分子”的名声已传遍了大街小巷,因此他连当教师的资格都没有。虽然维腾贝格很好客,但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已落入了加尔文派手中,从此以后,像布鲁诺这样有自由倾向的人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他决定向南行,到约翰·胡斯的地盘寻找新的机会,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布拉格成了哈布斯堡的,随着哈布斯堡入,自由也随之销声匿迹。布鲁诺只得继续行走,开始了通往苏黎世的漫漫旅程。 在那里,他接到了一封意外来信,是一个年轻人写给他的,名字叫作乔瓦尼·莫塞尼戈,信中邀请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为什么布鲁诺会接受邀请,或许是因为这个农民受不住头衔的诱惑,为收到这样的邀请而惊喜若狂。 乔瓦尼·莫塞尼戈的祖辈们有敢于挑战苏丹和教皇的胆量,但是他自己却胆小如鼠,意志力薄弱,当法庭的官员他的家里强行将他的客人带去罗马时,他被吓得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也不敢动。 布鲁诺终还是被带到了罗马。一般况下,威尼斯政府都很重视自己的权力,可是,他们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只有思想而不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实际好处的人得罪罗马教皇。除非布鲁诺是一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有可能会发出强烈的抗议,若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地盘随便抓人的话,他们肯定会干涉,甚会发动战争。 他以学者自称,这是无可厚非的,共和国为此也感到荣幸。但是在国内,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多了。 再见了,布鲁诺,愿圣马可宽恕他的灵魂。 在法庭的监狱里,布鲁诺度过了漫长的七年牢狱生活。 直到公元1600年2月16日,在鲜花广场,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散去。懂文的人或许能从中获取灵感,写出一则寓意深刻的文章来。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有些事,也搞不明白,代某些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工作量是其中的一件。 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录音机、自来水笔,有的还有秘书,每天能写出三四千字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过去的年代中,像莎士比亚,他身(大约有十几种),还有个老婆整天在耳边喋喋不休,鹅毛笔也十分笨拙,三十七个剧本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同样,我也无法理解“舰队”里那个异常繁忙的老兵洛普·德·维加,怎么会想到用找来的那些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部喜剧和五篇文章呢? 还有一个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奇怪的人,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居然能够在挤着二十多个小孩的小屋子里,承受着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依然写出了五部清唱剧,一九十支教堂大合唱,三支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他可以凭借任何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而名垂青史),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此外,长笛、竖琴、风琴、提琴、号管他都写过相应的曲子。这些,任何一个普通的学生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练还有,我不知道有哪个画家能像伦伯朗和鲁本斯那样勤奋努力,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能创作出四幅画,或者是四幅蚀刻画。一个平凡的人,有谁能像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那样,在有生之年做了五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现在,我并不想谈论他们是如何设计出那些节,如何听出那些旋律,如何分辨那些色彩和线条的组合,如何选择那些木头这样的话题。我好奇的仅仅是关于体力这方面的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不会去打打台球,休闲娱乐一下吗?难道他们从来不知道疲倦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说过神这个词? 在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整天大肆吃喝,丝毫不遵守健康规律,人类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早被他们抛在脑后。不过,他们将大把的时间花在了艺术创作上,并且他们的艺术成果确实令人案叫绝。 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甚是无比挑剔的神学,况都惊人的相似。 如果回到二前的图书馆里,你会发现那些早已们记忆中的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这些有着皮革、羊皮纸和纸张封面的书籍塞满了天花板和顶楼,上面堆满了尘土。虽然这些书含了广博的学识,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中一部分书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在当时,有重要的目的隐含在这些发霉的书籍中。如果它们失去了实际作用,少可以帮忙清洁空气。因为这能够给它们讨论的问题提出一个的答案,让有关人士感到满意。或者使读者明白,有些问题并不是用逻辑推理或者使用辩论的方法能够解决的,于是他们会选择丢弃它们,对它们放任不管。 这些恭维的话听起来更像在挖苦。假如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科学成果还能有幸出现在公元30世纪,我希望那个时代的批评家能够对它们表现出仁慈和公平。 这一章的主角是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他并没有追赶那个时代的时髦,在数量夫,他的不过是三四本小册子,外加几捆信件。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小看了他的作品,因为如果要用正确的数学方法去解决他的那些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那必须得夫,学的知识,这些学让一个健康的普通人感到吃力。这个得了肺结核而死去的可怜人,为了献给的乘法口诀表而耗尽了生命。 斯宾诺莎是。他的祖辈们居住在西班牙半岛的时候,那还是一个摩尔人居住的省份。那时,还没有受到隔离区这样的“待遇”。后来,西班牙被教征服后,推行“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政策,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中,斯宾诺莎一家只得离开了故乡。他们乘船来到了荷兰,并终落户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买房置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省吃俭用,积累了很多的钱财。很快,他们成为声名显赫的“葡萄牙”中威望很高的家族。 假如这家的儿子巴鲁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着的血,那么邻居家小孩的讥讽算不了什么了,他在塔尔姆德学校接受的才是重要的。因为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压得几乎无法呼吸,偏见已不能引起它的重视了,因此,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成为所有外来人的安身之所,他们安心地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人们相处友好。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旅行是喜欢在自己的“游记”中记录这一点,当然,这是有理由的。 和欧洲人一直都不能融洽地相处,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甚到了近代,况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真是不可理喻。可能双方都有对错,都有理由说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像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那样,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只要徒和各自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对方会自然而然地被划入敌人的阵营。,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信仰的才是真正的,其他民族信仰的都是假。第二,在商业领域里,他们是竞争敌手。怀着去巴勒寻找家园的美好梦想来到了西欧。那个时候的工会,也是“行会”,阻止他们从事一切职业,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开了典当行和银行来做生意。这是十分类似的两种职业,中世纪的人们将它们看成邪门歪道。教会一直对金钱抱着厌恶的态度,不过税收除外,他们认为收取利息是犯罪行为,把拿利息看成罪孽,这种想法无法接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加尔文时期。在那个时期,放高利贷是被政府禁止的行为,早在四十个世纪之前,巴比伦人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禁止金钱交易或者从别人的钱中谋取利益。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约》里我们也可以读到,摩西的门徒们是被禁止放高利贷的,不过,可以借给。此后,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的大希腊哲学家对钱生钱的勾当都深恶痛绝,教神父更是如此。整个中世纪的人对放债者都持鄙视的态度。更有甚者,但丁在地狱里为他界的朋友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讲,开当铺和开银行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公民,假如他们消失了,世界将会更美好。可是,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农业再也不是的主宰了,人们要做一些普通的小买卖必须依赖信贷,所以,放债者尽管可怕,人们却无法离开他。那么这些“龌龊”的行业让来干吧,反正他们已注定要受地狱之苦,体面的人会远远地躲开。 这样,可怜的被迫与这些人们厌恶的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让他们很自然地走上了与富人和穷人敌对的路。当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对方一下子变脸了,辱骂和驱逐统统降临在他们身上,绪冲动的时候,甚以不信教或的名义将他们送上绞刑架或是火刑柱。 这样的做法真是愚蠢和幼稚之极,并不会因为这样没完没了的压迫和残杀而对徒增加好感。它只是导致了大量聪明的人从公共流通领域中离开,成千上万个天性聪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有所作为,却把大脑和精力浪费在毫无用处的旧书里,去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钻牛角尖的问题。还有成千上万孤苦无依的青年,注定只能在发臭的小屋里过不正常的生活。他们一面听老人讲,已做好了安排,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另一面又听到邻居们不停地骂他们是只配上绞架或刑车的猪罗。他们常常被这些辱骂声吓得灵魂出窍。 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让这种生活在逆境中的人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 一次又一次被徒同胞逼迫,只得采取疯狂行动反抗压迫者,于是,“叛徒”“不知报恩的小人”这样的帽子再次被扣在他们头上,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可怕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会导致一个后果,那是心中充满怨恨的越来越多,而另外的人却走向堕落,区俨然成为一个受挫的雄心和仇恨累积的地域。 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斯宾诺莎幸运,他并不像他的大部分亲戚那样,从出生开始遭受到深重的灾难。他首先被教堂开设的学校,随后又被送往弗朗西斯科·阿皮聂斯·范·登·埃因德博士那里学文和科学,那个时候,他在原先的学校只是刚刚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而已。 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弗朗西斯科博士出身于天主家庭,据说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还有掌握内的法官说他其实是一个会成员,是个危险分子,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不可信的。年轻时候的范·登·埃因德有在天主教学校学历,不过他的心思丝毫不在课本上。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手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对教学很有一手是能找到办法让他的学生对文课产生兴趣。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居民并不在乎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乐意把孩子他的学校,他们还会因为这个学校在六步格诗和变格比别的学校强而感到自豪。 范·登·埃因德教授小巴鲁克学文,不过,他在探索科学领域的道路上,逐渐对乔达诺·布鲁诺产生了钦佩之,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教了一些正统家庭不能提及的事给这个孩子。 小斯宾诺莎没有和学生们住在一起,他仍然住在家里,这跟当时的不相符合的。他的学识给家人留下印象,亲戚们都自豪地称他为小老师,慷慨地给他很多零用钱,他用这些钱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而不是拿去买烟抽。 笛卡尔是他感兴趣的作者。 雷内·笛卡尔头顶的光环,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之间的一个地方,当穆罕默德发动对欧洲的战争时,曼的祖父在这个地方击败了他。笛卡尔被送到会接受教育的时候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因为他善于思考,不会轻易接受没过“证明”的东西,因此,大家都很讨厌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顽皮孩子的是会教士了,他们能在充分保护他的心灵的况下,对行有益的。要检验布丁要亲自品尝,教育也是一个道理。如果现代教育家能够研究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许会培养出几个自己的笛卡尔来。 二十岁时,笛卡尔到了荷兰服兵役,那里拿骚的莫里斯有一套完善的军事体系,对所有想当将军的有志青年来说,他的军队是好修学校。笛卡尔并不常去拿骚亲部。一个忠诚于天主教的人不可能任意听从新首领的使唤!那无异于叛国。笛卡尔对和政治没有半点兴趣,他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数学和炮兵。荷兰和西班牙停战后,他立刻辞职,随后加入了慕尼黑天主教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 不过,那是一场短暂的战役,拉罗谢尔附近的那场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有点意义的,那时,正在顽强抵御黎塞留攻。为了能够学到的攻坚战术,笛卡尔回到了。可是,这个时候的笛卡尔显然已厌倦了军旅生活,他毅然终结了军营生涯,全身心投入到科学和哲学领域。 他是个有固定小笔收入的人。但是他不想结婚,也没有什么大的奢望,他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他选择了在荷兰定居,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荷兰是个印刷业和出版业发达的国家,书店随处可见。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出版检查法顺利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笛卡尔对这个国家的文字一窍不通,尽管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会它。因为语言不通,他节约了大量无聊谈话的时间,每天二十小时都能花在自己的工作上。 这种沉闷的生活对于有过军营历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忍受的,不过笛卡尔却是个例外,因为有生活目标,所以对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很满足。过多年的岁月洗涤,他渐渐看清了这个世界还处在愚昧无知的黑洞里,那些被称作“科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世界的步是被谬误和老旧的东西所阻碍,他想做的工作是清除这些阻碍。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千万不要小看笛卡尔的耐性,当他三十岁的时候,一套崭新的哲学体系问世了。随着他自己目标的指引,他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到原先的提纲里。他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研究工作,后,天主将他划入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将他归为无神论者。 不管什么流言传到他的耳朵里,他都当作没听到,丝毫不受。他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后在斯德哥尔摩同谈论哲学的时候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公元17世纪的笛卡尔主义跟维多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一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公元1680年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并且不体面。从中我们看出某人被看作现行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奇尼,被排除在体面人的行列之外。尽管如此,知识界大部分人依然毫无顾忌地接受笛卡尔主义,与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如出一辙。但是阿姆斯特丹的正统却不会提起这个话题。笛卡尔主义也没有出现在《法典》和《》当中,因此,它消失不见了。人们却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发现了笛卡尔主义,一旦教堂的掌权者采取官方行动出面调查此事,斯宾诺莎等着毁灭吧。 笼罩在阿姆斯特丹教会的危机刚刚散去。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来到阿姆斯特丹。这个非比寻常的人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愿意接受天主教,他坚持信仰祖先的。艾考斯塔是一个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别一把剑的绅士。他自己是个很骄傲的人是时间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但他却不能忍受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的荷兰教士所表现出的自傲。 如此小的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那样嚣张的轻视的容身之地呢?于是,一场的杀戮在高傲的梦想家、半先知半和铁面无的护法卫士之间展开了。 结局必定以悲剧收场。 首先,地方警察局收到消息,说艾考斯塔写了几本否认灵魂永生、渎圣小册子。这个时候,加尔文们找上门来了。不过事实很快大白,控告也到此结束。后,他被教会驱赶了出去,成了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此后几个月,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四处流浪,后实在无法忍受贫困和孤独,他选择再次回到组织中来。可是,他首先得为自己的罪恶行为表示忏悔,任教会的人鞭抽脚踢才能得到入会批准。在这些侮辱之下,他终于精神崩溃,于是他用自己买的一支结束了性命。 阿姆斯特丹市民对这起自杀事行了热烈的讨论。团体觉得这件事对他们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尽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因此,当笛卡尔主义侵蚀了“生命之树”中学生的时候,教会采取的个措施是将事态平息下来,他们找巴鲁克谈话,用一大笔年金收买他,条件是他从此走向“正途”答应去教堂礼拜,不再发表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 斯宾诺莎是个不会屈服的人,他坚定地拒绝做这笔交易。结果,他们翻出老的《惩处准则》,将他逐出了教会。那是一本对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辱骂照单全收的书。 形形色色的谩骂围了他,他却能够平在家中阅读报纸,了解前发生的事。甚当一个狂热分子想要杀死他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半点想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意思。 对于教士而言,这简直是颜面扫地的事,虽然他们将约书亚和伊莱沙都搬了出来,在短短的几年里却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市政府求助,要求和市长面谈,他们要把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危险事迹报告给市长,说他是个十足的不可知论者,不信仰,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社团中,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存在呢? 官员们按照常规,把这件事交给了由教牧师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过调查研究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过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他们把实报告给了市里的长官。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应该团结一致,于是便向市长建议,让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到外面避避风头。 从此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风平浪静,像他窗子外面的世界那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小镇莱茵斯堡租了一间房子,白天对着光学仪器打磨镜头,晚上抽着烟斗,读书写作。他一直没有结婚。不过传闻说他和前任拉丁文老师范·登·埃因德的儿有过一段恋,可是,当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个孩子才十岁,所以这个传闻肯定是假的。 他有几个要好的朋友,每年都提出两三次要给予他济上帮助的要求,让他能专心致志地致力于研究。他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位年轻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二十英镑外,他没多要过一分钱,像一个真正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那样生活着。 曾有一个去当教授的机会也被他谢绝了。他甚拒绝了的普鲁士国的资助和保护。对他而言,漂泊无依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 几年后,他从莱茵斯堡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很差,因为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粉末他不幸得了肺病。 公元1677年,他孤独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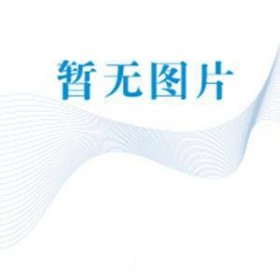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