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脱术9787541164637 秦羽墨四川文艺出版社
正版图书保证质量 七天无理由退货让您购物无忧
¥ 28.8 6.0折 ¥ 48 全新
库存117件
作者秦羽墨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64637
出版时间2020-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R_11869250
上书时间2023-11-1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全新正版
- 商品描述
- 一 我浑身是汗地爬上了三楼,思前想后,打算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她,尽管她并不认识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认识她够了。照目前的形,世界上除了她谁也救不了我。送送到西,既然她已为我解了一次围,有义务解次。 她宿舍里的灯亮着,咚咚咚,我敲了三下。 门开了。 她两手交叉在前,受惊似的看我。 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想跟你借点钱。 说到钱,她又吃了一惊,用力将我推向门外。 我要睡觉了,她说。 看起来,她好像隔三岔五受惊似的。我像抓救命稻一样抓住她的胳膊,不让她关门。她急了,奋力推搡摆脱。我说,别这样,我是来借钱的,又不是来打劫的。她说,这有什么区别,我又不认识你,我们俩没有任何交,你快点走吧。我望了她一眼说,作为同事怎么可以说没有交呢,而且前不久你还帮过我的忙。她说,我帮过你什么忙?我说,不记得啦,在峨眉山,猴子,满山的猴子。为了勾起她的回忆,我调动,学着猴子的模样在她面前抓耳挠腮。 几天前我在峨眉山看风景,一个人踽踽独行。暑期将尽,山上人影不多,走到一线天时,感到口渴,便找了一块光滑的石头坐下。拧开矿泉水瓶准备喝水的时候,那只猴子出现了。可怜兮兮的猴子。毛发凌乱,眼神清苦,茫茫然的表,体格瘦削嶙峋,像刚被人揍过快要死了的模样。我把水倒在手心,那只猴子走过来伸出狗一样的舌头快速舔舐。我打开,掏出一根香蕉,准备剥给它吃。这时,那只瘦猴猛地跃起,将香蕉从我手中夺去,同时,背后的林中杀出一大群猴子,它们抱的抱腿,搂的搂腰,猝不及防之下,我的旅被猴群掠去。它们抢完便跑,转眼消失在山林中,剩下地站在原地,眼中只有绝望。 一场阴谋。我如梦方醒,在背后拼命追赶。山中无路,又是绝壁,哪追得上。两小时后,有游客在别处捡到了我,旅游区的管理员通过话筒盒子喊人。拿时,里面的钱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本自费的诗集。有人顺手牵了羊。一只猴子的出现,让我陷入了从未遇到的困境。正生气,路边又跑来一只老猴,它姿态沉着,有恃无恐,我怒火中烧,上去逮住是一顿乱捶。管理员看见我在打猴子,几个人轰地上来,将我摁倒在地,也是一顿捶,我感觉骨头都被人拆散了。他们说我殴打国家保护动物,所以,便殴打殴打我,松松筋骨,好长记。他们动作纯熟,还相互配合,每一拳都落在实处,打起人来好像很有验。领头的说,要罚我的款,还要把我送到派出所拘留两天,将我的个人信息和不文明行为公布网上,以示惩戒。我挨了打,退维谷,口莫辩,像一条丧家之犬。这时候,一个讲四川话的妹子站出来为我说,这娃可怜,丢了东西,太不走运了,这么算了吧。我也趁机据理反驳。听完我的陈述,他们还算有点同心,把我给放了,但丢失的物件他们不管,景门的告示牌上写着:来往游客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遇有失窃,景区概不负责。何况还是一群猴子。我翻了翻裤袋,连同毛票,还剩一千二一十五块。幸好把这些钱揣在了裤袋里,否则身无分文了。再看那个姑娘,她人已走远。不过,我记得她的样子,她很漂亮,而且脖子上有一颗大痣。 听我拉拉杂杂说了这许多,算记起来了,问,怎么,你也是学校的老师?新学期开学典礼怎么没见你?我说,我新来的,才报到。她说,哦,是听说来了一个新老师,是你啊,这个学校中不断有老师来,也不断有老师走。我说,莫说这个,先借我点钱。大热天的,我看见她脸上飞过一道厚霜。她问,借好多?我说,两千吧,我个月工资归你,行不?她大叫,借这么多干什么?我说,你到底借不借呢?她说,多一千五。我说,好的,大恩不言谢。她说,怎么能不言谢,大恩小恩都是恩,你要时刻牢记。我说,好的,知道了,那感谢你的大恩。她说,算一千五,你这个月的工资也归我。我说,靠,打劫吧你这是?这时她终于忍不住笑了一下,那你还借不借?我说,借借借,秦琼卖马,关公质刀,沦落此,哪还有资格讨价还价,算是给地主打长工了,活命要紧。 她脸上松弛了些,说,峨眉上的猴子确实厉害,十五年前抢过我的贝雷帽。我说,那也不如山上的强盗厉害,你们四川人怎么能这样。话说到一半发觉不妥,便打住了。我说,打个欠条吧,立字为据。她说,那当然。于是,我抓起她案头上的水芯笔,坐下来写。刚写下“今日借到张颖人民币”几个字,她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说,打听的啊,教初中一年级物理课的长得很漂亮的张颖老师,住教师宿舍楼305。她呵呵笑了一下。继续写的时候,她说,算了算了,我都不知道你底细,你要是明天跑了,打欠条也找不到人啊,这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一样,都是临时工,算了,莫写了。她拿起那张只写了几个字的借条说,你的字巴适得很啊。我说那当然,大学那会儿得过全校书法。我问,你四川哪的?她说,嗯,都江堰的。她问,你哪的?我说,我啊,远了去了,是“大弗兰”的,家住洞庭湖边。她说,洞庭湖好啊,那里找不到事做吗,跑这么远干吗?是啊,我跑这么远干吗?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好端端的,去峨眉山干什么,现在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猴子。 二 他们说我有病。 严重的抑郁症,并且伴随人格分裂。否则,一切解释不通。 那么漂亮的姑娘,两家父母是知根知底的故交,门当户对,两个孩子也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谈了这么久怎么结不了婚?那次,去友家做客,因为一个菜的做法居然与未来丈母娘发生争执而不欢而散。对方的理由是充足的,一个连丈母娘做菜手法都无法忍受的男人,怎会善待她的儿。这娃肯定有病,不然怎么会这样,带他去看看吧。 家里先后请了四位医生,看过之后,一致认定,我病了,但还不精神病院的程度。母亲心疼,日夕忧愁,想方设法寻访名医。省城的精神科医生说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倒未必,却很复杂。他从母亲那打听到,除了繁重的工作,我还是个业余写作者,思想偏执。他们无法确诊,只是让我好好休养一段时日,好出去散散心,这样医生可以撒手不管,全身而退,把困难抛给病人自己。我不想拆穿他们的谎言,不过,那些不通的诊断书还有些用处。 母亲无奈,说,出去走走也好,玩累了回来。 我说,嗯。 本来只是去峨眉山走走,没想到会遇上那群猴子,然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成都。12年夏天,我在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被猴群洗劫之后,手里积蓄已所剩不多,我想跟家里暂时断绝往来,平日里的狐朋狗友也不想联系。是的,我是想一个人待着,过一段只有自己的生活,哪怕再辛苦,属于自己的行。这些年一直像木偶一样活着,从小到大都是,读书、考学、毕业后安排工作,到现在,每天被逼着相亲结婚,真是受够了。在老家泥城,那个洞庭湖边的小城,他们是活算的,乘凉的样子跟狗没有什么两样,在那里活个二十年,每个人的面孔都差不多,连灵魂都是那么乏味相像。如果说有病,那也只是对自由过于贪婪。算乞讨,我也要选择一个自己愿意接受的施主,比如说像张颖这样的。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所学校的招聘信息的。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很城者没有城市户口,子读公立学校的话,要交一大笔择校费,拿不出钱只能上私立学校。面试的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没想到说了没两句话,台说,打住,行了行了,明天赶紧来学校报到。后来才知道,学校因为扩招,增加了很多学生却找不到老师,那个时候应聘,是个瞎子都能蒙混过关。 成都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这里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多少钱可以支配,事到如今,我必须得让手里的每块钱都花得物有所值。上课之余,我会坐公交到处逛。我的上课不是为了上课,我的转悠也不是为了转悠,我只是想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而我的病,究竟什么时候能好。孤独难受的时候,也想过给家里打电话,让我妈重新办一张银行卡,打一笔钱过来,或者联系一下铁哥们,这样可以衣食无忧了,但还是忍住了,没到后时刻,绝不能向他们低头。 三 事发是在借钱的两天后。 我只上午有两节课,下午凉快一点,一个人出去转悠。回来的时候,听说张颖被打了,人都差点被绑走。来者是一胖一瘦两个男人,瘦的老一点,自称是她父亲,保安也没问个究竟,把人放来,幸好当时正是课间,人多,把两个家伙轰走了。不管是出于债务还是人文关怀,我觉得都应该去看看她。 到宿舍时,她正坐在那两眼发呆。我问,怎么回事?她沉默。我骂学校,什么鬼学校,保安是吃干饭的吗,什么人都来,要是来个杀人犯怎么办,学生出了事故谁负责,这种私立学校是乱!我想问她找麻烦的是什么人,又觉得不合适,毕竟我们并不很熟,我们之间,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不过是她萍水相逢被迫认下的债务人而已。估摸着拣话说,说我对成都的印象。我说,你们四川人说话真好听,跟唱歌似的,调子都是跟着音乐走的。她不说话,眼睛却湿润了,很委屈,很想流泪的样子。姑娘遇上了事,是大事,我只怕帮不了她。 我觉得自己应该走,让她一个人待着。这时,她却说,你多待一会儿好不好?我说,好,可是不说话,待着憋屈。她站起来,不由分说将我推出门外,然后一个人靠在门后大哭起来。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只好在外面对她说,下次他们要是再来,告诉我,老子捶死他们,欺负人算什么本事。 那天一个人去了宽窄巷子。之前听人说过,成都这个地方,只要带上三首像样的诗,待一个月,酒饭管够,吃喝不用花一分钱的。用诗句对一下暗号,像年代的地下工作者,自会有人接待。我心想,我也写过诗,还自费印了一本集子,虽然现在不写了,抄几首去或许可以混一混。在峨眉山时里的东西都丢了,唯有那本破诗集他们没要,是时候发挥它能了,验证一下传闻的真伪。 灯塔酒吧在成都名气很大,来之前,听说当天有一场诗歌美术联展。到了之后发现,两条巷子跟老家泥城的街没什么两样,宽巷子并不宽,窄巷子也没那么窄。壮汉们打赤膊,撩膀子,坐在街边喝茶,或者喝酒,有漂亮妹子走过,也不惊讶,抛个媚眼,彼此欣赏一把。也许,这是它的不同之处,成都人的生活姿态,慵懒如斯。 宽窄巷子32号。灯塔门前的广告牌上有很多诗人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可惜,我全不认识去的时候,他们已开始拿话筒开始朗诵了,听众不少,一半是大学生,坐不下的站起来挤着,我寻了边角的位置侧身而立。中国哪里的诗人能写我不知道,但要说能吹、能装的是成都。不管谁上去,都胡侃一通,先将传统诗歌鄙视一遍,然后,挨个拎出西方大师,轮流批斗,那架 势,舍我其谁。他们朗诵故意不用普通话,用的。好在湖南四川本是一家,成都方言我能听得个八九成,他们念的每句话,每个字我都认识,是不明白其中奥义,也可能真的太深刻了,我水平有限入不了诗人的世界。一位长发披肩,鼻梁上架一副巨大镜框的青年走上前台,他的诗是这样的:“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白/十分白/白特白/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我站立不稳,几欲跌倒。在场的其他听众也满头雾水,面露惊讶之。无声,静默了几秒,大概是听傻了。那人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他朗诵时的模样。这也叫诗?如果可以,我想冲上去,把这个鸟诗人揍一顿,揍得他一脸乌七八糟,连他妈都不认识。兄弟,你不能公然侮辱大众的智商,侮辱我们的母语!啊,诗歌,我叹了口气,不再听他们朗诵,转身看挂在墙上的画。 灯塔酒吧的画,比诗好多了,其中一幅油画,画的是废墟中倒塌的一所小学。教学楼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只剩一堵断墙,孩子们沾满灰尘的手从废墟中露出半截来,扭曲变形,作业本和课桌散落一地。画的署名“刘浪”。 我站在那幅画前看了许久,小声念叨,这画有劲道。旁边那人听见了问,你懂画?我说,不懂,但觉得画得好。他说,谢谢夸奖。我问,是你画的啊。他点点头。他说,当初我也想当诗人,可现在,却是个画家,你是写诗的吧?我连忙说,不不不,哪有那才华。他问,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想藏起抄有诗歌的那三张纸,已来不及,像犯了错的孩子,脸涨得通红。又一个被诗歌的人,他说。 我是来结交大腕诗人的,没想到却认识了个画家。 画展结束后,跟在几个人后面去刘浪的画室喝茶,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只有一个是此前跟他认得的。画室离宽窄巷子不远,走路过去十几分钟,某小区的栋五楼。门打开后,酒气扑鼻,其中伴有浓烈的油画颜料味,好像还有别的什么味道——我说不清楚——它们在那个夏天的午后一拥而上迎接我们几个人的到来。画室有一多平方米,除正厅用于创作外,还有三个小卧室。去,客厅地面上滚满了啤酒瓶,一抬脚,踢得乒乒乓乓直响,中间的大茶几上也是。画家很抱歉地说,昨天来了不少朋友,忙于画展,喝完没来得及收拾。他一边说,一边用脚将啤酒瓶扫到角落。天热,认识他的那个门喊,刘浪,刘浪,快拿啤酒来,热死老子了。于是,画家从屋角一个很大的冰箱里拎出五瓶黑啤,一人一瓶,五个人在画室里边喝边瞅,给人感觉像来过很多次似的。 真像一个旅馆,我是说,屋子里飘浮的气息闻起来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里写的某个的客栈分舵,来此拜码头的都是自家兄弟,不用客气。这个地方为很多人提供过栖脚之地。我发现挂在灯塔酒吧里的那幅画此时又出现在了他的画室,不对,不是一幅,而是三幅,内容一致,落款从09到11,斜在墙上,依次排开。也是说,他连着四年画了四幅构图一样的画。场面有点乱,画板、颜料盒以及那些画过的作品,东一件,西一件,不过表面都很洁净,色泽发亮,看起来一尘不染,是常拂拭的。 他们中有的是来看画家的,有的是来看诗人的,有的画家、诗人都不看,纯粹是来看成都的。我跟他们说自己在峨眉山被猴子打劫的事,他们哈哈大笑,一点没有同的意思。刘浪问我在成都干什么。我说,当老师。他停顿一下说,那不是个好职业。我说,肯定不是好职业。刘浪说,画家也不是好职业,你看我这么多画都没卖出去。不过,他又接着说,我一年卖两幅够喝酒了。我没搭话,心里却在想,没想到成都的画家比诗人还能装。临走时,刘浪说,他日如若不济,可来相投,别的不敢保证,吃住几天不成问题,我看你这人值得一交。我连忙道谢,充着江湖口吻说,您可真是当代的及时雨宋江啊,交浅言深,以后有事必然来求于您。他的话有些耳熟,出门时记起来,刘备落魄时,袁绍曾对他说过这话。
相关推荐
-

逃脱术9787541164637
全新广州
¥ 22.35
-

逃脱术9787541164637
全新广州
¥ 30.11
-

逃脱术秦羽墨9787541164637四川文艺出版社
全新北京
¥ 17.99
-

逃脱术秦羽墨9787541164637四川文艺出版社
全新成都
¥ 17.99
-

保正版!逃脱术9787541164637四川文艺出版社秦羽墨
全新天津
¥ 11.87
-

全新正版 逃脱术 秦羽墨 9787541164637 四川文艺出版社
全新北京
¥ 14.82
-

正版书籍逃脱术秦羽墨9787541164637新华仓库多仓直发
全新无锡
¥ 24.33
-

逃脱术
全新泰安
¥ 26.24
-

逃脱术
全新保定
¥ 26.40
-

逃脱术
全新广州
¥ 11.29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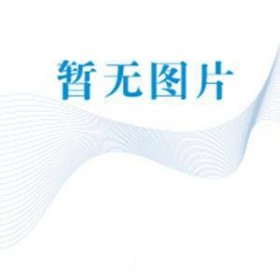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