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国人至甘青藏区进行考察研究,众多文章、专著随之发表出版,这些材料可称之为“早期民族志”。它们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甘青藏区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在表达着考察家“自己”,并反向映射出他们对甘青藏区的认识过程。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 俞湘文 —— 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0年印
¥ 688 八品
库存5件
作者俞湘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1-01-2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品
- 商品描述
-
“他者”的认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甘青藏区民族志文本之人类学解读
玻璃心 2018-03-19收藏赞分享
摘要: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自我”文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的过程,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大量涌现的过程。此种变化过程却是当时时代场域作用于作者群体及调查时间,进而再具体影响“他者”认识过程的变化。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国人至甘青藏区进行考察研究,众多文章、专著随之发表出版,这些材料可称之为“早期民族志”。它们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甘青藏区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在表达着考察家“自己”,并反向映射出他们对甘青藏区的认识过程。这种在知识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又与当时社会场域密切相关,而三、四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及抗战的胜利。本文试图以这三个事件为节点进行分期,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具体探讨当时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认识过程,以求呈现民国西北边疆研究史之一隅。
一、危机、国难与动荡——背景一览
“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一时民族救亡成为最重要之主题,在此种危机日趋严重之情形下,国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西北。“东北业已版图失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议从事开发,巩固国防。”[2]南京国民政府也感于形势紧迫,于1932年通过了《开发西北案》,并在1933年3月颁布了《行政院关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四届三中全会开发西北各案训令》,之后又陆续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等十余种法案。在个人、团体、政府的大力倡导下,“西北开发”之声,高唱入云。同时,在此种风潮的促动下,至西北地区考察的政府官员、新闻记者、青年学生等也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了西北,‘到西北’已经成为一种‘国是’了”[3]。甘青藏区地处西北,而随着西北调查研究进程的步步推进,大批的考察家也来到甘肃的拉卜楞、卓尼等藏区,青海的玉树、果洛等藏区,对该区域之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详加记录,之后或发表于诸报刊杂志,或结集出版,把甘青藏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国民政府为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筹办兵垦开发西北案交国府参考(1932年)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我国华北、华中、华东等大片地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国内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西移。大批国府要人纷纷发表言论或视察西北。蒋介石于1942年视察西北时,发表了著名的“开发西北方针”讲话,返重庆后他又宣告“西南是抗战的大后方,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一时西北开发变为朝野共识,“建设西北”之声风起云涌,再次高涨。直至抗战结束,大批官员、记者、民间人士、考察团体等摩肩擦踵,纷沓而至,西北边疆研究也在此时达到了高潮与鼎盛。另外该时期民族研究机构及相关学者的西移,也极大的推动了西北边疆研究的发展,“抗战以后的四年中……沦陷区出来的知识分子,西迁者极多,拉卜楞也就添了许多前来开发边地的人员了。”[4]地处西北的甘青藏区之调查研究也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考察人员络绎不绝,各类文章、游记、调查报告、著作等层出不群,无论从成果数量上还是研究深度上,较之前阶段更加丰富,是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最为繁盛的阶段。
解放战争爆发后,国内局势再次动荡不安。“抗战时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显得地位非常重要的边疆民族问题,已近不被社会上的多数人视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5] ,同时大批研究机构及学者也纷纷东迁,再加之内战正酣,阻隔了内地至西北的交通,在这种种原因的影响下,“西北开发”之声又很快消沉下去,至西北边疆调查研究的内地考察家骤减,而国人对甘青藏区的关注也自然急剧下降,相关研究成果虽偶有发表,但已不似往日之辉煌。
二、“自我”逻辑、科学理性与文化自觉——过程分析
“九一八”事变之前,国人对甘青藏区虽有认识,但极其有限。张文郁在1935年进入拉卜楞调查时言“说也惭愧,邵力子要我视察拉卜愣的藏民风俗,考察藏民教育及实业情况,我竟不晓得拉卜愣是个什么东西,我竟没分出拉卜愣和拿破仑在音调上的区别”[6],由此可知时人藏族知识之匮乏。而且绝大多数考察家都属首次入草地旅行,当他们面对与“自己”生活完全迥异的“他者”时,首先产生的普遍情绪是文化震惊。马鹤天先生曾长期游历北方草原,但至拉卜愣途中,看到藏民“巷口有经幡,家家门上有经文纸,屋上有转轮,风吹轮转,亦一奇观也。”[7]此种事例,在旅行游记中比比皆是。经历这种“异文化”带来的震惊之后,一些作者开始尝试对甘青藏族社会进行定性分析或价值评判,亦有人对该地藏民的行为方式进行理解,但三个阶段各有特点,兹详论于下。
“九一八”之后,“七七事变”之前。该时期对藏族社会的理解有三种倾向。其一,以“自我”之逻辑来评价“他者”之文化,最明显的是从农耕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藏族社会。有人“提倡建筑房屋,使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乡土观念”[8],以此来促进藏族社会之进步;游牧社会“贵壮健,贱老弱”习俗自古有之,有人目睹藏族社会上述风俗后,视之当然的认为“老年人制作账房,解决他们住的问题。在理应当孝敬老人才对,可是他们对老人并不敬重,大有‘置于鸡窝’之趋势”。[9]这种从“本位”文化出发来解释异文化时,或多或少的夹杂着文化误读或者文化歧视现象。有人把喇嘛描写为“万恶光头,铙钹喧天不竟休,口念糊涂咒,心想鸳鸯偶,两眼黑油油,为禽似兽,偏袒肩头,黑漆钢叉手”[10],可见对喇嘛形象歪曲与误读之深。对藏族社会文化评价过低或者文化歧视也相当常见。有人在言藏族文字时称“但其书法,至为笨拙”[11],另外文化低落,民族幼稚之说法则更为普遍,更有人称藏民“生性本极凶悍”[12],“民性槕野,尤喜争斗”[13]等等。
其二,以简单的社会科学知识来解释藏族社会之发展,最突出是社会进化论思想之应用。范长江在经过甘肃南部藏区时说“藏人社会由畜牧初入农业经济的阶段”[14]。林鹏侠对藏族社会女尊男卑现象有些关注,他曾解释道“人类在上古游牧时代,男女本自平等…。迨后人类进化,家庭组织由部落而国家…,男女不平等之分,愈演愈烈。”[15]然而,该时期对进化思想的运用尚处在初级阶段,相关论著数量较少,同时在研究深度上也较浅薄,仅涉及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或框架,并没有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
其三,个别经典论著带有早期历史特殊论或文化相对论之色彩。藏族的卫生情况历来都被内地考察家所诟病,但张元彬则精辟指出“总之说蒙藏人民怎样不讲卫生!吾不能为主观的辩护,但他们生活上的表现,是历史的,环境的背影使然的,许多有存在的价值,许多却又改革的必要。”[16]这种思想在该时期仅出现在个别杰出人物的个别论著中。
综合而言,该时期国人对于藏族社会文化的评价,主流还是站在“自己”的文化逻辑中去解释,论著“主体性”色彩十分明显,猜测臆想、贬低误读较为常见,科学理性知识虽有偶有应用,但都不够成熟,处于初级阶段,带有文化相对色彩之论著少之又少,有的也只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之后到抗战胜利。该时期对甘青藏族评价与理解,仍然有一些成果从“自我”逻辑出发,对该地社会进行直观的价值评判或行为理解,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歧视和误读现象也时有出现,但基本都属调查时间不长的游记类文章和一些猎奇性质的文字。邓俊康在解释藏族抢婚行为时说“壮年男子除了放牧,他们的精力没有完全的消耗,所以养成了抢婚的习惯”[17],显然这种原因归结的逻辑思路是从“自我”出发,其结论也相当随意、轻率。有人甚至评价藏族人民“生活很苦,比我们很笨。”[18]同样此种由跨文化比较而得出的观点与客观事实极其不符。但总体而言,与前阶段相比,此类文章在数量上大有下降,相反的是运用近代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撰写而成的文章、专著猛然增多。自然科学方面,地理、物产及畜牧三个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席连之于1942年对拉卜楞地区的土壤情况进行调查,并用西方地质学知识对该地的土壤进行科学分类,分为高山草原土、暗色钙层土、湿土、盐渍土四种,又具体论述每个土系下的土壤类别。郝景盛则更具代表性,他以科学方法对甘肃西南藏区云杉等树的年龄、高度、胸高的横切面积、材积生长、年龄与材积生长之增减等进行了调查,在收集诸多数据的基础上,对该地林木的总体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其所撰《甘肃西南之森林》一文专业术语极多,是民国时期藏区森林研究最为经典著作之一。李秀和李式金则更进一步,他们用现代化学公式来具体分析青海玉树地区的羊毛品质,在《玉树一带藏族之乳制品》和《玉树调查简报》二文中多有体现。
邓俊康的《改进俄洛游牧区教育之我见》(1943年)
社会科学方面,进化论思想的运用表现最为突出。朱允镶的在总结甘边藏区经济特点是曾云“从演进的观点看,边疆畜牧、农业少,工商业更为少。”[19]俞湘文则直接引用摩尔根的著作,对藏族家庭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她还认为游牧区藏民社会的家庭正处于由母系制阶段走向父系制阶段的过程中。20世纪初的美国人类学界,在博厄斯的推动下,文化相对观点大行其道。而抗战时期,国人书写的众多甘青藏区的民族志文本中,此种文化相对观点也流露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李安宅先生。在《喇嘛教育制度》一文中,他直接指出“我们需要新文化运动,他们也需要新文化运动……然就制度而论,他们可以贡献于我们的,已有甚多者。”[20]在《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中则引证的更加充分,李氏把喇嘛教的产生发展置于藏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对宗教之评价也没有偏听偏信,而是在细致调查之后,分析“拉卜楞作为一个寺院,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县的不同功能。”[21]在他眼里喇嘛教是藏族整体文化系统的一种制度,最后他还对藏传佛教存在的意义及缺点进行了探讨。另外,作者采用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也使得该书大放异彩,甚至还有人认为“《西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因此是李安宅试图从象征主义立场去研究藏族文明的一个实验性文本。”[22]除进化论外,俞湘文在进行藏边社会文本书写时,文化相对思想也对她影响极大。有人把俞氏的文化相对思想归结为农牧文明的互补性、喇嘛教存在的意义、游牧藏区相对民主制、寺院教育的大学模式及科学饮食方式等几个方面,并指出“俞湘文始终抱有某种对人类‘和而不同’、‘互通理解’、‘求同存异’的学术诉求。”[23]该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甘青藏区的社会性质的文章也有几篇,最著名的是徐旭的《甘肃藏区畜牧社会的建设问题》一文,文中指出“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产生相应的文化”[24],循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作者对甘肃藏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极其关注,着重讨论土地的分配及商业资本的猖獗,最后提出了“这个畜牧社会的本质,乃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性社会。”[25]此外,王匡一的《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虽未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文中对夏河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及生产关系有颇多涉及,唯物论色彩掺杂其中。对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文化生态学所开辟出的学术富矿。该时期亦有部分作者从藏区地理环境出发来解释藏族的文化系统。李式金认为“藏区喇嘛教的流行,实有其地理环境的关系。”[26]在另一文中,李氏以草地地形、少年山地、少年河谷、阶段地及扇状冲击地为例,分别讨论“以上五种地形,对人生之影响各异”[27],但作为人文地理学者,李氏更多的把焦点聚集在地理环境对藏族文化系统的改造与影响方面,对文化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则极少涉及,殊为可惜,但此种从文化地理学角度之探讨,在当时情景下已是超出前人很多。
以上论及的都属国人在理解藏边社会时所采用的现代科学的思想理论。然而,该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突破。自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参与式”田野工作的模式后,民族学人类学中科学民族志的时代也悄然开启。抗战之前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虽然实地考察者不乏其人,但深入到藏族社会内部,从学习语言始,进而研究藏边社会的国人,确是绝无仅有。所以,抗战时期李安宅、于式玉二先生扎根拉卜楞两载有余,与藏民吃住同处,极力学习藏语的学术实践,是科学规范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具体应用的最好例证,其成果受到广泛赞誉。正如李绍明先生所言“作者在这里采用了编写民族志的一般手法,以藏民一年或一生的基本活动为轴线加以叙述,由个别到一般,引人入胜,有清新之感。”[28]清华大学毕业生黄明信也是抗战时期应用“参与式”观察方法进行拉卜楞研究的典型人物,他曾在该地8年之久,不仅精通藏语,而且还获得了拉寺的然卷巴学位,其论著至今仍是藏族天文历法研究的必读之作。
另外,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也有两个突出特点,即跨文化比较和统计法。李安宅、于式玉、俞湘文等系统学习过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察家,对跨文化比较的理解和运用自不必多言,其论著中有较多体现。其他如顾颉刚、潘凌云、东方曼云、葛赤峰、徐旭、王树民、王志文、马无忌等众多考察家在草地旅行或者在后期写作时,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汉藏二族的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进行比较。东方曼云就对内地与藏区的“族”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她精辟的指出“番地的族是一种政治上的划分,而不是宗族上的系统”。[29]该时期统计方法的运用也更加普遍。就笔者所及,用数据表格等形式来统计甘青藏区的人口、牧场、物产、道路、贸易、畜牧、僧人、寺庙等情况的文章达四五十篇之多,与前阶段相比,进步极大,代表性成果有《川青康藏驿路程站及青康藏喇嘛寺庙之分布》、《甘肃西南边区考察记》、《拉卜楞农产物输出统计表》、《青海至西藏道路旅程》、《拉卜楞藏区机关调查报告》、《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夏河县工商业统计》、《夏河人口比例》、《甘肃西固藏民社区分布于沿革》、《甘肃西南之森林》、《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等。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诸考察家解释甘青藏区社会历史文化的思想工具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仅利用自然科学中的分类体系、定性标准、计算公式等,而且在其论著中,许多引领当时世界社会思潮的理论方法都有体现,如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地理学、功能主义、参与式调查法、跨文化比较法、数据统计法等。同样,也正是由于该时期国人用于解释甘青藏区社会的思想武器开始逐渐科学化与理性化,对藏族社会及文化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化,贬低误读式的言语较为少见。很多考察家对民风淳朴的藏族人民,极力赞扬。庄学本曾道“但事实上朴质忠厚为先天优秀的国民,兹举一实例证。”[30]另外一些考察家对藏族文化的评价极高,有人在目睹塔尔寺精美绝伦的寺庙建筑之后,反问道“谁说蒙藏民族没有先进的文化呢?”[31]顾颉刚先生的话则更具有代表性,他说“刚未到番地的时候总以为番民尚保持着野蛮之习惯,未受文化的陶冶,及亲涉其地,见其平民彬彬有礼貌,亦无赤贫之家,其寺院则精美宏伟逾于皇宫,其喇嘛则埋头治学,献其全部生命于经典……”[32]。
抗战胜利后,由于特殊的国内环境,内地考察家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又呈现出凋零之态。也正因如此,本地“学人”的调查研究成果得以凸显,从论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最大的特点是部分文章隐隐带有“文化自觉”之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甘青藏区的一些开明藏族人士兴办的地方性报纸,其中又以《拉卜愣实验日报》和《玉树实验简报》最为典型。两者都创刊于抗战末期,分藏汉版,每日一版,每版一面,内容除了国内国际形势外,也刊登一些介绍或研究玉树、夏河等地的文章。虽然这两份报纸的发行范围仅限部分地区,但其意义并不止于是甘青藏族人士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同时它们也宣告了藏族的精英人物已经开始自觉运用现代化传媒方式来向国人介绍本民族文化,其中一些文章也已开始思考改进藏族文化的出路,部分建议可圈可点。如拉卜愣的一些藏族人士有感于藏民卫生条件之恶劣,在《拉报》上积极呼吁改进该地的卫生情况,提出了清除街道、禁止随地大小便等意见,而且还在该报上设每日卫生专栏,刊登卫生医疗的常识。
其二是部分“本地”学人此时频频发声,且在某些领域的研究走在了当时的最前列,一些藏族精英人物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话语权也逐渐的转向“本地人”。此类人物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些藏族上层精英人物和青海本土培养的藏学学者,主要代表有锁藏佛、黄正清、杨复兴、吴均、杨质夫等。黄正清无疑是民国时期甘肃藏区声名最为显著的政治领袖之一,对本民族文化,他的看法颇有深意,道“同一种生活在观念和方法上习惯后,自有其心得和长处,若硬性改变,一定会生出毛病的”[33]。另外一位甘肃藏区的政治领袖—杨复兴对于藏区政教合一制度也有些言论,其《安多藏区卓尼之现状》一文虽多偏颇之语,有维护统治之嫌,但它是藏族精英人物对“自我”文化反观的一种尝试,而且文中对该制度有一些评价,虽有夸大,但对它在稳定社会、联系西藏等方面价值的考量亦不无道理。吴均和杨质夫是早年创办的青海藏文社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杨氏还被誉为青海“藏学之父”,他们藏语文娴熟,对喇嘛教经典也理解的较为透彻,是民国时期青海籍藏学学者的最杰出代表。吴均的《玉树区藏族部落之变迁》一文对历来混淆不清的玉树二十五族的族称、分布、分离、合并等作了研究,彻底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玉树调查研究者的难题,其史料运用之准确,探讨分析之深入,至今仍无法超越,是民国玉树研究的必读经典。杨质夫也发表了《塔尔寺研究》、《塔尔寺的灵魂—宗喀巴》等一系列文章,在《塔尔寺研究》一文中,他参考藏文史料对塔寺的位置及地势作了交待,另外他从“主位”角度来介绍藏族人民,称他们“心地坦白,诚挚善良”[34]。第二类是甘青籍旅外学人,主要有谷苞、马献瑞等。谷苞先生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专业,后在甘肃南部进行长期调查研究,陆续发表了《甘肃藏民的支派及分布》等9篇文章来具体阐述他对藏族社会的认识。从文章反映的内容看,他对藏族社会的理解,既有从人类学专业角度的分析,也有作为陇上学子对境内藏族的热爱与认识。他曾言“内地的很多重要问题,在边疆上照样发生着,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时候,由于内地与边疆发生问题的文化背景不同。”[35]这种看法看不到站在“客位”角度过度阐释或贬低误读的影子,也没有从“主位”角度一味的为藏族文化做辩护,评价相当清醒、客观,是“本地”学人对藏族社会认识的一大进步。马献瑞长期游学内地,学习畜牧卫生,本时期他返青后,经过细致调查,撰写了《青海防疫事业之重要性》等文章,他从多方论证青海兽疫防疫事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就后来青海发展而言,实际上抓住了青海畜牧事业的关键点,这也是“本地”人对“自我”发展科学认识的又一典型代表。总的来说,文中所言的文化自觉,显然不能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直接对应,这些著述仅仅是朦胧之中带有早期文化自觉色彩,至于甘青藏区文化自觉历程的真正发展,那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藏族知识分子的培养、成长,但笔者认为把民国后期的“本地”学人撰写的成果看作是文化自觉早期历程的起点之表现亦无不可。
三、时代场域与认识过程——原因总结
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认识由模糊不清渐能述其大致轮廓,乃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整个过程中,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各具特点,从倾向于“自我”文化运行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条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的大量涌现之过程。而我们知道20世纪30、40年代的相关甘青藏区的民族志文本,是当时特殊的时代场域与个人志趣相结合的产物,时代的影子不仅永远印刻在诸多民族志文本中,而且在国人认识甘青藏区的这个动态过程中处处体现,同样透过遗留下来材料,也能看出宏观大背景如何作用于微观的甘青藏区调查研究。
探究20年间“他者”对甘青藏区认识变化之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对民族志文本表述客体的分析,而其中作者群体的知识结构、身份职业显得极其重要。第一阶段作者群体身份结构最大的特点是官员类作者占据主导地位,经典论著皆系政府官员所撰,如马鹤天、杨希尧、张元彬、龚谨、邓隆、方范九、梁炳麟、田生兰、冯国瑞、林竟等,个别记者也有几篇突出著作,如顾执中、陆怡、范长江、陈赓亚等,然该时期学者群体对该地关注不够,表现低迷,仅出现了张其昀的《洮西区域调查简报》等几篇文章。另外从学历层次上看,自海外获学位归来者和国内研究生毕业者,寥寥无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专业出生的,尚无一人。第二阶段作者身份之组成则更加多元化,官员、学者、学生、记者、中小学教师、医生、银行职员、艺术家及其他类考察家都积极踊跃,尤其是学者群体表现尤为突出,诸多经典成果都系该群体所撰,如李安宅、于式玉、顾偕刚、李式金、梅怡宝、葛定邦、徐旭、郝景盛、张松荫、黄明信、韩儒林、何正徨、徐寅初、王子云、薛文波、高一涵、佟树蕃、吴信法、常英瑜、耿以礼等,此类作者或系归国博士,或系国内一流大学研究院毕业,或受教于学术大家,或是某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此外就所学专业而言,本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科班出生的有李安宅、俞湘文,文史地理教育经济类专业出生的有顾偕刚、陈秉渊、梅怡宝、史汝庸、葛定邦、郑西谷、黄明信、于式玉、韩儒林、徐旭等。总的来说,就知识结构及教育层次而言,较之上阶段,本时期专业学者的论述更多,学历结构也更进一步提高。从实地考察周期上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也明显逊色不少。马鹤天是第一阶段在甘青川边藏区旅行最长的作者,共计两年有余,其他如张文郁在拉卜愣考察三个月,顾执中、范长江、林鹏侠、高良佐、高长柱等在甘青藏区的旅行时间都在十几天左右,很多考察家都属在藏区走马观花式的一瞥。而在第二阶段情况大有改观,李安宅、于式玉在拉卜愣调查两年有余,至今在民族学人类学界仍保持记录,无人打破。黄明信在拉卜愣寺从事学习研究工作也有八年多的时间。李式金横穿甘青康云四省,在藏区旅行半年多。其他如顾偕刚、葛赤峰、王志文、俞湘文等人的考察时间基本都在一月以上,也有一些国人非连续性的旅行于甘青藏区,但多次深入,每次少则几十天多则几月之久,主要有阴景元、绳景信、倪楷等。
相关推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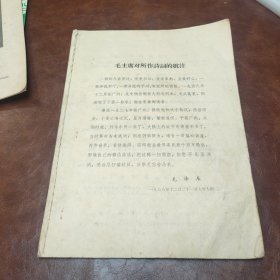
毛主席对所作诗词的批注 (书品见图)
八品武汉
¥ 40.00
-

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
九品长春
¥ 30.00
-

对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实拍图发货,所见及所得!
九品重庆
¥ 12.00
-

别册太阳 日本之心系列 韩国的民艺探访 “柳宗悦所见之世界”对谈
九五品北京
¥ 200.00
-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家山汉简中所见西汉初年国家对官吏犯罪的惩治措施
九品长春
¥ 48.00
-

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 北京联合出版 苏小懒 聚焦两个年龄人群对恋爱所抱持的不同态度 奋不顾身的爱 都市言情小说青春
全新吉安
¥ 33.88
-

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 北京联合出版 苏小懒 聚焦两个年龄人群对恋爱所抱持的不同态度 奋不顾身的爱 都市言情小说青春
全新益阳
¥ 33.88
-

人民日报,1973年8月21日把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办好,其他详情见图,对开6版。
八五品枣庄
¥ 18.00
-

建工部建研院结构所对目前全国有关新结构块的调查摘要资料【16开油印本/1965年见图】AA12
八五品天津
¥ 20.00
-

西方的智慧:从社会政治背景对西方哲学所作的历史考察 【大16开精装 一版一印 3000册 见描述 馆藏】
八五品石家庄
¥ 170.00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