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none
¥ 3 0.9折 ¥ 32 九五品
库存38件
作者()太宰治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1861
出版时间2017-08
版次1
装帧其他
开本32
页数280页
定价32元
货号xhwx_1201536961
上书时间2024-10-31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31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正版特价书籍
- 商品描述
-
目录:
译者序
人间失格
斜阳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太宰治经典小说人间失格斜阳。人间失格(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本小说家太宰治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48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描写主角从青到中年,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用药物麻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被爱的情愫。斜阳以战后本的混乱为背景,描写了落没贵族斜阳般的生活。全文除了表现颓废、无奈,还将生活的一缕光彩寄予了主人公和子,使得斜阳在颓废的暗调中闪出一抹亮。
作者简介:
太宰治(19091948),本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创作,五次殉情,很终情死,本无赖派大师,毁灭美学一代宗师。本战后新戏作派代表作家,生于清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本名津岛修治。父亲曾为贵族者员,并在本乡兼营银行。为农民,家筑高墙,太宰治住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有种内疚和不安感,甚至出现了一种罪恶感,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
精彩内容:
译者序主动选择丧失为人的资格 感谢您在不知凡几的太宰治译作中选择了这一本。下文会有少量“剧透”,可能妨碍阅读体验,因此建议您读完小说再回头来看这篇序言。 面对太宰治的著作,大部分疑问会围绕“他是怎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阴郁黑暗才会塑造出一个‘人间失格’,即丧失了为人资格的男主人公?”“为何要阅读太宰治?”“应如何解读他人生后一部代表作?”等展开。 我的回答是,请放弃对“过去”的好奇。关于太宰治的过去,既包含曾客观存在的事实(即“经历”),也容纳着人对这些事实的主观修饰和编译,是某种意义上的干扰信息。 一方面,在文学研究中,有所谓的“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概念,如同无形的绳索,将对作品原有价值的理解封锁于一座容量有限的幻境。一位作家的经历确与时代息息相关,然而他作品所能抵达的深度,却未必会受时代、受“过去”制约。有大智慧的作家,往往先时代而行。另一方面,小说是虚构的,作家笔下的“过去”可以由他重塑,由阅读者赋予五光十的诠释,这意味着小说中不存在客观既定的作家的“过去”。想要从“过去”解读作品这一认知本身,即会让自己陷入“原因论”的局限与障碍。邂逅一部小说,重要的是读者“如何解读”它说了什么,而非它为什么要这样说。 当然,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读者不应当了解作家的基本信息。适度的信息量有助于消解初次阅读带来的距离感。对太宰治较为陌生的读者,不妨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小说家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本东北地区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现五所川原市)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贵族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自1929年起,太宰治先后经历过至少四次未遂,有两次分别是与当时的情人和当时的妻子。他的人生终结于人间失格完稿一个月后的后那次。在他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文学、、药物、女人是将他与世间连接起来的主要介质,这让他受到的非议与褒奖几乎等量。比如致力于弘扬本传统美、凭小说雪国古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明确表达过对太宰治其人其作的不满;几年后又因太宰治的一部短篇小说女生徒,而对他大加赞赏。 太宰治以薄薄一部人间失格为本与中国读者所熟知。据统计,仅本新潮文库便累计发行超过600万部人间失格,可与夏目漱石代表作心几十年来的累计发行量媲美。在现代本,人间失格依然拥有大量读者,并被改编、再创作为电影和动画作品,如电影人间失格 、动画青之文学 等。 一直以来,都有人将人间失格视为半自传体小说,将男主人公大庭叶藏遭遇的“痛苦”归咎于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同时结合太宰治本人的生,认为太宰治在借叶藏之完成弱者的自白。这不失为一种大众式的解读方式。而这里我想提供一条不同的触碰路径。 需要借助的是阿德勒心理学 的几个概念: ,目的论。阿德勒认为人会采取何种行为,不是根据过往得出的经验,也不是由于曾经遭受的创伤,而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自主进行的选择。这一理论否定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潜意识论”。 第二,课题分离。比如,学走路是孩子的课题,孩子走路是父母的课题。理想的是,孩子学走路,父母从旁守护、提供支援,这是明确的“课题分离”;倘若父母在孩子走路的过程中,为了避孩子摔跤而剥夺其走路的权利,则属于擅自揽过孩子的课题。 第三,自我接纳。与自暴自弃的根本区别在于,自我接纳意味着正确审视、评价自我的优缺点,包含坚定向上的意愿,即人具备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 第四,“lifetyle”,即生活方式、生存之道。人能基于主观意愿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改变自我与人生。这一理论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内驱力,否定人会被过往经历、情绪、经验支配。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来具体看看。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书写的那一刻,他本身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他的所思所写均始于那一刻,既不是过去,也绝非未来。在那个当下,“过去”是不存在的,更不会对他造成束缚与支配。他会这样写、那样想,则来自他此刻拥有与“这样写”“那样想”所匹配的目的。因此我以为,整部人间失格展示的便是太宰治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让叶藏择取的某种生存之道。他的痛苦并非来自过去、他人、世道和时代,而是来自他对它们的诠释、对自我的定位。所谓的“丧失为人的资格”,是叶藏主动选择了活得不像个人样,是他自发贯彻了向下的人生观,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消解源于人际关系网的烦恼和伤害。 大庭叶藏从小对世俗生活、周遭环境与他人(包括家人、仆从、老师、同学以及去东京后结识的所有人)怀着强烈的不信赖和被害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个体,他很明白自己不可能置身“世”外。无论走到哪里,“世间”(人际关系)都包围着他,他也无法“对他们死心”。苦恼于面对世间的他,发现了一个办法,即扮演小丑,哗众取宠,以此缓和甚至消除他人对自己的“敌意”,用他的话说,是“之绝不能碍他们的眼”。而实质上,这是一种使他和他人关系得到某种“和解”的手段,能让自己从他人“不怀好意”的注视中解脱出来。比如,尽管根本不想要狮子舞,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礼物。他的理解是,这是父亲希望他要的,只有接受,才能实现不激怒父亲、于被父亲惩罚的目的。又比如,面对家里仆人对他身体的侵犯,他选择沉默地忍让,出发点是为避在此种人际关系中,自己得不偿失,反被玩弄。 那么,这样一种处理外界与自我关系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对讨厌的事物不敢说讨厌,对喜欢的事物,却如同行般偷偷地喜欢,到头来只能品尝到个中苦涩,以及难以言喻的恐惧感。”也是说,他变成了一个不敢自由表达自我意志,一味迎合他人、满足他人意愿的人。他的人生不再是“大庭叶藏的人生”,而是父亲的人生、他人的人生。 无论在老家还是在东京,他的行为指向在于“逗他人发笑”,终目的还是保护自己受人际关系中他所定义的“伤害”。哪怕多次被女人们心怀善意地收留,隐约感受到她们“毫无算计之心”的温柔,他依然紧抱被害意识,缺乏信赖对方(比如静子)的勇气,更缺乏即便受挫,即便颠覆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要坚定向上的勇气,转而使用让人生向下的廉价手段,如嫖妓、酗酒、与女人纵情声、装模作样地参加左翼运动、沉湎于药物比起坚定向上,这些手段要来得唾手可得得多。借由它们,他觉得同样可以维系现有的人际关系,保护自己立足于相对安全的境地。 长期以来,他置身在满足了他人意愿的象之中,逐渐模糊本来应有的“自我”,而一旦失去他人意愿作为指引,便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人生。比如小说后,长兄告诉他父亲病逝,他成了这样一种:“自从得知父亲病故后,我变得越发萎靡不振我觉得自己那装满苦恼的器皿仿佛变得空荡荡的。我甚至想着,那个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格外沉重,是那位严厉的父亲造成的。” 说起来,这个“苦恼的器皿”真的是由父亲造成的吗?难道不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说服自己,而刻意制造出来以求得心安的一种责任转嫁行为吗?事实上,父亲是怎么想的、父亲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是父亲的“课题”,不是他需要在意的。诚然,在文明社会,一个独立个体与他人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切断的联系,然而即便扮演“儿子”这一角,也不应干涉父亲的意志;同样作为父亲,亦无须干涉儿子的意志。但是,叶藏妄自揣摩父亲的意图,认为父亲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把他人的人生背负在肩上,以此替换掉“大庭叶藏”的人生,将自身定位为获得他人认可的滑稽道具,也难怪入目皆是敌意与。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篇小说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弟弟直治身上。 这部小说分四回连载于新潮1947年7月至10月号。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昭和二十年(1945)为起点,讲述了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和子,先后遭遇父亲病逝、离婚、产下死婴等一系列挫折后,与母亲搬离东京,去往伊豆乡间生活。不久,弟弟直治复员回家。母亲患上肺结核,身心俱疲地离世。而被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姐弟二人,面对翻覆的天地,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小说发表后,和子与弟弟直治备受读者关注,很快引发了不同阶层的声音。文辞典甚至为“斜阳”一词添加了新的注释:斜阳即没落,斜阳族即没落的上流阶层的代称。在太宰的故乡青森,修建于明治时期的津岛家老宅亦被辟作太宰治纪念馆——斜阳馆,并被指定为级保护建筑。 故事中,直治展现出与叶藏相似的苦恼,将自己定位为像“细草”一样无能。在他的主观认知里,身边大部分贵族徒有其名,只有纯粹美丽又优雅的母亲是真正的贵族。怀有重度劣等情结的他,将母亲的形象等价于一种理想人格——,更不可模仿。母亲以外的世界对自己充满敌意。“同那些与我出身截然不同、阶级截然不同的同学交往,他们像顽强的野草。我被他们的强势所压制,不愿屈服”,映现在他眼中的外界和他人从来缺乏善意,生来劣等的自己要想融入其中,唯有采取更加粗暴“向下”的手段,像他在遗书中提到的游手好闲、懒惰好、贪图享受等。这样做才能“变成一个下流的人,变成一个强悍,不,一个之徒。我想这才是成为所谓的民众之友的途径”。同时,这些粗暴手段还拥有附加效应,即利用它们,可以直接迅速地完成对“野草”的反抗与报复。 然而,四肢健全、爱好文学、具备洞察力的直治(即便复员后可能罹患了战后心理综合征)果真是个一无是处的无能之人吗?民众果真像他在意自己一样在意、挑剔他,并从一开始只想赏赐给他一张“恶意满满又中规中矩的旁听席”吗?他所处的世界果真处处伪善险恶吗?反过来思,倘若直治没有怀抱这种劣等情结,选择善意地看待民众,选择与原来相反的生存方式,坚定往上,颠覆自己的惯思维,他的人生会不会走向迥然不同的境地?我的判断是“会”,毕竟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哪个“他人”握有开启其人生每一条支路的钥匙呢? 在我看来,直治在进入“世间”的起初,已主动放弃了靠自我赋予人生彩的觉悟,而选择将人生的彩赋予权交由民众,交由他人,选择了一种看似轻松简便、风险系数相对较低的生存之道。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迎合他所以为的民众的需求。他所说的“我连对着人敲诈勒索的本事都没有”,也不是他的“无能”造成的,而是他为在民众阶层求得没有摩擦的一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为什么?因为与人相争必然产生摩擦,有摩擦便可能导致自己被排挤于他人之外。而被排挤于他人之外,则会进一步加剧他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敌意,让他双足悬空,连已经惯的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无法维系。的来说,是他的“无能”并非“过去”的经历所导致,而是为了延续至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他判断自己需要变得这样“无能”。 太宰治在小说中曾分别为叶藏和直治的行为做出过某种注解: 我不明白,越是努力思越是不明白,仿佛只有自己是异类,继而被巨大的恐惧和不安笼罩。我几乎不再同别人讲话,不知道说什么,更不知道怎么说。 ——人间失格 不论做什么都感觉难为情,感觉无尽的不安。终惴惴,丧失了容身之所。——斜阳 曾经我认为,正是由于叶藏和直治从小经历着这些“不安”,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才是不计后果、如履薄冰,永远站在世俗的对立面;在世俗不允许后退、放弃的地方,干脆而坚决地松手,被视作软弱无用、不合时宜的异类。但是现在,我想要推翻这一结论。 所有的“不安”,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叶藏和直治基于自身价值观进行解读、定义的泡影,作为生存之道的具体表现方式被他们挑中,并不断强化。他们生活在一个变形的主观世界中,无法接纳“劣等”的自己,却希望他人承认自己,让自己在其中寻到归属感。 我想,倘若叶藏和直治能够重新选择生存之道,不曲解、不在意他人的视线,不擅自闯入他人的领域,不背负他人的课题,转而恰当正视自我以及自我的能力,充实地用当下的一秒构筑人生,赋予自己改变现状的勇气,终切实踏出改变自我的步,那么他们原本怀抱的不安,也会从这一步开始逐渐消散。当然,这并不等于如此实践得来的未来不再存有任何阻碍或摩擦。有了阻碍或摩擦,去解决好了。重要的不是阻碍或摩擦的存在,而是人如何看待阻碍或摩擦,以及从中重拾坚定向上的勇气与方法。 如您对这一说法存疑,那么请对照看看故事中直治的姐姐和子所贯彻的生存之道,那是基于与直治迥异的价值观而进行的“道德”,二者的底与质地具有决定的不同。 后,我想说说书写这篇序言的初衷。一部作品的价值始于“被他人阅读”这一行为。也即是说,重要的是,阅读了作品的读者由此得出怎样的见解,在见解的作用下,如何重新思,与他人交流作品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碰撞,而终获得怎样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篇序言里写到的种种,包括借助阿德勒心理学进行的理解,仅是我的个人看法与思,并非导读,也不是太宰治作品的解读方式。 同时,要说明的一点是,阅读行为的障碍在于时空本身对文字的阻隔、沉淀和净化,在于一个独立个体无法对另一个独立个体地感同身受。为此,必须抛开表面的概念、、主义,抛开纠结于作家“过去”与“本意”的妄念,在“此时此刻”坦率地感受思。 感谢为本书出版工作予以耐心指导的编辑,感谢每一位阅读至此并愿意继续阅读下去的读者。廖雯雯2017年6月3
相关推荐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八品淮北
¥ 10.00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保定
¥ 14.43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3.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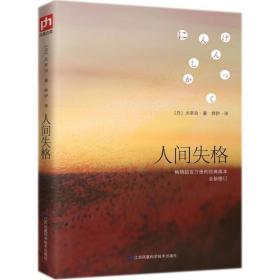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保定
¥ 5.86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9.85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9.45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7.35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6.95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17.55
-

人间失格 外国现当代文学 ()太宰治
全新北京
¥ 3.65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