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版】悉达多
⊙正版图书,库存10万,每日上新,择优发货~
¥ 20.37 5.8折 ¥ 35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SBN9787512513327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31290343
上书时间2024-04-06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8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作家,诗人,画家。1877年生于德国,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后一位骑士”。曾获歌德文学奖、冯塔纳文学奖。1946年由于“他那些富有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并为崇高的人道主义和高尚风格提供了范例”获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作有小说《彼得·卡门青》《在轮下》《德米安》《悉达多》《荒原狼》《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玻璃球游戏》,诗集《浪漫之歌》《孤独者之歌》等。
韩兆霆,于复旦德文系,现于德国慕尼黑攻读德语文学硕士。
目录
\\\"第一部
婆罗门之子
沙门
乔达摩
觉醒
第二部
迦摩罗
尘世间
轮回
小河边
船夫
儿子
唵
乔文达
《悉达多》文学大事记 \\\"
内容摘要
\\\"《悉达多》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的代表作。它并非是佛陀的故事,而是讲述了一个人追寻自我、叩问生命意义的精神历程。主人公悉达多的经历,象征了人生的九个阶段:作为婆罗门时,他追寻的是知识;作为沙门时,他追寻的是苦行;作为觉悟者时,他追寻的是自修;作为享乐者时,他追寻的是色欲;作为富人时,他追寻的是贪婪;作为底层人时,他面临的是危机;作为摆渡者时,他追寻的是倾听;作为父亲时,他追寻的是爱;作为觉悟者时,他质询的是超越。
黑塞说,人真正的职责,是找到自己的路。悉达多就是那些寻求自我之真理的人中的一个。\\\"
主编推荐
"至圣先师孔子曾在《论语》中留下这样的文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可当学习和思考遇到瓶颈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印度青年悉达多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为此,他烦恼多时,非常想找到解决之道。开始他跟随了苦修的沙门,后来又进入尘世经历了富贵和欢愉的洗礼,接着回到小河边迎来送往,最后终于有所得。
《悉达多》一书中努力探寻真理、实现自我成长的悉达多是无数追求自我成长的人的化身。此书一经推出,就深受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是欧美大学生人手一册的成长之书。荣格、托马斯·曼、亨利·米勒、保罗·科埃略都对其赞不绝口。"
精彩内容
\\\"这天晚上他们追上苦行僧,请求这几位身形瘦削的沙门接受他们的随行,还承诺会服从于他们。几位沙门同意了。
悉达多把他的衣服送给了街上一个穷苦的婆罗门。现在他身上只穿着一块遮羞布和一件未经缝制的土黄色大衫。他一天只吃一顿,且从不吃熟食。他先斋戒了十五天,然后又斋戒了二十八天。他的脸颊和双腿消瘦下去。他那双看起来比以前更大的眼睛中透出炽热的幻梦,干枯的手指上长出了长长的指甲,下巴上长出了干燥蓬乱的胡子。碰到女人时,他的目光变得冰冷;路遇衣着华贵之人时,他的嘴角露出了轻蔑。他看到商贩经商,王侯出猎,伤心的人哀悼亡者,妓女临街揽客,医生为患者忧心,僧侣指导播种,情人恋爱,母亲哺乳—但这一切在他眼里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在发臭,一切都因谎言而发臭,一切都假装是有意义的、幸福的、美好的,然而一切都已腐烂却无人言破。世味唯苦涩,人生是折磨。
悉达多只有唯一的目的:达到“空”。空无饥渴,空无欲望,空无幻想,空无喜乐与哀伤。超脱自身,不再做“我”,寻找放空心灵的平静,在无我的思索中迎接奇迹的到来,这便是他的目标。当“我”彻底被压抑以致不再存在,当心中所有追求和欲望都寂静下来,那时,那本质的、内在的、非自我的、终极的至高秘密必将觉醒。
悉达多一言不发地站在烈日下,饱受疼痛与焦渴的折磨,一直站到他不再感到疼痛和焦渴。他一言不发地站在连绵不断的雨中,水珠沿着头发滴落到冰凉的肩膀,落到冰凉的腰间和腿上,而这苦行人依然站着,直到肩和腿不再感到寒冷,直到它们失去知觉,全然麻木。他一言不发地蹲在荆棘藤蔓中,灼痛的皮肤下渗出了鲜血,溃疡中流出了脓水,悉达多却始终保持纹丝不动,直至他不再流血,不再感受到刺痛和灼热。
悉达多端坐着,修习如何留存气息,如何运用微弱的呼吸,如何屏息。他已学得随着呼吸使心跳平缓,随着呼吸让心跳减弱,直至心跳变得微弱到几乎消失。
在最年迈的那位沙门指导下,悉达多遵守沙门的戒律,不断修炼克己和冥想的能力。一只苍鹭飞过竹林上空,悉达多便将他的心魂寄于苍鹭之身,随它飞过森林和山岭。他化身苍鹭,以鱼为食,忍受苍鹭之饥,发出苍鹭之鸣,体验苍鹭之死。一匹胡狼遗尸沙滩,悉达多便将心魂滑入这具尸首,化身已死的胡狼,卧于岸边,任尸首膨胀、发臭、腐烂,遭鬣狗分食,被秃鹫撕扯,只剩骨架,只剩尘埃,散入原野。而悉达多的心魂重新归来时,已然经历了死去、腐烂、粉碎,品过轮回的神秘滋味,正满怀着捕猎般的期待,搜寻着打破轮回的缺口,根源的尽头,无虞永恒的起点。他摒弃自己的感官,抹去自己的记忆,从自我中脱离,化入万千陌生之物中,为动物、为腐尸、为石、为木、为水。每次在日光或夜色下重新醒来时,他又成为自我,跃入轮回,压抑这种渴求,又冒出新的渴求。
悉达多在几位沙门身边受益匪浅,他掌握了从自我中超脱出来的多种方法。他可以经受痛苦来脱离自我,面对疼痛、饥饿、焦渴、疲倦,他主动承受并将其一一克服。他可以通过冥思来脱离自我,面对一切表象进行探索奥义的空想,他已学得种种方法,千百次脱离自我而去,不顾时日地流连于无我之境。可是,这些修行之路均始于自我,最终也必将归于自我。尽管悉达多千百次逃离自我,逗留在虚空之中,逗留在动物、石头之中,回程也不可避免,归期也不可摆脱,但他会在日光或夜光下醒来,置身树影或阴雨中,重新成为自我、成为悉达多,也重新感知到轮回带来的折磨。
他身边伴随着乔文达,他的影子,与他同途修行,经受同样的磨炼。除非献祭和修行有所要求,两人极少互相说话。他们偶尔会结伴出门造访村庄,为自己和师父们乞食化缘。
“你怎么看,乔文达,”一次化缘途中,悉达多问道,“你觉得我们有所长进吗?我们已经实现目标了吗?”乔文达答道:“我们学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要再学。悉达多,你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沙门。每项修习你都掌握得很快,经常让几位老沙门感到惊喜。啊,悉达多,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一位圣人的。”悉达多说:“我的朋友,我并不这么觉得。乔文达啊,到目前为止,我从这些沙门身上学到的东西,我本可以更快、更轻易地学会。我的朋友,我在烟花柳巷的一处酒家中,跟着车夫和赌徒,都可以学到这些。”乔文达说:“你在和我开玩笑。在那种不幸的地方,你怎么能做到定心禅思,你怎么能做到屏息凝神,你怎么能做到对饥饿和疼痛无动于衷呢?”悉达多轻声回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一样:“禅定是什么?超脱凡胎是什么?斋戒是什么?屏息凝神又是什么?不过是逃离自我而已,是面对自我存在带来的折磨、生命的虚无和痛苦时,一段短暂的逃避和麻醉而已。寄宿在小客栈的牧牛人,痛饮起一碗碗米酒和发酵的椰奶,他也是在进行相同的逃避和麻醉。那时,他已感受不到自己,感受不到生命的苦痛。于是,他得到了短暂的麻痹。随着一碗碗米酒昏沉睡去之后,他所体味到的,却和你我在漫长的修习中脱离肉体、停留于无我时体味到的,是一样的感受。就是这样,乔文达。”乔文达说:“朋友啊,你虽这么说,但你也知道你毕竟不是牧牛人,沙门也不会是酒鬼。一个酒徒可能得到了麻痹,得到了短暂的逃避和喘息,但是他从幻想中回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切如旧,他没有变得更有智慧,没有增长学识,也没有登上更高的层次。”悉达多微笑着说:“这我不知道,我从没做过酒徒。但是我,悉达多,在我的修习和禅思中只找到了短暂的麻痹,如今依然和母胎中的婴儿一样,距离大智和解脱格外遥远。这我可知道,乔文达啊,这我可知道。”又有一次,悉达多和乔文达离开树林来到村中为他们的同门和师父乞食时,悉达多开口道:“现在如何呢,乔文达?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了吗?我们更接近知识了吗?我们更接近解脱了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在原地转圈—我们本来不是要打破轮回吗?”乔文达说:“我们学到了很多,悉达多,也还有很多要学。我们没有原地转圈,我们在向上攀登,这是一个螺旋,我们已经登高了好几层。”悉达多答道:“你说,那位最年长的沙门,我们尊敬的师父,他多大了?”乔文达说:“他大概有六十岁了。”悉达多说:“他已经六十岁了,还没有实现涅槃,他必然会迎来七十岁、八十岁。你和我也是,我们都会变得那么年老,我们会一直修习,一直斋戒,一直冥思,但是我们实现不了涅槃,他不行,我们也不行。乔文达啊,我相信,在所有沙门之中,可能没有一位,没有一位能实现涅槃。我们只是安慰自己,我们只是麻醉自己,我们只是用学来的各种技艺迷惑自己。然而最本质的东西,那条道中之道,我们却没有找到。”“别这么说,”乔文达说,“你不要危言耸听,悉达多!在这么多渊博的人,这么多婆罗门,这么多严谨而可敬的沙门,这么多求道者,这么多真心努力的人,这么多圣人之中,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找到过那道中之道?”悉达多的声音中有几分讥笑便有几分忧伤。他以一种半是忧伤半是讥笑的语气轻声说:“乔文达,你的朋友很快就将离开这条多年来同你共行的沙门之路。乔文达啊,我备受渴求的折磨,而在这段长长的沙门之旅中,我的渴求丝毫没有得到满足。我依旧向往知识,我依旧满心疑惑。我求教于婆罗门,年复一年;我求教于《吠陀经》,年复一年;我求教于虔敬的沙门,又是年复一年。也许,乔文达啊,假如我向犀鸟和猩猩求教,也一样有益,一样有启发,一样有成效。我已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现在依然在花时间,只是为了发现。乔文达啊,人无法学到任何东西!我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我们口中称为‘学习’的这种东西。我的朋友啊,只存在一种学识,它无处不在,它就是阿特曼,它在我之中,在你之中,在每个本体之中。我开始相信,这种知识最大的敌人就是对它的探求,就是学习。”乔文达停下脚步,举起双手说道:“悉达多,你难道想用这番言论吓坏你的朋友吗?说真的,你的话让我心生恐惧。你就想一想: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没有‘学习’的话,祈祷的神圣何在?婆罗门身份的崇高何在?沙门的伟大何在?!那些,悉达多啊,那些世间神圣的、珍贵的、令人敬仰的东西,又都成了什么?!”随后,乔文达低声诵起一段《奥义书》中的诗句:魂灵澄净,沉思禅定于阿特曼者,其心之极乐无以言表。
悉达多沉默了。他思考着乔文达的话,思考这话的一切含义。
他垂头伫立,思忖道:“对啊,我们看起来神圣的东西,还会剩下什么?什么东西能留下?什么东西能保存?”他摇了摇头。
当两位青年跟随沙门修行了将近三年时,他们从各地大街小巷听闻了一则流言,或者说一则传说:有一人现身,唤作乔达摩,他是世尊佛陀,他已战胜现世苦难,止息转生轮回。他云游于世间,传道授业,身边弟子环绕。他一文不名,居无定所,遑论妻小。他是一位身披黄色长衫的苦行僧,也是一位明智的得道之人。婆罗门和王侯们纷纷向他躬身行礼,拜师为徒。
这流言蜚语,或者说这个传说流传开来,一时间各地议论纷纷。城中的婆罗门和林中的沙门都谈及此事,两位青年的耳边不断响起佛陀乔达摩的名字,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倘若有一国瘟疫横行,必然会出现传言称,某处有一位智慧的圣人,仅凭秘语和仙气便可以拯救深陷于水火之中的人们。这传言也必然鼓噪一时,举国皆知,人人议论,有人深信,有人质疑,也有人不由分说出发上路,要去寻访这位智者、救星。正如此一般,佛陀乔达摩,这位释迦宗族智者那诱人的传说,就这样传遍了全国。一众信徒声称,他已然掌握了至高的知识,记得前世生命;他已然实现了涅槃并且摆脱了轮回,不再隐匿于形貌的浊流之下。他口中所言奇妙绚丽,令人难以置信;他曾留下神迹,制服妖魔,得与众神明交谈。他的敌人们和反对者则称,这个乔达摩是个虚荣自大的骗子,他挥霍度日,鄙夷祭祀,不学无术,况且他既不懂潜心修炼,又不会清苦修行。
佛陀的传说听起来十分诱人,散发着一股魔力。世间的确病入膏肓,人生也令人难以承受—但是看啊,这里好似有一股清泉喷涌而出,这里好似有一个预兆已然彰显,予人慰藉,温柔委婉,带来了高尚的诺言。印度众邦国中,无论何处,只要传来佛陀的传闻,少年们便侧耳倾听,满怀渴慕,满怀希望。婆罗门迎宾接客,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来者是旅途中的僧人还是陌生人,只要他们带来了他,那位圣人,那位释迦牟尼的消息,就会受到欢迎。
即使是林中的沙门,即使是悉达多和乔文达,也渐渐地、一点一滴地、半含希望半含怀疑地对这传说有所耳闻。他们很少谈论此事,因为那位最年长的师父并不喜欢这则传言。他听说,这个自称佛陀的人也曾是住在林中的苦行僧,后来却重归世俗的富足与享乐之中,因此他对这个乔达摩丝毫没有好感。
“悉达多啊,”一天,乔文达问他的朋友,“今天我在村里时,一位婆罗门邀请我去他家,他家里有一位来自摩揭陀 的婆罗门之子,那人亲眼目睹过佛陀真身,还听过佛陀的施教。真的,我顿时就感到一阵胸闷。我就想:难道我,难道悉达多和我,我们两个不该经历一次那位圆满者的亲口施教吗?你说,朋友,我们难道不想去那里聆听一次佛陀的亲口施教吗?”悉达多说:“乔文达啊,一直我都以为,乔文达会留在沙门之中;一直以来我都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活到六七十岁,然后继续修习锻炼沙门这一套表面功夫。不过,你看,我对乔文达太不了解了,我太不懂得他的心了。如今你,我的挚友,也想要选择去走一条新的道路,一条追随佛陀教义的道路。”乔文达说:“你总是喜欢嘲笑我。你想嘲笑就嘲笑吧,悉达多!你心中难道不也升起想去聆听佛陀施教的愿望和兴趣吗?你不也有一次跟我说过,你不想再继续走沙门之路了吗?”悉达多听闻此话,以他独有的方式莞尔一笑,笑声中带有一丝忧伤,也带有一丝嘲讽。他回答道:“很好,乔文达,你说的不错,你的记忆也无误。希望你也记得你从我这里听到的其他话,我说过我已经对教和学感到失望和无奈了,我不怎么相信师父传授给我们的言辞了。但是好吧,亲爱的,我已经准备好听听这次的施教—尽管我内心坚信,我们已经品尝过他的教义中最美味的果实了。”乔文达说:“我很开心你愿意去,但是你说说,这怎么可能?我们尚未领受乔达摩的施教前,怎么可能已经摘下其中最美味的果实了呢?”悉达多说:“让我们好好享用这颗果实,然后继续期待吧,乔文达!我们要感谢乔达摩送来这颗硕果,是他召唤我们离开这些沙门!至于他还能不能带给我们其他更好的东西,朋友啊,我们就平心静气地等待吧。”就在这一天,悉达多告知最年长的师父,他去意已决。他以作为后辈和学生最为得体的礼仪谦卑地向师父提出请求,然而这位沙门恼羞成怒,听说两位青年都要离开,对他们高声痛斥,破口大骂。
乔文达惊慌失措,窘迫不安,悉达多则凑到乔文达耳边低声说道:“现在我要让老师父看看,我在他身上还是学了些东西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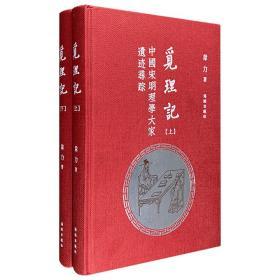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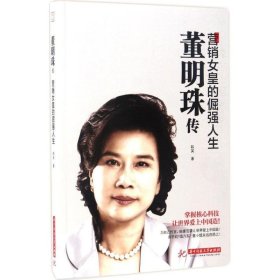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