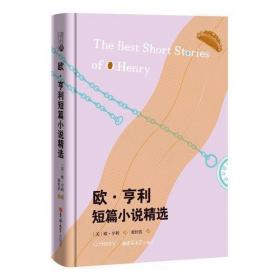
读经典-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16.66 4.6折 ¥ 36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美]欧·亨利 著;张经浩 译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3
版次1
装帧精装
货号603 12-16
上书时间2024-12-17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美]欧·亨利 著;张经浩 译
- 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9-03
- 版次 1
- ISBN 9787569227796
- 定价 36.00元
- 装帧 精装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内容简介】
- 本书是欧·亨利短篇小说经典精选集,包括《圣贤的礼物》《*后一片叶》《警察与圣歌》《带家具的房间》《二十年后》《财神与爱神》《一千元》等。这些作品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脍炙人口,流传不衰。作品轻松幽默,情节曲折,结局出人意料。我们用*接近原著的笔触更准确、更幽默、更真实地还原欧·亨利的写作风格,向读者展示这位世界*作家独具特色和风格的短篇小说的魅力,以期读者在感受原作的魅力之余,熟悉其历史背景、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了解其社会习俗、人文心理及价值观念;品味人生,增强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感悟,提高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 【作者简介】
-
欧·亨利(1862-1910),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欧·亨利”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以“含泪微笑”的创作风格,出人意料的“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他的一生十分传奇,曾做过药剂师、画家、出纳员,歌手、演员、记者等多种职业,并一度入狱,服刑期间认真写作,后成为职业作家,共留下一部长篇小说和近三百篇的短篇小说作品。
张经浩,生于1942年,湖南长沙人。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曾先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1986—1992年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著作与编著有:《简明英语语法》《英语常用同义词解说》《译论》《名家名论名译》;译作有:《冰岛迷雾》《爱玛》《世界名作家小说精华欣赏》《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司各特短篇小说选》《傲慢与偏见》《马丁·伊登》。
- 【目录】
-
警察与圣歌
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带家具的房间
托宾的手相
圣贤的礼物
二十年后
最后一片时
为麦克花的钱
财神与爱神
没说完的故事
五月是个结婚月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命运之路
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
好汉的妙计
剪狼毛
决斗
布莱克·比尔藏身记
各有所长的结局
绿色门
经验与狗
几位侦探
一千元
十只与六月
纪念品
“真凶
无缘
似戏非戏
寻找巧遇的人
托尼娅的红玫瑰
生活的波折
多情女的面包
忙碌经纪人的婚姻大事
赶车人的乘客
某天下午的奇遇
杰夫·彼得斯的感应功
一枚银圆的妙用
改邪归正
贝尔二六九二号档案
人心难料
抢劫列车
心与十字
内容摘要·亨利短篇小说经典精选集,包括《圣贤的礼物》《·亨利的写作风格,向读者展示这位世界*作家独具特色和风格的短篇小说的魅力,以期读者在感受原作的魅力之余,熟悉其历史背景、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了解其社会习俗、人文心理及价值观念;品味人生,增强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感悟,提高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主编推荐·亨利1862-1910)·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欧·亨利”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以“含泪微笑”的创作风格,出人意料的“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他的一生十分传奇,曾做过药剂师、画家、出纳员,歌手、演员、记者等多种职业,并一度入狱,服刑期间认真写作,后成为职业作家,共留下一部长篇小说和近三百篇的短篇小说作品。
1942
精彩内容警察与圣歌
索彼在麦迪逊广场麦迪逊广场是纽约市的街心花园。的长凳上总不得安稳。等到夜晚听到雁群拉大嗓门儿叫唤时,等到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丈夫殷勤起来时,也等到索彼在公园的凳子上总不得安稳时,你就知道,冬天即将来临。
一片落叶飘到索彼的膝上。这是冬先生送的名片。冬先生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素来体贴,每年来前总要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交叉路口处他的名片是叫北风送的,因为风是露天大厦的看门人,这一来睡街头的人就会有所准备。
索彼的心里已经有数,知道严冬逼近,他得单枪匹马想办法对付。所以他在凳上不得安稳了。
索彼过冬的打算并非什么宏图大略,他既没想去地中海游弋,也没想到南国休眠,或者在维苏威湾位于意大利,为避寒胜地。泛舟。他只巴望能到岛上监狱设在岛上。待三个月。三个月里不愁吃住,有合得来的伙伴,北风吹不着,警察不找麻烦,他就谢天谢地,心满意足。
好些年冬天他待在大方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比他命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两处均是避寒胜地,前者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后者在意大利。,而索彼可怜巴巴,年年只能当穆罕默德,逃亡到岛上。现在又到这种时候了。昨天夜里,他睡在这个老广场靠近喷泉的长凳上,用三份星期天的报纸星期天的报纸张数多,作者的这种说法也是种幽默的说法。垫着上身,盖住腿、脚,还是挡不住寒气。所以那个避难岛又浮现到索彼的脑海里。市里对无家可归的人本有一些救济,即所谓“施舍”,可他瞧不上眼。在索彼看来,“博爱”的慈悲之心还比不过法律。市里办的和慈善团体办的机构比比皆是,只要他肯进,有吃有住,能过规范的简朴生活。但索彼性傲,不肯要别人发善心相助。出自慈善家之手的馈赠,虽说你不破钞即可得,但要以心灵受屈辱为代价,件件如此。恺撒大将尚且没逃过布鲁特斯之手恺撒原为古罗马大将,后成为皇帝。布鲁特斯为罗马元老贵族。据史载,恺撒的执政方针侵犯了元老贵族的利益,结果被以布鲁特斯为首的元老派刺死。作者提到这个典故也是一种夸张和幽默。;哪个要住慈善机构的床,非得先把一身洗干净不可;哪个要吃块面包,就得让人盘问自己的隐秘。因此还不如做一趟牢中客,固然监狱中规矩严格,但毕竟不会瞎干预君子的私事。
索彼一旦决定了去那岛上,便着手实现他的打算。要办到办法又多又容易。惬意的是到哪家高档餐馆美餐一顿,吃完直截了当说钱已用得精光,让人往警察局一送,干干脆脆,没声没响。往下的事自有好说话的法官料理。
索彼从凳上起身,走出广场,穿过百老汇与五马路相交处老大一块平坦的柏油路口。他转进百老汇,在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前停了下来,这儿夜夜摆着上等的美酒佳肴,坐着衣冠华丽的宾客和社会中坚人物。
从背心下一颗纽扣往上看,索彼觉得自己的仪表准没问题。脸刮得干干净净,上衣还算体面,还打了一根干净的黑色活结领带,那是感恩节一位女传教士送的。如果他没引起人怀疑,能走到这家店的一张桌子边,那就稳操胜券了。露出桌子的上半身叫服务员看不出破绽。索彼想,要只烤野鸭差不多,外带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和法国名干酪,一杯黑咖啡,一根雪茄。一美元一根的雪茄足够了。几件东西加起来钱不会太多,太多了店老板会狠狠教训他一顿的。吃完了喝完了他也就饱了,高高兴兴地上路,去他过冬的避难所。
没承想索彼一踏进店门,领班服务员一眼就瞧见了他那已经磨破的裤子和不成体统的鞋子。他被一双又有力又利落的手扳转身,没声没响推出来,那只野鸭也就逃脱了遭暗算的厄运。
索彼没再走百老汇路,觉得美餐一顿白食不是个办法,到岛上去此路不通,进那个既非天堂又非地狱的地方得另想办法。
走到六马路的一个路口,只见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电灯通亮,商品琳琅满目。索彼捡起块铺路石把玻璃砸碎了。行人从两边拥过来;跑在前头的正是个警察。索彼站着没动,双手插在衣袋里,望着那衣上有铜纽扣的人警察服上的纽扣为铜质。直笑。
“干这事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警察气喘吁吁地问。
“难道你就不怀疑我?”索彼反问,声气里听得出带点儿挖苦味道,然而笑容可掬,像是在迎候好运道。
警察根本没怀疑索彼。谁砸了橱窗都不会站着等警察抓,会拔腿就跑的。警察发现有人跑过了半条马路,想赶搭一辆车,便拿着追。索彼虽满心瞧不起他,但还是走了,第二次也没达到目的。
马路对过有家餐馆不太气派,是为那些食量大而钱包小的人开的,餐具厚重,空气污浊,汤清,餐巾布稀稀拉拉。索彼进这种地方穿着不像样的鞋和露出穷酸相的裤子是没人阻拦的。他坐到一张桌边,享用了牛排、烙饼、油煎卷还有果馅饼。吃完他对服务员道出了实情:他身无分文。
索彼说:“你去叫警察吧,别让你大爷久等。”
“用不着叫警察,”服务员说,声气柔和,眼里的火星却直往外冒,“来呀,康!”
两名服务员抓着索彼一推,他的左耳首先着地,哐当摔倒在硬邦邦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弯动着关节站起来,像是个木匠一段一段地打开曲尺,然后拍干净身上的灰。想叫警察抓起来似乎也是做美梦,到避难岛看来还路漫漫。站在相隔两家的药店门外的一名警察打了两声哈哈,巡马路去了。
索彼走过五个路口才算恢复勇气,又追求起警察来。这一次他异想天开,以为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着一位模样端庄可爱的年轻女郎,在津津有味地看里面摆的洗漱杯和墨水瓶架。离橱窗两码处站着一位威严的大个子警察,背靠在消防龙头上。
索彼的方案是扮演一次惹人嫌遭人骂的“骚公鸡”。他瞄准的人儿文雅高贵,近在咫尺的警察忠于职守,使他信心十足,肯定会让警察扭住胳膊。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只要一扭他过冬就不用愁,可以上那个小岛,那个有好处又自由的小岛。
索彼把他那女教士送的领带结整平,缩进去了的衣袖扯出来,帽子歪戴得不像话,轻手轻脚朝那姑娘走去。他又是向她飞媚眼,又是无缘无故地咳嗽,又是清嗓门儿,一下子微笑,一下子又傻笑,骚公鸡那套可鄙可恶的伎俩,他厚起脸皮耍了个够。索彼斜眼一瞧,果见警察在盯着他看。女郎挪开几步,又聚精会神看着洗漱杯。索彼跟了过去,竟然挨到了她身边,抓起帽子,说:
“是你呀,贝德丽娅这是索彼信口叫出的名,非真名。。到我家玩玩,行吗?”
警察还在看着。被纠缠的姑娘只要弯一弯小指头,索彼就可以住到岛上的避难所了。他想得真美,仿佛警察局的舒舒服服的暖气都能感觉到了。姑娘转过脸来,伸出一只手,抓着索彼的衣袖。
“那当然,迈克。不过,你得请我喝杯啤酒。”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本早想对你说话,就怪警察在死盯着。”
索彼大失所望,从警察身边走过时一点事也没有,还被那年轻女郎挽着,就像树上缠了根常春藤。监狱似乎与他无缘。
拐了一个弯儿后他甩开那女的撒腿就跑,直跑到一个街上灯光亮的地段。入夜以后,上这里的人有来找称心事的,有来赌咒发誓的,有来看歌剧的。穿长大衣和裘皮衣的男男女女不怕冬天的寒气,来来去去走得欢快。突然,索彼担心起来,怕自己中了什么邪,就不能让警察抓去。他想着想着有点胆寒,但就在这时又遇上了一名警察。那人在家剧院前站着,挺精神,使他立即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想起有“扰乱治安行为”这一条。
索彼扯开粗嗓门儿,在人行道上醉汉般乱叫起来。他跳着,喊着,胡说八道着,无所不为,搅得连天公也不安宁。
警察甩着,背转身干脆不瞧索彼,还对一个人说:
“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庆祝他们赛球给了哈德福学院一个大鸭蛋。就叫唤叫唤,没事。上头有交代,别理他们。”
索彼泄了气,徒劳无益的事只好作罢。难道不会有警察来逮他吗?他认为那个岛有些可望而不可即。风刮得冷飕飕,他把薄薄的上衣的纽扣扣上了。
他发现一个衣着漂亮的人在烟店里点雪茄,点烟的火晃来晃去。他的一把丝绸伞进门时放在门边了。索彼走进店,拿起伞,慢吞吞地走开。点雪茄的人忙赶过来。
“是我的伞!”他厉声道。
“这会是你的?”索彼用挖苦的声气反问,既强占他人财产,还污辱他人。“那你干吗不叫警察呀?我就要拿。是你的伞哪!干吗不叫警察呀?街口就站着一个!”
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彼也放慢脚步,心头有种不祥之感,觉得命运又会与他作对。警察看着他们俩,好生纳闷。
伞主人说:“当——当然,唔——唔,你知道这种误会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要真是你的伞得请你原谅——我今天上午在餐馆捡到的。现在你认出来了,那——那还请你——”
“当然是我的伞!”索彼恶声恶气地说。
伞的前主人收兵回营。警察呢,发现一位披着在剧场看戏用的大外套的高个金发女郎在横过马路,便赶去帮那女的一把;一辆电车正开来,隔着两个街口。
索彼往东走到一条在翻修的马路。他气得把伞扔进一个坑里,还咒骂那些戴头盔拿棍子的家伙。他有心让他们来抓,可是他们把他当成不可能有过失的圣贤。
后索彼到了东西向一条没那么明亮和热闹的马路。他打定主意顺这条路回麦迪逊广场,因为他回家的天性并未泯灭,尽管他的家只是广场的一条长凳。
然而,在一个特别幽静的街口索彼站住了。这里有一座山形墙老教堂,盖得很糟,模样古怪。一扇紫罗兰色的窗里还亮着灯,有位琴师反反复复练着琴,当然是为了在安息日唱圣歌时把琴弹得格外出色。索彼被飘来的优美音乐迷住了,靠在铁栏的圆环上出神。
天空挂着轮皎洁的明月,车辆与行人寥寥无几,屋檐下的麻雀睡梦中只会叽叽喳喳叫几声,眼下的景象会使人想起乡间教堂的墓地。琴师弹奏的圣歌把索彼牢牢拴在铁栏上了。以往他也曾享受过温暖、甜蜜,有过朋友,产生过抱负,思想洁白无瑕,衣服干干净净,那些日子里他对圣歌非常熟悉。
索彼的心本就容易受感化,老教堂又有它的神力,所以,他的灵魂豁然醒悟。回想他跌进的泥坑,回想那些不光彩的岁月、卑鄙的欲望、破灭的希望、毁弃的才能以及为谋生计而有过的肮脏动机,心头掠过一阵恐惧。
也是在一瞬间,经过这种反省后,他振作起来了。他感到一阵来得又快又猛的冲动,决心与坎坷的命运搏斗。他要从泥坑中走出来,要洗心革面,要战胜缠住了他的邪气。时间还来得及,他还相当年轻。他要重振往日的雄心,不屈不挠地实现远大抱负。庄严而优美的琴声激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变化。明天他就去闹市区找工作。一位皮货进口商曾说愿雇他当司机。他明天去找这个皮货商要这份工作。他会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他会……
索彼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忙一回头,看见了一个大脸盘的警察。
“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问。
“没干什么。”索彼说。
“跟我走。”警察说。
第二天上午,警庭的法官宣布道:“在岛上关押三个月。”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有一次打猎以后我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小镇上等南行列车,车子晚点一小时。我坐在楼的门厅里与旅社主人蒂勒默克斯·希克斯谈起了人生的责任。
看到他性格并不怪僻,我便问,他那只左耳朵是不是在很久以前让什么野兽咬伤了。我爱打猎,自然而然会想到人在追野兽时可能遇到的凶险。
“这只耳朵是真朋友关系的纪念品。”蒂勒默克斯答道。
“那是遇到了意外?”我追问。
“朋友关系拉扯不上意外。”蒂勒默克斯说。我没有再问。
我的旅店主人却接着说了下去:“完全够得上朋友的例子我以往只知道一件,是一个康涅狄克州人和一只猴子,他俩真够意思。在巴兰基利亚时巴兰基利亚是哥伦比亚北部一城市。,猴子爬椰子树,摘了椰子丢给人。人把椰子锯成两半,做成大勺子,每个卖两银币,再买回甜酒。猴子喝椰子汁。赃物两人有份,谁也离不了谁,他们成了亲兄弟。
“人与人之间是另一码事,交朋友是玩手腕,顾顾眼前,二话不说就可以不干了。
“原来我有位朋友,大名佩斯利·菲什,我原以为与我会天长地久。七年里不论是挖矿,办农场,卖专利产品搅奶器,放羊,照相等,还有搭铁丝网,采干梅,我们都在一起。瞧着吧,人家会凶杀,瞎吹捧,争钱财,讲歪理,喝酒闹事,我们哥俩绝不会闹出这些翻脸事来。我俩那股子要好劲儿叫你猜也猜不出。干正经事我们够味,到玩起来,犯起傻劲儿来,也还是一样哥儿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确确实实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有年夏天,我跟佩斯利赶着马儿进圣安德烈斯山,我们身穿刚买来的衣服。因为一个月的事完了,想要轻快轻快。我们到了这洛斯皮诺斯镇。这地方称得上世界的屋顶花园屋顶花园是将土运到屋顶而建起的花园。说话人认为该镇风景优美,又地处高山区,所以有此一比。故事开头的“楼”也是作者暗示地势高而取的名。,炼乳、蜂蜜多得四处流。有一两条街,一个馆子,还有鸡,空气好,反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意。
“我们到镇上时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铁路边只开着那家馆子,我们只好进去,看有什么能饱肚皮的就吃什么。还没等我们坐下拿起刀把红油布上的盘子挠起来,进来了个人,端着热腾腾的甜面包和炒鸡肝。她叫杰塞普太太,丈夫已死。
“你看看,这女人叫石头见了也会动心。她的个子不能说小,倒要算大。模样招人喜欢,一看就觉得很好相处,是热心直肠人。脸色发红,是下惯了厨房的结果。一笑起来,十二月里也会引得山茱萸小乔木,早春开花,可供观赏。开花。
“杰塞普太太话多,跟我们聊起来,一会儿天气,一会儿历史,又扯到坦尼森坦尼森(1809—1892),英国诗人,1850年被英国王室评为桂冠诗人。,干梅,还有羊肉难买,临了问我们从哪儿来。
“我答道:‘斯普林瓦利。’
“佩斯利嘴里塞满了土豆和火腿的小骨,他插了进来:‘大斯普林瓦利。’
“这一下我次察觉到了苗头,我和佩斯利·菲什的八辈子交情就此完了。他知道我讨厌唠唠叨叨的人,这次却插了进来,把话讲个明白透彻。地图上标的是大斯普林瓦利,可是佩斯利他自己说斯普林瓦利也说过上千次。
“吃过饭,我们话没多说出了店门,往铁路上走。两个人相交了那么长时间,谁的心在想什么谁还不知道?
“佩利斯开口了,说:‘我不说你一定知道,我横下一条心要把那寡妇弄到手,家里是我的人,外面是我的人,法律上是我的人,算什么都是我的,除非死了才分开。’
“我答道:‘这不假。你只开了一次口,我听话听音。要说呢,你也心里有数,我也有我的打算,这样寡妇就要改姓,叫希克斯太太,那你就得给报纸的社交栏写信问问,男傧相在婚礼上要不要戴日本产的花,穿无缝袜。’
“佩利斯说:‘你的算盘别打得太如意。’他把铁路枕木扳下一块,‘要是遇上平常什么事情,十有八九我都会让你,不过这一回不同,’他嘴没停,‘女人笑起来可抵挡不住,你就像进了大漩涡,朋友关系这条好船会给吞了,摔得粉碎。’佩斯利还是在说着,‘要是有只大熊想吃掉你,我跟它拼。你的账我可以替你付,我还可以替你摸肩擦背,什么都像以往一样。可是这件事我顾不得什么交情不交情了。这次要把杰塞普太太抢到手,我们只好顾自己。现在我把话全向你挑明了。’
“听了他的话,我想了想,也亮出了主意和规矩。
“我说:‘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自古就有。古时候抵挡有八十英尺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03048米。长的蜥蜴和长翅膀的乌龟就靠你帮我我帮你。这个习惯保留到今天,大家一听说有野兽会聚到一堆,非要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其实没野兽才会散开。我常听说,有了女人,一些原来是朋友的男人就散了伙。干吗要那样?跟你说实话,佩斯利,一看到杰塞普太太,一吃到她烤的面包,我们俩心里就都沉不住气了。我们谁有本领谁娶她。我跟你摆开阵势比,不背着你做手脚。我用什么办法追她都当着你的面,这样就机会均等。将来无论谁得手,我们还会是朋友,船不会在漩涡里翻。’
“佩斯利紧握着我的手说:‘真有你的!我也照办。我们同时追这寡妇,别像旁人那样假装正经,到头来又捅刀子。成也好,败也好,我们仍然是朋友。’
“杰塞普太太的馆子旁的树下有条长靠椅,南行火车上完旅客开走以后,她爱坐在靠椅上乘凉。我跟佩斯利吃过饭聚到这里,找我们俩都看中的人,各显本领。我们真算得上君子,能沉住气,每次去时无论谁先到,都等着另一个来了才开始玩手腕。
“杰塞普太太终于察觉到了我们的安排,那天晚上是我比佩斯利先坐到椅子上。刚刚吃过晚饭,杰塞普太太穿了件新粉红色衣服,而且心绪正好。
“我坐到她身边,说了些这儿的风光显得怎么怎么美,环境如何如何好的话。那天晚上说这种话合适。月亮守着老规矩,升到了该升的地方。落在地上的树影既符合科学原理,又遵守自然规律。树丛中,林子里,小夜莺、金莺、长耳朵兔,还有别的有羽毛的昆虫原文feathered insects按词义确实只能译为“有羽毛的昆虫”。说话人在这里不是用词不当便是信口开河,同类型例子本文还有。闹成一团。山里刮来的风唱着歌,像是犹太人坐在铁路边弹着旧番茄酱做的琴。
“忽然我在左边有了感觉,我像是被放在火炉边上瓦罐里的生面粉团一样发起胀来。原来,是杰塞普太太挨近了我。
“她说:‘哎,希克斯先生,世界上的单身人遇上这样好的夜晚,心里会更不是滋味,你说对吗?’
“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了身。
“我说:‘太太,对不起,我得等佩斯利来,如果他不来我就回答了你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能算正大光明。’
“接着,我向她解释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有了危难也好,出门也好,串通合谋也好,都拴在一块儿。我们已经有约定,要是遇到更伤脑筋的情况,比方说牵涉感情和关系的事,谁都不能干对不起人的勾当。杰塞普太太似乎认真想了一会儿我的话,想过以后不停打起哈哈来,笑得树林都震动了。
“没多久,佩斯利来了,头上抹着佛手柑香油。他坐到杰塞普太太的另一侧,讲了一段辛酸而不寻常的经历。一八九五年圣丽塔山谷连续九个月干旱,他跟皮弗斯·拉姆利比赛剥死牛皮,赌一副镶银马鞍。
“从开始角逐起,比起我来,佩斯利·菲什就处于劣势。我们俩各显神通,想攻破女人心上的薄弱点。佩斯利的办法是往女人耳里灌风,讲那些亲自经历的或大字体大字体书多为儿童或文化层次低的人用。印刷的书上看来的故事。我看过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叫《奥赛罗》,我想他的主意定是受了那个剧的影响。剧里有个黑皮肤人,把这人那人编出的话搅到一堆,结果把一位公爵的女儿弄到了手。《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剧中主人公奥赛罗向公爵女儿所述全系本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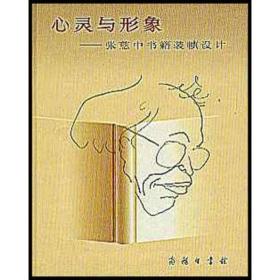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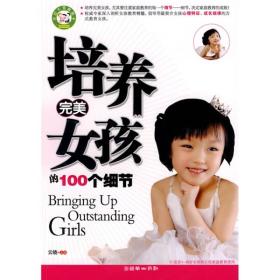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