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亲热
¥ 5.29 1.9折 ¥ 28 全新
库存3件
山东泰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罗曼·加里 著;李一枝 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
版次1
装帧平装
货号605 12-23
上书时间2024-12-2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法]罗曼·加里 著;李一枝 译
-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2-07
- 版次 1
- ISBN 9787229051457
- 定价 28.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276页
- 字数 151千字
- 原版书名 Gros-Câlin
- 【内容简介】
-
《大亲热》主人公库森是繁华都市里的一个公司职员,他每天碌奔波,却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与其他人,与整个社会之间都产生了隔阂,他的爱情与生活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模样,只能在一条名叫“大亲热”的蟒蛇身上找到慰藉。最终,库森精神错乱,混淆了自己与“大亲热”的界限,以为蟒蛇是自己,自己才是蟒蛇,从而真切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与寂寞。
当一条蟒蛇缠绕着您,紧紧地抱住您的腰,您的肩膀,然后把它的脑袋贴在您的脖子上,您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被一股温暖的爱所包围。那简直就是一切不可能的尽头,是我的灵魂之源。
我叫库森,Cousin,我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兄弟,我就是你。
我三十七岁,单身,在公司统计部工作。
同事都在背后议论我。在只有两人的地铁车厢里,我喜欢紧挨着另外一个人坐。
我的爱人,穿超短裙的办公室同事,我和她的恋情发生在每天共乘电梯旅行的1分零10秒。我知道她爱我,但她不敢告诉我。
我和一条蟒蛇同居,它叫“大亲热”,它对我很亲热。它完全依赖我,我就是它的一切,离开我它没法活。它爱吃老鼠,不,老鼠是我的食物。蟒蛇是库森,我才是“大亲热”。
我爱上的,不只是一条蟒蛇。 - 【作者简介】
-
罗曼·加里(RomainGary1914-1980),法国著名作家。原名罗曼·卡谢夫,俄籍犹太人后裔,童年时代在俄国和波兰度过,1026年移居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赴伦敦投奔戴高乐,参加“自由法国”空军,转战欧洲、北非和中东,获十字军功章和代表法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解放勋章。战后二十年间在外交界工作,曾任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罗曼·加里于1945年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其长篇小说《天根》于1956年荣获龚古尔奖。1980年,罗曼·加里在巴黎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他死后的第二年,遗著《艾米尔o阿雅尔的生死》发表,解开了法国文坛的一个迷团:罗曼o加里就是阿雅尔。
用阿雅尔这个名字署名的几部小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大温柔》便是其中之一,而《来日方长》则斩获了1975年的“龚古尔”奖,从而使罗曼o加里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 - 【目录】
-
《大亲热》主人公库森是繁华都市里的一个公司职员,他每天碌奔波,却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与其他人,与整个社会之间都产生了隔阂,他的爱情与生活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模样,只能在一条名叫“大亲热”的蟒蛇身上找到慰藉。最终,库森精神错乱,混淆了自己与“大亲热”的界限,以为蟒蛇是自己,自己才是蟒蛇,从而真切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与寂寞。 当一条蟒蛇缠绕着您,紧紧地抱住您的腰,您的肩膀,然后把它的脑袋贴在您的脖子上,您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被一股温暖的爱所包围。那简直就是一切不可能的尽头,是我的灵魂之源。 我叫库森,Cousin,我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兄弟,我就是你。 我三十七岁,单身,在公司统计部工作。 同事都在背后议论我。在只有两人的地铁车厢里,我喜欢紧挨着另外一个人坐。 我的爱人,穿超短裙的办公室同事,我和她的恋情发生在每天共乘电梯旅行的1分零10秒。我知道她爱我,但她不敢告诉我。 我和一条蟒蛇同居,它叫“大亲热”,它对我很亲热。它完全依赖我,我就是它的一切,离开我它没法活。它爱吃老鼠,不,老鼠是我的食物。蟒蛇是库森,我才是“大亲热”。 我爱上的,不只是一条蟒蛇。
作者介绍
序言
导读:这个库森,我们的人让-弗朗索瓦?安古埃
1974年年初,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和墨丘利出版社的编辑和审读专家们先后审阅了《大亲热》的稿子。这部不见真人的年轻作者(这已让人有点怀疑)的处女作表现出了异常的天赋(一些人认为这背离了作者成长的常规,“一个捣蛋鬼”,雷蒙?格诺在他的审读报告中一语蔽之),总之只知道这是某个叫埃米尔?阿雅尔的人写的。在米歇尔?古尔诺与西蒙尼?伽利马的热情支持下,《大亲热》最终得以在法国墨丘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当年秋季一上市便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声音令评论界和读者们欣喜若狂。当时,编辑们一致认为小说中的故事别出心裁,令人惊奇,虽然不免稍嫌荒诞(您想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巴黎男人赞同以动物作为伴侣,被他视为伴侣的蟒蛇还偶尔从下水道逃走),而且还有些地方稍嫌冒犯(书中有些情节似乎在戏谑社会时事,还有涉及堕胎的激烈讨论),但从文学上来看的确非同寻常。不过,他们认为,小说结尾处叙述者(即库森)摆脱蟒蛇“大亲热”的一段应该删去。编辑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小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触及了当时社会热议的人工流产问题”,克里斯蒂娜?巴罗什后来谈到,不过这个故事仍然令她感动到落泪;结尾“写歪了,这是小说的一处败笔”,与巴罗什一起审读书稿的米歇尔?古尔诺主要从文学角度作了评判。皮埃尔?米肖,受罗曼?加里之托在埃米尔?阿雅尔和出版社之间扮演中间人,向罗曼?加里忠实地报告了编辑们坚持的修改建议:这个结尾在小说中实为多余,应该删之。罗曼?加里,这个隐藏在不知名的年轻作者背后的大作家,照办了。说真的,罗曼?加里此举如同自断手足。今天,带着对这部取得巨大成功的小说的崇敬,人们已经知道埃米尔?阿雅尔就是罗曼?加里的另一重生命,不过在阿雅尔烟花般的不凡经历之下,人们也许还未察觉,小说中主人公库森的生活何尝不又是罗曼?加里本人的真实写照。这位罗曼?加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从多本关于他的传记中,从他的多重文化经历中,从他为世人所知的年岁中(《大亲热》中的库森和其他作品中的加里同样宣称自己的年龄是八岁),从他不同的名字中,从他在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外交界留下的不同成果中,人们也许有了对罗曼?加里的定义。然而恰恰相反,真实的罗曼?加里超越了所有这些定义。在这些复杂经历背后的罗曼?加里,不论他曾经做过什么,拥有过什么,或者创造过什么,首先要面对一个冰冷的矛盾,一面是自己幸福的愿景,一面是恐惧,惧怕这些愿景从来不会被那对虚无之中张开的手臂所接受。而加里认为,一个人活着,为了爱,总该对什么东西寄予一点希望。这点与愿景有关的东西,让人在罗曼?加里的所有作品中总能不约而同地发现同样的主题,例如:对另一个世界的梦想,对另一种生活的梦想,对另一种自然与人类规则的梦想,还有弱者的胜利,博爱的胜利,女性的胜利,爱的胜利,这些不都正是让愿景继续存在的方式吗?而用罗曼?加里自己的话来说,当然也是他借用自己多重身份之一的莱尼耶说出的话,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种不顾一切地迫不及待的意愿,对一种明知的不可能所怀揣的战战兢兢的希望,同时也是每一次重新发现事与愿违时的痛苦”。哲学家保罗?奥迪在他《不可能的尽头》一书中的文字给库森也给加里本人带来了希望,同时在加里眼中,也为“最公正地书写自己的方式提供了注解”。正是这份既灿烂又焦灼的情感,融入了加里心中认真和执著的坚信、愿景和相信爱能带来希望的勇气;正是这份内心深处的生活摆脱了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摆脱了所有寄生的社会准则,摆脱了对所有既定条件的屈服;正是最丰富也是最具颠覆性的生活中天然的一点真金,让平凡人的生活互相碰撞。也许是加里借助了文学的魔力,这一切在他绝对彻底和难以置信的文笔之下,成功地移植到了书中的主人公身上:让库森的生活如此令人感动,让我们置身于他的情感之中,与他一同为可笑的东西发笑,为可悲的东西哭泣,为绝望呐喊,与他一同怀着赤裸裸的愿望预感未来。如果说罗曼?加里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大亲热》的创作中,这一点都不足为奇,这部小说他先后重写了二十次,如今保存在法国出版史料研究所的若干个黑色笔记本可以为证。这些笔记本上保留了他不断地写,不断地修改,又不断地重写、粘贴、润色、再粘贴的过程。那些不同的标记,不同的笔留下的轻重粗细不同的痕迹,就像留在手稿上的一道道咒语。为何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如此复杂?为何罗曼?加里要数易其稿?因为要描绘出一个人最隐秘的内心世界首先需要认识自己,因为需要有一种挖掘自我,辨认自我的能力,需要懂得去质疑自己确信的东西(以及别人确信的东西);当然了,同时也因为要懂得如何安排素材,如何重构小说的叙述,如何运用好抓住读者的材料,另外,加里的写作方式的确与众不同;因为这如此接近现实的生活有种非同一般的多面性品质:不论是从一些深层次的坚信上(比如,绝望,或者与世界和谐相反的东西),还是从一种寻求宗教或者道德信仰的保护上,抑或是从某种表现出来的冲动上(比如,诗人的冲动,或者作家的狂热),人们都能看到罗曼?加里个人生活的影子,他承载着永恒、博爱和爱情。人生就像一个有很多棱角的多边形,有很多条边相交在一起,知道必将失败仍然满怀期望,一边肩负起希望的义务,一边付出着爱的代价……“这就是希望,希望就是不可理喻的焦虑,带着预感,期待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人的可能性,也带着冷汗。”库森一语道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生活的原形。一部小说也许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事物,不一样的世界,让人们能够逃离自己的生活去经历不一样的生活。一个使用化名的作者,当这个名字出现在封面上,出现在周围的环境中,就是一个作者的故事的完整翻版:“重新开始,重新活着……”加里在《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一书中如此写道。不过,还有很多小说,它们看起来长得差不多,它们互相重复,类型明显,很容易被常见的文学形式归类,但是,读起来总让人觉得缺乏力度,无法让人们体会到那种有如狂乱青春年代的激情。要想真正吸引读者,必须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必须像《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中所写的一样,要与重复的文学决裂。罗曼?加里不仅仅利用埃米尔?阿雅尔之名重新开始,同时他本人也在重新开始,一如安娜?莫朗吉对《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一书做出的文学分析中揭示,这本书会让人们“将加里和阿雅尔联合在一起来阅读,加里-阿雅尔才是最本色的作家”。如果不这样,小说中的人物就会像库森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就如蜕皮一样,只是换一副皮囊,其他一切还是一模一样的。”要么在同类型语言中做着各种重复,要么如加里写的,“为了真正成为人,必须先试图从人字中摆脱出来”。《大亲热》终于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不过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库森先生并不是一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他正是罗曼?加里的生命的纯净状态(此种纯净状态是从化学元素上来理解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借用库森的话来说就是“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直接的观察”。保罗?帕洛维什曾为他的舅公罗曼?加里扮演阿雅尔背后的真人,关于这次历史性的文学冒险,他写了一本《一个人们曾经认为存在的人》,书中写道:《大亲热》并不意味着(罗曼?加里)创作生涯上的新阶段,它不是一个新作家创作出来的带着未来色彩的新作品,而是某些最为根本的东西。保罗?帕洛维什在此处提到的引发人们思考的某些最为根本的东西,便是一种纯净状态。这种纯净状态不是通过经历他人的生活达到的,而是通过思考自己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完全生活在生命原液中达到的。罗曼?加里正是通过这本小说进一步净化自己,以求将自己与周围的冗赘分离开来。净化的过程在小说中被处理得非常低调。罗曼?加里最后给主人公定名库森,这立刻让读者有了亲近感(库森,法语Cousin,除了做人名以外,亦有表兄弟的意思。——译注)。在之前的几遍弃稿中,罗曼?加里还用过罗玛(Roma)作为主人公的名字。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此特别提及,Roma是amor(爱情)一词首尾字母颠倒过来的拼法。另外,Roma还是罗曼?加里的母亲唤他的爱称。在加里的笔下,主人公库森被塑造成一个带着点幻想的孤独的漫步者,他不知疲倦地走在那些烂熟于心的,一半真实一半虚构的巴黎的街巷里。我们猜想库森先生是一个抵抗分子,因为他总是在谈论如何潜伏,总是在向我们透露他家藏着让?穆林和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两人为法国二战时期抵抗运动成员。——译注)……不过,我们理解(读者们比他周围的大部分人更理解他)这是将他那些深埋在内心的敏感和回忆生动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方式。其实,库森先生有着非同一般的隐藏信息的本领。比如,他提到的“望福街”,是战争时期巴黎十四区一条连接蒙帕纳斯公墓和望福门的街道。罗曼?加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整个年轻学生时代。通过库森,他与这条街的联系得以延续。了解巴黎历史的读者们还会从中发现库森隐藏了一位伟大的抵抗运动成员的名字:从1945年开始,望福街被改名为雷蒙?罗斯朗街,为的是纪念这位牺牲在瓦莱里安高地的抵抗运动成员。是的,可以肯定的是,库森这个默默无闻的男人,每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同样包括这本书的读者),除了会停下来欣赏一下他那条令人称奇的蟒蛇以外,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那条被他唤作“大亲热”的从非洲带回来的两米二长的蟒蛇,为他在他的同事、邻居,甚至是他的读者和批评家那里赢得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称号。这条蛇是一种奇异眷恋的吉祥物,也是库森充满焦虑的人物性格的显影剂。没有了这条蛇,库森就是一个无趣的办公室职员,有点儿神经兮兮,一个典型的法国巴黎小市民,在五月风暴中被划分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秩序的合法代表,头脑简单,容易轻信。正如同小说里警长对他说的,“您的思想很健康,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您这么想,世界就消停了。”不,这位库森先生融进了平庸的普通人当中,带着蟒蛇的面具,藏在阿雅尔名字的阴影下,而他那些在逆光下被发觉的内心感受却映衬出我们自己的孤独,我们对此毫无觉察。库森是一个凡人先生,是一个反主人公式的主人公。在炼金师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他远离了外在形象,远离了自我,远离了加里曾经创造过的人物。库森的形象塑造是一项伟大的艺术,是罗曼?加里的伪装杰作,是一件精心雕琢的成功的艺术品。懂得如何让自己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开始另一重生活,甚至蒙蔽了所有仔细观察者的眼睛,在得心应手地运用这项奢侈的技巧同时,罗曼?加里还不忘发表一些带有保护色的表白。在1976年他出版的《假名》一书中,他说:“我是一个经缝制拼凑起来的人,手工缝制的。”“缝制”一词的法语cousu与库森cousin相似,这就好比承认“我是库森”,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加里与真实的自我保持着距离,他把自我藏起来,藏在安全的地方。这位平凡的库森却有着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小说中的苏雷斯教授对他说,“您讲的法语真特别”)。比如,他说“我在如我思”,这种带有偏差的法语,从他嘴里说出来倒是格外的自然,这给他的人物性格增添了几分魅力。这同样也是作家笔下的一次壮举:这种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自由随意的法语,却只有库森一个人在说。这是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语言,它从那些被遗忘的用语中找回了陌生的熟悉感,它让那些被语法和文体理论抽干了的文字奇迹般地重现表现力,总之,这种诗歌般的小说语言形式取得了成功,这要归功于作家的天才,归功于日后人们所知的埃米尔?阿雅尔背后的罗曼?加里。大卫?拜罗斯在对《大亲热》进行了一番语言学研究之后指出,不能说库森的语言是“阿雅尔式的”语言,也许在读者眼里,阿雅尔随后的作品延续了这种风格。但是,应该说这是一种在阿雅尔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语言:因为在罗曼?加里全身心地创作这部小说和库森这个人物的同时,他也在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的灵感也在此期间迸发。在这期间,埃米尔?阿雅尔还不存在。在《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一书中,加里承认他“是在写完《大亲热》之后,才决定用埃米尔?阿雅尔的名字瞒过出版社的编辑们”。库森在阿雅尔存在之前就已经自称“我”了,阿雅尔的语言就是在模仿库森的语言,这是一种先前存在的内在的语言。阿雅尔占据了所有位置。阿雅尔,作为最大的诱饵,出色地夺走了一切。因为将库森放入阿雅尔的怀抱之中,毫无疑问是加里做出的最庄严的行动。在《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一书中,加里谨慎地写道:“我感到这本书的本质与我以前的作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之间有一种不可兼容性,人们对我的印象是建立在我已有的名声和影响力之上的。”他承认,期望让库森生活在一种完全本原的状态中,正是他做出此举的最大动力。加里把这份私密而真实的书稿,把这个他本人化身而成的小说主人公托付给了无人知晓、形单影只的埃米尔?阿雅尔,他似乎缺乏一点勇气……然而另一个埃米尔(《爱弥尔》)的作者,那位把《对话录》的手稿交给教堂,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孤儿院的卢梭却有这个勇气。卢梭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加里的影子,他们都是打算把自己的身后托付给陌生人的人。他们有彻底的勇气,有一股精神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他们的坚信,坚信通过写下无人敢做的忏悔,通过创造前所未闻的生活和难以置信的作品,能将自己从无限的虚无中争夺回来。而完成这一举动只需命运动动手指头,只需命运拿出它的宽厚,不计较身份标签,不追溯从前经历,去接受创作者的天赋,以最宽容的姿态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敏感与颠覆性的思想。加里将不可估量的库森借给年轻的埃米尔?阿雅尔,让他还原这个令人称奇的角色,这一做法无疑给自己增加了不少勇气。正如小说《有罪的头颅》中的科恩(罗曼?加里的另一重生命)在得知他的塔希提女友弥瓦生下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后的情景:
这个并非他亲生骨肉的孩子只可能是个好人,甚至还可能是个出色的人。那个期待一个非同一般的新生命的、被撕碎的梦还在,简直就像一个人最后的希望。不过,库森的到来对于阿雅尔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新生命,因为他是为他而生,对于库森来说这将是另一段故事……因为阿雅尔,这个缺席的年轻陌生人,还没有能力去抵抗被要求的删节。他需要一个保罗?帕洛维什:可是他也没有这个气度。当他的朋友皮埃尔?米肖将编辑们打算删除整个结尾的建议转告他的时候,罗曼?加里进退两难,他肯定陷入了深刻的痛苦当中。以文字质量为由否定作者整个创作的一部分,让作者非常恼火(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不会这么做了),这不仅有损作者的面子,更是一种身份的撕裂。出版界的运作机制迫使他立即做出选择,不论采取怎样的举动,都会失去库森。要去捍卫作品的完整性吗?可是这会把埃米尔?阿雅尔和出版社的关系搞僵,那么或者暴露自己算了……埃米尔?阿雅尔还太嫩,没有底气,必须加里亲自出马,摘下阿雅尔的面具。但是此举又会影响到库森的问世……如果阿雅尔此时已经有了一副结实的肩膀该多好啊,他需要迅速地成长起来。刀架在了脖子上,怎样?接不接受删掉结尾?好吧,算了……目前缺乏人气,下不为例。库森失去了某些东西,不是全部,不过是某些东西。也许将来有机会让这个并不一样的角色取得圆满的成功。于是,不仅仅是小说,而且库森本人就这么被截肢了,这个纯洁的生命期待完整。因为,如果不在这篇前言中揭示这部小说的结尾的原本面貌,就无法突出库森的变形对于罗曼?加里的意义,库森罕见而带有拯救意味的变形记正是来自罗曼?加里与虚无的短兵相接的灵感。担负着希望承载着爱的加里,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爱的分享和爱的回归……颠覆世界的作品往往会得到回报。在完整的《大亲热》中,库森找到了大爱,而在罗曼?加里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的悲剧性结尾中,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邀请信,得以让他“不通过考试进入这个行业”,不过他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只因他为解放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时刻,罗曼?加里在美国版本的《童年的许诺》中甚至如此描述,“一个真正的童话故事的结尾”,因为这封信“不是用行政机构那种一贯不带个人色彩的公文体写的。我从中读到了一丝好感甚至是一点友谊,然而这却让我深深地困惑了:我从未感到自己被如此了解过,更确切地说,被想象过”。被想象,被爱:这是在一个只能看得见可能的世界里,孤独元素的终结,即使无法直接响应心中迸发出的憧憬,至少也要交给一个穿行在千万“凡人”的巴黎中的库森,让他去散播说明文字,或者交给一个穿行在被战争撕裂的欧洲大地上的加里。在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受到保护的珍稀世界里,生活在他人的爱当中的人们,要比生活在孤独中更能找到自我。库森在小说中告诉我们:“当我们得到解脱的那一天,我们将会明白心心相印就意味着被爱,这是一回事。”在1974年的《大亲热》里,只有库森没有得到解脱。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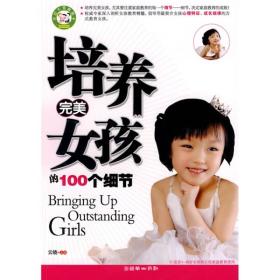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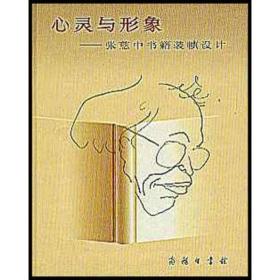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