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追问 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 陈胜前著 三联书店 正版书籍(全新塑封)
考古学角度深度阐释史前人类简史。人与人的关系如何从史前找到灵感?权力如何产生?社会的复杂性如何起源?看不见摸不到的情感,如何在考古的学问中寻根?
¥ 25 6.6折 ¥ 3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陈胜前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01
装帧其他
上书时间2019-10-26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书籍!全新未拆封!
- 商品描述
- 个人收藏,全新未拆封!售出不退换!现货,可以直接拍下付款,随时寄出!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陈胜前
-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时间 2019-01
- 版次 1
- ISBN 9787108064295
- 定价 38.00元
- 装帧 其他
- 开本 32开
- 页数 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页
- 【内容简介】
- 直立行走和狩猎为何成就了人类?从狩猎- 采集到农业产生,人类在演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转折事件?战争如何影响人口变化?……史前考古学家研究人类超过99%的历史,本书探讨了现代人起源演化中的生计策略和文化适应,从各个细微方面体现了考古学的洞察力。
- 【作者简介】
-
陈胜前,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于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mu)攻读博士,师从美国古学会、美国科学院院士弗雷德•温道夫(fred wendorf)和“新古学”开创者、有名人类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 binford),2004年获得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学理论、古学思想史、农业起源、石器分析、遗址过程动态解读、史前艺术和古教育等。
精彩内容:
大动物狩猎:事实还是幻觉?有两项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动物古学方面的研究,分别根据许昌、许家窑遗址的动物化石材料认为:十万年前后,人类(两个遗址都出土了人类化石与丰富的石器材料)可以进行选择的狩猎,而且主要狩猎壮年个体;许家窑遗址而言,人类还选择了马科动物——肉质感好,脑髓或骨髓中有人类发育所需要的特殊营养。如果结论成立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人类早在解剖学概念上的现代人出现之前已经能够有效地组织狩猎,不仅可以依赖狩猎,而且对象是大动物;不仅是大动物,而且是感营养很好的物种;不仅是很适合的物种,而且是不错壮的个体;不仅可以季节地利用,而且可以全年利用;不仅可以根据季节利用,而且可以把动物尸体搬运回中心营地一起分享(许家窑的材料包括近五千颗马科动物牙齿)。据说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也是这样,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的话,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些人类群体为什么灭绝了呢?是他们太依赖狩猎,把大动物都赶尽杀绝了,以至于无法生存下去?抑或是适应上高度特化,面对新挑战时冥顽不化,很终被现代人取代了?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成功组织大动物狩猎?人类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依赖大动物狩猎为生(主要食物来源都是大动物)?现代人的狩猎能力与尼安德特人或其他早期智人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早期智人甚至更早的人类已经拥有比肩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的狩猎能力,那么现代人究竟靠什么的能力替代了这批远古的“武林高手”呢?除了要回答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狩猎差别的问题,还需要解释与民族志中狩猎采集者的差别。人类学、古学以及历史学积累了大量有关狩猎采集者的材料,还有许多从古学角度出发的田野调查,对狩猎采集者的狩猎方式、狩猎的依赖程度以及所留下遗存的特征等都有不少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得到的基本认识与上面所说的大动物狩猎说之间存在较大的盾。首先需要承认古学上“壮年居优”的狩猎模式是的确存在的,但是条件比较特殊,而且并不常见,如北美地区的加乐尼斯(garney)遗址。这是一处15世纪的野牛猎杀遗址,古学家发现印第安猎人捕杀的主要是壮年雄动物个体。原因是春季壮年雄公牛状况比较好,尤其是脂肪比较多。显然,印第安猎人狩猎并不是为了蛋白质。我们现在知道蛋白质的摄入达到量以后,更多的摄入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非洲的狩猎采集者如布须曼人或是哈扎(hadza)猎人是不遗余力地追猎大动物,尽管这些动物都已经很消瘦了。再者,获取脂肪的途径并不有且只有于大动物,含油脂高的坚果、昆虫等都可以提供脂肪,风险要小得多,也更加可靠。理查德?李(richard lee)和欧文?德沃雷(irven devore)于1968年出版了有名的人,狩猎者(man the hunter)一书,强调狩猎对人类演化的重要,如促进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高质量的食物,等等。然而,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之一理查德是布须曼人研究专家,他的一项重要贡献是20世纪60年代对布须曼人的田野调查,他发现植物食物在布须曼人的饮食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女的采集是很有保障的食物来源;相反,狩猎并不是一项很靠谱的生计方式,如猎人花费五天时间去追踪一头受伤的猎物,而这头猎物有可能成为其他食肉类的盘中餐,到头来一无所获。蛋白质、脂肪,还是政治?——狩猎大型动物行为的古人类学和古学研究(the paleo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biggame hunting: protein fat or politic?)作者是古学家约翰?斯佩思(john d. peth),2010年在施普林格(pringer)出版社出版。斯佩思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研究大动物狩猎的问题,很好熟悉古与民族志材料。经过长期研究,他越来越发现无法从功能的角度——无论是为了脂肪还是吃肉——来解释人类为什么狩猎大动物。大动物狩猎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成功率不高,即便是成功了,大量的肉还要送给其他人甚至是陌生人,很难指望回报。而采取更广谱的觅食方法,成本更低,社会关系上的麻烦更少。民族志或历目前大动物狩猎者大多有其他目的,也是斯佩思所认为的社会政治上的原因。回到古材料上,有一项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骨骼上的伤痕与现代的牛圈骑手所受的伤很相似。牛圈骑手是骑在狂颠乱跳模拟牛背上的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摔下来而告终。尼安德特人的这种受伤模式表明,他们在狩猎时曾与动物近距离搏杀。尽管尼安德特人身体结实,粗壮有力,但跟体重是他们若干倍的动物相比,近距离搏杀仍是高风险的行为。依赖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模式,要把狩猎当成一项常活动,是难以持久的。有种观点认为,在寒冷地带,狩猎大动物才是专享能够生存下去的途径,而且计算出来尼安德特人每天至少需要多少肉食才能生存下去。这里需要定尼安德特人的狩猎很好成功,每次捕猎与消费能够接续得上。即便是民族学上的狩猎采集者是也无法保证这一点,尽管他们是现代人,周围的猎物也很丰富,而且有远程的狩猎工具,甚至是金属制作的。许家窑的石器材料中包括1200多件石球,这可能是狩猎工具,而其他石器工具都比较细小。这两年我们石球做了一系列的石器实验,包括如何制作与使用。我们现在已知道为什么大多数石球的直径是9厘米,重1千克,石球的大小与成年男手掌的大小有密切关系(我们定许家窑人体质发展特征与现代人一致,即身材越高手掌越大),这说明石球是用手直接握持使用的。我们的使用实验表明1千克是徒手投掷的很好重量,熟练的投掷者能够把这个重量的石球扔到二三十米开外。为什么不选择同等重量的天然砾石呢?我们的对比实验显示,投掷同等重量的砾石不仅距离短,而且由于砾石的形状不一,很难控制落点。如果石球的功能确实如实验所示,那么它是一种徒手投掷使用的狩猎工具,与之相应的狩猎是近距离的。进一步说,如果按很远距离投掷石球,石球的打击力量其实很有限,为了获得更大的打击力度,需要再缩短距离。许家窑人把加工好的石球储存在一个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可能是一处泉水,也可能是一处盐碱场,待动物群过来的时候,埋伏好的猎人拿起石球群起而攻之。石球是钝兵器,打击动物的腿部或是头部是不错的选择,由于有限,需要集中攻击有限的目标才行。野马是奔跑迅速的动物,能够给猎人多次打击的机会不多。许家窑人如果跟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一样的话,那么他们会在击伤猎物之后,群起与之搏杀。这样的狩猎方式是不大可能一次捕猎多头动物的,当然这么做也没有必要。也是说,许家窑遗址是古人反复利用的猎杀地点。猎杀完成之后,地屠宰,进行消费,包括敲骨吸髓,因此,我们才看到如此之多的牙齿。许家窑人的狩猎方式有点类似守株待兔,通过埋伏发起突然袭击,成功率可能比较高,但是频率不会太高。试想一下,前面的野马尸骨未干,后面又来了一批野马,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许家窑人周期(每年或每几年)回到这个遗址进行捕猎。这里大量马类动物骨骼的积累说明,这样的狩猎模式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同时也可以说明,许家窑人的狩猎方式没有变化(智力上可能也缺乏认知弹)。再有一点,由于人类只是短时间将这里作为猎杀、屠宰地点,其他时间不可能没有其他动物利用这一地点,比如食肉类也会发现这个很好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们也有可能在这里进行捕猎与消费,如果它们留下的动物骨骼与人类利用的混合在一起,会导致辨别上的困难,至少在牙齿上是无法看出来的。这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方式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拥有一些长程投工具,可能包括标投掷器、回飞镖,甚至可能有弓箭,还可能会用毒药,如布须曼人那样。像许家窑人那种埋伏式的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可能用一些设施如陷阱、套索等来替代。他们甚至可以在动物行进路线上设置障碍,然后将动物驱赶下悬崖摔死,北美有这样的史前遗址。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现代人的社会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我现在比较认同一种观点,即尼安德特人或其他早期智人与现代人的主要区别是社会认知能力上的。早期智人没有如现代人发展出有效的符号体系——它是知识存储、传递的更有效的方式,也是社会关系网络扩展的更有效的途径。单纯搏杀猎物而言,现代人可能还不如早期智人,但是他们有更好的工具与方法、更好的社会组织,以及更多的经验积累。这些东西是否会表现在古材料上呢?离许家窑遗址不远,还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以猎马著称的是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二者是否有区别呢?目前没有人研究过,值得关注。这里既没有否认大动物狩猎,也没能肯定它。问题很终还是回到了古材料。自然下动物骨骼富集也是可能存在的,并不需要依赖人类狩猎。有石器、动物骨骼,并不意味着人类是动物富集的原因,共存关系不等于有因果关系!尤其我们把长时段(可能数千年的时间)的地层浓缩到一个时期进行察的时候,所谓“共存”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共时(属于同一个事件)。再者,我们还需要排除其他动物的贡献,像我们抓“凶手”一样,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需要排除各种可能,才能很后确定人类是真正的“凶手”。这无疑需要高精度发掘材料以及各方面的细致观察,甚至是实验验证,这应该是我们以后需要加强的。 - 【目录】
-
代序 古学家的洞察力.......................... 001人与自然........................................ 001人之为人的困惑................................. 001人的世界之一:人的本质......................... 005人的世界之二:精神古......................... 008人的世界之三:人是如何行动的.................... 009讲究“讲究”................................... 011人的独特................................... 015人的异化..................................... 019能力........................................ 024自然何以可能.................................. 027我们还有没有未来?人类利用能量的效率的问题........ 030城市:新的生态单元......................... 032洛南盆地的盛宴................................ 037贵州:史前狩猎采集者的天堂...................... 043演化的节奏...................................... 049人之为人的里程碑:直立行走与积极狩猎............... 049旧石器时代的文凭.............................. 053技术的意义................................ 066节奏........................................ 070史前人类的狩猎................................ 073大动物狩猎:事实还是幻觉?...................... 077时间尺度与人类的命运........................... 082关于象征古.................................. 084心智的维度................................... 087将进行到底................................ 090看不见的“现代化”.......................... 093意义的起源................................... 098史前的现代化.................................. 100永远的狩猎采集者.............................. 106人与农业起源................................ 109人之驯化..................................... 113社会与...................................... 116社交的................................... 116人群关系的演化................................ 121权力的起源................................... 124信用的起源................................... 127人类别战争史................................ 129人啊!人.................................. 134合作之源..................................... 136追溯世故——思中国传统结构的起源............. 139so grooming................................. 142家庭的起源................................... 146思社会复杂................................ 150社会复杂的起源.............................. 153文明的神................................... 158暴力、战争与控制.............................. 162强权与神:信息传递与社会组织................... 167战争的古学:为战争的合理辩护................. 174作为的技术................................ 182的选择................................... 186有关不等的古学............................. 190与社会................................... 194时代与人生...................................... 198垃圾时代的选择................................ 198思适者生存.................................. 203不确定的确定................................ 207从莫维斯线到自我殖义.................... 211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 218驯化........................................ 2262016——技术、社会与断想.................... 231的生活断想................................ 235经济的爱情.................................. 239爱情古..................................... 241古学的视角.................................... 247历史的价值.................................... 247史前史的意义.................................. 252古学的贡献.................................. 254后记............................................ 259
点击展开
点击收起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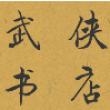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