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的逻辑 修订版 经济理论、法规 周其仁
新华书店全新正版书籍 支持7天无理由
¥ 24.4 4.2折 ¥ 58 全新
库存20件
北京丰台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74490
出版时间2017-10
版次2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392页
字数330千字
定价58元
货号122_9787508674490
上书时间2024-09-12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改革的逻辑是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周其仁教授关于中国改革的力作,多年。
改革的逻辑,足够的高水准和的接地气,摆脱了只停留在呼吁改革层面,是一部执政者和大众都亟需阅读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务实之作。
改革的逻辑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回望、深察、预见改革之大势,揭示中国经济未来之走向,探索中国经济前行之方向与路径。
厉以宁、汪丁丁、等鼎力!
目录:
自序 /v
部分 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30年感言 / 003
做对了什么? / 006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 026
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收获的十年 / 033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 047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 054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 077
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 / 091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改革: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 121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 187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 / 206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 / 221
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 226
成都试验的新进展 / 236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 249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 265
货币无侥幸 / 269
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 273
主导投资的经济质 / 277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 281
第五部分 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
向内转型的困难 / 291
不能仅靠拉动经济 / 293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 296
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 / 301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 310
科斯定理与国资 / 318
第六部分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改革是对未来重要的投资 / 325
民贫国衰、民富国强 / 329
体制政策要靠前 / 334
止改革成为半拉子工程 / 337
避糟糕的政策组合 / 339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 347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 353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 357
接着石头过河 / 363
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 汪丁丁 /371
内容简介:
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回望改革,探索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从改革标志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他善于从现实世界出发,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风趣、直白的文字,将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从“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糟糕的政策组合”,周其仁教授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同时,周其仁教授对未来中国改革之路提出了独特看法。
作者简介:
周其仁,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众多经济政策制定背后的智囊,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入民大学经济系。后工作于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已出版著作有改革的教训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数网竞争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精彩内容: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辑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那听他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的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共也不过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怎么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难了。
但是,哪个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退出比赛,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公司来处理,那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可以消灭市场关系、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对那套“大词汇”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宣言说它创造了以往时代的的经济成,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有一种舆论认为我们的体制是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新闻,刘铁男案、案、东北四天里的三场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有负面新闻,也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觉,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额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见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粮库,一次过火面积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权。是说,土地制度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场大火,工人在车间里干活儿,门却被反锁了,着火后人跑不出来,活活被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出“缺位”,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办,用什么机制来监管,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不很远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这样的官制不改,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能有的新中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衡的难度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公社、“大”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的主体,也是产业结构中活跃的人、消费结构中活跃的人、活动中活跃的人,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有希望,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惯于批评中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吗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过时的人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得很热闹。可走进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辑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那听他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的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共也不过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怎么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难了。
但是,哪个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退出比赛,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公司来处理,那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可以消灭市场关系、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对那套“大词汇”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宣言说它创造了以往时代的的经济成,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有一种舆论认为我们的体制是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新闻,刘铁男案、案、东北四天里的三场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有负面新闻,也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觉,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额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见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粮库,一次过火面积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权。是说,土地制度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场大火,工人在车间里干活儿,门却被反锁了,着火后人跑不出来,活活被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出“缺位”,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办,用什么机制来监管,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不很远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这样的官制不改,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能有的新中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衡的难度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公社、“大”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的主体,也是产业结构中活跃的人、消费结构中活跃的人、活动中活跃的人,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有希望,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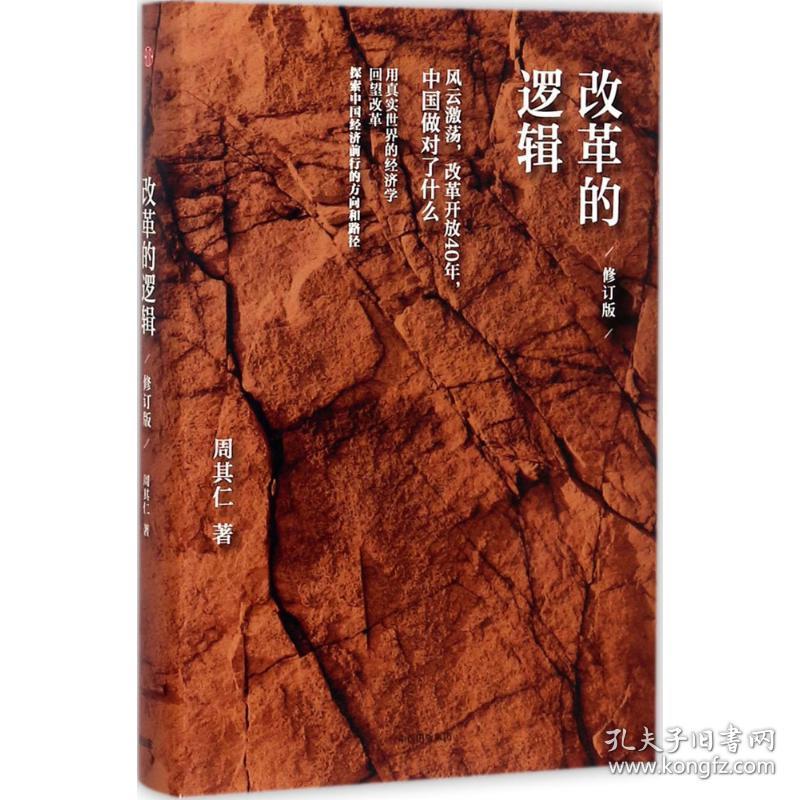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