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晓声作品 父亲+母亲 中国现当代文学 梁晓声
新华书店全新正版书籍 支持7天无理由
¥ 52.2 4.4折 ¥ 118 全新
库存36件
北京丰台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70149
出版时间2022-06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256页
字数222千字
定价118元
货号xhwx_1202664332
上书时间2024-06-25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8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父亲茅盾文学奖得主、电视剧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父亲曾获很好小说奖入选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中文不错课本教材央视读书栏目倾情,听众和读者广泛共鸣每一位父亲和孩子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尽管父亲再坚强沉默也会有自己想说还没说的话母亲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电视剧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书写中国式母亲的凡与,彰显女在逆境中的乐观和坚强!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
目录:
《父亲》
《母亲》
【注】本套装以商品标题及实物为准,因仓位不同可能会拆单发货,如有需要购买前可联系客服确认后再下单,谢谢!
内容简介:
父亲父亲用朴素真挚的文字记录了梁晓声与自己父亲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全家人都靠他出体力供吃穿,不善于表达的父亲是默默吞下生活中所有的苦。他的愚昧与狭隘曾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磨难、让家人之间有了隔阂,但当他开始老了他也终于慢慢对自己和家人有了新的理解。当一个儿子也步入中年时,父亲在他眼里已需要依附于自己的人格才能继续在社会上存在,这时如何让父亲重新获得与自己并存的人格已是父子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本书除了父亲还收录了北方的森林钳工王军鸽带锁的记冰坝。母亲母亲是作家梁晓声的小说。该小说部分内容被选入了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8课。作者在小说中记叙了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勤劳节俭,保持善良、纯正的品格,以身作则,在做人、做事方面给儿女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表现了慈母对子女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敬爱之情。
同时,作者以母亲为缩影,描述了会的起伏变迁,多层次描写了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
小说语言朴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感人至深的意境,在严肃的同时,作者巧妙的文笔又让文章时不时充满幽默氛围。作品体现了对家的看重,也含有父母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精神,具备及其强烈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父亲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政协委员、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母亲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政协委员、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精彩内容:
父亲 父亲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保证非常不错,靠出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很好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次对我发脾气,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人的不足十六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吃联系在一起
p12母亲 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 这一个孤独的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做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那儿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 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 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
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在当年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四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要回咱家去一遭!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感到同样的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可以算作名人的人。 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她的老家的话。
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 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 有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来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哇哇大哭,哭得背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 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 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 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女人没有放过的。 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是我对母亲身世的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我的母亲在她没有成为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们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的衣襟长大成.人。 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优选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 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因为我曾这样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
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以及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雨潇潇的孤独的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趁机向建筑部门讨要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 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家。 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孙”。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一个底层女人廉价的体力。翻沙——那是男人们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 母亲几乎没有哪不带着轻伤回家的。 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出一片片的洞。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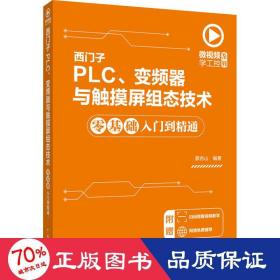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