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瓮葬
¥ 38 4.9折 ¥ 78 全新
库存40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托马斯·布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57100773
出版时间2021-06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06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344页
字数300千字
定价78元
上书时间2021-07-02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2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图书信息】
书名:瓮葬
著者:(英)托马斯·布朗
译者:缪哲
责编:李鑫
定价:78.00元
字数:300千字
页码:344
印张:10.75
开本:32开
装帧:裸脊精装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
版次:2021年6月 第1版
印次:2021年6月 第1次印刷
ISBN:978-7-5571-0077-3
中图分类号·CIP第四项:①I561.14
主题词·CIP第三项: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英国-近代
【编辑推荐】
◎爱默生、伍尔夫、艾略特、博尔赫斯等大师仰慕的文学奇才。关于死生、信仰、仁恕、希望的古怪之书。
◎托马斯·布朗是十七世*一位怪僻而低调的英国散文家,但他好奇多思的性格,幽深艰涩的文风,独对灵魂的神秘思考,以造物主的眼睛对尘世的观察,却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爱默生是其忠实读者,T.S.艾略特盛赞其“不朽”,博尔赫斯甚至一度是其模仿者。
◎缪哲经典译著:英国文学中三部各具个性而难于翻译的经典——《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其中文版均由缪哲先生首先完整移译,三部作品的风格也正符合译者的个性与趣味。缪哲先生中英文功底深厚,其译笔朴拙,雅洁,以精妙的文辞准确还原原著气质,读其译作,是一种双重享受。
◎本书包括托马斯·布朗三种作品:《医生的宗教》《瓮葬》《致友人书》。前两种堪称“布朗声誉之堂的两根支柱”。书中特别收入了约翰逊的《布朗传》一文。
◎本版精选插画三十余幅,紧扣书中信仰、死亡、丧葬等主题。
◎裸脊锁线,翻阅舒适,易于捧读;精装书壳,手工裱糊,美观耐久;封面贴画压凹,烫金印黑,雅致大方。
◎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两张。
【内容介绍】
本书收录了十七世纪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布朗的三种作品——《医生的宗教》《瓮葬》《致友人书》,同时将约翰逊的《布朗传》置于书前,以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布朗其人其文。
《医生的宗教》是关于宗教信仰的灵性思辨,也是布朗的一幅心灵自画像:他一面脸朝着过去,有中世纪的狂信、古怪和迷信,另一面脸对着将来,有十七世纪正在发展起来的情理态度和科学精神,而两者又往往杂糅一处,为严肃甚至枯燥的神学带来独具个性的诗化理解。
《瓮葬》源于一次古罗马葬瓮的出土,好奇心盛的布朗不但对这些遗骸做出一番阐释,而且谈论自古以来各国的丧葬之道,进而探讨生死问题,深刻曲折,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以上二者是为托马斯•布朗“声誉之堂的两根支柱”。
《致友人书》中,布朗向朋友通报另一位友人的死讯,由此谈及生命、疾病与死亡,并追念亡友之懿德,劝导友人见贤思齐,以警句体的语言为人称道。
【作者及译者简介】
作者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0.19—1682.10.19)
17世纪英国作家、医生、哲学家,巴洛克散文风格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想象新奇,行文曲折,深刻而广博,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柯勒律治、爱默生、T.S.艾略特、麦尔维尔、伍尔夫、博尔赫斯等几代名家一致尊崇。著有《瓮葬》《医生的宗教》《流行的谬误》《居鲁士的花园》等。
译者
缪哲
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中西艺术史学者。著有《祸枣集》。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鲁滨逊漂流记》等。其译笔精妙风雅,古色古香,于译界颇受推崇。
【名人推荐】
培根和弥尔顿之外,布朗是十七世纪极伟大的散文作家,他是不朽的。
——T.S.艾略特
我写的东西怎么敢与托马斯·布朗爵士或是爱默生的巨著为邻呢?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莎士比亚以来极具想象力的心灵。
——詹姆斯·洛威尔
独对灵魂的神秘思考,因罕见的天才托马斯·布朗爵士而有了最合适的表达。他极强的自我中心感,为所有心理小说家、自传作者、忏悔家及情感随笔作家铺平了道路。他是第一个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转向其孤独的内心生活之人。
——维吉尼亚·伍尔夫
触动我们内心的事物,其不可见性和不可捉摸性对于托马斯•布朗而言,也是一个到最后都无法探测的谜团,他把我们的世界看作仅仅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托马斯·布朗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书写,试图从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或者也可以说,用造物主的眼睛去观察尘世的存在,观察他身边的事物,观察宇宙的领域。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土星之环》
当我看到这些晦暗却华丽的文字时,我似乎是在俯瞰一潭深渊,在深渊的底部埋藏着无数珠宝;也可以说它是一座由怀疑与苦想构成的宏伟的迷宫,我愿意唤醒作者的魂灵,让他引导我穿过它。
——查尔斯•兰姆
我们读布朗,他的弥足欣赏之处主要在他的散文风格,即所谓的巴洛克。他的文字形象化;想象奇特而突兀,使人惊喜;行义曲折,信笔所之,很像浪漫派;他的文字隐晦而多义,又古色古香;他善于用事用典;他的情调幽默、挑逗、微讽。总之,他的散文是具有诗意的散文。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长期以来,这几朵英国文学中的奇葩(《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一直都乏人问津,直到缪哲先生的出现。……缪哲先生的译笔在下是极为佩服的,也几次向别人推荐他翻译的书。床头所放的书里,那些书是伴我入梦的,《瓮葬》是其中宠儿。
——诗人多多
【目录】
译序
布朗传
医生的宗教
托马斯·布朗致读者
第一部
第二部
瓮葬
简论诺福克郡新近出土之葬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致友人书
布朗年谱
【试读章节】
瓮葬 第五章(节选)
这些死人的骸骨,早已经超过了玛士撒拉的年寿,埋在地下一米深的地方和一堵薄墙之下,上面坚固而华贵的大厦早已倾颓,它仍完好,地面上三次征服军的战鼓和脚步掠过,它仍静静地安息,若能保证自己的遗骨能如此长久,哪一位君主不会高兴地说:
Sic ego componi versus in ossa velim.
(当我只剩下残骨时,我愿这样静静地安息。)
时间是先于古物的,它可以把万物化为土灰,却保存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遗物。我们指望大庭广众下的纪念碑为我们扬名,却是徒然之想,因为湮没无闻反能延续,不为人知倒成了保护。倘若他们是死于非命并被塞进瓮里的,则这些遗骨就惹人遐想了,古代的哲人也会礼赞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被暴力掠走的灵魂是最纯洁的,它们保留着更不同寻常的倾向,它们带着一丝形神重聚的盼想,疲倦地离开了枯萎的肉体。假如他们是耗尽了岁月,年老体衰,却仍被时间包裹着,那也就无从辨认,而与婴儿合成一摊墨渍了。假如说,人打有生起就开始了死亡,那长寿就只是死期的延长,生命就成了一件可悲的作品。我们活着是与死亡相伴的,我们并非死在某一时辰;多少次脉搏的跳动,才构成了玛士撒拉的一生,这是阿基米德的事,普通人则计算摩西所说的人之寿命。我们的年寿是很可观的,正像微数累加起的一个小数额,在这里,无数个分数才可以凑成一个小小的整数。我们那一拃宽的寿命,还凑不满一根小拇指呢。
假如那必然的末日之临近,能给我们带来乐天知命的心境,那么苍苍白发也是幸福,半傻不呆亦非灾难。但我们长期习惯于活着,因此厌见于死亡,贪欲使我们视死亡如儿戏,甚至大卫也播权弄柄,残酷杀人,所罗门也难以称得上最智慧的人。
但许多人却老得太早,还远不到老耄之年呢。苦难拉长了白日,而悲惨的生活,则造成了阿克梅的暗夜;对于这一种生活,时间是不插翅膀的。但最令人厌烦的生活,是那种但愿自己之无生,而甘心于乌有的生活,这超过了约伯的不满;他所诅咒的,并非他活着的日子,而是他的出生;他满足于现有之态,以便能有来生的权利,尽管他在尘世的生活只是一种胎腹般的黑暗生活,像一个流产的胎儿那样。
塞壬唱的是什么歌?阿喀琉斯躲藏在女人中间时叫什么名字?这些问题虽然费解,却还可以推测。这些瓮中人何时进入那著名的死亡国度,与君主、谋士们一同安眠?也可以约略索解。而这一堆骸骨的尸主是谁,这骨灰又会变成谁的尸体,却是博古之士也无法回答的。不仅凡人,即使是精灵也难以了断,除非我们去叩问本地的保护天使,或是死者的监护神。假如他们的名字,能像他们的骸骨那样保存完好,那么在不朽的路上,便不是这样跋前踬后了,但托身于遗骨,不过如金字塔之空存那样,是垂世的歧途。这些无谓的尸灰,空存于天地之间,名字、身份、时代以及性别,都已经湮没不存了,即使落在后人的眼前,也不过是人生虚幻的象征,骄傲、虚荣和丧心病狂的解剂。虚荣的异教徒们,认为天地是永存的,人的永世大名,没有哪位神灵可以剪断,于是纵容自己的野心,从不因湮灭不存的必然命运而心灰意冷。甚至古人的雄心,也在我们之上,为满足虚荣,他们早试身手,在时间的亭午之前,就已经大遂其志,因此那些古代英雄,虽然早已是碑版荡然,尸首无存,名字却流传到了今天。到了这晚近的时代舞台上,雄心则害怕伊利亚的预言;查理五世也不能指望自己的声名,活得过赫克托尔的两个玛士撒拉之年寿。
所以,在今天看来,为名垂久远的事而恓恓惶惶,似乎是过时的虚荣,一宗墓木已拱的愚蠢。我们不能指望像某些人年寿久长那样,想靠名字永寿;雅努斯的两张面孔,是不成比例的。抱有雄心大志,已经为时过晚。人世浮沉的戏剧,早已经演完,虽然人意恒多,却已是世日苦短了。我们想靠纪念碑延续声名,却又天天祈祷碑版荡然的事,我们不希望它永存,以免在末日来临时,破坏我们对来生的期望,所以想借墓碑垂名,是和我们的信仰相抵触的。既然我们落生于日落时代是出于天意,则天命就不许我们抱有非分之想。我们行将目睹的,是所余无多之来日,所以出于天性,我们就得寄希望于来生,也没有理由不去考虑一下它的长短,而对于它来说,金字塔是雪做的廊柱,逝去的百代光阴,不过如白驹过隙而已。
圆和直线拢束着一切,而圆加直线,则必然要结束一切。时间的鸦片是没有解药的,尽管在短期里,它会留意于万物。我们父辈的坟墓在我们短暂的记忆里,而且还凄凉地告诉我们,我们将怎样被埋葬于后人的记忆。墓碑能讲实话的时间,不会超过四十年;一代代人过去,有些树却依然屹立,古老的家族活不过三棵橡树。指望别人来读我们干巴巴的墓铭,像格鲁特书中的许多墓铭那样,或想靠那些谜一般的绰号,以及名字的起首字母来获得永生,或指望博古者来考求我们是谁,或像对付木乃伊那样,为我们重新起名,这对研究永恒的人来说,只是冰冷的安慰,即使它们使用了永恒的语言。
只满足于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而不计较他们是否了解得更多,这是卡尔丹的僵冷的野心。命星所定的性情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他一笑了之,只愿像希波克拉底的病人,或荷马诗中阿喀琉斯的骏马那样,单靠一个光秃秃的名字垂世,而不计功业与懿行,但功业与懿行,却是涂在我们名声上的香膏,是我们存在的entelachia(贞实)与灵魂。立下伟业却无声无臭,要比遗臭万年好得多。与有名有姓的希罗底相比,那个无名的迦南女子是更幸福的。谁愿做彼拉多而不愿做那名善良的小偷呢?
然而不公正的遗忘,却盲目播撒它的罂粟,不加区别地对待人的身后之名。谁不可怜金字塔的建造者?建庙者声名无存,而焚毁狄安娜神庙的希罗司特拉图斯,却留名千载。时间保存了哈德良的坐骑之碑铭,反倒湮没了他本人的名号。我们靠英名来计算幸福的多少,其实是徒然,因为秽名同样永存;特尔西特斯之名垂千古,恐怕是不下于阿伽门侬的。谁知道好人定能扬名?谁又知道被人遗忘的俊杰,一定多于载入史册中的人?假如没有那永恒的记录,则第一个人恐怕和最后一个人一样,都不会为人所知,玛士撒拉固然长寿,却也只会名随身灭。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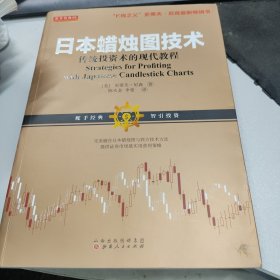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