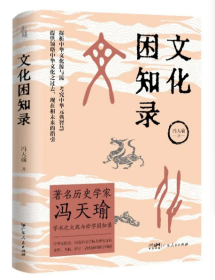
文化困知录 现货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学术之大成与修学困知录 中华文化史、历史语义学两大研究方向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修学理论
¥ 64 5.0折 ¥ 12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冯天瑜 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66728
出版时间2023-07
版次1
印刷时间2023-07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128元
上书时间2023-07-2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4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学术之大成与修学困知录 , 中华文化史、历史语义学两大研究方向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修学理论, 把课堂上老师们不容易讲明白的东西讲得既专业又易懂。
内容简介
本书是传承中华文明传统、借鉴中国智慧、弘扬中华精神的优秀学术普及著作,收录了冯天瑜教授最新研究成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以中西文化互动为视野,探析中华文化源流,考究中华元典智慧,提供领略中华文化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指引。
目录
壹 文化史片议
古典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定 / 2
“五伦”“三纲”分梳 / 13
“劳心”与“劳力”的离合变迁 / 24
科举制度——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 42
贰 历史语义学
中国衍为国名历程 / 74
“革命”概念的迁衍建立 / 92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 121
“共和”内涵的衍生发展 / 133
叁 中华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说 / 148
农耕文明思维探略 / 158
循环论与循环经济 / 171
试析“李约瑟悖论” / 176
“中国世纪”说当缓议 / 184
肆 明清文化五百年
“集古”与“萌新” / 194
明代理学流变考 / 206
明清之际文化近代性初萌——以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例 / 226
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 238
近人对传统文化的两极评判 / 250
伍 中日文化交际
中日何以“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 / 264
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 / 271
近代日本新语入华评议 / 288
中日间关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 / 302
近代日本中国调查的历史警示与文献价值 / 308
陆 问学历程
修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 324
庭教记略 / 332
未成文的家训 / 335
“住读”湖北省图书馆八年记 / 338
“看家书” / 346
书摘
书摘
小引
吾辈处古今更化、中外对接的大时代,种种文化问题纷至沓来,时处困惑中,困而思解,遂有若干断想,今择以呈现诸君,盼相与切磋,有以教我。
冯天瑜 2022年夏日于武昌珞珈山
“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新探求
中国人勤劳智慧,在古代即显示科技方面卓越的创造能力。16世纪以前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在农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学、数学、水利学等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涌现过墨子、张衡、祖冲之(429—500)、沈括(1031—1095)、李时珍(1518—1593)、徐光启(1562—1633)、徐霞客(1587—1641)、宋应星(1587—1666)等精研自然科学及生产技艺的卓越士人。他们可谓“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先驱。然而,在小生产和宗法社会条件下,在“重政务、轻技艺”的文化氛围下,精研自然科学及生产技艺的先驱们往往被忽视,“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典范——墨学,自秦汉以降被视为“小人之学”,几乎灭绝。清人汪中对墨子略加褒评,即被斥为“名教罪人”。直至晚清,孙诒让(1848—1908)著《墨子间诂》,方重振墨学,发掘墨子的贡献。中古、近古,先驱们的科技成就很少转化为社会普及知识,相关论著或作为一般笔记小说聊供谈资(如沈括的《梦溪笔谈》),甚或全然被弃置、遗忘(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即使徐光启以内阁大学士之尊所著《农政全书》,也未入学术主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成就,除天文历法、农学、水利、河工受到朝廷重视外,大都委屈于民间底层,如同大石镇压下的小草,无法雄强壮大。受到重视的天文历法、农学、水利、河工,也只由少数专门家授受,工匠农人实施,没有引进官学、私学的教学系统,多数士人并不闻问。手脑分离、崇思鄙行的大势,弥漫于文化教育界并影响全社会。
在西方学术史上,科学技术的受重视程度也有起伏变化。古希腊对自然哲学的关注不亚于对人文学的关注,科学技术是知识阶层研习的重要领域。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对力学、天文学、植物学皆有专门研究,并将探讨自然界的论著总括入《物理学》之中,哲学领域称之为“物理学之后”。中世纪欧洲神学统治精神领域,自然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生产技艺被压抑和扭曲。发展生产力是近代文明强劲的社会需求,科学及生产技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知识界逐渐走向哲思与技艺结合,文艺复兴的巨匠们承袭希腊精神,将“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起来,成为近代文化的典范。
以“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1452—1519)为例,他不仅以《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被世界公认为伟大的美术家,同时又是发明家、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设计家等。他最早用蜡制模型表现人脑内部结构,设想用玻璃、陶器制作心脏与眼睛,发明水下呼吸装置,创制发条,提出利用太阳能的构想;他关于人体比例及内部结构的研究,即使在今日看来也堪称精密。他是把科学、技术与人文学、艺术完美结合的范例。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培根(1561—1626)在《知识的进步》中提出建立综合知识体系的设计,将实用科学、手工技艺与抽象学术并列,纳入新知识体系,突破中世纪神学笼罩,昭示了近代文明的走势。
至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狄德罗(1713—1784)与数学家达朗贝尔(1717—1783)编纂《百科全书》(全名《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1772年完成),重视生产技术知识,广设实用科学、工艺、技术和贸易词条。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主流仍崇思鄙行,生产技术不入学问之门,而狄德罗、达朗贝尔力纠此弊,推崇“机械艺术”,将大量生产技艺词条收入百科全书中。该书的名称即突出对“科学、艺术和工艺”的“详解”,“从制造一枚缝衣针到冶铸大炮、制造一架羽管琴键,巨细工艺悉数包罗,呈现18世纪法国传统技术工艺的知识全景”。为收集整理生产技术知识,“狄德罗遍访法国各行业最好的作坊和工匠,观察、采访、记录,亲自操作复杂的工艺,将所得第一手资料分析编纂成图文,再回访提供资料的作坊与工匠,讨论修正”。百科全书派运用新知识体系整理法国传统生产技艺,完成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知识准备,法国在18—19世纪之交紧随英国成为世界科学及工业强国,与此大有关系。
近代初期的中国,“轻自然、斥技艺”的传统尚未扭转,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无力采用先进技艺,而“临民”“治世”的士大夫阶层则漠视科技。这种状况在清末显得十分突出。19世纪中叶,魏源(1794—1857)指出:
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
谭嗣同(1865—1898)更具体揭露清末当政者科技常识方面的无知:
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若何,击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
清末当政者这种对科技的无知,不仅使中国连连惨败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而且,当政者将近现代科技视作败坏心术的“奇技淫巧”“形器之末”,加剧了他们政治上的冥顽不灵。
晚清以降,随着工业文明初萌,涌现出李善兰(1811—1882)、徐寿(1818—1884)等兼通中西、学贯文理的新士人,他们走上“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之路。中国近代科技前驱李善兰,幼阅《九章算术》,14岁自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利玛窦、徐光启译本),走上会通中西数理之路,著《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椭圆拾遗》《史器真诀》《对数尖锥变法释》《级数四术》《垛积比类》等,汇集《则古昔斋算学》13种24卷;又译西方天文学、力学、植物细胞学等,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京师同文馆从事数学教学十余年,审定《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踌针》等数学教材,培养一批数学人才,是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鼻祖。
严复(1854—1921)是清末民初人文—科技双轮并进观的倡导者,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其译著是中国20世纪初重要的启蒙读物。严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并将“天演”规则推及社会,力主变法以图存。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会通的早期名作。
随着现代文明的演进,中国人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在文—理的取向上发生很大变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流行语,“重理轻文”则成为趋势。这是“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传统的反向运动。“重理轻文”当然包蕴着别样的偏颇,而此种倾向的出现,肇因于近百年间政治强势干预人文学,导致人文学失范和人们对人文学的疏离,而科学技术的社会实效性及超然于政治之外,给人们以吸引力。而文理并重方为正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人文与科技不可偏废。“重政务,斥技艺”与“重理轻文”是两种极端的取向,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动共进,达成二者的协调发展,方是健全的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
五、清末“废科举”的得与失
作为拔擢民间英才的善政,科举制也有其流弊,这便是助长读书做官、升官即得荣华富贵的社会风尚。宋真宗(968—1022)的《劝学诗》将科举考试的“好处”归结为: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功名利禄成为指挥棒,引导士人奔竞于仕途,其高明者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末流则沦为“禄蠹”,“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便是碌碌终生的士人典型。读书当官成为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理念,一些下层父老也谆谆告诫子弟苦读入仕,由民入官,享受荣华。这种风靡千载的风尚,既是“官本位”的产物,也助长了“官本位”的膨胀。
科举制的另一弊端,是引导士人以经史为唯一学问,使科学技术等实际知识不入社会文化主流。而宋代“右文抑武”,高调实行科举制,导致士人柔弱,宋代经济文化发达而武功不强。科举制的此一缺陷,当时即遭有识者诟病,南宋朱熹有“谋恢复,当废科举三十年”的愤语。元代初中期停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在儒臣力倡下,重启科举。
明清两代科举极盛,而八股取士等积弊渐深。延及清末,科考内容及考试方法的迂腐愈益昭彰,康有为指出,科举出身的“翰苑清才”不堪新政之用,除熟悉八股制艺之外,“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固有的科举制已无法适应社会近代转型的需求,废改的呼声遍起朝野。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1835—1902)上《图存四策折》,其一为“废科目以兴学校”。山东巡抚袁世凯(1859—1916)有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以增学堂之议;刘坤一(1830—1902)、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内容之一是变革科举。
顺应朝野呼声,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武举,此为变科举的第一步。
1904年1月,张之洞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在修订学堂章程时奏称: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此奏折获清廷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从学堂选拔人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隋唐以降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戛然而止,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随之走向崩解。历史的吊诡处在于,领衔上奏废除科举的,早年多为科举骄子,如张之洞15岁中乡试头名、26岁中殿试第三名(探花)。身为重臣的张之洞等人,晚岁面对纷至沓来的近代转型,困于科举弊端,又无法在此制之内更张变通,终于决定将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一废了之。
对于清末废科举,赞扬有之,如维新派所办《时报》发文,称此举“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另类评议亦接踵而至。废科举后四个月,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评议“废科举”说:
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在这中性语句中,深蕴着对科举制贸然全盘废弃的忧思。
1905年前后曾力主废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即颇有悔意,他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称废科举是因噎废食的不智之举,提出“复科举”的建议。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批评清末“废科举”“铸成大错”: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姑息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
-

-

-

-

-

-

-

-

-

-

-

-

-

【封底】
-

-

-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