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联大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31.43 5.4折 ¥ 58 全新
库存2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丁元元,真故图书 出品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559661999
出版时间2021-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1613056
上书时间2024-12-3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丁元元,有名记者。上世纪90年代接触西南联大研究,2014年开始寻找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通过大量亲历者的口述,抢救下一段珍贵的历史底本。历史学者傅国涌评论说,丁元元的采访补充了联大档案史料中缺乏的生活和教育细节。
目录
序
自序
就当一个普通人
联大世家
国之大“义”
“救国”的梦
活着的“烈士”
从联大到黄埔
冲上云霄
浪里白条
归去来兮
何为纺织?
隐姓埋名于404
百岁发明家
清醒时分
师从“”
参悟
糊涂“大玩家”
言必称先生
机缘人生
过去的人很厚道
深藏
后记
内容摘要
就当一个普通人 据《国立西南联大校史》记载,从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九届毕业生共一百五十三人——人数之少,堪比慢工出细活的手工作坊——吴德鋐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西路的一处老式石库门里,走过狭窄陡峭的楼梯,吴德鋐从二楼的“斗室”里打开门,热情地招呼我进去。房子不大,所以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有些乱,他几次说:“一直说要拆迁一直没有动。” 即便年过九旬,吴德鋐依然精神矍铄,说话条理清晰。几次见面,我们聊起过许多联大的名师,还有那些扬名立万的毕业生。讲到自己,他坦然地笑言:“我不出名的。”的确,他并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成为领导人、科学家、名教授、名作家、名记者,而是在上海的纺织系统默默无闻地搞了一辈子的经济工作。 关于母校,他常把自己的恩师、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挂在嘴边。这位政治学家曾经对学生们说过:“想要当官的不要来,我这里是‘政治学系’。攻读政治学绝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一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 吴德鋐后来的人生,大概没有实现恩师所说的“上策”“中策”。那就当一个普通人——他的一生,终究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 2014年9月16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吴德鋐,他是我见到的第二位联大校友。 他的家在北京西路上的道达里,路牌是318弄,走进去其实是前面一排街面房子的后门。从一个旧式的红木门走进去,可以看到一楼过道口自上而下排着六七个电灯开关,这也代表了小楼内的住户数。拾级而上,过道很窄,几乎只能容一个人通行,而楼梯还有点陡峭。1922年出生的吴德鋐每天就在这样的楼梯里上上下下。 因为不知道吴德鋐家具体是哪一间,我拨通了他家的座机,听到声音从楼上传来,就循着声音的方向上楼,一直到了三楼才发现他已经在二楼打开了房门,招呼我进去。 显然,里面的空间也不大,把房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人要让开,我才能走进屋子内的一个细小通道,再走进去也要时时小心不要碰到边上的东西。 走过小通道之后,里面似乎是个客厅,房间里的东西堆得很杂。再里面可能是一个小屋子。客厅的角落里架着一张沙发床,他的女儿躺在上面玩电脑。我后来再去的时候进过里面吴老的卧室,空间也很小,堆满了他的东西,走动都不容易。 在我呈上自己的名片之后,吴老也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谦虚地说:“这个供你参考。”名片上的内容很多: 吴德鋐仲龢 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研讨者今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校友之一西南联大法商学院 1941-1946法学士 高级会计师、经济师 因为家里地方小,女儿又在场,他提议出去找个地方坐坐。我们打车去了两公里外的一家星巴克,我给他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加了两袋“健康糖”。吴老作为一个曾经的名校高才生,丝毫没有因为年纪的关系而与这个坐满年轻人的空间产生太多的违和感。 吴老说星巴克的味道挺不错的,于是喝着咖啡,向我讲起了从前的事。回来的时候,他执意说喝咖啡的钱要和我AA,我说您就给一个“联大脑残粉”一点表达心意的机会吧。他还是很坚持,在出租车上还折着几张皱皱的人民币一定要塞给我。 出租车停在弄堂口的对面。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北京西路上,我试图保护这位1922年出生的老人安全地穿过马路。我试探性地伸出左手,有些忐忑地等待着他的态度。他终于握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右手,可是我分明能感觉到其中的力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温暖甚至激动,仿佛握住了让自己心动的初恋女友的纤纤玉手。 1922年阴历二月,吴德鋐出生在镇江。他的家庭可谓书香门第,祖父在两江做“督学”(学政),属于朝廷派驻各省督导视察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的官员。说起来官不算小,但坐的是清水衙门,经济情况并不富裕。好在祖父被自己的上司兼同乡看中,招他做了女婿,并且分了一些土地作为祖母的嫁妆。 然而,这桩看似不错的姻缘为这个家庭未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婚后若干年,祖父的岳父家执意要将祖母一个因为近亲结婚造成先天性目盲的妹妹嫁给吴德鋐的父亲。“虽然当时言明允许我父亲另娶妻子,但毕竟女方也比我父亲要大几岁,辈分更是不对。可是,我父亲也没有钱,又在帮他们家工作,于是做了他们家的‘奴隶’,只能接受了。” 因为遗传原因,吴德鋐的大哥也是一位先天性的盲人,比他大许多岁。而家中老二吴德鋐则是父亲另娶的妻子所生。“父亲娶我的母亲时已经30多岁了,后来生下了我。” 说到这段不幸的家史,吴德鋐至今还有些愤恨:“传统的资本家,往往不惜牺牲下一代的利益甚至幸福,还觉得这是他们为家里做了事情。” P1-4
主编推荐
1.对联大学子的抢救式访谈,很可能是蕞后一份以亲历者口述形式,记录联大精英教育模式的珍贵资料。 原子弹研造者赵仲兴 铁血救国会骨干陈志竞 汪曾祺好友吴德鋐 …… 2.以课程设计、师资配置、学员家世等具体细节,揭示联大精英教育本质。 通识教育 作坊式教学 去化 去精致利己 3. 20位联大学子的求学实录,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参考。shou度从联大群体学子的视角,讲述联大精英教育模式的细节。给当代大学生很好的求学参考。 选专业是听从自己内心喜好,还是看哪个更好找工作? 大学期间是要参加社团、积累人脉,还是一心一意搞学术? 是考研深造,还是找工作? 是做个精致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 4.补充了关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新鲜资料,比如闻一多之死、杨振宁回国、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等。
精彩内容
“救国”的梦 在看了我记录下来的陈志竞的故事之后,有位朋了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故事的核心人物当然是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 片中也有一支以往不为人知却又十分重要的力量—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规模不算大,其成员皆为蒋经国效力,因而他们也被认为是“”。 在《北平无战事》中,一共出现了四位“铁血救国会”成员的形象— 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在中共地下党的梁经伦及分别“潜伏”在中统、军统系统内的王蒲忱和孙朝忠。四个人物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在于,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他们口中的那位“建”。 当然,在艺术创作中,历史的在程度上被夸张了,“铁血救国会”的成员其实数量多时大概也只有百余人,主要工作也不是“潜伏”。那么, 揭开虚构的面纱,历真正的“铁血救国会”成员究竟是怎样的? 我十分幸运,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找到了这样一位曾经的“铁血救国会”和“”成员、曾挂国军少将军衔的西南联大政治系 1942 届毕业生陈志竞先生,并且在他生命的后时刻,有了“五面之缘”。 拜访陈志竞,缘起于 1940 届政治系毕业生夏胤中的儿子夏敦义。他曾经对我说,联大校友会是一座“富矿”,并提到了陈志竞,说了两个关键信息—蒋经国的“”和曾经被判处死刑。 后来,我在 2012 年的联大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会的留影中,次看到了陈志竞的形象。当时九十五岁的陈志竞,安在中间一排的角落里,一件夹克衫,一头银发,很是精神,看起来只有七十多岁。 我试图在网络上搜寻一些关于陈志竞的线索,终找到两篇采访他的报道,其中之一的作者还是我的朋友、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杂志编辑周晓瑛。 周晓瑛告诉我,印象中的陈志竞和善,“很有联大气质”,但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即便是接受采访,也已经有些程式化。她还告诉我:“关于过去的许多事情,老人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幸而我写稿子的时候查到了一些关于陈志竞的档案,把其中的内容作为补充。”不过现在这些档案也已经不对外公开了。 在这两篇关于陈志竞的报道中,我大致了解了他九十多年人生经历的主要脉络。 陈志竞,浙江舟山定海人,1919 年出生,1942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央日报社工作。1943 年进入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很快进入了蒋经国的视线。1944 年,抗日战势胶着,正是“一山河一血”的年代。陈志竞和一批干校毕业生,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以政工干部身份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1945 年,陈志竞来到上海,先后担任杨浦区副区长、新泾区区长,再后来又竞选上海市议员。 此后,蒋经国要求步入政坛的陈志竞“归队”,担任上海青年军联谊干事,仅二十八岁挂上了少将军衔。 1948 年,蒋经国在南京励志社成立“铁血救国会”,陈志竞成为“铁血救国会”及其核心组织“中正学社”成员,之后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上海解放前夕,陈志竞携未婚妻洪小姐经广州抵达香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他再未“归队”,而是于 1950 年下半年回到了大陆。 他先到北京投奔联大的老师张奚若、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想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但由于他没有户口,无法工作,于是,陈志竞随建国会负责人李葆和前往河南办机械厂,担任其私人秘书。 原以为到了那里没人认识自己,没想到在当地遇到了一个复原的青年军, 问他:干事,你怎么在这里?”于是,厂里人都知道了陈志竞曾经是的“大官”。 “运动”开始了,厂里让他“投案自首”。陈志竞于 1951 年 2 月离开河南,先去杭州见了读于浙大医学院的未婚妻,她也让陈志竞相信, 还安慰他说:“万一你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先去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从杭州到上海,陈志竞去了杨浦区局登记“交代问题”,然后他被送进拘留所、看守所,后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4 年,陈志竞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1972 年,已超过法定刑期一年多的他又被送往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5 年,陈志竞重获自由,专车把他送到了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上海市领导在那里举行了招待会,宴请他和同一批被释放的二十多名前“国军” 人员。 但很快政治风向又有了变化,他被送到南汇的上海第三十七棉纺厂,在那里扫地、煮开水、喂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到厂里的学校教英文和数学。 1980 年,对陈志竞的判决改为“无罪”,他开始在上海市政协担任办公厅专员。 1982 年,64 岁的陈志竞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校医结婚,妻子给他带来了几位继子继女,但他本人没有亲生子女。 当年的未婚妻洪小姐,在获知陈志竞被判死缓之后,果然走上了朝鲜战场,从此杳无音讯。 周晓瑛和我说过,自己很挂念陈志竞:“但是老先生年纪大了,我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后来,随着走访的联大老校友越来越多,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有了共鸣。 我打定主意,要见到这位经历丰富的老人。 2015 年 1 月 28日、2 月 4 日,我接连两次去了陈志竞位于南丹路、番禺路路口的家中。次家里没人,隔壁邻居说,不太清楚情况,可能老先生和老太太身体不太好,都去了医院。次,我听到里面有声音,有点意外, 开门的是个二三十岁的女生,是他太太的孙女,说自己也是碰巧回家来给奶奶拿点东西,然后告诉我陈志竞住在的第六人民医院,病情主要是“器官老化”了。 2 月 7 日下午,我终于在第六人民医院十五楼老年科病房 29 床见到了陈志竞先生。 病房里有两张床,躺着两位病人。虽然我见过陈志竞两年前的照片,可一下子还是没有认出他来。此刻的陈志竞,毕竟没有当初那么精神了,戴着一顶绒线帽,遮住了头发,脸上的皮肤也不像照片中那么好,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紧紧地裹着被子,像是一个新生儿的“”。 里面那一张病床上的老人,床边围着三四个家属,一直有说有笑,这更显得陈志竞床头的落寞。但这也并不让人意外,毕竟陈志竞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何况,他的人生,已经落寞了六十多年。 我坐下后不久,照顾他的护工阿姨来和我打了个招呼,大概以为我是亲属。 初次见面,自报家门,然后询问陈老身体情况。他说:“身体还可以, 是每天要吃点东西(药),所以才住到医院里。” 这时,护士小姐来给他推静脉针。因为六院的老年科都是干部病房,所以护士十分恭敬,问了一声:“是不是陈志竞陈老师?”护士刚推针时,陈老喊了一声疼。护士尽量推得很慢,看得出老人很克制,但问他还是会说疼。护士有些无奈,表示自己已经推得够慢了,但病人血管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后还剩下一些,干脆不打了。 护士走了,我坐在病床边,看着连接的袋子里装着满满的黄色的尿液,心里很是难过。 因为之前已经看过关于陈志竞的两篇报道,加之预感到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很糟糕,所以我只是想陪他稍微聊几句,简单问了几个我想听他亲口说出的问题。 我问他关于联大还有什么记忆,他说:“联大,联大是西南联大……” 后来我们说起过他的老师张奚若,我提到张奚若的三个子女,分别是新华社记者、驻加使和空军参谋长,陈志竞两眼放光,频频惊异地说“噢”,还说:“张奚若是不错的,对我也很好。” 我问他:“当时您已经到了香港,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因为之前关于他的报道中,有的说是陈志竞自己不愿去,也有说因为没有得到蒋经国的征召,于是“心灰意懒”。老人想了半天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 这个问题,也许是围绕陈志竞一生为核心的关键选择,但如今似乎成为历史之谜了。 我又问他:“您后来有没有后悔没有去台湾?”他先是以为我说的是出狱之后,说:“那时候经国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又说是 1949 年,他说: “时间太久不记得了……” “解放之后,您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受了很多苦吧?”“这些事情,过去了不觉得苦……”百岁的陈志竞看待一切的苦难,都已经如此从容。 我问他洪小姐的消息:“是牺牲了吗?”他回答:“不知道,反正再没有音信了……” 我问他其他的“”成员,如负责台湾情报工作的王升,后来有没有来大陆看过他。陈志竞说:“王升和我通过信。台湾没什么人来看我,当年去台湾的同学倒是蛮多的。” 护工阿姨在边上插话说,自己老家有些从台湾回来的人,回到大陆不走了。我笑着说:“当年和他一起的人,在台湾当’(行政院院长李焕)。” 陈老看起来已经很虚弱了,实在不能打扰他太久,能够得到他亲口给出的这些答复,我已经心满意足。 其中还有个提到了他太太是不是也在医院,这时坐在病床另一边的护工阿姨连忙朝我摆摆手,我立刻此打住。 我起身告辞时,陈志竞很有绅士风度地说:“谢谢你来看我,还有事的话请便。”然后从盖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中,两次伸出相对灵便的左手,与我握手。 我又一次被打动。试问,若不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我有什么资格与一位 28 岁成为国军少将的“大人物”握手? 离开的时候,我把护工阿姨拉到病房外。阿姨姓李,河南人,一直在六院照顾病人。但对于这位病人的经历,她知道的很少,只以为陈志竞是一个教书先生,她告诉我:“陈老师很喜欢看打仗的电视节目。” 于是,我大概告诉阿姨,她照顾的是一位怎样的病人—他是中代牛的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表人才,又是浙江老乡,所以才被蒋经国看重, 做过青年军的教官,挂国军少将军衔。 阿姨补充说:“他真的很好,很和气,从来不发脾气,对太太也很好, 也不像隔壁床的老头整天要说外语。他之前还能走路,穿着一身红颜色的衣服,别人都跟我说,你照顾的老先生好精神,好漂亮!” 因为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还问我:“你说的那个牛的大学,长得不好看也不能被录取吗?” 此外,护工阿姨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他太太也在这个医院里,在上面十六楼,家里人都瞒着他这个事情,怕他受刺激,刚才真怕你说漏嘴……” 后来听说老太太出院了,但是腿脚不好,能来看他的次数也很有限,来得较多的是他的侄子和侄媳。 “之前他在十四楼急救,1 月 10 号转到这里来,我开始照顾他的。医生说怀疑是胃癌晚期了,可能他平时一直吃得少,营养不良。前一段用了药,一直吐血,后来把药停了,这才好一点。之前床头挂的牌子是‘禁止饮食’,这两天已经可以吃半流质了,今天还吃了半个馒头和鸡蛋。” 虽然病情有些好转,但面对他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直盘桓着一个词— 风中之烛。百岁的陈志竞先生,曾经何等少年得志,曾经受到何等折磨, 如今真的成为一支风中的,虽然他的意识还很清醒,但生命之火已经到了可能熄灭的关头。 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善良,告诉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探视者,说自己的情况还好,还要避免我担心。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命运坎坷的“”,可是见了他之后,我的心中反而更加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于是悄悄塞了一点钱给护工阿姨,希望她能够好好照顾陈老。也许我这样做是徒劳的,其实阿姨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只是觉得,他的一生被很多人亏欠了。任何人,或者少是我,应该做一些弥补的事情,虽然远远弥补不了这“有志者事未成”的遗憾。 3月 3 日,放心不下陈老,我又去看他。原本担心他熬不过新年,没想到老人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那时已经过了羊年春节,我问陈老:“您九十八岁了吧?”他笑着点点头。 我这次去除了带着陈老可以喝的饮料,还给他买了尿布。阿姨先是和我客气了一番,后来说:“要不再给他买块毛巾吧,毛巾已经有点硬了。” 因为羊年春节陈志竞没能回家,据说情绪不太好,一直吐血,直到我去了, 才有了笑容,所以我特意挑了一块红色的毛巾,想让他觉得喜气一点。我看到他嘴角有一丝白的印子,我小心地拿出一张湿巾纸帮他擦去,好像给我们家的新生儿擦口水那样。 走的时候,我对陈老说:“我不知道能帮您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您……”陈老却说:“国家对我很好,为我做了很多。” 那一刻,我紧紧地握着他清瘦却依然挺拔的手。可是,我到底能为他做什么呢? 我曾问陈志竞,洪小姐的全名是什么,他和我说不记得了。但后来,周晓瑛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些洪小姐的信息—她没有在朝鲜战场牺牲,生活得还很不错,成了部队系统一位级别较高的专家,在网络上还能找到一点点关于她的信息。 周晓瑛觉得:“她可能也因为和陈志竞的关系受到一些牵连,但当初离开陈志竞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风烛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的初恋是惦记着的。4 月 1 日晚上,想到此事,我怕陈老来日无多,给护工阿姨发了条消息,请她转告陈志竞“洪小姐后来过得很好”。由于一直没收到回音,加之又是清明,有点放心不下, 于是 5 日我又抽空去了趟六院。 一见到陈老我在他耳边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阿姨笑着说:“前两天已经告诉陈老师了。我把你的短信放在他眼前,他看了以后点点头。”我再次告诉他的时候,陈志竞还是笑着点点头,而且告诉我说自己之前确实不知道洪小姐的事情,所以知道她还好,也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护工阿姨说:“我问他洪小姐是什么人,是不是以前的妻子或者女朋友, 他跟我点点头。”还说之前想打电话给我,说好让我当面告诉陈志竞。 此刻的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出我的样子,是否记得我,除了洪小姐的事情之外,也实在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只是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样子,心里很难过。 阿姨撩开陈老的被子,给我看陈老的一双脚。因为有些脚气,脚趾缝中间都塞着棉花。 这是 2015 年的清明。阿姨说:“其实我很怕他今天走,今天这里已经走了两个老人了,20 床和 28 床。” 临走前我又塞了点钱给阿姨,她执意不肯收,我说:“请你为陈老送终吧。”她没有再执拗。 我突然想到,如果陈老时日无多,能帮他找到初恋情人,或许是后可以给他的安慰。 几天后,周晓瑛找到了洪小姐的全名,根据网上找到的线索,洪小姐应该八十八岁了,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还健在,但得试着找找看。 4月 13 日,我在家打了长途电话,先联系了她原来工作的单位,被告知洪小姐的关系已经转出,虽然电话已经更改,但还是提供给了我一个北京海淀区的住址。依照这个住址,我打了楼下小店的电话,但没人愿意代为寻找,于是又一路联系了这个地址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小组。居民小组的人说,老太太很好,但见面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儿,对方还算爽快地给了我洪小姐家的电话。 我忐忑地打过去,电话竟然通了。曾经的洪小姐发出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而且作为一个南方人,她的口音也变成了一口北京味儿。想必,当她从我的口中听到如此茫远的“陈志竞”的名字时,也很惊讶。迟疑片刻后, 她说:“陈志竞,我认识。” 我告诉洪小姐,陈志竞先生胃不好,恐怕时日不多。她问是不是胃癌, 我说应该是,所以希望和您联系一下。老太太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呗。” 之后我给陈志竞的护工打了电话,交代了其中的情况。天,我打电话去问,护工说对方并未来过电话。这让我有些不甘,于是又打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是洪小姐的儿媳妇,她说:“老太太也快九十岁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平时我们都当她是小孩对待。”儿媳妇坚信,婆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我知道,这分明是洪小姐根本不愿意讲。 儿媳妇说,老太太年事已高,要她打这个电话已经不大可能,于是我提议干脆我们这边打过来,对此她倒并不反对。 和李阿姨沟通了几次,她说陈身体又好了很多,精神起来了, 于是我决定 15 日周三下午干脆再去一次第六人民医院,帮老人完成这个心愿—于我自己来说,也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够见证这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意义特殊的通话。 到医院后,我先给陈老看了赵仲兴校友提供的几张现在云南师大的照片, 之后便借口上厕所,往北京打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起来竟然是洪小姐本人。也许有些唐突了,我也没有询问对方究竟态度如何,但是为了完成陈志竞的心愿,我还是立即把电话递给了他。 我原以为那一刻那一幕应该很神圣,其实它来得很普通。陈志竞拿起电话,用上海话(我想是他们年轻时交流用的语言)问:“××(洪小姐的名字)……侬是×× 是伐?侬现在在撒地方?……侬听不太清楚啊?手机的关系还是啥关系?侬几时休息伐啦?侬休息?……” 我原本说我和阿姨退出去,随便他们两个说些什么,可眼见陈老无法自己拿住手机,只能在他边上扶着话筒。我正为他问的那句“侬休息伐啦?” 这个没话找话的说法感到搞笑,可没想到,通话竟然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陈志竞示意听不清楚,我便接起电话来。这一头,老先生含着笑,轻声地自言自语:“嘿嘿嘿,洪 ××,寻着了。”而那一头,老太太冷淡地说:“他说的话我听不清楚,我现在耳朵不好。”我问有什么可以代为转达,她却说: “没什么好谈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悦,但为了让陈志竞不要感到异样,只能带着地和她说完挂断。 另一位之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提起洪小姐,陈志竞依然充满着爱意甚甜蜜。 挂了电话之后,李阿姨告诉我,之前我打电话给她时,虽然她已经走到了远离病床的床边,跟我确认是叫“洪什么”,结果陈老竟然灵敏地听到了这个名字,追问“洪 ×× 怎么了”。 陈志竞甚一度以为洪小姐要去医院看他,激动得很,后来才晓得只是我去医院帮他通话。阿姨说:“他昨天一直在等电话,等了都没怎么休息,所以今天睡到很晚才醒,我也没有叫他。” 她还对陈志竞的两个侄子和侄媳妇说:“你们的‘大妈’找到了。”小侄子甚很激动地说:“既然有号码,那我们现在打过去。”侄媳妇还问他, 是洪小姐漂亮还是现在的妻子漂亮。陈志竞竟然打趣地回答她:“都没有你漂亮。” 我告诉阿姨,你看他二十八岁做了杨浦区区长,还是少将,长得又帅, 身边怎么会少美女,女朋友怎么可能不漂亮。 当然,六十多年过去了,漂亮不漂亮的都只是浮云。对于走到生命尽头的陈志竞来说,此时此刻的洪小姐也许会是他的某种精神支柱。 于是,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九十八岁的陈志竞听说洪小姐在北京之后,竟然问我:“现在去北京方便吗?” 我说:“难道您想去北京看她?那也得等身体恢复到可以把身上的管子都拔掉才能去啊。” 他点点头,笑了。 因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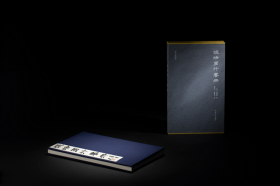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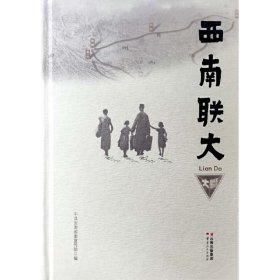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