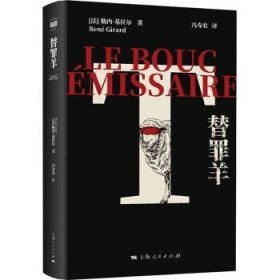
替罪羊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20.94 2.9折 ¥ 72 全新
库存4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勒内·基拉尔 著; 冯寿农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77499
出版时间2021-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2元
货号11720938
上书时间2024-12-17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序言 / 1 章.纪尧姆·德·马肖和犹太人 / 1 章.迫害的诸类范式 / 15 第三章.什么是神话?/ 28 第四章.与 / 56 第五章.特奥蒂瓦坎神话 / 70 第六章.阿萨神话、库尔特斯神话和提坦神话 / 81 第七章.众神的罪孽 / 93 第八章.神话科学 / 117 第九章.《》中耶稣受难的关键词 / 125 第十章.人死去…… / 139 第十一章.施洗约翰被斩首 / 156 第十二章.彼得的否认 / 185 第十三章.格拉森魔鬼 / 4 第十四章.自相纷争的撒但 / 228 第十五章.历史与保惠师 / 245
精彩内容
14世纪中叶,法国诗人纪尧姆 ·德·马肖(纪尧姆 ·德·马肖( 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法国诗人、音乐家。——译注)写的《纳瓦的审判》值得好好阅读。当然,作品的主要部分只是一首传统风格和主题的艳情长诗。但是诗歌的开头叙述了触目惊心的故事,描写了一系列混乱的灾难事件。纪尧姆曾亲眼目睹,惶惶不安,终隐居在家中,等待死亡,或者说等待这场难以描述的灾难的结束。一些事件是作者虚构的,另一些事件也半真半假。然而读了这首叙述诗,字里行间给人的感觉是:大概发生了某些真实的事件。 天上有迹象,下了石头般的雹雨,砸伤了行人。一些城镇被雷击。在纪尧姆居住的城市里——他没有说明哪一个城市——大批大批人倒毙死去。其中一些人的死因是犹太人和他们在徒中的同谋干的恶行。这些人究竟是干了什么,会在当地居民中引起这么多的居民死亡?他们在河里下毒。河水是的饮水源。天庭审判向居民揭示罪行的肇事者,要清算恶行,杀死肇事者。然而,人还是 不停地死去,而且越来越多,直到春天的,纪尧姆听见街上男男女女嬉笑着,唱着歌。一切都过去了,情诗又再度开始了。 自从他的诗问世后到 16和 17世纪,现代批评家对这首诗里提及的事件没有盲目相信。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学者要求批评家具备怀疑的精神,相信与时俱进的文学批评具有真知灼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的解读和释义,过去还认为存在真实信息的诗句今天反被怀疑不实了。另一方面,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经历了一场的危机,这场危机撼动了过去称为历史科学的东西。所有习惯于从文本中吸取营养的学者醒悟过来,都认为过去许多诠释不可能是确凿的。 乍看来,在事关史实方面,纪尧姆 ·德·马肖的诗歌的确经不起现代怀疑主义的批评。但认真思索一番,是在今天,读者仍可以通过虚构叙事揣测到背后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他们可以既不相信天上的迹象,也不相信对犹太人的指控,但他们不能用同一方式看待所有难以置信的题材,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视为虚假的。纪尧姆不会无中生有。的确,他是位轻信的人,他描述了人群歇斯底里的情绪。尽管如此,他在诗中所说的无数死者却是真实的,这显然是由法国北部在 1349年 1350年爆发的黑死病引起的。屠杀犹太人也是真实的,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群几乎在到处谣传是犹太人投了毒。在他们眼里,犹太人该杀。这场鼠疫给大家带来的恐怖足够证实了这些流言蜚语,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 是《纳瓦的审判》中有关犹太人的片段: 此后,来了一帮阴险恶毒、 背信弃义的歹徒: 那是穷凶极恶、 令人憎恨的犹地亚人, 他们喜恶憎善, 他们敛财聚钱, 神谕子民: 江河井泉 水清澄澈, 数处已变毒液, 数人已被毒死。 倘若饮之 顷刻暴死。 果然,乡镇小城 人畜成批死亡。 终于,致死的投毒 不打自招地暴露。 坐高望远, 君领天下,权倾朝野。 他再也不容倒行逆施, 揭露恶行于光天化日下, 要让恶徒知道 他们同样要付出生命和财产。 所有犹太人都该死: 上绞架,下油锅, 溺水淹死, 刀斩斧剁, 同样要处死可耻的徒内的同谋。 [1] 中世纪社会害怕鼠疫,一提起它的名字,人们惊慌失色。他们尽量避免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宁可看着疫情日益严重,也不肯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无能到极点,承认瘟疫降临,却逆来顺受,拒绝反抗,任凭瘟疫肆虐。所有人都愿意视若无睹,如同往常一样生活。这种置若罔闻、绝望的态度助长了对“替罪羊” [2]的围猎。无偶,拉封丹在他的寓言《鼠疫的病动物》里,也微妙地暗示了中世纪人对那个恐怖的名字几乎是从心里感到反感,怕一旦说出口,会给社群带来巨大的灾难: 鼠疫(既然应该用它的名字来叫它)…… 这位寓言家让我们了解到集体的:把瘟疫视为上天的惩罚, 凡人均等不一地犯罪,激怒了神的报复。为了摆脱灾难,必须找到 罪犯,让他自食其果,或者如拉封丹所写的,把他“奉献给”上天。 在寓言里,被查问的批嫌疑犯是那些猛兽,它们恭顺地表 述它们的行为,它们立即被宽恕。后,轮到驴,它是不残暴的 牲畜,因此,它也是弱小的、但不受保护的动物,后被定为 瘟疫的罪魁祸首。 历史学家在想:在一些城镇里,人们一听说发生鼠疫,瘟疫还未袭来,开始屠杀犹太人。纪尧姆的叙事诗证实了这一类现象:在瘟疫袭击前,屠杀已经发生了。但是作者把许多死亡归因于犹太人投毒,暗示着另一种解释:如果这些死亡是真实的——把它们当作虚构毫无道理,那么,他们可能是这场灾难的批受害者。但是,纪尧姆并没有这样感觉到,甚在事后回顾时也没有想到。在他看来,传统的替罪是被解释为瘟疫开始阶段的祸端。而对于随后阶段,作者承认存在一种纯粹是病理的现象。灾难蔓延之大,终使以阴谋投毒的解释不攻自破。但是纪尧姆不是根据事实去解释瘟疫的后期事件。 此外,人们在自忖:疫情要到何种程度,诗人才会承认其存在?因为他一直在避免白纸黑字地直接写下这个不祥的字眼。在关键的时刻,他谨慎地用一个好像那时还很少使用的希腊语词: “epydimie”(疫疠)。显然这个词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像在我们的作品里那样使用。它还不是一个相当令人畏惧的词,而更像是一个替代词,一个不直称“鼠疫”其名的新名称,这一次纯粹是在语言上找到一个新的替罪羊。纪尧姆告诉我们:在那么短时间内造成那么多人死亡的病因和质从来无法确定: 物理学家、医生, 无人知道死因, 究竟是来自何方?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任何无法) 除了只知道它是一种病, 人们称为“疫疠”。 在这一点上,纪尧姆还是相信舆论,而不是凭着自己思考。在14世纪,从“ epydimie”(疫疠)这个学术的词是会闻到“科学”的香味,它有点像过去人们为驱除鼠疫在街头巷尾用烟熏疗法散发的芬芳气味,有助于减缓人心里的恐惧。为行病取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了一半;给一个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命名,错以为已经控制住它。在我们的科学易发生错觉的、或依然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地诱惑着我们。简言之,人们通过拒绝称呼鼠疫,把“鼠疫”一词“献祭给”了神,这种语言的和当时或以前的人祭相比,是相当无辜的,但这两种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 在纪尧姆的叙事诗里,作者继续往前回溯,地叙述一切真实的和虚构的集体替罪羊、犹太人和鞭笞派 (13、14世纪天主教的一派,当众自笞借以赎罪。——译注)、下石头雹雨和疫疠现象。其实,他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所说的“黑死病”一类灾害的统一。他继续热衷于叙述灾难的多样:它们或多或少是生,但有时用意义把它们相互联系,像埃及十灾(根据《》的记载,古埃及确实存在过这十大灾难: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杀长子之灾。传闻十灾爆发的原因,是埃及法老王心理刚硬,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屡次的请求,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神吩咐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多行神迹奇事,用十灾降临埃及。——译注)一样。 我上述所说的东西几乎是显而易见。以来,我们都以同一种方式理解纪尧姆的叙事,读者也不需要我了。然而坚持这种阅读法不是无用的,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我们显露出勇气和能力。整整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承认这一阅读法,几乎众口一致,从未见过其他异义。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抛开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我们确定他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今,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现代人比他知道得更多,我们能够 纠正他的说法。我们有能力确定一个作者没有看到。我们还以一种更勇敢的胆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个恰恰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尽管他是盲目的。 难道说这种解读不值得广泛赞同吗?我们对它是否过分宽容?在司法上,只要在一点上证明证人不够公正,足以驳回一件证据。通常,我们把历史文献作为司法证据来处理。然而,为了纪尧姆·德·马肖,我们却违反常情,其实他也许不值得这般优惠的处理。我们确定在《纳瓦的审判》这首诗里所提及的迫害是一种历史事实之,我们意欲从一个基本点大概都弄错的文本中梳理出真实的东西。如果有理由不信任这个文本,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当作的嫌疑物,会拒绝据其寻找任何真实的东西,连迫害的原始事实也不例外。 由此,我们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犹太人被屠杀是件事实。我们脑海里一下子出现个答案。我们没有孤立地阅读这个文本。在同一时期还存在其他文献,它们讲述着同一主题,另一些文献比纪尧姆的诗作更有参考价值。那些作者表现出较少的轻信。这些作品形成了一个实的史料网络,我们把纪尧姆的诗作置于这个网络中间审视。正是依靠这个历史语境,我们地在我所援引的段落中分与假。 事实上,黑死病期间的反犹迫害成了相对众所周知的一组史实。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知识,在我们心中激起某种期待。纪尧姆的作品回应了这种期待。从我们个人的体验和与作品的直接接触上产生这种期待视野并没有错,但诚然,从理论上看,它还是不足够的。 虽然存在着历史知识的网络,但从大同小异的原因上看,这一网络中的诸文献,比纪尧姆的诗作更加可信。而且,因为我已经说过,我们不知道他讲述的事件发生在何处,我们也无法地把纪尧姆的作品置于背景中。事件发生可能在巴黎,也可能在兰斯,或者可能在另外的第三个城市。但不管怎么样,背景并不起关键作用;即使它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发生的地方,现代读者终会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错杀受害者的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读者会想到文本所说是假的,因为这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同时又会想到文本所说是真的,因为受害者是真实存在的。他会像我们一样地分与假。是什么给了我们这种能力?“苹果框里一个苹果烂了,那将它整框扔掉”,根据这种原则行事是确当的吗?如果让现代“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放任自由,他们可能会全盘否定作者的一时轻信和一点天真,我们难道该像他们一样怀疑吗?有人说所有历史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从我们所研究的文本中也无法梳理出任何东西,更别提找出迫害的史实,他的这种说法对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绝不!”不加区别的怀疑主义并不考虑文本的质。在文本的真实资料与虚构资料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关系。当然,刚开始,读者不会说:这是假的,那是真的。他只看到一些或多或少可信与不可信的题材。死者越来越多是可信的,这可能是一场瘟疫;但投毒是不大可信的,尤其是纪尧姆所表述的规模如此之大。在 14世纪,不可能有一种毒如此巨大的。作者对所谓罪犯的仇恨是很明显的,这种仇恨使人怀疑他的观点。 少,我们会隐隐约约地看到两类资料之间互相影响着,否则,我们无法辨认它们。倘若真的暴发一场瘟疫,那它可能燃起沉睡的偏见之火。迫害者的自然集中于的少数派,尤其是在危机的时刻。与此相对,纪尧姆所轻信的指控又证明了一场真实迫害的合法。像他这样的诗人大概不会残暴。他之所以相信他所叙述的故事,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大概都相信它。因此,文本暗示着狂嗥咆哮的舆论准备接受荒诞不经的谣传之,它暗示着作者已证实的大屠杀前风雨满楼的气氛。 在非真实表征的语境里,其他表征的真实却得到证实,并演变成可能。反之亦然。在真实表征的语境里,其他的非真实不太可能来自为虚构而虚构的“杜能”。然而,我们承认想象,但不是任何想象,而是那些追求者的特定想象。 因此,在文本的所有表征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契合,一种相互的对应,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假设才能了解它。我们所读的文本植根于一场真实的迫害,而这场迫害是作者以迫害者的观点报道的。这种观点必定具有欺骗的,因为迫害者深信他们的具有法律依据,他们把自己当作伸张正义的人。在他们看来,受害者是罪该万死!但是这种观点也具有部分真实,因为自恃有理的确定鼓励这些迫害者毫不掩饰他们的屠杀。 信息的真实而言,整个文本的价值远不如其坏的一条信息,这已成常识。但诠释纪尧姆 ·德·马肖的文本时,应该打破这个常识。倘若作品描写一些有利于迫害的背景,把这些受害者视为某类罪犯,或为了增加可靠,描述他们触犯了迫害者通常归咎于他们的罪行,那么这场迫害的真实是强的。如果文本本身肯定这一事实,我们更有理由接受它,而不是怀疑它。 一旦读者感受到迫害者(作者)的观点,指控的荒谬远没有损害一个文本的信息价值,还加强了它的可信,但这于它本身所反映的方面。如果纪尧姆把杀婴仪式的故事添加入投毒事件里,那么他的表述显得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向我们传达的屠杀事实的真实没有丝毫减弱。在这类文本中,指控越是不可信,屠杀的事实越可信,因为它们向我们传递了一个社会心理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屠杀几乎是肯定会发生的。反过来看,屠杀的主题,加上瘟疫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素有修养的文人理应认真对待投毒故事。 毫无疑问,迫害表征对我们来说是谎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一般迫害者和中世纪迫害者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文本的确可以证实其谎言本质所提出的所有猜想。当可能的迫害者描述自己进行迫害的真实,他们值得人们相信。 两类资料的结合才产生确定。倘若仅在极少数例子上遇见这种结合,那么这种确定是不的。但是它的出现频率太高,因此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唯有从迫害者的角度考虑真实迫害,才能解释这些资料的规则的结合。我们对所有文本的解读在统计上具有确定。 这种统计学特征,并不意味着确定建立在那些均是不确定的文献的纯粹、简单的累加上。这种确定的优势相当显著。纪尧姆·德·马肖作品的每一则资料都有很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它身上能找到可信与不可信,两者相得益彰,互相解释,互相确定存在的合理。我们在统计上具有确定,是因为任何一则被孤立考察的资料可能是一个伪造者的作品。这种可能很小,不过在个别文献中,可能并非为零;反而在大量文献中,可能等于零。 现代西方世界为揭露“迫害文本”(textes de persécution)中的真实所采取的现实主义解决方法是可能的方法,它也是确定的,因为它能解释这一类文本中所有资料。不是人道主义或思想意识命令我们去采取这种方法,而是决定的理智支配我们去这么做。这种诠释并没有篡夺它所享受到的共识。历史无法提供我们更可靠的结果。对于那些考察“心态史”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值得依赖的基本证据,也是一个不赞同纪尧姆 ·德·马肖的虚构的历史学家的证据,与迫害者或同谋者的可耻证据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要更有力,因为它是从潜意识里流露出真实。关键的证据是迫害者的证据,他们相当天真,没有乔装洗刷去罪行的痕迹。而现代迫害者却不同,他们太狡猾,不给人留下任何用以指控他们的把柄。 我说的天真,是指迫害者相当相信自己有理,并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以于没有掩饰和销毁证明他们迫害的部分资料,在他们的作品里这些资料有时以真实和直接袒露的形式出现,有时以误导但间接暴露的形式出现。所有资料都高度定式化,而正是两类定式( stéréotypes)——真实与误导——的结合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文本的质。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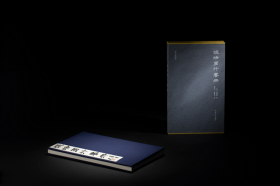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