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刀宗:3:云旗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28.56
5.1折
¥
56
全新
仅1件
作者雨楼清歌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ISBN9787545564884
出版时间2020-0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6元
货号11278148
上书时间2024-12-08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雨楼清歌,青年武侠作家。曾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武侠玄幻类大奖,第三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武侠组首奖,“戏剧时刻”豆瓣阅读短篇写作比赛最佳作品奖,首届掌阅文学创作大赛科幻中篇一等奖,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作品奖,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赛总冠军、幻想组首奖。已出版图书《天下刀宗》《一瓣河川》。
目录
章 浮舟问剑 章 临江梦龙 第三章 风清雨白
内容摘要
长篇武侠小说“天下刀宗”系列第三部。昔年中原武林决战北荒摩云教,刀客云荆山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于危难,从此被尊为“天下刀宗”。十三年过去,正气长锋阁号令高手共赴昆仑诛杀刀宗。在这一部中,杨仞武功精进,与秋剪水彼此暗生情愫,所领导的乘锋帮日益壮大,和正气长峰阁在洞庭湖对峙……
主编推荐
◇雨楼清歌作为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其作品既有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又深受武侠文学的浸染,同时还充满个人独特的灵性和领悟力,先后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武侠玄幻类大奖”、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赛总优选等多项文学奖项。◇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吸引力,用双线叙事的结构,以叶凉和雷璎珞、陈彻和宁简、杨仞和秋剪水等主人公进行叙事,展现了一场贯穿武林十余年的江户众门派与刀宗的恩怨情仇。◇小说中的剑法与各派武功,不仅是普通的技术,还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吸收了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非凡气象和大格局。
精彩内容
产品
◇雨楼清歌作为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其作品既有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又深受武侠文学的浸染,同时还充满个人的灵和领悟力,先后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武侠玄幻类大奖”、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等多项文学奖项。
◇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吸引力,用双线叙事的结构,以叶凉和雷璎珞、陈彻和宁简、杨仞和秋剪水等主人行叙事,展现了一场贯穿武林十余年的江户众门派与刀宗的恩怨情仇。
◇小说中的剑法与各派,不仅是普通的技术,还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吸收了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非凡气象和大格局。
内容简介
长篇武侠小说“天下刀宗”系列第三部。昔年中原武林决战北荒摩云教,刀客云荆山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于危难,从此被尊为“天下刀宗”。十三年过去,正气长锋阁号令高手共赴昆仑诛杀刀宗。在这一部中,杨仞,与秋剪水彼此暗生情愫,的乘锋帮日益壮大,和正气长锋阁在洞庭湖对峙……
作者简介
雨楼清歌,青年武侠作家。曾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武侠玄幻类大奖,第三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武侠组首奖,“戏剧时刻”豆瓣阅读短篇写作比赛佳作品奖,首届掌阅文学创作大赛科幻中篇,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作品奖,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幻想组首奖。已出版图书《天下刀宗》《一瓣河川》。
精彩书评
《天下刀宗》连续6期以diyiming强势上榜幻想组关注名单,加入书架的读者数超过了12000人,拥180万阅读量票高达5.7万张,并获四家观察团投票,是一部兼具人气和实力,为一代武侠写作新局的佳作。
——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赛语
雨楼清歌是一位令人惊异的青年武侠作家,他的小说风格清奇凌厉,充满古典的诗意。精妙的武学背后,是凌越众生、超尘脱俗的生命大格局。
——陈楸帆
雨楼清歌用清新俊逸的语言和诡谲多变的情节,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华美雅致的武侠诗歌。
——安迪斯晨风
目录
章 浮舟问剑
章 临江梦龙
第三章 风青雨白
精彩书摘
一
初春,巴山,夜雨寒峭。
秋剪水独坐堂中,怔怔出神。山深处偶有凄哀的猿啼传来,在雨声中若有若无。
清影堂本是烛照剑掌门凝心静修之所,可是今夜她却怎么也难以沉静心绪;先前她归返巴山不久便请副掌门穆清池率人到江湖上打探消息,这一两日便是约定的归期了。
去年在舂雪镇上,燕寄羽本已答应对烛照剑一派既往不咎,但到了肃州城外,她却终究又与燕寄羽交手,并用郁师姐留下的那支鸿翼笔将他迫退,后来又曾助杨仞逃脱了岳凌歌与温蔚的追捕,也不知如今燕寄羽究竟作何计较,心中颇为门派担忧。
窗明桌净,烛火微摇,秋剪水渐想渐觉烦乱,起身拿过行囊,从中取出一个叠好的,轻轻打开,将一粒小小的物事拈在手里,默然端详一阵,不知不觉中,微蹙的眉头已舒展开来。
过得良久,敲门声乍起,随即便听一个清脆的语声道:“掌门师姐,是我。”却是师妹李剪荷求见。
秋剪水微微吁了口气,心知李剪荷随着穆清池同去打探,她既回到巴山,想来穆清池亦已返回,当即道:“李师妹一路辛苦,快吧。”
话音方落,李剪荷已推门而入,一双灵动的眼珠四下转动,瞧见秋剪水正端坐窗前,便步履轻快地行礼,道:“我们刚刚回山,穆师叔说深夜不便打扰掌门师姐,便命我代他来向师姐禀告详情。”
秋剪水起身回礼,又听李剪荷道:“与我们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停云书院的书生,是来给咱们送华山武林大会的请帖的,穆师叔也已让那书生明日再来拜见掌门师姐。”
秋剪水心弦一松,道:“原来如此。不知会期是在几月?”心想燕寄羽既请烛照剑赴会,多半便是不会再为难自己的门派。
李剪荷道:“听说是在九月,燕山长请帖送得倒早。”说话中瞥见桌上有一颗糖渍的青梅,不禁好奇道:“秋师姐,你在吃蜜饯吗?我记得你从前可不怎么吃甜食呀?”
方才李剪荷来得猝然,秋剪水不及将那颗蜜饯收起,便放在了桌上,此刻闻言,道:“这是许久前吃剩下的,只有后一颗了。”
李剪荷诧异道:“许久前便只剩后一颗,那为何还不吃掉,难道舍不得吃吗?”
秋剪水脸颊微红,蹙眉道:“有什么舍不得的,你若想吃,便给你吃吧。”
李剪荷嘻嘻一笑,正要拈起那颗青梅,转念一想,又笑道:“想来这蜜饯是极好吃的,还是留给秋师姐吃吧。”
秋剪水看也不看桌上,径自问道:日江湖上可有什么大事吗?”
李剪荷道:“那天我们动身之前,秋师姐要我们着意留心乘锋帮的动向……”
秋剪水摇头道:“我是要你们留心江湖上任何大的动向……”
李剪荷道:“嗯日江湖上大的动向,便是乘锋帮了,帮主杨仞向正气长锋阁宣战,更扬言要将被囚在华山的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救出,武林各派对此将信将疑,有人说杨仞不过是虚张声势,乘锋帮其实只有寥寥几个帮众,但也有人说,乘锋帮暗中已聚结了许多高手,势力不可小觑……”
秋剪水沉吟道:“那么正气长锋阁又是作何看法?”
李剪荷道:“正气长锋阁说杨仞只是个不成气候的小而已,将他称为‘刃贼’。”
秋剪水蹙眉道:“‘刃贼’是什么意思?”
李剪荷道:“听闻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一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传出消息,说杨仞窃走了刀宗昔年所用的雪刃,拿着这把刀四处招摇撞骗;还说杨仞实是武林败类‘癞头蛇’佘灿的徒弟,佘灿偷了晴川刀,杨仞又偷了雪刃,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凡我侠义辈,绝容不得杨仞这偷刀贼’。”
秋剪水道:“正气长锋阁这是想让那些崇敬刀宗之人也都与杨仞为敌。”凝思片刻,便与李剪荷出了清影堂,各自回寝居歇息去了。
翌日清晨,春雨初歇,秋剪水漫步于山道,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徐徐,却是副掌门穆清池前来拜见。穆清池年约四十,身形颀长,神情举止颇显精干,拱手道:“回禀掌门,我已探得清楚,早前燕寄羽遣向我派的青锋令使,却是红罗山庄的庄主虞夙。”
秋剪水神色微变,道:“红罗山庄与咱们烛照剑同为武林七大剑派之一,听闻虞庄主的剑术修为是很神妙的。”
穆清池笑道:“虞夙情高傲,一向以贵胄自居,难得他竟愿听燕寄羽的调遣。我已将他过去数月的行踪查明,他接到燕寄羽的传令极早,本来已快赶到巴山,却又突兀折返,想是途中接到了新的传书,得知了燕寄羽已不欲和我派为敌。”顿了顿,又道:“不过燕寄羽心思深远,谁也猜不透他的打算,咱们仍须小心提防。”
秋剪水道:“穆师叔所言极是。”
穆清池道:“我还探知,现今秦川木余刀、冀州游刃坊、江州弹霜亭这三大刀派均已听奉正气长锋阁之命,暂由三位青锋令使接管了门派。”
秋剪水一惊,道:“这三派竟愿意如此?”
穆清池莞尔道:“自然是不愿的。副掌门裴烽、丁厌忧和代掌门谈寒雁都只是传书回去,号令各自的门派在名义上听命于燕寄羽遣去的青锋令使,但他们三人自己却并未返回门派,而是率前带往舂山的精锐弟子,在江湖上失踪了……”
“失踪了?三派精锐一齐失踪吗?”
“不错,料想是他们易容改扮,分散潜藏起来了。此举可谓是一着妙棋,也不知正气长锋阁将会如何应对。”
——两人说话中来到烛照剑一派的正殿明烛殿,随后,秋剪水便请停云书院的信使相见,来者却是“停云五贤”之中晏格的徒弟刘万山。
刘万山在舂雪镇外初见秋剪水,后来随郭正与青箫白马盟一众人短暂同行时,也曾与她打过照面,心里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掌门记忆颇深,今日再逢,眼见她清丽绰约更胜去年,不自禁地一怔,随即才身姿潇洒地踏前一揖,道:“秋掌门别来无恙?”
秋剪水从前未曾留意过刘万山,早已不记得他,听他此问,只淡淡地嗯了一声,道:“刘师兄此行劳累,实在多谢。”
刘万山微笑道:“不敢当。”说完从行囊里取出一个样式精致、加盖封泥的木匣。李剪前接过木匣,转身呈给秋剪水。
秋剪水道:“多谢。”打开木匣,拿起请帖略略扫了两眼,倏而轻咦一声,瞥见木匣中竟另有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夏姑娘亲启”几个字,笔迹潦,宛如孩童涂鸦。
秋剪水心跳莫名一促,隐约猜到了这封书信是来自何人。刘万山瞧不见木匣中的物事,眼看秋剪水神情异样,心头疑惑不解;李剪荷站在秋剪水身侧,却瞧得清楚,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刘万山讶声道:“秋掌门,莫非是燕山长手书的这张请帖有何不妥之处吗?”
秋剪水一怔,道:“自然不是,刘师兄何出此言?嗯……请刘师兄代我谢过燕山长,今秋九月,我们巴山剑派准时赴会。”心想:“这位姓刘的书生做事当真粗心,被人偷走木匣,往匣中加了一封书信,重又盖好封泥放回他的行囊,他竟全无察觉。”
她心中转念,仔细看了一遍请帖,眼角瞟见木匣中的那封信,忍不住微微一笑。
刘万山见秋剪水低头看请帖之际,却忽然面露温柔笑意,更加不明所以,但觉她明眸笑靥,颇为动人,也不禁心神微荡。
等到刘万山告退,李剪荷脱口道:“掌门师姐,匣子里怎么还有一封信,这可奇了,咱们快拆开来瞧瞧吧。”
秋剪水有些担心信中写了什么胡言妄语,一时犹豫不语。穆清池见状,道:“掌门有要事须得静思,剪荷,你们随我来。”言毕领着一众弟子出了明烛殿。
秋剪水拆信看过,斟酌良久,步出殿外,但见不远处穆清池正自斥责李剪荷言行太过莽撞,便了轻声道:“穆师叔,你别责怪李师妹了。”
穆清池转身施礼,苦笑道:“谨遵掌门之命。”
李剪荷在穆清池背后偷偷吐了吐舌头,随即也正色施礼,问道:“不知掌门师姐看信后有何示下?”语气中却着意加重了“看信”二字。
秋剪水瞪她一眼,道:“日里须得去一趟岳州,烦请穆师叔坐镇门派,处置各项事宜。”
穆清池一怔,道:“掌门怎么突然便要出远门?”
秋剪水想了想,答道:“方才那封书信,是我的一位……朋友所写,他邀我去岳州游湖赏春。”
“游湖赏春?”李剪荷不待穆清池接口,便抢先叫道,“那写信之人是谁?那人自己愿做这闲逸事也罢了,又怎敢轻易劳请掌门师姐的大驾?”
“倒也并非全为了闲事,”秋剪水微笑道,“那人以前和我打了一个赌,算来也快到他该兑现赌约的时日了。”
…………
一驾马车停在滁州城外的荒野,车夫侍立一旁,眼看雷缨络下了马车,犹豫片刻,问道:“要在这里等吗?此地距离临江集还颇有些路程。”
雷缨络道:“在这里等。”那车夫便不再多言。雷缨络眺望,但见稀疏的春之间尚有些残雪未化,忽而轻声道:“师尊她老人家爱看雪了。”
那车夫接口道:“戚前辈心质高洁,喜爱看雪也是理所应当。”
雷缨络闻言微怔,道:“心质高洁吗?江湖中倒是甚少有人这般说师尊。”抿嘴一笑,转口道:手下人可有再探到杨仞的行踪吗?”
那车夫摇头道:“的一次,仍是在半月前,杨仞曾于江州城外短暂现身。”
雷缨络沉吟道:“过去两个月里,杨仞先后与木余刀、游刃坊订下盟约,他到江州,定然也是去和谈寒雁结盟……嗯,离江州弹霜亭的门派便是岳州洞庭湖上的留影舫了,听闻留影舫始终不肯听奉正气长锋阁的号令,已经和燕寄羽派去的青锋令使对峙月余,杨仞此后多半便会赶去岳州,相助留影舫。”
那车夫略作思索,道:“不错。”又问道:“乘锋帮与三大刀派结盟,多半也瞒不过燕寄羽,难道他竟放任不管吗?”
雷缨络道:“如今乘锋帮有六百‘意劲’高手,便是燕寄羽也不得不忌惮,杨仞又扬言要在各派聚会华山之前将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救出,停云书院多半更要严守门户,不敢轻易离开华山。”
那车夫淡淡一笑,道:“看来这姓杨的小子也有些狡诈手段,倒也不仅仅是个跳梁小丑。”
雷缨络微笑道:“怎么,你瞧不起杨仞吗?”
车夫避而不答,只道:“红罗山庄庄主虞夙从荆州改道,怕是也快到岳州了,有他和徐开霁这两大青锋令使,料想便是杨仞去到洞庭湖,也救不得留影舫。”
雷缨络颔首道:“嗯,听说徐开霁虽出身于云梦山白鹤剑一派,但早年便已脱离门派,是个独来独往的江湖浪客;而虞夙不但己身修为高绝,出行时更往往多携车马仆从,手下高手甚众,确能是徐开霁的一大助力。”
“原来如此。”车夫神情微凛,道,“留影舫虽是九大刀派中人数少的,但也有百余名刀客,徐开霁能以一人之力和留影舫对峙月余,当真不简单。”
雷缨络沉思片刻,忽道:“今日咱们见过吴重之后,你便快马传书给我师尊,告知她老人家:杨仞将岳州。”
车夫一惊,心知过去数月里戚晚词一直在四处搜找杨仞,而雷缨络却曾在暗中数次相助杨仞,实不知她现下为何要将杨仞的行踪说与戚晚词;转念一想,又觉心下惕然:“以杨仞现下力,戚晚词若真去到岳州,恐怕谁生谁死还说不准。”
两人默然对视一眼,车夫点头答应。
过得一个时辰,仍不见有人来到,那车夫侧头瞧了雷缨络一眼,欲言又止。
雷缨络淡然道:“吴重会来的。他今日会交给我一幅画,这是他答应付给我的酬劳。”
“一幅画?不知是什么画?”车夫闻言微愕,问道,“雷姑娘,你自离舂山以来,替吴重做了这么多事,便只是为了一幅画吗?”
“嗯,”雷缨络轻声道,“那是萧野谣所画的叶凉的骨相。”
媒体评论
◇雨楼清歌作为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其作品既有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又深受武侠文学的浸染,同时还充满个人独特的灵性和领悟力,先后获首届梁羽生文学奖“武侠玄幻类大奖”、首届豆瓣阅读长篇拉力赛总冠军等多项文学奖项。◇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吸引力,用双线叙事的结构,以叶凉和雷璎珞、陈彻和宁简、杨仞和秋剪水等主人公进行叙事,展现了一场贯穿武林十余年的江户众门派与刀宗的恩怨情仇。◇小说中的剑法与各派武功,不仅是普通的技术,还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吸收了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超乎寻常的非凡气象和大格局。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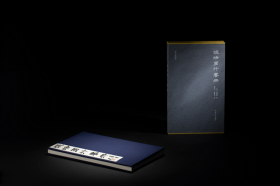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