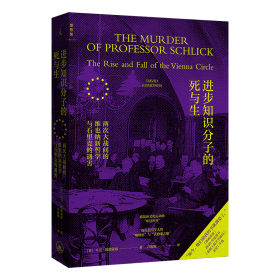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49 7.4折 ¥ 66 全新
库存4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英)大卫·埃德蒙兹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79000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6元
货号31619601
上书时间2024-11-12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5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维也纳黄金时代尾声的学人群像★思想史和外部史相结合,能提供怎样的镜鉴?
科学、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等众多领域,可能都有其所处时代的共通气质?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只遵循理性和证据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在很多时代都受到保守派的忌惮和打击?同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或者同情者,为什么彼此之间也会存在强烈、持久的争论,甚至断绝往来?谁早在1931年就迁居外国,谁又到了1939年还从海外返回奥地利?他们的性格、判断力和学术趣味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学界人士逃亡时,在资源和失落方面,有怎样的共性?历史的行程,对学者个人及学术风潮的走向又有怎样的影响?……★追求科学精神,造就了怎样的哲学和哲学家?
★一幅见微知著的欧洲画卷
作者简介
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 哲学博士,牛津上广(Uehiro)实践伦理学中心高级副研究员,哲学的公众传播者,播客Philosophy Bites的联合创办人。(合)著有《维特根斯坦的火钳》《卢梭与休谟》《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等。
目录
前 言 1
致 谢 5
1 序 章 11
2 小公鸡和大象 17
3 逐渐扩大的学圈 31
4 秃头法国国王 52
5 维特根斯坦施魔法啦 60
6 红色维也纳的纽拉特 85
7 咖啡与学圈 97
8 建筑与沙发 110
9 石里克不喜欢的礼物 129
10 外国的陌生人 144
11 漫长的仇恨 161
12 红色维也纳的黑暗岁月 180
13 哲学论争 199
14 非正式反对派 225
15 喂,你这该死的混蛋 234
16 学圈活在心中 247
17 出 逃 255
18 辛普森小姐的“孩子们” 270
19 战 时 282
20 流亡后的岁月 306
21 遗 产 335
出场人物表 351
年 表 358
注 释 366
部分参考文献 383
专名对照表 392
内容摘要
“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和希特勒——那么其中显然发生着重要之事……他们都渴望革除陈腐,以踏实、务实的新风取而代之。他们都不敬传统,但崇尚科学,拥抱进步,也都在推动统一化的议程……一切势利的旧时代等级制度都要一扫而空。”“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预见到了事件的走向。要离开奥地利,有着各种理由,包括事业的发展;但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想法依然看似荒谬,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受着积极看待事态发展的诱惑,就比如弗洛伊德。 1933年,当听说自己的书在柏林被付之一炬时,他说:‘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本人;如今,他们烧我的书就满意了。’”“人在流亡中,往往都做着回家的梦。但如果离别非常痛苦、屈辱,使还乡几乎不堪想象,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会不会考虑回维也纳?’‘不,决不会!’……离开奥地利后,学圈成员生活的一大惊人之处就是他们适应英语的速度……亨普尔告诉女儿,他做梦都是用英语做的……用英语交流代表着与过去的心理决裂,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本书从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一批科学、哲学界知识分子们形成的“维也纳学圈”切入,勾勒了前后约70年的相关“硬文化”兴衰嬗变,既涉及我们熟知的罗素、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包豪斯,更有纽拉特、卡尔纳普等枢纽性人物……他们一起点亮的旧大陆文化盛焰已在时代风雨中熄为余烬,四散的星火是否已然燎原?这幅宏大画卷不但覆盖欧美,包含科学与文艺的新气象,更有风云骤变,以及战后新哲学的硬核……性格决定命运,也与个人文化观暗暗相连。其中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也许就是温良的豪门学术明星石里克,唯一一个被无端刺杀的人。
主编推荐
★ 维也纳黄金时代尾声的学人群像
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一方面大众处在货币贬值、心绪不安的境地;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文艺、政见都走上了新高度,活跃在讨论室、沙龙、咖啡馆、博物馆等空间之中……追求成为世界公民的新型犹太人,更是其中的代表乃至枢纽型人物,他们憧憬着进步和平等,甚至吸引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其中的代表性群体,就是反对旧形而上学、倡导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维也纳学圈”。
笼统而言,维特根斯坦是这个学圈(以及凯恩斯)的神(罗素是施洗约翰);学圈领袖石里克,这位普朗克的高足、爱因斯坦激赏的后辈,是维氏的虔诚门徒。宽厚的石里克也是波普尔的博士答辩导师,但认为波普尔“为人粗鲁,哗众取宠,是个不容异说的恶霸”;尽管如此,石里克并不在意波普尔批评乃至挖苦自己——但挖苦维特根斯坦可不行!学圈骨干还有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后者对维特根斯坦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性格糟糕,表达独断,精神不稳定,但跑路嗅觉敏锐,为数很少的一生交好有拉姆齐和卢斯。同样和建筑界(包豪斯)有良好关系的,还有博物馆主、社会改造者、超聒噪大型“社牛”纽拉特。英国青年数学家拉姆齐曾亲至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的长时段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豪富家族,还是理查·施特劳斯、克里姆特等许多艺术家的恩主……众多人物,就这样织造在一起。
然而一朝风云变幻——不,风云一直在变,只是常人往往一朝方始惊醒……
★ 思想史和外部史相结合,能提供怎样的镜鉴?
科学、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等众多领域,可能都有其所处时代的共通气质?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只遵循理性和证据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在很多时代都受到保守派的忌惮和打击?同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或者同情者,为什么彼此之间也会存在强烈、持久的争论,甚至断绝往来?谁早在1931年就迁居外国,谁又到了1939年还从海外返回奥地利?他们的性格、判断力和学术趣味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学界人士逃亡时,在资源和失落方面,有怎样的共性?历史的行程,对学者个人及学术风潮的走向又有怎样的影响?……
★ 追求科学精神,造就了怎样的哲学和哲学家?
“逻辑经验主义”不似“存在主义”那么广有受众,但它的潜流余续,是今日学院哲学的础石。比如奠定二战后美国哲学研究基调的蒯因,就是维也纳学圈的学生甚至成员。学圈内部也有学术甚至处事争论,但追求清晰的论证和证据,亲近科学方法,不迷信传统,拒斥天启般的形而上学,憧憬社会公平,是他们共同的底色,纽拉特说:“我们的共同点将保留下来;我们的差异是时代的产物,会逐渐消失。”海德格尔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早在海德格尔刚刚出名时,卡尔纳普就激烈抨击其作品。波普尔则说:“只要读过海德格尔的原著,就会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骗子……用绝对空洞的陈述,拼凑出空洞的连篇废话……我呼吁各国的哲学家团结起来,决不再提海德格尔,也决不再和其他为海德格尔辩护的哲学家交谈。这人是魔鬼。我的意思是,他对他可敬的老师表现得像个魔鬼,对德国也有着魔鬼般的影响。”
★ 一幅见微知著的欧洲画卷
主楼大学,学院联盟,教席、编外教授、授课资质和Habilitation,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及市民业余学校;高桌晚宴,有轨电车,巴洛克式宫殿对峙直线条大厦,历史上多次改易国籍乃至名称的小城,更有众多的小街、咖啡馆、故居、学界协会、民间团体、国际交流甚至上课时间后的c.t.……在这里,你能了解到旅游攻略之外的,既是近百年前的、也是当下的欧洲。
精彩内容
7咖啡与学圈就像石里克之于维也纳学圈那样,门格尔也是数学讨论会的领导者。虽然各个学圈往往是松散的聚会,但通常只有学圈召集人才会发出邀请。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学和学圈之外,另一类无需邀请、无需门票、无需资格的维也纳“机构”,对这个城市的繁荣如此关键。
***这类“机构”就是咖啡馆。在这里,人们可以读报、追八卦,可以独处但不会寂寞,可以和朋友坐坐,下棋、打扑克、玩多米诺骨牌,可以做生意,可以卷入激烈的政治争论,可以仔细琢磨曲线理论。维也纳的公寓供不应求,而且一般都狭小、阴暗又寒冷;咖啡馆提供了一个比家里更吸引人的选择。当然,它们各不相同,不是所有咖啡馆都有大理石桌子,都有深色的皮椅和沉重的吊灯。它们供应自己的独门糕点。然而,所有的咖啡馆都按类似的路线经营,受一套类似的非正式规则控制。随咖啡本身,还有一杯水奉上。报纸堆放在竹架上,有时可选范围惊人,连外国报纸都有。 1933年,一位来维也纳的游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在晚报上读到一篇犹太学者在纳粹德国被解雇的报道。这篇报道将促使他成立一个救生组织(后文再加介绍)。咖啡馆白天和晚上都开放,忙人和闲人都惠顾。只要愿意,你尽可只慢慢呷一杯咖啡,而不会招致服务员的愤怒。想要放纵一下?那可以听听服务员报上菜单,用一块苹果卷或萨赫蛋糕来犒劳自己。
在当时的一本维也纳小说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厌倦了在咖啡馆里混日子,后者说完全不会:在咖啡馆里坐着,是对强制性活动的对抗,正是这些活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痛苦……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在错过一些无可挽回的东西……仿佛有一堆活计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在我们这个拜物时代,这个体力劳动和先进科技的时代,可是有害影响……但进入咖啡馆的那一刻,你就放假了——枷锁从你的肩上解除,断成两半。
一位高傲的英国游客把维也纳的懒散归咎于咖啡馆:“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比维也纳更适合愉快地坐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毫无疑问,这就是到头来,这里的居民做得如此之少的原因。”但奥地利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却把维也纳咖啡馆尊为“一种只花一杯咖啡钱就能买到入场券的民主俱乐部”。
这里面略有不实之处。工人阶级往往光顾自己常去的酒馆,而非咖啡馆,尽管咖啡馆之间也有贵贱之分。咖啡馆往往是中产阶级光顾,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空间,但收银员(Sitzkassiererin)是个例外,她通常是一位女性。 19世纪维也纳的一本旅游指南这样描述女收银员:稳坐在吧台之后,在酒樽杯盏之间,是更美的那个性别的使者——收银员。她总是和蔼可亲地代表着她的性别。”维也纳大可夸耀它的咖啡馆不止千家。关于它们有很多记载:对于这座城市,它们不仅象征着城市生活的活力和创造性,还是城市的连通管道。就我们的故事而言,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对维也纳学圈所起的特殊作用。维也纳大学的研讨班、讲座课以及学术薪酬为城市的学术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石;然而由于制度的繁冗和氛围的窒闷,由于其中的反犹主义和保守主义,zui令人振奋的讨论经常发生在大学的墙外。
不同的咖啡馆因特定的领域和职业而闻名:魏格胡伯咖啡馆(Weghuber)在男女演员中很受欢迎;兰特曼咖啡馆是弗洛伊德和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碰面的地方;格林施泰德咖啡馆(Griensteidl)直到20世纪初关闭之前,都有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等作家常来光顾——第yi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转投罗伯特·穆齐尔和约瑟夫·罗特喜欢的贵族庄园咖啡馆(Herrenhof),尽管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更喜欢博物馆咖啡馆(Museum)。1907—1912年间,维也纳学圈的先驱(哈恩、弗兰克、纽拉特,以及不经常参加的冯·米塞斯)相聚之际,有着美丽穹顶和拱门的中央咖啡馆(Central)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地点,尽管他们可能太过沉迷于相对论带来的哲学问题,而没太注意这里的常客:其中有论战家卡尔·克劳斯、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以及流亡的俄国人列夫·布朗斯坦,他在那里下棋消磨时间,回国以后他变得更为出名,那时候他化名为托洛茨基。
后来,在维也纳学圈正式成立后,咖啡馆仍是其成员在周四的工作之余继续晚间讨论,或是学圈有外国友人在城里时他们聚会的地方。帝国议会咖啡馆(Reichsrat)、 苏格兰门咖啡馆(Schottentor)、 拱廊咖啡馆(Arkaden,在帝国议会街上)和约瑟夫咖啡馆(Josephinum)都很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玻尔兹曼巷的约瑟夫咖啡馆。作家们的偷闲所在——贵族庄园咖啡馆——也是纽拉特的zui爱,他开玩笑说,咖啡馆的气氛值得观察和分析,就像“某地土著人的生活”值得人类学家观察分析一样。
在贵族庄园咖啡馆,每周都能看到纽拉特好几次,结果它也开始吸引学圈的其他人。它有一种现代感,照明好过中央咖啡馆。学圈的一位国外访客,挪威哲学家阿尔内·内斯回忆说,咖啡馆里的谈话比在玻尔兹曼巷的学圈会议上更加活跃。“我要在快速的讨论中插嘴并不容易。有时我会突然出乎意料地用德语说,‘恰恰相反’。然后会有一秒钟惊讶的沉默,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继续了。”诗人彼得·阿尔滕贝格表示自己的地址是“维也纳第yi区的中央咖啡馆”,而咖啡馆也有“常客桌”(derStammtisch)的传统,按照惯例,这一桌在某一天的同一时间会为同一批人保留。这些团体可能是封闭的,有点小圈子调调。但更一般的氛围是友好的:在这里,个人在社交上一般不会被孤立。“交融”对咖啡馆中的知识孕育至关重要。在这里,数学家可以与记者交换故事,商人可以和历史学家交谈。在“中欧”(Mitteleuropa)的许多地方,咖啡馆都是社会的黏合剂,能将不同的个人和团体联结起来——而维也纳无疑是个中之zui。咖啡馆提供了一种环境,在咖啡的热气和香烟的烟雾中,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交换理论。
这种开放性对维也纳的犹太人特别有吸引力。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咖啡馆是“犹太会堂(synagogue)的世俗版:犹太男子可以在去过犹太学堂(Shul)之后在那里碰面,而后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只去咖啡馆”。 16一份关于维也纳及其他州咖啡馆的全面研究报告指出,在维也纳咖啡馆里,“主要是新犹太人或说第二代犹太人”。 咖啡馆里面的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界公民乌托邦的形象,其中种族或宗教背景不是参与社团、获得工作的障碍。在咖啡馆的围墙内,外界的等级不复存在。学生和图书馆员可以与领薪水的教授平等地辩论数学、逻辑、语言和哲学。
谁又能反对咖啡馆呢?还有什么比这更无害的呢?但实际上,“纤弱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抽象的争论中消磨时间”的这一形象,同时引起了反犹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满。 1898年,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诺尔道,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畅想了一幅肌肉发达的犹太人在圣地的田间劳作的未来景象,以取代流散的“咖啡馆犹太人”。同时,对保守派来说,咖啡馆里飘荡的抽象思想可远非无害。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20世纪前三十年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世界观颠覆现有秩序的时期。逻辑经验主义即与这场后被称为“现代主义”的运动有关。而右翼,即社会及政治的保守主义者,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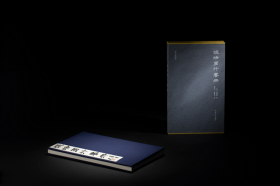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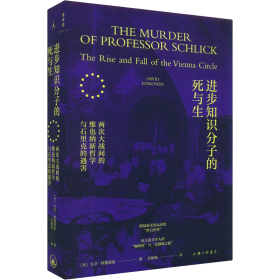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