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和它的自行车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40.37 5.9折 ¥ 69 全新
库存10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陈丹燕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3883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9元
货号31628425
上书时间2024-11-1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5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陈丹燕,1958年出生,以非虚构纪实类作品和其漫游世界的旅行文学广受关注。主要作品有“陈丹燕的上海”系列7本(《陈丹燕的上海》《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永不拓宽的街道》《慢船去中国》《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白雪公主的简历》以及12本陈丹燕旅行文学丛书。
目录
第1章 标本
他离一个浪漫故事实在相差太远了。
那时我并没有学会遗憾,这是大人才有的感情。我只是愤怒,怒火中烧。
第2章 果珍
我感到自己像一朵白花,在绿色的癌病室的背景前,极慢,但不能阻挡地伸展自己硕大欣长的骨朵,又娇嫩、又茁壮。
第3章 车铃
他什么都装作不知道,照样天天晚上按时回家,在桌子旁边看书,查词典,或者发呆,像一只热水瓶,或者一只冰箱,我觉得里面有东西,可在外面一点也看不出里面藏着什么。
内容摘要
17岁的王朵莱是个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的女孩,懵懂天真,不甘平凡,一心想有白马王子把自己从俗杂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她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望,使尽全力与庸常的命运抗争,最后却伤痕累累。
一个总也不肯平凡的女子,在平凡的生活中,怎么也不肯平庸的故事。
主编推荐
一个女孩像气球一样每当吹大,就会破灭的爱情
一个女孩像雀斑一样会因防护而变浅,但永不会消退的痛苦
一个女孩在平凡生活中,怎么也不肯平庸的故事
一部细小而漫长的,女性心灵成长的史诗
精彩内容
摄影师丁晓文的话:“她是真人吗?”“她为什么会在微博上叫自己王朵莱呢?”“她真的肯见你啊?”201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陈丹燕和我讲,要和她的一位读者见面。我就问了一堆问题。很好奇这位叫自己“王朵莱”的人。
因为要给她们见面拍点照片,我找出这本小说,又翻看了一遍。
上海图书馆的小砖楼四楼楼梯拐角处,就是1990年代的阅览室。2016年,它是个多功能厅,里面放着成排的台式电脑,应该是职称考试用的计算机教室。
教室里成排的老式铁窗,窗外树影和藤蔓过滤了洒进教室的光线,它们是青黄色的,陈丹燕写到过的。空间没有改变,光影、气味、颜色,窗框浮着细细的灰尘,是1990年代的氛围。
王朵莱进来了。
她真的是我想象中的、被陈丹燕写出来的样子,人瘦高,单薄,不太吭声的模样。
见到了陈丹燕的王朵莱,却不停地在讲话,滔滔不绝,都没有喘息的时候。有时候,她会碰一下陈丹燕,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她们说话的声音时近时远,断断续续。
镜头中,王朵莱一直在阴影里。
在故事写下来的空间里,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见面,被相机记录了下来。
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会在时间的流淌中瞬间更迭。
我在想,会不会2016年的陈丹燕随便一伸手,就触碰到了1993年坐在这里写小说的自己呢?
陈丹燕和王朵莱见面六年后的今天,2022年8月,《鱼和它的自行车》再版。没想到当年只是好奇跟去拍的照片,现在倒还真的成为这部小说的后续。 丁小文2022年8月评论家李伟长的话:最好的相遇,莫过于此你无想象你写下的文字,会在另一个时空里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这种影响可以被描述为安慰,安顿,抑或拯救,乃至重塑了他人的生活。这是写作的迷人之处,也是写作者的幸运。
当我听陈丹燕老师讲述这个故事时,小说家的眼里闪烁着光。这是一个理想的阅读接受美学的范例。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从一部小说里获得情感的滋养和生命的启迪,多年以后,与作者相遇并向她讲述这一切。于写作者而言,这就像某种历经漫长的时间之河突然而至身边的漂流瓶,打开后发现里面的寄语竟与自己相关,不啻于一种意外的惊喜,以及必然的温柔的感动。
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的际遇。一个写作者多少设想过她的读者会是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境况下阅读她的书,但她永远也无法想象出这影响的确切程度,除非某一天有个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确定地告诉你,在你的小说里我找到了自己,我就是你小说里写的那个姑娘,你的小说塑造了我的生活。
而今,这个人出现在了陈丹燕的面前,并且温柔地告诉她,她的文字拯救了她。我之所以用了两个“她”字,因为在这一刻,一个作者和她的读者如此接近又如此平等。
这是虚构与真实最近的一次相遇。多少写作者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试图用虚构建立真正的生活。一旦小说中人来到面前,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面对她所表达的一切?陈丹燕牵起了这个女孩子的手,与她温柔地拥抱。这个人是王朵莱,是吴小初,也是发现生活是一个圈、走着走着又转回来的陈丹燕自己。
这是一次与生活的远程和解吗?如此近,似乎又如此远。这是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的心灵交互,和对生活的爱得以再次确立的一次跃迁吗?我所能理解的最好的相遇莫过于此,彼此得以安放。
故事被写好后,就像已经被养大的孩子,终于要飞离养育他的人,去别处生活。如果足够幸运,他会去许多地方漫游,经过很多人的手,与有缘的人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用小王子的话说,就是得以驯养,别处亦是此处,那便是爱的达成。也有不幸的事,有的故事就像孤儿,一直在孤独地流浪,直至消亡。吴小初的出现,以及她与这本书的故事,是对写作多年的陈丹燕一次友好而又充满爱意的馈赠。
一本书得以重版,得以将它的接受史以具象的方式重新绽放,这本书里的故事,以及被王朵莱和吴小初叠合的生命轨迹所扬起的爱的精神都将获得二次生命。当然,相遇之后,分别总会如期而至。
当吴小初和陈丹燕拥抱着、笑着分别,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她们未来,会怎样谈论这一次遇见?
精彩试读:那是八十年代初夏的一个黄昏。我十七岁,考上了医学院附属的护士学校。在工厂的职业学校和医院的护士学校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护士学校,那是因为,我以为护士与人打交道,与死亡打交道,更加容易遇见奇迹。我的爸爸妈妈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因为他们认为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在生活上会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在生命的每一处哪怕最最微小的转折处,我都在心里热烈地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只是生活总是宁静无声地流转着,在每一处最细微的转折以后,总是什么变化也没有。我进护士学校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与中学不同的,只是现在班上都是女生,上课时放起屁来肆无忌惮,发出很响的声音来。
我像从前一样默不做声地接受了这种失望。
在吃完晚饭以后,我就到校园里去散步。暮色灰黄而凉爽,本来就宁静的黄昏,此刻犹如静止了一般。
那天,我在教师办公楼和教室之间的林荫道上慢慢地走,门房后挂着大钟,钟绳被晚风吹动,使钟发出轻响。在那时,我又一次感觉到日子的宁静与漫长,它像一条不能快也不会慢的水流,无声无息地向前淌去。对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得太久太久。
这时,我看到教师办公楼底层解剖实验室的红门仿佛微微张开。平时那里是锁着的,而且同学们都不愿意到那里去,楼外有棵特别高大的树,向红门投下了重重阴影。
将近半年以来的解剖课上,我已经许多次看到过从那里拿出来的被肢解的人体,它们使我越来越感到亲切。
脊背上一阵一阵微微紧着,我走过去。我知道我背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喜欢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解剖实验室是底楼最大的一间教室,这时教室里已经十分昏暗,轻轻将门推开,一股福尔马林气味起伏而来,十分刺鼻。屋角的几只老式的大浴缸盖着木盖,那里浸泡着我们上课用的标本。被福尔马林浸过的尸体,全变成了棕红色的,干瘪而潮湿。
有个微驼的男人站在陈列局部人体的玻璃柜前面。他头顶微微秃了,所以脸显得长,古怪,而且十分苍白。他怔怔地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玻璃柜里的一个鼻咽标本。走近他,看清那是英文老师。在充满了福尔马林的暮色里,他像一件粗心人晒在竹竿上,夜里忘了收回家的衣服。
鼻咽标本其实是一个人的半边头颅。它向我们展示鼻咽的构造和鼻、耳、咽以及胸部那块无法形容指点的中心区域的关系。
我是在不久前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看到它的。那时我路过黑板报,打算去教室上课,被解剖老师叫住,让我去帮她搬个标本到教室。她喜欢我,因为我一点也不怕标本,不像班上的林小育那样逃走,也不像芬那样惊叫。
标本放在一个有锈迹的铁盘里,上面盖了块浸满福尔马林的纱布。我走到半路上,突然吹来一阵风,风把纱布掀开,我正好看到被整齐切开的半个头颅,上嘴唇上,甚至留着几毫米长的花白胡子……回想起来,仿佛在梦里。我心里惊雷滚滚,但却一声不吭,软绵绵地继续走着,没惊呼,也没把托盘扔掉。所以,我很熟悉英文老师背上的神态,他的背部像我那时一样的震惊而又茫然,如同一个梦游者。我们都被这半张脸上的胡子吓住了,或者说魔住了。
英文老师感觉到了我,他的脸转向我时,还留着做梦一样的神情。
这时看着英文老师,我突然感到他陌生起来。回想起来,本来我并没注意到他,只是听说他是大学中文系出身,毕业分配到外地去了,后来好容易调回上海来。他爱人到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当遗传学的研究员,他只能到我们学校,还是研究所出面来说情,照顾的。我们没有语文课,他便教我们英文。他在黑板上写着不好看的拉丁文和英文的药名,用手在玻璃黑板上窘迫地点着它们,艰难地读给我们听。他出汗的手会在黑板上留下一团团手掌的汗气,他的样子使人感到他就是个倒霉蛋。他眼眶的四周,有中年男子奇怪的浮肿,总像昨晚没枕在枕头上睡觉那样。而在福尔马林的暮色里,他的脸却变成了一张有着成熟故事又有青春余温的脸。我想,他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的人。
他很窘地朝我笑,说:“奇怪。”他一点也没有成年人的架子,很诚恳。
我禁不住说:“没有关系,是这样的。”他说:“我一直觉得奇怪,实际上也是很奇怪,看到没关门,就进来了,里面很——”他顿住。
我朝他笑了一下。是啊,那种心里的感受是说不出来的。
他还在琢磨怎样把无法表达的表达出来,他说:“每次我经过这里,就想进来看看,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太不安静。”我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想到他是老师,我是学生,这样说不好,就没说。
我们又看那个标本。它浮沉在福尔马林里,它的嘴唇像熟睡一样地张开,死命盯住它看的时候,仿佛还有微微的呼吸。
我一直努力保持着脸上的笑容,慢慢地,笑退去,嘴唇粘在干燥的牙上。我拿不准现在该怎么办。四周是这样的安静而且充满了含义,如果不说点什么,好像会显得很蠢,想到这些,我就紧张起来,我说:“这也是一个人噢。”这是句好蠢的话,刚说了几个字,我就后悔了。但英文老师那边,却传来了赞同的声音,他说:“是啊,不知道有多少故事,才使一个人变成这些东西。”而这,就是至今我认识到的很少的生活中的真理之一。成熟的男人会把你模糊不清但感觉强烈的想法变成一句话,这也是当时英文老师猛然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英文老师猛然就吸引了我,我像发现了新大陆。我望了他一眼,望到了他脸上苍苍茫茫的样子,像是有许多故事似的,又像有许多伤心事似的。我心里咕咚响了一声,然后,浑身的鸡皮疙瘩又起来了。我说:“每次我见到这些标本,就希望马上发生什么事情。”英文老师说:“我也是这样的感觉。生活太平淡了。”这时我们四周的地上,突然跳动出无数细细的树叶的黑影子,大概是大树外面的路灯亮了。门房老头当当敲着钟,不知为什么,我们学校到很晚还留着这样声音缓慢而洪亮的老钟,而不用电铃。在钟声回荡的几分钟里,使我暗暗惊奇,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夜自修开始了。
隔着林荫道的教室里,传来女孩子的喧哗,远远听上去,是那样明媚流利。这声音和光亮反衬出了解剖实验室的秘而不宣的黑暗。
那天的夜自修,正好是英文,我进教室坐了一会儿,英文老师便出现在讲台上。那天下午正好学校组织我们去教学医院看医大学生的尸体解剖。直到晚上,大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各自在那时受到的刺激和惊吓,见到老师进来,说话声也没有轻下来的意思。大家都不害怕英文老师。在护士学校里,女生对中年男老师,总有种撒娇似的轻慢,特别是对真诚的,却不怎么出色的男老师,像英文老师。他们懂得爱护和欣赏女孩,但却又没有出色男子的傲气和神气,使人不敢生非分之想。
其实,一切端始就在这里。如果那时我们中有一个人客气地笑一笑,或者有一个人做出拒绝的姿态,一切都会像开了瓶的啤酒,不一会儿气就跑掉了。而我们却在日光灯很明亮的教室里没有表情地对视,这就是开始。
也许,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地弥漫开来,我想起语文课上学过的一个词:油然而生。这就是油然而生的一种东西。
从那天傍晚后,英文老师就像是在我眼前突然打开的一盏灯。
在我的少女时代,在漫长的临睡之前的清醒时刻,我总是合上眼,躺在枕头上,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我曾经想象过多少次将要和我手拉着手向前走的那个男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两个人手拉着手,在有梧桐树的马路上走路。
那时和我手拉手的人,是一个佩剑的白发苍苍的将军,而且是外国人。这样的奇迹当然没有出现。那时我是一个由于不平衡和害羞而非常严肃的女孩,甚至没有机会在校园里与一个男孩有哪怕是很蒙眬的感情。我非常洁白也非常寂寞地从中学毕了业。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我认真看不起那些骄傲但又惶惑不安的同龄的男孩子,我仿佛生来就期待着有阅历的男人,以及有军队背景的男人。这是我对男人的一种至高的礼赞,男人就应该是勇猛的、威武的而且是历经沧桑的,所谓侠骨柔肠吧。
在睡前的种种含混不清的幻想故事中,这样的理想一次次闪烁着,好像幻想一样含混不清,而且又光辉四射。但是这一个晚上,突然英文老师的脸出现了,他在那儿,像一盆风干的花一样,等着我,让我起鸡皮疙瘩。
几天以后,我从班主任的办公室出来,沿着磨石走廊走过去,经过一扇扇办公室门,最终就能看见英文老师坐在他的小办公室靠窗的桌旁。他常常双手合十,撑在下巴上,在大大的老式教师写字桌上沉思。那是种奇怪的姿势,看上去坐得很不舒服,仿佛已深深将自己投向什么地方,而将四周与躯体置之度外。他的手掌长而松弛,毛孔很大,看上去是双厚道可是也敏感的男人的手。他嘴角深深往下巴两边滑下去,脸色十分的困倦。
一路在磨石地上滑溜溜地走过,锃亮的地使我想到唠叨而烦恼的家庭主妇。有时锃亮的地令人压抑,尤其对中年男子和年轻不安宁的女孩,因为他想到的是陈旧而厉害的太太,她想到的是精明而毫无诗意的母亲,这是他们共同想逃避的。我怀着比解剖实验室里更进一步的,同盟般亲切的心情走过英文老师的门,我猜想他一定有许多默默不言的哀伤。因为他们默默忍受的态度,男人的哀伤比女人的,更值得也更容易让人同情。那时候我几乎断定英文老师的太太也是个厉害而唠叨的角色,把英文老师逼得走投无路,只等我的爱情去救他。我就是那么肯定,而且那么激动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每天清晨早锻炼时,我都得昏昏欲睡地随着哨声在操场上跑步。从开始寄宿,我最痛恨的就是早锻炼。那天英文老师也下楼来。他穿着与他并不相配的运动衣,反而显得落伍而且滑稽。他跟在我们队伍后面跑着。我们的体育老师在队伍前帅气而又懒洋洋地吹着哨子,他是护士学校最年轻的男教师,高个子,宽肩膀,眼睛似笑非笑,是全体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当他从头排跑到操场当中,让我们围着他沿着跑道绕圈时,所有的人全竭力使自己更轻盈,像书里形容的那样:像头小鹿。
而我昂然从童话里那骄傲的公鸡面前跑过,心里想象着英文老师默默地在队伍末尾注视我的情景。我才不讨好什么人,我要别人来讨好我,而且了解我的重要性。我在拐弯时回过头去,的确找到英文老师的目光,那是迷惑而温柔的眼神。然而我假装天真地转回头去。
跑步以后,就自由活动。许多人围着体育老师打排球,她们疯疯癫癫,欣喜若狂又彼此争风吃醋,我想她们背上的鸡皮疙瘩也一定是竖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而我则去远远的跑道尽头的角落,去木头秋千上荡秋千。我想象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穿着红的运动服,在大丛大丛很绿的夹竹桃树前荡秋千,铁索咿呀咿呀地响着。连我自己都陶醉了。
果然,我又收获到了那个迷惑而温柔的眼神。操场上乱成一团,所有女班主任和舍监老师都紧紧盯住她们。这时,英文老师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他略有点结巴地说:“你真像我爱人年轻时的样子,她那时也喜欢穿红衣服,也喜欢荡秋千。”当我眼睛忽然一暗的时候,他又说:“现在变了很多。年轻多么好!”他扬起他那被岁月腐蚀的英俊的脸,他头发微微鬈曲着。
我在秋千上对他点着头,我感到清晨清新如冰的风从脸上划过,拂起伏在肩上的头发,头发扬得像鸟的翅膀。那时我的心的确充满了对英文老师的同情和怜惜,我想我能够像救出怪兽的美人那样救他,使他重新变成英俊的骑白马的王子。我希望他不爱他的妻子而来爱我,离开了我,他就还得不幸下去。
我在秋千上越荡越高,因为有老师在看我,我望见了围墙外面灰色的街道,街面房子前卖大饼油条的小摊子,还有拿了一根筷子在等油条出锅的女人。我把那个睡眼惺忪的女人想成老师的太太,我把老师想成正在看着买油条的女人和荡秋千的我,所以我越荡越高,一直到自己都怕了,整个操场上的人都停下来看我,老师远远地叫:“慢点!慢点!”我像鸟在飞。
天天都是一样,天没亮钟声就响了,舍监老师在走廊里大声催促我们起床。盥洗室的长排水池前总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同学,隔壁的厕所,钉着弹簧的矮拉门再三被推拉,呼呼地急响。不知为什么,寄宿女生常喜欢只穿短裤和短内衣出来洗漱。初夏仍旧气温很低的清晨里,到处都能看见同学们裸露的身体,还没完全醒来,散发着熟睡暖气的胳膊和大腿,是微紫的玫瑰色。
窗外被极密的水杉林遮掩住了。对面教师宿舍的灯光被阻隔得遥远迷蒙。但我还是能想象英文老师站在他的窗前,遥遥看着我们这边的情景。借着他成年男子对以往一切疲倦的忧郁眼光,我意识到青春肌体的非凡美好,并朦朦胧胧地希望在它还没老的时候,将它显示在一双能欣赏和需要它们的眼睛面前。和许多这个尴尬年龄的女孩一样,我也很希望被爱自己的人偷看,像湖畔半夜洗澡的仙女和牧童的故事。
那时我渐渐沉迷,仿佛生活马上就要打开奇妙的大门,仿佛从小至今我所过的平静日子,我认为是被莫名其妙关在生活大门外的日子就要戛然而止。每晚我都希望做书上写的那些热恋人们做过的美梦,但我的梦总是一如既往的淡灰紫色,而且和日常生活一样松散、拖拉,没有意义。甚至还不如它,因为我始终没梦到过英文老师。
周六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英文。
周六是寄宿生最兴奋的时候,好像要从笼里放出的鸟,屏住呼吸在听笼门抽开的唰唰声一样忍受最后一节课。只是我这种好心情常常在走进家所在的那条熟悉的弄堂时,转化成失望和愤怒。
英文课时不时有人把书包弄得哗哗响,那是将吃光了菜的玻璃瓶带回家。课桌下面靠着大塑料袋,里面装着换下来的脏内衣。
英文老师仍旧把手紧贴在绿色玻璃黑板上,在上面留下汗湿的手印。远远地看去,他的手骨节突出,很符合想象中真正的男人的手。
直到下课,我和英文老师像裹在河流里的两片树叶,与蜂拥回家的人一同走到太阳下面。我看到英文老师也提着一个鼓鼓的旧塑料袋,塑料袋里也露出一个大口瓶的轮廓。这使我猛然感到恼恨:英文老师也奔向他的家,也从他太太的炒菜锅里盛出菜带到学校里来吃。一个热的炒菜锅,就代表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不应该这样,应该像我想象的那样,他这样是不对的。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与一个挤着了我的满脸疲惫的中年男人恶吵,我没吵赢,因为那人骂出了非常恶心的话,他结实的脸上又下流又自私,穿了一件缝了许多口袋的帆布马夹,看上去像个拍照片的人,那种一看就是生活得不顺心的人。我这种年龄的女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最后,我闭上嘴,听着他唠叨,到我下车前,我回了一句嘴:“垃圾。”我说,然后赶快逃下车去。这才算是扯平了,但我的心情变得更为恶劣。
回家看到厨房绿茵茵的节能灯下爸爸妈妈的脸,一成不变的就像旧了的赛璐珞娃娃。爸爸妈妈因为我回家,特地杀了一只童子鸡,他们忙了两个小时,收拾那只小鸡身上和翅膀上的毛,把它用护士剪刀剪碎了,放在汽锅里蒸。爸爸把鸡毛铺在厨房的窗台上晒干,那是为了卖给收鸡毛的人。我看他们在昏暗的灯下忙,真为他们感到绝望。我们家的厨房在底楼,我们一栋楼里四家人合用一个厨房,每家人都很热心烧饭烧菜吃,所以厨房的墙上,挂着厚厚一层黑黄色的油污,是多少年以来炝油锅的油气熏出来的,灯座上也附着油乎乎的灰尘。爸爸妈妈在我的记忆里,总是在厨房里忙着烧东西吃。厨房的窗台上也总是晒着准备卖钱的东西:鸡毛、橘子皮、甲鱼壳和乌贼鱼的白骨头,有时是我家的,有时是邻居家的。每次还没有进家门,在弄堂里看到我家厨房间窗台上的东西,我就已经生气了,刚才在最后一节课要回家了的高兴劲,一点也没了。
妈在门口迎住我,眉开眼笑地说:“妹妹回来了。”妈妈穿着她厂里的蓝工作服,她到厨房干事情,总是穿着那件衣服,怕油烟气沾在她的衣服上,头上戴着纺织工人戴的帽子,也是怕油气的意思。
我“哼”了一声,把塑料袋里的脏衣服和装小菜的瓶子塞到妈妈伸出来的手里,急忙忙地穿过后门的厨房间。楼上的王家姆妈也在她家的煤气灶前面忙着,她和妈妈一样的打扮,别提有多难看,手上还戴着医院手术间弄出来的橡皮手套,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手。这是一间要多腐朽,就有多腐朽的厨房间。妈妈在我身后对王家姆妈说:“妹妹人大了,不高兴多说话了,连人也不叫。真正没有规矩。”王家姆妈说:“小姑娘都是这样的,过了这一向,就好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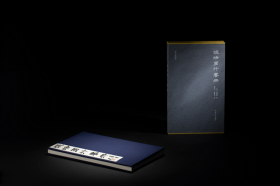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