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区柯克传(精)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55.5 7.5折 ¥ 74 全新
库存2件
山西太原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559648419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4元
货号31049892
上书时间2024-11-10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Ⅰ 从来不哭的孩子
Ⅱ 我来做
Ⅲ 来吧,声音
Ⅳ 我是灰色的
Ⅴ 在家里
Ⅵ 去假装吧
Ⅶ 哦,我的天
Ⅷ 我被定性了
Ⅸ 晚上好
Ⅹ 鸟与兽
Ⅺ 回归初心
参考书目
作品年表
出版后记
内容摘要
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希区柯克的故事,其中大部分都很残忍,他的真实面貌却始终是个谜。
在本书中,希区柯克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日常的恐惧令他迷恋秩序。他把生活安排得如同军事行动;衣橱里的衣服剪裁必须一模一样,成对匹配;每天下午茶都会摔碎一个茶杯,以此提醒自己生命是多么脆弱;必须事先精确设计每一
个镜头,不给任何人留下横加干涉的机会。电影不仅是他的事业,也是他唯一的避难所。
当然,人来人往的片场本身也足够令人生畏,因此,他始终要求现场要保持安静、整洁、高度可控,仿佛这样方能无坚不摧。最终,他将恐惧和颤抖从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带到了银幕上,以反抗社会留给他的伤痕。
精彩内容
I 从来不哭的孩子1899年8月13日,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出生在他父亲开的店铺楼上,这家小店位于莱顿斯通大道517号。在他出生时,莱顿斯通还是个总被人遗忘的城郊小镇,夏季闷热难耐,冬季寒冷肃杀。当时,这个地方仅仅是通往伦敦的罗马路上的一个小村落,有着标志性的空旷感。它位于伦敦城外东北方向八千米处,希区柯克出生时,这里名义上还是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但伦敦的巨大轰鸣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大东部铁路在1856年时通到了莱顿斯通,这个小镇很快就变成了“睡城”,住满了每天早上通勤去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普通中产。父亲威廉·希区柯克(William Hitchcock)是个小菜贩,卖一卖卷心菜和萝卜这类东西。这条路和其他的公路一样繁忙,街道上混杂着香蕉熟烂的气味、土豆发霉的土灰味,还有马粪更刺鼻的恶臭。1906年,莱顿斯通通上了电车,这种气味才开始慢慢消失,希区柯克对此记忆犹新。一张看上去拍摄于当时新近设立的“帝国纪念日”(Empire Day)的照片,记录下了希区柯克和他父亲在家族生意的门店外的场景。他骑在一匹马上,无疑是他家那匹从科芬园(Covent Garden)市场驮货回来的马。威廉·希区柯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生意很快扩张了,希区柯克曾经对一位传记作者说:“我记得父亲上班的时候,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和浆得笔直的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起码在这一点上,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威廉·希区柯克也是一个极度紧张的男人,一生饱受皮肤损伤等各种神经痛状况的困扰。母亲埃玛·希区柯克(Emma Hitchcock)据说也穿戴得一丝不苟,体体面面。和其他大多数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一样,希区柯克的母亲从家里的洗洗擦擦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她还善于烹饪,并且非常享受这一过程。希区柯克说,家里人告诉他,他在婴幼儿时期从不哭泣。但他也谈到自己的恐惧:当他还是个摇篮中的婴儿时,一位女性亲戚曾把她的脸贴得离他过近,还故意发出婴儿的声音。他还说,当一个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往往就会开始试着吓他,这应该是母亲和孩子都享受的事情。在另一次讲话里,他回忆起,他母亲曾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对着他说:“砰!”即使他从来没哭过,他也不是不知害怕为何物。他有一个哥哥,随他父亲,名叫威廉;还有一位姐姐,埃伦(Ellen),大家都叫她内莉(Nellie)。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对希区柯克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希区柯克家族非常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祖父母辈中有三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对他们来说,信教是天生的,甚至是原初的人性。希区柯克的父亲曾称他为“我纯洁的羔羊”;希区柯克自己也记得,他每天临睡前都会站在母亲的床尾,复述这一天发生的好事和坏事。这是一种家庭告解方式。一家人在希区柯克六七岁的时候搬到了莱姆豪斯。莱姆豪斯在17 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伦敦东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靠近河流,聚集了七千多人口。男人和男孩们在此处乘船下海。这里在18和19世纪时是伦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所以,现在这个男孩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伦敦人了,或者用当时的老话来说,就是“伦敦佬”(cockney)。在希区柯克搬来这里的二十年前,莱姆豪斯来了许多华人,他们给他的童年时光增加了一种不同的颜色。威廉·希区柯克在地如其名的鲑鱼巷(Salmon Lane)里买了两间水产店,用来扩张自己的业务;一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间店的楼上,门牌号是175号。这条巷子距离莱姆豪斯港湾和泰晤士河不远,因此本就刺鼻的鱼腥味又混进了浑浊河水发出的持久臭味,变得更加难闻。在希区柯克一家来到这里不久前的1905年,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英国风情》(English Hours)中写道:在泰晤士河旁,“湿漉漉,脏兮兮,黑沉沉则是无处不在的色调。河水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从延伸得很远的码头和船坞中间,耸立起一片荒草丛似的昏暗的桅杆”。彼时的莱姆豪斯所见之处一片杂乱粗俗,曾经是人们口中伦敦东区“垃圾堆”的实质所在。利河流经的此处,几百年来一直是被放逐到城郊的工厂的所在地,其中包括染织厂、化工厂和胶水厂。年轻的希区柯克曾经读过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一篇文章——《谋杀,一种优雅的艺术》(“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1812年的莱姆豪斯形容为“最危险的区域”,“充斥着流氓习气”的“险恶地界”。希区柯克刚搬来的时候,这里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这是一个由小商店和房子组成的街区,商店和房子离人行道不过几英尺远,形成了一块块贫穷的小地块。大多数伦敦人不愿意来这里。希区柯克在这里长大的时候,小酒馆会从清晨开到午夜,一便士就能买一杯杜松子酒或者半品脱啤酒。希区柯克在采访时鲜少提及这个发着霉味的狂乱地方,但是在他早期的英国电影里,伦敦的街头生活被他呈现在了银幕上:音乐厅、小酒馆、电影院和街头市场,其中来来往往的正是他熟知的那些活生生的机智灵敏的伦敦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叫他作“阿尔菲”(Alfie)或者“弗雷德”(Fred);长大后,他称自己为“希区”(Hitch)。他谈及童年和家庭时总是惜字如金,但他还是设法回忆起了一些片段。他喜欢讲述这样一个场景:犯了一个很小的过失,他的父亲与警察就合谋把他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两三分钟。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一次穿越伦敦的“探险”之后回来得有些晚。他提起这件事,原本是为了解释他自己终生对于警察的害怕以及对于罪恶和惩罚的痴迷。然而,为何威廉·希区柯克要给他“纯洁的羔羊”安排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不清楚了。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折磨。它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垂直线条、水平线条或交错的光线阴影就此成了一个常见的视觉主题。很明显,这种恐惧在他年纪尚轻时就已形成。他也许编造了这个父亲与警察的有些象征性的小故事,不断地讲给那些记者听,作为一种驱散黑暗的祷告。但的确有某种东西将希区柯克塑造成了一个内心充满战栗与恐惧,害怕指责和惩罚的人。对此,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从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他自己从未提过),到他和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关系(被他反复提及)。他成年后的性幻想奇特而丰富,他的电影显现了他是多么享受设计女性被强暴或杀害之类的桥段。他说他总是遵从法国剧作家维克托里安·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意见 —“折磨她们!”所以,很可能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本能和欲望。对于世界的恐惧成了他个性的一部分。他害怕穿过制片厂的食堂,担心有人会接近他。他逃离了混乱。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军事行动一样,尽管不清楚敌人是谁——或者什么。他对于生活的恐惧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缓解。从根本上说,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童年产生的恐惧和执着,一直陪伴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从未消失。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孩子。他沉浸于他的电影情节,想象出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场景,与他深深着迷于对攻击和隐秘灾祸的幻想完美并行。这些,起码,也是他的人生。******他早年似乎很喜爱旅行和交通,可能在幻想中,他想要远离莱姆豪斯、伦敦东区和河畔的那个世界,无论去哪儿都好。他收集地图、交通时刻表、车票、旅程表,以及一切与旅行相关的物品。他在卧室墙上钉了一张地图,根据他在《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上读到的最新信息,使用小旗子标出远洋船的航行路线。他去背诵《库克大陆时间表》(Cook’s Continental Time Tables)上东方快车和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站名。仅仅通过背诵目的地的名称,凝视地图上海洋的蓝色部分,他便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中遨游世界。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记录着每一次出行和返回的时间,以便让所有的票根和时间表可以得到精确排列。还只是个孩子,他就对自己的幻想世界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在他之后的人生里,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有一张欧洲列车的时刻表。他可不只是想想罢了。他说,在他8岁前,他就已经坐遍了伦敦通用公共汽车公司的每一条完整的线路。这家公司的地图上有“乘车和骑马”旅行的广告。他坐过伦敦蒂尔伯里和绍森德铁路线,这条铁路线从芬丘奇街延伸至舒伯里内斯。不难看出,这就是他对火车和轮船的迷恋的起源,这种迷恋从他早期的默片开始,一直持续到《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1951)及一些以后的电影中。他对于自己电影的拍摄进度安排得非常严苛,就像他在1936年的期刊《舞台》(The Stage)中说的那样:“我时时刻刻都必须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这是一个紧张不安的旅行者的人生信条。******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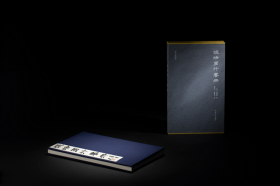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