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正版现货 可开具图书发票 下单后当天即可发货
¥ 46.87 6.9折 ¥ 6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口述:贾建国//连丽如|整理:吴欣还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84115
出版时间2012-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2174145
上书时间2024-09-16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贾建国、连丽如口述,吴欣还整理的《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以著名评书艺术家贾建国、连丽如夫妇从艺五十余年的艺术人生为主线,通过他们对生活的真实还原,从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评书艺术传承发展的美丽画卷。全书共十六章,自“评书世家”起,讲述了呕心沥血的说书人的坎坷经历、北京评书艺术的起起伏伏,以及各种人情世态,包括对父母、对亲朋、对同行、对徒弟,这里有亲情、有爱情、有道义、有恩怨,最后至“传承发展”结束。字里行间流露着夫妇二人对评书艺术及传统文化的执着与挚爱。
目录
一、评书世家
1. 三十多口的大家庭
2. 会抽烟的七姑娘
3. 曲艺戏曲界的邻居们
4. 想考北大数学系的中学生
5.“爸爸不让我接触评书”
6. 六岁登台贾建国
二、第一个评书女演员
1.“为什么把我爸爸打成右派”
2. 退学听书
3. 新书小组与宣武说唱团
4. 不太适应环境的新学员
5. 团里不同意我和贾建国谈恋爱
6. 凤凰厅一个月,一辈子得父爱
7. 第一次亮报儿说《三国》:我叫连丽如
三、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
1. 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
2. 贾建国当兵三年
3. 为结婚一“闯”部队5
4. 与命相争
5. 为孩子再“闯”部队
6. 团里要开除我
7. 夜里哭着唱单弦
四、十二年没上台说书
1. 1966 年,还不知道说唱团就要解散
2. 去北京食品厂当工人
3. 父亲走了—“也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说书”
4. 放不下的曲艺
5. 差点儿成了反革命
6. 王张江姚连?!
五、1979年
1. 已然不会说书了
2. 从查资料开始
3. 恢复宣武说唱团
4. 看到“连丽如”三个字,眼泪下来了
5. 为父亲跑平反
六、为北京评书闯关东
1. 刘兰芳进北京
2. 北京的评书太弱了
3. 寻找机会上电台
4. 到东北说书去
5. 哈尔滨电台录《东汉》
6. 录完《东汉》,母亲哭了
七、盛极一时 电视评书
1. 李鑫荃一句话错失良机
2. 最早的电视评书
3. 千山书荟交益友
4.《东汉》、《三国》上电视
5. 两部《三国》一“打架”,错过北京电视台
6. 被更多的电视观众认识,从《康熙私访》开始
7. 和电视台的官司打赢了
八、永远的书馆
1. 没有现成的书馆了
2. 木板房里把地扎
3. 鼓楼的回忆
4. 去农村开书馆
5. 宣武公园,说《隋唐》,摘“鬼脸儿”
6. 差点儿死在天桥
7. 地坛庙会贾掌柜
8. 我图什么
九、转折点上—调入煤矿文工团
1. 遇上王昌厚老团长
2. 下煤矿
3. 石嘴山贾建国说书再惹事
4. 评上国家一级演员,贾建国说“咱们离婚吧”
十、一个人不叫评书界
1. 永远不参赛
2. 全国评书评话艺术座谈会没我
3. 田连元说:“你真是在这儿奉献呢!”单田芳说:“你太刚强了!”
4. 我参加的几次书荟
十一、把评书带向世界—新加坡、马来西亚
1. 去新加坡,第一次走出中国
2. 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开书场
3. 狮城客串主持人
4. 马来西亚疯《三国》
十二、把评书带向世界—美国
1. 结识常春藤名校教授白素贞
2. 北京评书进哈佛7
3. 把曹宝禄的录像从美国带回来
4. 华盛顿史密森尼“洋庙会”
5. 书馆开到洛杉矶
十三、书“外”的功夫
1. 开古玩店的说书人
2.《康熙私访》与《康熙微服私访》
3.《鹿鼎记》—小说朗诵与评书
4. 新的尝试:动漫评书与音像制品
5. 父亲的三段绝版录音和遗著
6. 连丽如书场
7.《采桑子》里的大福晋
十四、连派评书
1. 重“评”才叫评书
2. 连派评书的“文”
3. 连派评书的“精气神”
4. 评书与京剧
5. 说透人情方是书
十五、传承
1. 再开书馆—小梨园和月明楼
2. 北京评书的非遗传承人
3. 收徒
4. 宣南、崇文、东城—年轻人的舞台
十六、弟子儿女说
1. 王玥波:“我为评书生”,人家敢这么说,人家就是这么做的
2. 李菁:连派第四代都是连先生亲自带着
3. 吴荻:敬、 爱、传、 承
4. 贾林: 师父现场的控制能力太强了
5. 祝兆良:老两口像父母,比父母还操心
6. 梁彦:如师父所说,做一个能登台说书的曲艺研究者
7. 贾琳、郑昕:爸爸妈妈跟徒弟说的话比跟我们说的话多多了
附录一 贾建国、连丽如出版评书文本目录
附录二 贾建国、连丽如评书音像制品目录
后 记
内容摘要
贾建国、连丽如口述,吴欣还整理的《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内容简介:我是“咬着黄瓜尾巴”来的,刚生下来比较甜,没几年就不行了,但这对我的性格养成也有好处。没有“反右”,我说不了评书,这么多年有这么口气一直顶着我,支撑着我。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中19岁的我问爸爸:“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评书艺术家?”爸爸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再聪明,再能干,再能说,可是有一样你记住:说透人情方是书,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心眼儿窄的人绝说不了肚量宽的书。你将来懂得人情世态了,必能成家。”一个人不叫评书界,只有大家共同在评书领域中努力奋斗,才叫评书界。
无论是开古玩店,还是小说朗诵,参演电视剧,客串主持人,我都感觉是评书给了我文化底蕴,没有评书的积累,我做不好这些。反过来,在做这些的同时又加深了我对评书的理解。
我现在把自己摆到一个传承的位置,我觉得我摆得很正。
精彩内容
一、评书世家小时候这些事和说书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冥冥之中又好像很有关系。
1.三十多口的大家庭我出生在北京琉璃厂西街国门关1号,1942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辰时。
国门关1号在今天椿树医院附近,是四合房,南三间北三间,东西各两小问。北房靠东边里间是父母住,我就出生在里间的大炕上。本来父母盼着
生个男孩。因为我大哥大我12岁,属马,二哥生下来就死了,后来又有三个女孩,死了一个,到我出生时活着的就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当然希望再有个男孩。但我一生下来嗓门大,“哇”一声儿,特别脆,还睁着两只大眼睛,我爸一看,挺高兴。提起大眼睛,我长得哪儿都像我爸爸,就眼睛不像,我眼睛大。我太太(奶奶,满族人称奶奶为太太)就喜欢眼睛大的,当年给我爸爸找媳妇就专门找的“大眼睛媳妇”,结果我们家的孩子个儿个儿两只大眼睛。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爸爸喜欢我,我出生以后还给我按老北京人的习俗办了“12天”。那天家里来人非常多,后来很多客人都成了和我们子一辈父一辈的好朋友。
我们家是满族镶黄旗毕鲁氏,老姓儿毕,到我爸爸出生时早已没落。我爷爷叫毕凌保,清末在午门那儿做门甲(把守城门的士卒的最小头目),也
做过几天笔帖式(满语,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算是文书秘书兼翻译,翻译点满文之类的,家里有点儿文化基础可能就是打那时候传下来的。满族人有个习俗,辈辈改姓儿,以名儿为姓儿,爷爷就姓凌,我爸爸叫毕连寿,就姓连了,我们这支儿都姓连,但现在我大爷和二大爷他们那边儿没改,还姓毕。爸爸行三,是暮生儿②,他出生前一个月,我爷爷就去世了。大爷袭了爷爷当门甲,在午门那儿,挣些钱供家用。我大爷和我爸爸是隔山的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大爷是我头一个太太生的,我的太太是续弦,生了我二大爷,跟我爸爸。太太没上过学,连名字都没有,但却是个特别聪明能干、也特别厉害的人,年纪轻轻拉扯着几个孩子,靠给一位王府的格格梳头挣钱养家。所以爸爸一直非常敬重我太太,太太去世后,家里正中的墙上永远挂着太太的大照片。
爸爸是个苦命人,13岁离家,独自在天津闯荡,20多岁看着家里的寻人启事才回来。他摆过卦摊儿,做过小买卖,后来拜评书艺人李磔恩为师,学说评书《西汉演义》,取艺名连阔如。自说书、开广告社挣钱后,日子渐好。等到我出生时,爸爸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开着连阔如广告社、连记杂货店、北洋药社,再加上命馆,还在几个电台直播评书。解放前在电台说书,演员不是从电台拿钱,而是从电台包钟点儿——我包一个钟头,得给电台钱,然后自己接广告,挣这广告费。我爸爸过去在广播电台说书的时候就插广告:“秦琼一分双锏——您要吃‘避瘟散’请上哪哪哪儿——然后这双锏才下来呢。”所以为了经营方便,爸爸开办了连阔如广告社,还当过广告行业会的会长。广告社在北平相当知名,寄信不用写地址,写“连阔如广告社”就能寄到。后来作家王蒙的书里还提过我爸爸的广告社名列前茅。
事业好了,爸爸就把自己的哥哥、侄子都接到家里,小姨子、小舅子也
都来。我姥姥、姥爷死得早,舅舅和我两个姨儿都是在我们家长大的。爸爸对他们特别好,舅舅字写得好就是我爸爸开命馆给人家批八字的时候,他在旁边负责给写,练出来的。当时家里不算佣人,住着30多口子,都养活着。
一开饭,孩子、侄子、徒弟、伙计和我爸爸都吃一样的,人家说没有这样的老板。一过年,我们家东屋全都是肉,拌好的饺子馅儿、蒸好的荸荠丸子、
做好的米粉肉……三舅妈头过年来了,我哥给雇一辆人力车,饺子馅儿、羊肉、牛肉,拿一车走了;我嫂子娘家妈来了,又照样,拉一车走了……街坊邻居也给。
那时北洋药房里面有个伙计叫韩长发,一到饭点儿,我们家的人就到药房门口喊他吃饭,后来我爸在北洋药房养的八哥都学会了,一看见叫长发大哥吃饭的人来了,它就叫:“长发,吃饭了!长发,吃饭了!”这八哥特别可爱,后来让国民党的一个残兵愣给拿走了。韩长发解放以后到了东北哈尔滨,在市公安局信访处工作。“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人去找他调查我爸爸,说:“连阔如当初是你们掌柜的,怎么剥削的你,如实写来。”韩长发大哥是贫农出身,家里非常穷,人特别厚道。他就跟那调查的人说:“您回去吧,当初连阔如吃什么我吃什么,连阔如穿什么我穿什么,一到冬天我们家一
家子所有的棉衣,连阔如老先生都给做得了,派人送到我们家去,不让我有后顾之忧,我没得揭发连阔如,连阔如对我太好了。”这个北洋药房是给我舅舅开的,其实开广告社,广告社不开了之后又开
连记杂货铺,都是给孩子开的,都在家附近。我大爷娶儿媳妇,二大爷聘闺女,都是我爸爸花的钱。爸爸就是想,要是将来自己不能干了,这一摊儿那一摊儿,大家都能有份产业。
爸爸会算命,按迷信的说法,他本身是一个出家的命,四大空亡,本不该结婚,就算有儿女财产自己也留不下。可能是知道自己的命,把几家人都招到一起养活,多少也有这方面原因。爸爸对这个家用心良苦,但没想到自己后来成了右派,一下子掉下来了。生活事业一落千丈,这个家也就散了(我舅舅解放后就上东北了,二大爷全家1950年也上口外了)……打成右派以后,亲戚们几乎都不来了。都说亲故亲故,世态炎凉啊!
2.会抽烟的七姑娘我是辰时生的,7点多正是太阳刚出来,所以小名儿叫桂辰。大名叫桂
霞,但我长大了不喜欢这名字,觉得贫。桂辰这名字一直没叫起来,因为大家都叫我七姑娘。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按大排行,大爷二大爷我们家,一共有姐妹八个,我行七,岁数大的管我叫七姑娘,同辈人就叫我七妹。
在我出生以前,家里有两个奶妈,老白和老宋。老白带着我桂华姐姐,桂华姐姐大我4岁,又聪明又好看,从小爱唱戏,唱京剧学程派像程派,唱评戏学小白玉霜像小白玉霜,连相声《黄鹤楼》都会说。非常可惜,后来29岁得心脏病肺结核死了。我二姐连桂贤比我大1岁多,跟着老宋,老宋又倔又难看,所以二姐长得没我好看,有点儿笨。两个奶妈不一样,喂出来的孩子也不一样,可能长期吃谁的奶也随谁。到我这儿我妈也没奶,但就不请奶妈了,我吃羊奶长大的。从小我就淘气,小姨儿看着我,她大我9岁,跟姐姐似的。父母住北屋,里屋是一个炕,靠着玻璃窗前放一个小桌,是我爸爸批八字的地方。炕旁边是梳妆台,外屋中间儿靠山墙放着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后面一张条案;西面窗户下面是一张漆皮的大字台;靠西墙是书柜;北墙放一大木椅子,撂下来能当床,我和二姐就是在这大木椅子上面睡大的。椅子是民国时期菲律宾木洋式的,现在家里还留着呢。P1-6
相关推荐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广州
¥ 33.35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广州
¥ 33.40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广州
¥ 33.36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广州
¥ 33.40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广州
¥ 33.43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 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泰安
¥ 40.01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天津
¥ 34.54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 连丽如口述自传
九品北京
¥ 20.13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 连丽如口述自传
九品北京
¥ 19.82
-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全新嘉兴
¥ 40.90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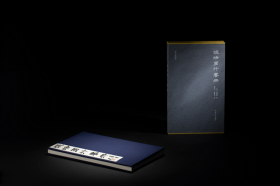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