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夫林日记(全一册)英文原版 #寰宇文献#
¥ 420 7.0折 ¥ 600 九五品
库存50件
上海杨浦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约翰·伊夫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58203
出版时间2017-02
装帧精装
定价600元
上书时间2017-03-29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8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
十七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日记著作,一部是塞缪尔·皮普斯的日记,一部便是约翰·伊夫林日记,堪称英语日记的双璧。可是由于其卷帙浩繁,语言偏于古奥久远,在汉语世界中多闻其名,未见其书。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两本日记影印出版,使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十七世纪中后期英国官僚绅士阶层的日常生活和风俗风貌,为过于概括的历史论述提供一些直观而具体的细节材料,或许不无裨益吧。
一
约翰·伊夫林(1620—1706) 是一位富裕乡绅之子,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Surrey) 风景秀丽的沃顿(Wotton),那里溪流清澈,生长着令人敬畏的茂密森林。
伊夫林家族祖上来自什罗普郡(Shropshire),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役前后,伊夫林的祖父乔治取得了火药专卖权(一直到1637 年其家族还拥有这项垄断权),从而走上了家族兴旺发达之路。乔治娶了两任妻子,其家财足以供养二十四个孩子。乔治的幼子、约翰之父亲理查德分得的田产即在萨里郡,并于1633 年担任了萨里郡的长官,家里拥有一百多个穿绿色绸缎制服的仆人,年收入高达4000 英镑,其家庭之富足可以想见。不过约翰·伊夫林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位于萨塞克斯郡(Sussex)首府刘易斯(Lewes)的外祖父家,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仅因喜丧之事回过几次沃顿。少年时代,他的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师负责,其父曾有意将他送进伊顿公学,因为畏惧那里严苛的纪律,伊夫林没有前往。像他的兄弟们一样,伊夫林后来进入牛津大学的贝列尔(Balliol)学院深造,——作为一个惯例,他们都不是为了取得学位而接受高等教育。1640 年,伊夫林曾短暂就读于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TheMiddle Temple),但对法律没有什么兴趣。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伊夫林继承了一份位于刘易斯的田产以及4000 英镑,使他能够在伦敦优哉游哉地过上一种闲散的生活,可以自由地赴欧洲大陆游历。二年后第一次内战爆发,从欧洲返回的伊夫林参加了保皇党军队,由于萨里郡在议会军的控制之下,伊夫林又担心家族利益遭受灭顶之灾,遂经查理一世许可后再次游历欧洲,直到1647 年方返回英国。
伊夫林的此次游历,先后与数位贝列尔人同行,第一站是法国巴黎查理二世的公馆以及英国驻法国大使理查德·布朗爵士(Richard Browne)的大使馆,那儿是英国流亡者的大本营。随后,伊夫林及其同伴一同南下,经法国戛纳抵达热那亚,先后游历了意大利的比萨、利沃诺、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后又返回罗马,游历了锡耶纳、卢卡、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威尼斯、帕杜瓦等地,又经维罗纳、米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辛普朗山口抵达日内瓦。
1946 年至1947 年的那个冬天,他又返回巴黎,与布朗爵士十三岁的女儿结婚(两年后方同居)。这次游历不仅使伊夫林增长了对欧洲大陆科学与艺术的了解,目睹了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风土人情,也改善了他的法语、西班
牙语、荷兰语水平,在日记中留下了同时代罕见的关于欧洲大陆风俗史、社会史的材料。玛格丽特·威利在《英国日记作家:伊夫林与皮普斯》(English Diarists:Evelyn andPepys,by Longmans,Green & Co.,1963)指出从来没有一个观光客这样认真地履行他见证者的角色:他像十七世纪其他旅行者一样相信探寻异域风情的教育意义,因而不厌其烦地描述所至之处、所观之物(建筑、纪念碑、艺术收藏等)以及仪式的细节和客观信息,而并不给出他自己的个人观感,但他的日记仍不乏可读性,许多的场景如在目前。不仅如此,在伊夫林的时代把自然景色作为欣赏的对象并不普遍,而伊夫林日记中的某些片段已经出色地传递了他对于自然的天才感觉。
伊夫林于1647 年10 月返回英国,处理个人事务,并到汉普顿宫拜见了在押的查理一世,随后定居在德特福德的赛耶斯庭园(Sayes Court),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克伦威尔当政的整个1650 年代,伊夫林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一直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不过护国主时代的当政者中也有他的不少朋友。到了1660 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他的日子好过了很多,经常出入宫廷,乐于为查理二世的文化与科学事务出谋划策。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获得重要的职务,仅仅参与过皇家铸币厂、硝石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参与了伦敦大火之后的规划重建工作,还曾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负责繁重的伤病员救助工作。他的这些工作年薪不高,徘徊在300 至500 镑之间。伊夫林活了八十七岁,在他那个时代属于高寿了。他五十岁以后的生活始终忙于家族事务,忙着为儿孙谋取职务,已经有些乏善可陈。大概在1694 年开始,他已经将家族与财产迁回沃顿,并于1706 年死在位于多佛街的宅子里。
二
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政治十分动荡,国教徒与清教徒、天主教与新教的纷争十分激烈,皇权与议会、保皇与革命的争斗此起彼伏,战争与流血充斥着“处于政治上的试验期”的后半个世纪,正处于从君权神授的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制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伊夫林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没有占据过历史舞台的中心,更像是一个有意识地适度参与历史的旁观者,但事实上他的政治与宗教
倾向十分明显。
由于其家族与皇室的关系,作为既得利益者后裔的伊夫林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与几任皇帝均保持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因而其情感好恶还是很明显地体现在其日记中。一般说来,伊夫林很少在日记中披露自己的私人情感,尤其是私生活,但是他向来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和宗教立场。比如,当他看到从坟墓中被挖出来的克伦威尔等人被施予绞刑的时候,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畅快之感:1661 年1 月30 日 今天——真乃上帝的惊人的不可捉摸的裁判啊!——众首要叛逆的尸体,克伦威尔、判处国王死刑的布拉德肖、篡位者的女婿艾尔顿,从威斯敏斯特华丽的坟墓里,被拖了出来,拖到强盗王所在的泰本,吊在绞架上,从上午九时迄晚六时,然后埋入在该命中注定的、可耻的纪念物下的一个深坑内;成千上万过去看到他们不可一世的人也在场观看。回顾1658 年10 月22 日,惊讶吧!敬畏上帝,崇敬国王吧;勿与喜好变革者有任何干系!(杨周翰译,转引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29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在这段文字中,伊夫林前后用了几个感叹句式,其保皇党的立场昭然若揭。当年10 月22 日举行了耗资六万英镑的克伦威尔葬礼,伊夫林记下了隆重葬礼的大致过程,但语含讥讽:奥利佛的雕像躺在那里,穿着皇家的袍子,配带着王冠、权杖,像个国王一样。看着这个“篡位者”风光的葬礼,伊夫林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葬礼,无人为之哭泣,只有犬吠,士兵们粗野地喝退那吠犬,一边喝酒,一边吸烟,在街道上前进。”反讽的语调很强烈,甚至有些刻薄。同样是喜悦之情,伊夫林对查理二世1660 年5 月29 日重返伦敦的描写更为强烈:“我站在斯特兰大街上注视这一切,向上帝祈祷。所有这一切没有流一滴血,而且是由曾经反对他的军队完成的: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样的复位在犹太人从巴比伦监狱中获得自由以来的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未被提及,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欢乐与光明的一天。这样的情景是人们所未曾设想过,也不能用人力使之实现的。”
当时查理二世正带着两万骑兵、步兵重返伦敦,到处是欢迎的人群和嘈杂的音乐,一直闹到晚上九点。这两段文字,一段记的是为敌对者之死而高兴,一段是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而向上苍祈祷,从中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伊夫林的政治立场了。
当然,也有学者把伊夫林视为心地温良而道学气息较重的势利小人,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为德比尔编订的日记所写的评论里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平心而论,这多少有些苛刻。伊夫林固然偶有不甚妥当的行为,但那也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历史研究者常常从人性完美的角度来评判人,缺少“同情之了解”,殊不可取。尤其是从他与宫廷的关系来看,并未一味地附势趋炎,欺下瞒上,为自己谋取利益。查理一世被处决时,他拒绝到场观看这令人诅咒的行为,当宫廷不断堕落之时,则能够逐渐保持疏离的关系,甚至不乏批评,也说明伊夫林虽然道学气息颇重,言行却能一致,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位君主都具有过人的魅力,查理二世身上濡染了浓郁的法式教养,乐善好施,活力四射,詹姆斯二世自奉简朴,服役海军时常常身先士卒,但是他们都未能准确地认知所处的时代,也未能很好地约束自身的权力和欲望。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曾指出:在男女关系上查理二世是那个时代丑闻最多的领袖,他的宫廷、伦敦社交界和王政复辟时期的演艺界,以他为效仿对象,频涉淫秽;詹姆士二世也是如此,常在左拥右抱之中(华夏出版社,2010)。伊夫林《戈多尔芬夫人传》编者前言也指出,当时国王的周围聚集了一帮宠臣,诸如白金汉、罗切斯特等已成为了丑行的代名词,是英国历史上最堕落腐化的时代。在私人生活中,“美德即羞耻,真相即歪曲,宗教即笑谈”;在公共生活中,路易十四的政治黑金和外来影响也让整个国家陷入腐败。无怪乎伊夫林愤愤不平地说:“英国的堕落子弟,其淫乱放荡,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国家之疯狂。”并且特别讨厌当时还是约克公爵的詹姆斯二世与德纳姆夫人的“杂交”。在詹姆士二世表明其天主教信仰后,伊夫林就与宫廷越走越远了。
日记中所记录的内容,与政治态度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伊夫林的宗教生活,这是了解他的一把重要钥匙。即此而言,他比塞缪尔·皮普斯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伊夫林的母亲是一位勤谨而虔诚的国
教徒,看起来有一种宗教式的忧郁和虔诚的悲伤,因而家庭和社会的宗教氛围将伊夫林塑造成一位坚定的国教徒,甚至因参加礼拜仪式而被捕。他对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非常不满,在日记中把1655 年圣诞节视为自宗教改革以来他生命中以及英国教会最悲伤的一天,因为克伦威尔禁止布道、主持圣餐仪式的宣言开始生效,他和妻子家人的眼里布满了泪水。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的信仰,而是更加虔诚,甚至在日记中不间断地记录了他参加的每一次布道以及领受圣餐的时间。希尔的研究认为,伊夫林对宗教的兴趣远高于科学,其日记如实记录的布道辞验证了那个时代布道风格的演变,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不少布道都宣扬王权,反对平等派,十分关注社会问题,甚至主张财富是上帝恩宠的一部分,穷人要驯顺,不要抱怨等等。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伊夫林的记载是十七世纪宗教生活非常宝贵的材料。同样是出于宗教立场,伊夫林对詹姆斯二世及其皇后的天主教倾向也非常不满,作为掌玺大臣的他甚至拒绝为一位他认为要出版天主教书籍的出版人签发证照。可以说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到情感思想影响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复辟皇室奢华腐败的生活全无好感。人们常常指责伊夫林的日记“无我”,事实上不然,他的政治与宗教态度在日记中有非常强烈的体现,每每对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倾注了更多笔墨。他对克伦威尔以及詹姆斯二世的态度,关涉的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三
除了政治上的极度动荡,十七世纪也是一个在文学、艺术、哲学与科学方面天才辈出的时代。威尔·杜兰特说:“拿全部历史来讲,17 世纪是科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看看它高耸如拱的全景吧,从培根号召人为促进学问而奋斗到笛卡儿使代数和几何结合;从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等仪器的发明和数学的进步;从开普勒的行星定律、伽利略的扩张天空说、哈维的血液图、盖里克那难以分开的两个半球、玻意耳怀疑论的化学、惠更斯五花八门的物理、胡克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哈雷的宇宙预测,最终导致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和牛顿的宇宙论。从前哪一个世纪能创造这些成绩? 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现代人‘是在17 世纪的天才们所积聚供应的思想资本上讨生活’(包括科学、文学和哲学)。”(《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时代》,第550 页)理查德·邓恩也在《现代欧洲史》中称之为“天才的时代”,“如果衡量天才的终极标准是创造出永恒的美丽和普世的意义,那么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能够与历史上任何天才媲美。”(《现代欧洲史》第二卷第296 页,康睿超译,中信出版社,2016)当时的许多巨人做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贡献,不断挑战旧秩序,探索新世界,关涉的内容往往兼跨多个领域。伊夫林虽然不是那个时代最璀璨的星星,但也是那个时代在多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物。除了日记,他的著述有三十多种,内容极为广泛。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为“人人文库”本《伊夫林日记》撰写的前言就称他兴趣广博,在教育、植物学、园林史、医药解剖、数学、化学、神学、钱币徽章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抓住了后培根时代科学实验的时代潮
流。
伊夫林是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1654 年的夏天,伊夫林在牛津结识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r),并参加了牛津哲学学会的会议。五年后,一部分科学家在格雷汉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继续他们的会议,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的提议,伊夫林、雷恩以及威廉·佩蒂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据研究,皇家学会这个名称就是由伊夫林提出的。由于伊夫林与皇室的关系以及多方面的声誉,曾被提名为皇家学会的主席人选,但伊夫林拒绝担任这一职务,有学者推测与其政治态度有关,或许也与伊夫林谦退内敛的性格不无关系。他在欧洲大陆的旅行,对于艺术、科学、建筑、园林都曾经用心考察,并在日记中留下了相应的十分丰富的记录,对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以及著述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为他带来广泛声誉的园林以及森林研究,即奠基于他对欧洲园林艺术的考察。伊夫林青少年的乡村生活,培养了他对自然以及园林的兴趣,其家族位于沃顿的地产种植着非常丰富的橡树、桉树、榆树、山毛榉等树种,为周边的火药制作以及冶铁提供了足够的木材(但是到了1676 年前后木材的匮乏已经开始显现)。他很早就注意到农夫们砍伐木材时如何被堆放、测量,如何有技巧地捆扎柴束、剥下桉树的树皮等。同时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地的开拓,数以百计的植物以及树种被运抵欧洲,惹得人们狂热不已。故而在欧洲大陆游历的这一段时期,他非常热衷于参观各地的园林、新引进的物种、美丽的自然风景和人造风景,对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园林风格及其技艺有了直观的了解。如果说这一时期是他在园林艺术方面的观摩期,那么他定居赛耶斯庭园以后的十年则是其实践期。赛耶斯庭园本是皇家地产,占地100 英亩,由其岳父的家族租住,内战后被议会抄没出售,伊夫林1653 年花了3500镑租金获得了居住权,复辟时期仍经皇帝批准继续居住伊夫林花了大量时间来重建赛耶斯庭园,构建了椭圆形的花园以及具有欧洲风格的绿篱、走道以及其他景观,将法国、意大利的园林理念与英伦传统相结合,修建了著名的新式园林,使它成为一个著名的庭园和私人聚会场所。在建造的过程中,伊夫林从法国人莫林(Morin)的著作中获得不少灵感,栽种了大量果树(有些柑橘类树种是从法国引进),建造了凉亭、壕沟等,还将玻璃蜂箱引入其中。为了有效地管理赛耶斯庭园,伊夫林甚至写作了一本《赛耶斯园丁指南》(Directions for the Gardiner at Says-Court)。彼得大帝逗留英国期间居住在这座庭园里,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伊夫林大概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二十六年这座庭园就颓败了,被改建为劳教所(Workhouse),一直延续了两百多年。
在当时的伦敦社交界,伊夫林被认为是园林专家,曾为很多贵族的园林建设提供专业建议,日记中频频出现相关记载。但伊夫林在科学方面的声誉更主要地是建立在著作的基础上。他曾经翻译过一本《法国园艺指南》(The French Gardiner: Instructing How to Cultivate AllSorts of Fruit-trees and Herbs,for the Garden. Together withDirections to Dry and Conserve them in their Natural),并曾野心勃勃地设想写作一本涵包园林所有内容的《至乐之境不列颠》(Elysium Britannicum),一直写了四十多年仍未完成。不过,其中的一些内容曾经出版过。据玛吉·坎贝尔—卡尔夫(Maggie Campbell-Culver)《树之爱:约翰·伊夫林的遗产》(A Passion for Trees: The Legacy of John Evelyn,Eden Project Books ,2006) 一书的研究,1664 年伊夫林曾出版过其中一章, 即名为Kalendarium Hortense or the ard’nersAlamanac 的植物日历,按月份(每月分为四部分)提供园艺指导,包括一份每月瓜果花卉首选目录,要算是同类出版物中的第一部。1699 年,又发表了Acetaria:A Discourse of Sallets,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色拉和香草的食用和种植方法。而真正为伊夫林带来持久声誉的是1664 年出版的《森林志》(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 Tre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Timber in His Majesties Dominions)。在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燃料的木材短缺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玻璃业、冶铁业、酿酒业、造船业等几乎每个行业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而处于海上争霸最关键时期的海军要求最为强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现实需求,1662 年9 月在皇家学会创始人罗伯特·莫雷爵士的提议下,一个四人小组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并由伊夫林撰写了概要,并可能在1663 年上半年完成了这本书,作为皇家学会的第一种书予以出版。这本提倡种树的书,分析了英国树种的由来,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树木的栽种、管理、以及木材的砍伐和储存,时至今日仍有其可取之处。正像据玛吉·坎贝尔—卡尔夫所指出的,这本书的核心是如何种植与保存树木,以便它们可以在实用性以及美学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后者方面其影响更为深远。伊夫林曾说:“一言以蔽之,一个真正的园艺家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伊夫林的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诠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十七世纪是个小册子的世纪,像弥尔顿等人的有些小册子至今仍熠熠生辉。伊夫林也有一本名为《除烟法》(Fumifugium)的小册子,现在也还常常被环保人士提起。这本书出版于1661 年,当时伦敦正被“如同地狱般的令人厌恶的海煤云雾”所笼罩,伊夫林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其中包括将某些多烟行业迁出伦敦、栽种大量植物等等。
有人据此认为,伊夫林是英格兰第一位环保激进主义。此外,伊夫林在建筑等方面也有一定建树,在伦敦大火之后提出了重建的具体规划。十七世纪的许多博学之士以及科学家都是业余人士,他们所思考的问题、知识的广度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学从业人员。伊夫林对知识的探索以及社会问题的关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四
在伊夫林的所有著作中,日记无疑是最重要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不过这部日记历来不乏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就说伊夫林那样极有文化、极为聪明的人也在那里郑重其事地记载着彗星出现和种种异象,一条鲸鱼游入泰晤士河,就被他看做是不祥之兆,甚至预言了克伦威尔的死亡。这种指责对一个科学知识的探索者来说是很致命的。又说他“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另一个人的肌肉一块块被活活撕裂、骨头被扯得嗑吧吧响,能够毫不畏缩地看着那木刑架垫得愈来愈高”(《伍尔夫散文》,刘炳善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云云,指责他关于痛苦的看法与今人差别巨大,也不免苛求古人了。其实,伊夫林与伍尔夫的歧异,恰好说明了一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党分子与一个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家对于痛苦与人道的观点歧异,当然这种歧异在道德、审美方面或许要更大些。其
实二人根本的差异应该是对日记的看法不同,伍尔夫以为日记应该是为自己或遥远的后代写作,故而不必装模作样、吞吞吐吐,要有私密性——皮普斯的日记比较符合这一要求,所以直到现在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伊夫林则显然抱持并遵循着另一种写作观念,更关注自身的道德形象。因此,伊夫林日记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即时性写作的私密性文本,而是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叙述和个人编年史、家族史的性质。伊夫林日记开始于1641 年,并在日记开头部分回顾了自己的家族概况和此前的一些重要事件,结束于1706 年去世前的一个月,历时六十五年之久。关于这一日记文本的撰写、形态及性质,德比尔曾有过细致的考证,罗伊·斯
特朗依据其研究所撰前言亦有所述及:现存日记手稿有两种, 第一种命名为De Vita Propria, 有76 页, 写于1697年,内容介于1620 年至1644 年之间;第二种手稿命名为Kalendarium,涵盖时间更长,一部分上溯自1645 年的记事
于1660 年写作,另一部分涵盖1649 至1684 年间的记事则写于1680 年至1684 年间,1684 年以后的日记条目才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即时性写作的(参见“人人文库”节本前言,2006)。此外,伊夫林还在某些日记条目的装订空白处或者插入的空白页上做了一些注解和增补,其材料往往来自一些旅游指南、地形介绍和报纸新闻,德比尔在此基础上编订了新的六卷本版本,并于1955 年出版,是目前较为完备、通行的本子。这个版本,较之1818 年出版的古物收藏家威廉·巴里(W. Bray)编订的初版本有了很大的增补和改动,也比后来的诸多版本更接近日记文本的原貌。
从文本写作的时间可以看出,伊夫林日记是一个经过作者精心重构的文本,不注重文本的私密性、即时性等今人看来日记的重要特征,作者的主观意图严重影响了文本的形态和性质。首先,伊夫林日记似乎已经预设了公共读者,因而其素材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选择和重组,突出了某些内容,忽略了某些内容。在伊夫林十来岁的时候,就养成了记录一些自传性笔记的习惯,是日记中某些记录的原始资料,他以之为基础对内容进行了筛选、重写,着重突出了政治和宗教倾向,淡化了作者私密性情感和心灵起伏。其次,伊夫林日记更像一部回忆录或自传,兼具个人及家族编年史的性质,有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将某些事后发生的影响或评论添加到记叙的事件中(参见唐岫敏等著《英国传记发展史》第96 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复次,伊夫林借助于这部日记塑造了自身虔诚、公正、博学的形象,似乎要为这个正在堕落的时代注入一些道义的力量,其道
德家的立场常常让后来者感觉不适。十九世纪的斯科特曾说过,伊夫林“在其回忆录中所诠释的生活、举止以及原则,应该……成为英国绅士的手册”(转引自威利一文,第15页)。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日记中的那个绅士形象的质疑越来越多,伍尔芙说“他的文字写得晦暗而不透明,通过它我们看不出深层的东西,也看不出思想感情的隐蔽活动。他不能使我们超越理性去痛恨弑君者或者去喜爱戈多尔芬夫人。”这种冷嘲热讽实在有些道理。《英国传记文学史》在此基础上指出:“伊夫林力图通过这部日记教育后代,帮助他们自我提高和进步,并为实现英国国教的道德教化目的塑造威严、虔诚的自我与他人形象。一方面作者将大量篇幅用于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伊夫林塑造出理想化的虔诚信徒形象以实施示范作用,使日记落入了圣徒传的窠臼。”(第97 页)则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打量伊夫林的这部日记。人们浏览前人日记的时候,有的是为了寻找研究历史的线索,有的是从前人的失误、无知中获得理性方面的优越感,有的则纯粹出于对他人生活的好奇,并能够从当事人的绯闻或糗事中获得快感,在最后一点上伊夫林日记显然令人失望。诚如威利的长文所说,皮普斯日记对伊夫林的一瞥所提供的生动性以及幽默感足以胜过伊夫林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可是我们若从历史——而不是文学——的角度来衡量这部日记,除了皮普斯日记以外,可以说伊夫林日记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一幅细大不捐、内涵丰富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伦敦大火、大瘟疫、克伦威尔之死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记录了包括工匠技术以及大霜冻之类的气候异常等历史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英国六十余年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虽然作者对事件和道德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人物性格及其复杂性的关注,或许使它缺少所谓的深度,
时不时还要冒出来些宗教家的气息,也并非富有盎然的意趣,但是这部日记在社会史、风俗史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对于真正的有心人来说,“说不定哪个人在离去时燕尾服的后摆一闪,那比坐在强光之下的整个人体还要暗示出更多的东西来呢”(伍尔夫语)。
鉴于以德比尔编订的本子为基础的伊夫林日记比较常见,本书还是选用了威廉·巴里编订的、不常见的一个印本,而且已将古英语转化为现代英语,更有助于更多的读者阅读、了解伊夫林其人及其时代。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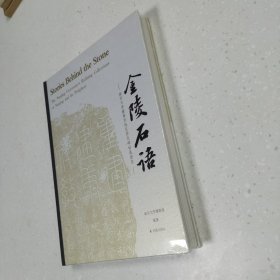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