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
正版图书保证质量 七天无理由退货让您购物无忧
¥ 85.8 6.7折 ¥ 128 全新
库存39件
北京朝阳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奥)弗兰茨·卡夫卡著
出版社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ISBN9787547061404
出版时间2023-0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128元
货号R_11988063
上书时间2024-04-0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全新正版
- 商品描述
- 《变形记》篇注: 本篇是卡夫卡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之一,完成于1912年11月、12月间,1915年10月表于月刊《白页》:全篇印刷后约占70页篇幅,是卡夫卡一生中真正完整印刷出版的故事当中长的一部。 《变形记》与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存在着大量可从或心理学角度给出诠释的可能。德语文学界中尤其流行的诠释方式,是将《变形记》理解为卡夫卡与父亲之间角力的反映。关于这一方式,有观点认为:《变形记》是以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复杂关系、以及伴随他一生的罪孽感为背景的。“害虫”这一形象,将卡夫卡在父亲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无足轻重恰如其分地具象化了。社会学方面的诠释亦拥有大批追随者——在这类诠释当中,文学家们普遍会将萨姆沙家族发生的故事视为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 作家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一书中专门探讨过卡夫卡与《变形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存的一切诠释皆不符合卡夫卡本人所持的文学理念。与之相对应的,纳博科夫也对《变形记》给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一番诠释——该诠释是以叙事上的种种细节作为导向的,但又断然排除了所有象征与寓意层面的分析。针对界流行的父亲结论,纳博科夫认为,《变形记》故事中残忍的角色,与其说是父亲,倒不如认为是妹妹格蕾特,因为她才是那个真正背叛了格里高尔的家人。在谈到《变形记》的写作风格时,纳博科夫写道:“清晰、又正式的语气,与故事整体噩梦般的黑暗内容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卡夫卡笔下这种的风格,强化了他幻想世界中所暗藏黑暗的层次感。对比与统一、风格与内容、表象与寓言达到了的统合。” 实际上,格里高尔与他的妹妹格蕾特——这两个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组典型的、卡夫卡式的人物关系。在卡夫卡的诸多小说当中,这样一组人物关系通常都是由一个事事被动、持禁欲主义思想的人物,以及另一个事事主动、依靠本能来行动的人物所组成的。以如此方式构筑而成的人物关系,本质上是难以调和、甚不可调和的。以本书中的篇目为例:《判决》当中的格奥尔格与彼得堡朋友,《乡村医生》当中的乡村医生与马车夫,《饥饿艺术家》当中的饥饿艺术家与美洲豹,皆是如此。这样成对出现的人物,恰恰类似一个人内心中彼此对立的两部分,或者说卡夫卡格当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两个部分。对于卡夫卡本人而言,无论写作还是生活,实际上都是对这两个部分之间角力的一种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变形记》当中,由于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的自限,这两部分的对立统一感十分明显——“格里高尔”和“格蕾特”这两个名字本身所具备的同一,似乎也是在暗示这点。 格里高尔究竟为什么要变成害虫?社会学观念上有一种说法,即将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生存抗争”,定义为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后的一种生存斗争——这个归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逐渐摧毁了他作为“人类个体”的本质。换句话说,害虫的形象也因此成为了格里高尔被剥夺感驱使的生存方式的激烈表现。在身体变形为害虫之前,他在精神上已先一步“劣化”了:基本没有个人生活,为商旅客这一职位的维系而焦虑,为自己是否能够在各方面取步而焦虑,为业务上可能会失败而焦虑。“害虫”正是这种内在的外化,是结能主义作用于工作和生活的产物。 变形成害虫之后,格里高尔几乎是马上开始了自我否定与压抑现实的行为。在变形之前,格里高尔早已放弃了自我,以此来为全家人换取充满感、甚可说是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且以此为荣。变形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份产生了重大转变,不得不要求家人们关注、照顾自己,沦为了一只“米虫”——他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身份,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内心因为受到家人们的照顾而对自身现状感到失望。在小说中,格里高尔选择实施自我否定的行为不胜枚举,例如:将自己的身形藏匿于贵妃椅下方,一步隐藏在床单里面,与世界隔绝开来;为了顺从家人们或多或少已向他公开挑明的意愿,他愿将自己活活饿毙。格里高尔因为自限而逐渐变得消瘦下去,某种程度上而言,此事亦具有致命绝食行为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格里高是不自觉地被家人误解或忽略,他变形后在家中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可以说是不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变形记》逐渐变得像是一幅与疫病者群像密切相关的麻风病图景;“害虫”格里高尔则更像是逃避传染病或癫痫发作的一名重症流放者,或是像一种被从事之职业毁败掉的存在主义造像;萨姆沙全家人居住的出租寓所,恰如一处徐徐揭开帷幕的舞台,打破了日常生活状态的表面,暴露出了其固有结构下的非人内核——卡夫卡式描写所具备的典型风格,一方面是现实主义与幻想、世俗和理,透过能够令读者联想到某种敏锐观察力的放大,将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疯癫、怪异与反常的杂烩,一切荒诞和悲剧的、类似无声电影般的元素,在成文手法上反而通常是多变、无稽且无理的。 叙事不稳定也常常被认为是《变形记》研究中的不确定因素。格里高尔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各种描述当中常存在着相互矛盾、抑或含混不清之处。关于格里高尔变形后的躯体特征、他所发出的声音、他究竟是生病了还是正在好转中?他是否是在做梦?他究竟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以及——他所持的道德立场究竟如何?他的家庭是否无罪?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推测。实际上,根据卡夫卡日记中的描述,早在1915年小说初次发表之前,他已下了定论:对格里高行任何形象上的描绘都是不恰当的。对于卡夫卡创作出来的这篇小说而言,不存在对格里高行任何可视化描绘的可能,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试图去描绘格里高尔的形象,都会因此而使自己变成一个的叙述者,但卡夫卡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认为,读者自身的阅读过程还没有开始,如果这时已出现了一幅画面,那这位读者无疑被这幅画面给带偏了,心中产生了偏见,小说也没法读下去了。 况且,我们也并不能将格里高尔视作一个具体的人,因为单单从小说首段的描述内容来看,这不符合作者的设定:如果我们将格里高尔视作具体的人,那恰恰说明开篇句中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反之,如果读者们不愿被这句话说服,宁愿继续将格里高尔视作人类、视作一名结构化社会贬庶过程下的受害者,那么所有的叙述都将自然而然地演化为定论,偏见也因而得以自证。 实际上,“变化”的也不只是格里高尔,还有与格里高尔之间具有某种特定同一的格蕾特。甚可以说,在这整个故事当中,起到决定变化的反而是格蕾特的“变形”,而非格里高尔的“变形”。唯有格蕾特,才是“变形”这一概念所对应的物。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的选择是虚度光阴,终走向,格蕾特却在新的家庭环境当中变得成熟,也担负起了责任。哥哥死去之后,在萨姆沙夫妇眼中,他们的儿反而“绪逐渐变得开朗”“到底还是成长绽放为一个美丽又有丰韵的大姑娘了”。于是,在小说的后,父母也开始想要为她寻找一名伴侣。格蕾特的转变——她从孩到人的转变,少从这一点上来看,是整套叙事下的潜台词。 格里高尔变形后成为畸形“害虫”的相关描述颇为详细具体,也很符合现实,几乎是以冷静的、如新闻报道一般的文描绘的。无感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内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不可能的事物具备了不言而喻的、日常化的特征。恰恰是这桩离奇的事件,与看似枯燥的、写实主义语言表达方式的结合,才使这篇小说的叙事显得如此。 《变形记》的大部分篇幅都是由主人公的人称视角来起作用的,一切虚构的现实,都是由格里高尔以现象学反映的方式行的。真正的叙述者本人,仅在格里高尔死后才出现。 全文共分为三个章节,格里高尔的房间共有三道门,他的家括三个人,整篇小说程中一共出现了三名佣人、三个房客,冠以“萨姆沙”这一姓氏的三个人各写了一张请假条——这些明显浮于表象的数字“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格里高尔在全文的三个章节当中,每个章节都会闯出过一次房间;然后,等到每一章结尾时,格里高尔又都会收获一道新的伤痕、一次精神上的侮辱,乃。这样一种象征意味极强的宿命论式结构,强调了他逐渐被孤立的全过程。格里高尔的衰颓伴随着家族其他成员的崛起,两者之间并行不悖、相互依存。从变形到,这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展示了一个有问题的、脆弱的生命体是如何沉沦下去的;与此同时,也展现出另一个与之对应的、富有活力的生命是如何存活下来,并拥有光明未来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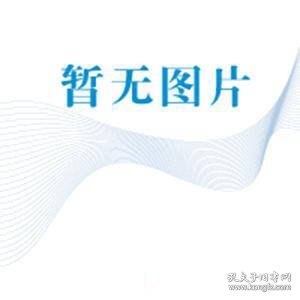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