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记 中国历史 何兆武 述;文靖 执笔 新华正版
¥ 21.76 6.8折 ¥ 32 全新
库存113件
河北保定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何兆武 述;文靖 执笔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14665
出版时间2016-03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297页
字数193千字
定价32元
货号xhwx_1201265320
上书时间2024-12-1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目录:
修订版序言
序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和自由
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义的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事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返乡
也是故乡,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大学附中
2.西洋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力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闹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大学之谓:忆先生
1.闻一多先生
2.张奚若先生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硝烟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滔滔不绝的殷福生(海光)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书台湾
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新版后记:横成岭,侧成峰
内容简介:
上学记是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清华大学思想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曾学于两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在两南联大外文系读。1956年至1986年任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文靖,1975年生,本名文静,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精彩内容:
“对我来说,生读书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惬意、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兆武
目次
修订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和自由葛兆光
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义的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 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 无事乱翻书
3. 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返乡
也是故乡,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 大学附中
2. 西洋教科书
3. 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力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闹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转变
大学之谓:忆先生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硝烟
“一二?一”运动
1.“打到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增订版后记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终于写出了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方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和,能和能,能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是真理,需要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做其和美梦的时候,被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的。当然,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2004年卷期,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
2008年2月28
北京清华园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和自由
葛兆光
小引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一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本人打进来,把中国成了一个杀戮场,八年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旗变成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好的读书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gulliver travel(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对于我,好像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什么是”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不应该是pleaure,而应该是happine,plea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我说,应该是bleedne(赐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的东西。他说,那么的虔诚应该是一种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 . eliot的一段话:“there i a higher level of doubt it i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 if we live to the end i holine. the only ecape i 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它的归宿是圣洁,的逃脱办法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是圣洁,是高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 freun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二 :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是圣洁,是高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看成是追求理的和的理之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越?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有什么具体的、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比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重要的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是说,个人的和整个社会的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可以说,对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时候的中小,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马上泪流满面,现在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个时代的情结是仇恨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到1931年的东北沦陷,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说,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述历史中,他说:“我的父亲不是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大都是不满当时的,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游行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是只参加爱国。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自己不是(政治)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1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自立、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是强调自己的特,而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有特,但是这特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真理,质疑源自西方的、科学和自由,强调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搞党国一体的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乃是一种世界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没有跟随英美,而效仿苏联的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同样也批评的胡搅蛮干。何先生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他说:“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长,看得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不是)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应当是“局外人”(out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pirit in opition),而不是调适(ac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心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三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决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读“开明”,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 from hake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t ong)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法国古诺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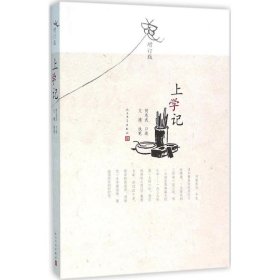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