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治阶级/人文与社会译丛/(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政治理论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新华正版
¥ 64.49 6.6折 ¥ 98 全新
库存5件
河北保定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9529
出版时间2012-07
版次2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640页
定价98元
货号xhwx_1201922328
上书时间2024-05-1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统治阶级一书是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加塔诺莫斯卡在书中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有名的统治阶级论,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莫斯卡也凭此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者。
目录:
英译本前言
章 政治科学
第二章 统治阶级
第三章 封建和官官僚制度
第四章 统治阶级和社会类型
第五章 卫
第六章 选举权和社会势力
第七章 、党派和教派
第八章
第九章 常备军
第十章 议会政治
第十一章 集体主义
第十二章 统治阶级的理论
第十三章 政治组织的类型
第十四章 政治组织的演化
第十五章 统治阶级中的原则和倾向
第十六章 统治阶级和个人
第十七章 代议制的未来
索引与参文献
内容简介:
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作者简介:
加塔诺莫斯卡,意在利都灵大学宪法教授、罗马政治制度和理论讲座教授,有名政治社会学家,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作为一名长期参与政务的学者,他曾担任议会议员和参议员,并在1914――1916年间担任殖民部次长职务。主要著述有:关于和议地制的理论、统治阶级等。莫斯卡系统而全面提出了有名的统治阶级论,他与帕雷托一道,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中“统治精英理论”的者。
精彩内容:
章 政治科学
1. 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思想家们有许多次作这样的设,即在他们视野中展现的社会事件不仅仅是机会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某些超自然的全能意志的表现,而是决定人类大众的恒常心理倾向的结果。甚至在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他已经努力去发现支配这些倾向发挥作用和它们行为方式的法则。致力于这一目标的科学被称作“政治学”。
在16和17世纪,许多作家特别是意大利的作家,投身于政治学的研究。这些作家中打头的是马基雅弗利,他也是所有人中的一个。然而这些作家对人类社会中确定的恒常法则关注较少,他们更注意那些政治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阶级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功地获取极高权力,或者挫败其他个人或集体想取代他们的努力。
尽管两者有许多联系,但它们是实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下面的类比可以说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研究支配人类社会中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或者趋势,但是这门科学与怎样积聚和保持财富的技艺不同。极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可能无法赚到钱财,而银行家或者商人可能从经济法则的知识中获得一些理解,但是不需要掌握它们。实际上,他们即使对这些法则浑然无知,仍然能够把生意做好。
2. 在我们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创建的科学已经被细分和专业化了,以至于我们不是拥有一门政治科学而是一组有关政治的科学。这还不是。人们已经作出努力,把这些科学的结果综合或者结合起来,这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出现。在解释立法时,或者在公共法令时,法理学家或者公法的起草者是研究那些激发立法的一般趋势。历史学家在描写关于人类2兴亡变迁的故事时,经常寻求从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中推论出指导或者决定这些变迁的法则。古人中的波利比乌斯和塔西陀,16世纪的圭西亚迪尼,以及上个世纪的麦莱和泰纳是这一类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法理学家——而言之,所有希望改善人类社会,并且因而研究调节社会组织的法则的思想家——可以被认为是从一种或者另一种角度处理政治科学的问题。结果,人类思想领域的一大半,人类为研究过去、探索未来以及分析自身的道德和社会特付出的巨大知识努力(intellectual effort),都可以归为政治科学。
章政治科学在政治和社会的诸门科学中,一个分支迄今为止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相当的成熟,以至于它已经以其丰富和准确的成果靠前。我们谈的是政治经济学。
临近18世纪末期,一些才智很好之士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涉及的现象从大量的其它社会现象中分离出来,把它们与其它资料分开来虑,从而成功地确定了支配这些现象的许多恒常的心理法则或者倾向。这种把经济现象从社会活动的其它领域中分离出来的方法,以及把经济现象独立于影响政治机构组织方式的其它现象进行思的惯,无疑解释了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但是同时它也应该为这一事实承担主要责任:经济科学中某些设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能够设法把它的观察与人们从人类心理的其它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它也许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并且可能是决定的进步。
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间,有一种企图以经济原因作为基础解释人类历所有政治事件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太片面,太狭隘。有些社会或者政治现象(例如,重要的兴起和扩张,某些古代民族的复兴、某些强有力的军事政体的建立等)无法仅仅用财富分配的变化,或者用资本和劳动之间,或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盾来解释。
然而,如果不虑政治经济学这个早熟学科已经取得的成果,无法研究那些指导政治机构组织方式的趋势。研究上面提到的这些趋势是本文的目的。我们把这种研究称作“政治科学”。我们选择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目前次使用的词汇,因为它还没有被误用,也因为自奥古斯都孔德以来,许多人采用“社会学”(ociology)这个词,但是它的意思还没有得到准确限定(在通常用法中,它涵盖了所有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犯罪学,而不是与政治现象的研究直接相关的科学,人们已经专门并且恰当地指定了哪些现象是政治现象)。
3. 一门科学是建立在系统观察的基础上。人们采用适当的方法观察特定的现象秩序,这些观察进行得如此协调,从而可以揭示凡人通常的观察无法发现的确定真理。
数学科学为真正的科学程序的发展,提供了简明和现成的说明。在数学中,公理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观察的结果,它的真理甚至对普通人也很明显。从一系列公理出发,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证明较为简单的定理。然后,进一步把从这些定理中得到的真理与从公理中得出的真理结合起来,我们能证得新的、更困难的定理,任何没有4受过数学训练的人都无法猜出或者证明这些定理的真实。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程序也十分类似,但是在这些科学中,新的因素使得方法更加复杂。把一系列简单的观察结合起来经常不足以证明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合的”(ite)真理——换句话说,即那些一眼看来不明显的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数学中某些与公理相应的内容,只有通过试验或者长期观察才能得到,当那些受过特定方法训练过的人以这些方法进行试验和长期观察时,两者都有它们的价值。在各种科学的早期阶段,人们几乎是在那些很幸运的设的结果中,发现了合理的程序,这些设后要被试验、以及对事实的观察所确证,而反过来这些设又解释了许多其它的观察和事实。在任何一门科学中,长期的经验主义,或者不完善或错误的观察方法,或者阻碍了将相关个体现象的资料结合起来的错误理论,是早于严格科学的阶段。只有经过人类智力(mind)在特定的现象序列中长期耕耘,累计起来的资料、更好的方法、更的观察仪器、以及有识之士的洞见和不松懈的耐心,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那些幸运的设,使得真正的科学成为可能。
在特定现象的序列中,单纯使用观察和经验并不能保证结果的真正科学。弗兰西斯培根错误地认为试验方法具有发现科学真理的能力,而且在我们的时代许多思想家和作家也都抱有同样的幻想。如许多人所知,培根曾经把试验方法与圆规相比较——圆规可以让未经练的手画出的圆形,同样,试验方法可以得到准确的科学结论。事实上,如果观察和试验可以产生健全的结论,我们上面指出的条件是基本的。不准确的和以错误的科学程序进行的观察和试验会导致错误的发现,甚至会使无稽之谈貌似有理——占星术和炼金术是以或真或的观察和试验为基础的。但是它们的观察方法,或者说观察所依据的观点却是错误的。颇为人所知的马丁德里约在他的魔法研究(diquiitone magicae)中,认为能够依赖观察弄清爱情魔法 (love magic)、仇恨魔法 (hate magic) 和催眠魔法 (leepinducing magic) 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揭示诡计及男女巫师的行为。的确,他希望他的观察将帮助人们识别男女巫师并提他们。因而当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坚持一个的财富仅仅在于它的金钱和土地产出这一结论时,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依照对事实的观察;曼佐尼富有成效地记述了17世纪典型的科学家邓费兰特(don ferrante), 后者从在他的时代广为接受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论证,表明黑死病可能并不传染,他的推理其表面而言,是无可置疑地合乎逻辑和确定的。费兰特的推理如下所述:在rerum natura〔拉丁文:自然本身〕包括实体和事件(accident)。传染病不可能是一个事件,因为事件不能从一个身体传递到另一个身体。它也不能是一个实体,因为实体是似土的(terreou)、似火的(igneou)、水状的(aqueou)和气态的。如果传染病是土质的,它应该是可见的;如果它是水状的,它应该是湿的;如果它似火,它将燃烧;如果它是气态的,它应该上升到它合适的范围。
4. 甚至政治科学还没有进入真正科学的阶段。尽管学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普通人无法觉察到的东西,它似乎还是不能提供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形式,让所有熟悉这门科学规则的人都能接受,迄今为止它也没有获得一种可信赖的、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无法探究它们。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说,这些原因不在于对政治题目进行沉思的人缺少天赋,而在于这一题目包含的现象靠前复杂,特别是在于这种情形,即直到几十年前,几乎还不可能获得关于事实的确切和接近的信息,而我们则被迫依赖这些事实,去发现决定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恒常规律或者趋势。
不论我们认为迄今与政治科学领域相关的各种方法或思想体系多么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对这些方法和体系尽快作出研究仍然是我们的责任。它们中的一些曾经或者仍然不过是对某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行哲学、神学或者理的辩护,这些政治组织几百年来已经,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正在人类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持久的倾向之一,是以一些合理的理论或是一些超自然的信仰,证明现有的组织形式是正当的。我们相应地有了一个所谓的为社会服务的政治科学,其中,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仍然被置于人类理智之上,并且因而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可以从上帝(或者诸神)的意志中找到解释。我们已经拥有了另一种政治科学,它认为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它是意志、或者是组成某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意志的自由和自发的表达,我们现在仍然拥有这种政治科学。
在政治观察的各种形式和方法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两种,它们在特点上比其它形式或方法更为客观和普遍,而且人们特意用它们来发现法则,这些法则可以解释出现在世界上的各种形式。种方法认为各种社会的政治差异是因为它们外部条件的不同,特别是气候的不同。第二种方法则把差异与各民族体质上的因而是心理上的不同联系起来。种方法强调自然条件标准,第二种则强调民族或人种的标准。两种方法在科学史和当代科学上占据了如此重要地位,而且表面来看它们的特征如此确定并具有试验,以至于不能不研究它们实际具有的科学价值。
5. 从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到本世纪为数不少的作家,定气候对通常的社会现象和特定的政治现象具有影响。许多人试图证明这种影响,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础。这些作家中,打头的是孟德斯鸠,他强调气候对民族道德和政治制度的决定影响。他写道:“一个民族离南方国度越近,它看起来距离德行越远。”而且,他宣布自由与温暖的国度互不调和,在橘子生长的地方,自由从来不会兴盛起来。其他作家承认温暖的国度也许曾产生文明,但是他们坚持说,主要的文明中心已经持续北移,现在政治上组织得优选的均位于北方。
现在让我们从以下内容开始讨论,一个的气候并不接近取决于它的纬度而是依赖如下因素,诸如海面的高度、光照程度、风力情况等等。进一步讲,并非所有物理环境都依赖于气候,换句话说,它们的变化并不与温度和降雨一致。其它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一个地区拥有的人多寡,它的农业发展程度,以及经常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等。地广人稀的牧业或者森林地区的居民生活的物理环境与人烟稠密的因而也即广泛耕种地区居民的环境接近不同。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对作为体的民族生活、以及对作为特殊形式的该民族政治组织的影响肯定会随着该民族文明的增进而减弱。植物王国毫无疑问是依赖于大气和土地因素,除非植物被种在温室中,它们都将生长于大气和土壤中,它们几乎接近缺少反抗或者抵御外界影响的手段。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好一点,因为自卫和反抗对它们并非绝无可能。原始的或者野蛮人处境更好,因为他自卫的手段至少比动物强。处于优选境况的是文明人。他在智谋上如此充沛,以至于气候变化对他的影响很少——而且他正在复一地使他的智谋更为完善。
算有这个前提,下面的观念在我们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初的文明兴起于自然可以提供优选多工具,或者自然带来的障碍小少的地方;从而这些文明可以在广阔的江河流域兴旺发达,这些流域的气候温和、适宜灌溉,能够种植某种农作物。适当的人密度是文明兴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当一百个人分散于一千方英里土地上时,文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较大数目的人类居住在相对小一些的土地上(例如每方英里至少十个或者二十个居民),农业是必需的。实际上,我们发现中华文明的兴起,同步或晚于水稻种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靠小麦、大麦、黍子,原始的美洲文明依靠玉米。在一些热带,某种果实,如香蕉,或者淀粉根茎如树薯可能取代谷类作物。
历史确证了这种归纳,它显示了早期的文明是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以及黄河流域,以及在阿纳瓦克高原——这些土地代表着我们已经提到的物理条件。但是一旦人类成功地汇集他的力量,在某些特别适宜的地方来驯服自然,他也可以在其它更加难以驯服的地方控制自然。在我们的时代——除了两极地区,和一些如赤道附近的地方,以及一些特别干旱的或者瘴气横行人类不适居住的地方——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容纳文明民族,或者能被创造以容纳他们。
6. 我们认为文明是从南方向北方扩展,或者从温暖的地到寒冷地区扩展的这一原则是那些过分简单的公式之一,这些公式尝试用单一原因来解释特别复杂的现象。它建立在历史的一些单纯的片断上——建立在欧洲文明某些单一阶段的历,以及对这些这些片断历史肤浅的研究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人用这种方法检查一幅地图——例如一幅北部德意志,或者西伯利亚的地图——可能会推断所有的河流从南方流向北方,因为在这些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它们的高山在南方,海洋在北方。如果一个人研究俄罗斯南部,情况可能刚好相反,而南美洲可能适用别的法则,也是所有河流从西流向东。真理是,河流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山脉或高原流向海洋或者湖泊,与纬度或经度无关。如果一个人把那种提供较少阻力的土地称作“低级的”土地,他也许可以说统治文明扩展的是非常相同的法则。文明的潮流互不相属地从南方流向北方,以及从北方流向南方,但是它优先流向那些它遇到小自然和社会阻力的方向——这里“社会阻力”一词指的是反方向发展着的原有文明的冲击。
中华文明从帝国的中部兴起。在北方它被中亚荒芜和寒冷的高原所阻碍,而在南方不仅流向了中国的南方各省,而且也流向了印度。印度文明在北方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喜玛拉雅山脉,它从北往南发展,从北部印度进入德干(deccan)高原, 并进入了锡兰和爪哇岛。埃及文明向北扩展,直到它遇到希泰人(hitte)的有力阻挡,即在叙利亚北部遇到了另一种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埃及文明向南方发展更广阔,实际上它沿着尼罗河从孟斐斯到底比斯(thebe)地区,从底比斯又发展到摩洛(moroe)现在看来,埃及早期王朝无疑兴盛于塔尼斯和孟斐斯,只是在牧人国王(hepherd king)入侵之后,底比斯才开始显赫起来,埃塞俄比亚也是被埃及人所开化,直到很晚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之后,波斯文明是从东到西扩展——即它所遇到的自然障碍小的方向——直到它与希腊文明碰撞。希腊—罗马文明包含了整个地中海盆地。希腊—罗马文明在南部为沙漠所阻,在东面又遇到了东方文明,这些文明先是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然后是波斯帝国。于是它向北扩展,一直到达当时无法通过的德意志北部的沼泽和森林地带。文明在南部为海洋和沙漠所阻,被迫向西北扩张。在中世纪,欧洲文明在南部被阿拉伯文明所抑制,后者从欧洲夺取了地中海盆地整个南部地区。欧洲文明相应地向北扩张到了苏格兰、德意志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欧洲文明向所有方向扩展,不管是人烟稀少容易殖民的土地,还是那些等待征服的衰败。
文明的中心,像一个文明一样在某个方向上传播,它的移动看起来与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则一致。位于一种类型的人类文明边缘的通常不是在该文明中领先的。当欧洲文明包括整个地中海盆地时,希腊本土和南部意大利是文明世界的核心,它们是其中有活力、有和繁荣的。当它们成了面对世界的文明的前哨时,衰落了。在一个,条件一样的话,文明和繁荣的地区似乎是拥有文明的核心,或与这个所属的文明辐中心的地区有便捷的。西西里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时,希腊世界的中心是在西西里以东,西西里岛繁荣和开化的地方是它的东海岸。在阿拉伯时期,西部西西里是开化、繁荣和人密集的地区,它靠近非洲,文明由此辐。该岛人多和富裕的是其北部海岸,它北部面对欧洲。
7. 我们认为,把北方民族的道德水置于南方民族之上的设非常鲁莽。道德是复杂的心理和精神特征的产物,人类生活其中的外界环境在道德的积极或者消极表现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潜在地比另一个人更有道德,这种比较本身很困难。对两个社会这种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人类群体下判断同样非常困难。关于这个题目的统计资料不能说明情况——它们经常无法说出足够多的信息。个人印象是太主观——它们在体上不如统计资料可信。通常来说,人们对不熟悉的不道德模式印象更深,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另一个的人们比我们自己的要差。进一步讲,我们通常惯认为那些我们次到的,或者我们非常了解和估价其某些恶和弱点的比其它道德要差,而实际上所有人都可能具有这些恶和弱点。
经常归咎于南方人的恶是纵欲,而北方人较普遍地被指责为酗酒。然而也许可以看到,刚果黑人在酗酒方面比俄罗斯农民或者瑞士工人更不检点;至于纵欲,看起来民间俗和社会组织类型比气候对它有更深广的影响,这些俗和社会组织类型作为一系列历史情境(circumtance)的结果,是每个民族为其自身创造的。圣弗拉基米尔(即沙皇,他被追封为圣徒,成为所有俄罗斯人的保护神)在后宫拥有比哈伦哈里发更多的女人。 可怕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在残忍和纵欲上超过了尼禄、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以及东方嗜血的苏丹们。 在我们这个时代,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也许比古代的巴比伦和德里有更多的。在现代欧洲,德国在犯罪上处于领先地位,往下数是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意大利接近这一排名的底线,而西班牙少。
许多犯罪学家定南方针对人的暴力犯罪或者冒犯占绝大多数,北方针对财产的罪行比例更大。但是塔尔德和拉贾尼认为,人们在气候和犯罪类型之间寻求的这种关系,应该被归结为社会条件的差异,正如一个的不同地区可能遇到的情况不同。的确,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通常发生在南部,而这些的北部显示出较高比例的财产犯罪。但是正如塔尔德指出的那样,这些的南部地区比起北部来,通讯设施较为落后,也更远离重要的城市和文明的中心;可以想见,暴力犯罪在较不发达的地区更为猖獗,而与气候无关,而那些要求技能和智谋的犯罪在教育发达地区更为常见。实际上,这看来是这一现象充分的解释。法国暴力犯罪优选的地区(在东部的比利牛斯山脉的阿尔代什和洛泽尔)固然位于南方,但这些地区因为其高山地形而较为寒冷。在意大利,巴斯利卡塔(bailicata)是暴力犯罪比例优选的地区,但它是多山地区,相对较为寒冷——马蒂斯(matee)、加尔加诺(gargano) 和西拉(ila)诸山的很好每年大部分时间为积雪覆盖,在这些高地上分布着一些因血腥和劫事件而臭名昭著的西西里城镇。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统治阶级/人文与社会译丛/(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政治理论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新华正版](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dcdbaaaa/b391e83954d0348e_b.jpg)
![统治阶级/人文与社会译丛/(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政治理论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新华正版](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5701970/122cabe7f75564c0_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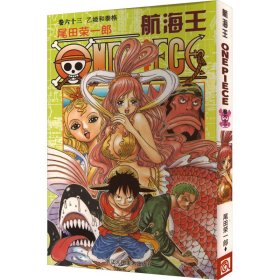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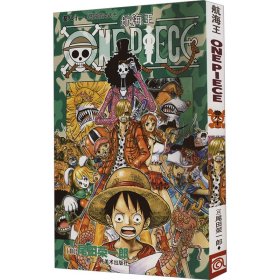

![合肥词钞(点校本) 历史古籍 [民国]李国模 辑李庆霞点校 新华正版](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baabeadc/e6a7593a8984208f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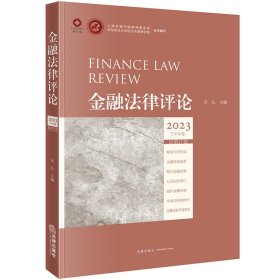
![统治阶级/人文与社会译丛/(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政治理论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 新华正版](/dist/img/error.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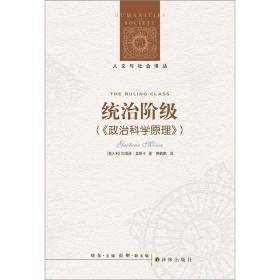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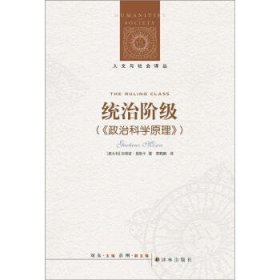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