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井中国 摄影作品 陈锦 著 新华正版
30年只做一件事,他用100000张照片把家乡还原成《清明上河图》,震惊摄影界,治愈无数寻乡的心
¥ 33.24 4.9折 ¥ 68 全新
库存9件
作者陈锦 著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26157
出版时间2017-03
版次1
装帧线装
开本16开
页数237页
字数220千字
定价68元
货号xhwx_1201490772
上书时间2023-12-1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有名摄影家肖全、胡武功、陈楠nanc影像家那松、李媚、陈小波倾情。有名摄影家肖全说:我才只看了几张照片来电了!
目录:
市井
蜀地
街坊
家事
赶场
生意经
市民玩
茶铺
戏班子
内容简介:
市井中国(20世纪末街巷里的流年影像)由中国有名摄影家陈锦扎根故乡,拍摄市井生活30年创作而成。记述了在大时代环境中个人的童年往事以及故乡的风俗家事。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曾经生活的地方已经消失、即将消失和仍然存在的中国老百姓们的常生活片断,在作者的镜头中、文字间,百姓的常生活方方面面丰富有趣,热情的街坊、家中的琐事、热闹的集市、攒动的茶铺,旧书店、字画摊、蜂窝煤、各家门前的腊肉腊肠,这些不仅是作者笔下的往时光,也是童年的集体记忆。作者用风趣、朴实的讲述方式,以自己的回忆为线索,加上极具现场感的黑白照片,让那段逝去的时光跃然纸上。本书为每一个还原了20世纪末期原汁原味的市井中国百姓生活,极为珍贵。治愈每一刻寻找乡愁的心灵。摄影家肖全说:我只看了几张照片来电了!
作者简介:
陈锦,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四川美术出版社编辑。陈锦老师扎根故乡,一个人行走30年,只做一件事,拍摄中国老百姓的常人生百态,用影像记录下20世纪末期一个原汁原味的市井中国。
精彩内容:
戏班子
几杯跟斗儿酒下肚,万国兵老师的“话匣子”打开了,只要话题是“川剧”,且摆且唱,言语滔滔像决了堤的洪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万老师曾经是一名颇有造诣的川剧武生演员, l952年从家乡宜宾来省城成都学艺,时年九岁,插班进入有名的川剧梨园三一宫的学徒班(万老师颇为自豪地称其为“黄埔期”),为徒七年,在严师曾绍明调教下练得一身扎实的基本功。那些年,川剧艺术占据着四川人娱乐生活的重要位置,作为川剧演员更是非常荣耀,社会地位高,走到哪里都受人追捧,学徒娃儿们享受着令同龄人十分羡慕的“三个四” 生活待遇,即每四餐饭,每月四次理发洗澡,每年四季衣装的配发……而且,还要学知识。但旧社会过来的曾绍明老师是没有读过书的,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连时钟都不会认。有一次,曾老师将时钟的长短针看反了,楞是把半夜二时三十五分认作凌晨六时十分,急忙将弟子们从酣梦中唤起,练功数小时仍不见天明……。当然,曾老师敬业爱岗受人尊敬,带学徒更是出了名的严厉,谁要不听招呼,或做了错事,是要被竹片打手板心的,若遇到顶不住打而抽手躲闪的,让你将手掌持于额前,再敢抽手,竹片下来会打在额头上,看你还敢不敢躲!
提起当年的情景,万老师两眼放光,跟斗儿酒一杯接一杯,在他看来,不论再苦再累甚至还挨竹片子,一概都是“过去的好子”,赞许怀念之意溢于言表——酒没了,意犹未竟,“掌柜的,再来一瓶” !
的确,川剧艺术曾一度融入巴蜀百姓的精神生活,听川剧、看川剧、唱川剧,成为*普及、*时尚的群众娱乐活动。清末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描绘:川人“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烈中亦自甘”,或“街上夜行,中好唱戏”,甚至“妇女好看戏,不怕被戏子看她”云云。至于川剧爱好者们相聚于街头院內、茶铺之中,摆弄起鼓板锣钹、唢呐胡琴等,清唱几段以过戏瘾,称之为“打围鼓”,或“吼玩友”,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自娱行为。玩友中有的熟谙音律,精研唱腔,还自编剧本;演艺高超者常客串演戏,人称“票友”,过去不少有名川剧艺人如浣花仙、贾培之、陈淡然等,都是从玩友再票友而后“下海”搞起专业来的。
万老师讲述了一则曾经发生在家乡宜宾与川剧有关的故事:旧社会军阀刘湘统治四川时期,宜宾的一个肖姓头子与当地驻军勾结串通,搞起了贩和军火的营生。后“东窗事发”,刘湘追查下来,驻军为推卸责任只能“丢卒保车”,将罪状算在了肖姓账上,被判了极刑。行刑之际,肖姓提出了一个条件:死可以,但要死得“漂亮”!不上绑插标,着戏装,扮作川剧《肖方杀船》中武生的模样,坐车游街演唱,以示自已仗义赴死,20年后又是好汉一条。当地驻军居然同意了这一滑稽的要求,那,黄包车上拉着一位扮花脸、着铠甲、手舞刀锏的死囚,招摇过市,沿途大唱川剧,与押送插科打浑,并不时向瞧热闹的人群行袍哥礼……这一旧时宜宾街头的“川剧秀”,想必深深地嵌在了老宜宾人的记忆里,而川剧艺术对于四川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地方戏曲,川剧有了数百年的历史,经历过与京剧、昆剧、秦腔、豫剧、越剧、黄梅戏等兄弟剧种并驾齐驱的辉煌岁月。追溯川剧艺术的源头,有来自两汉时期的“角觝百戏”,唐五代的“蜀戏”,以及宋元时代的“川杂剧”,明代的“川戏”等。明末清初,随着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带来了不同的地方戏曲种类,融汇入四川本土的民间曲调,创造出以“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为特的“川剧”艺术。可以说,川剧是汲取了各方戏曲的:其中昆腔,来自于昆曲;高腔,来自于江西的弋阳腔;胡琴,又分西皮和二黄,源于同属皮、黄系统的安徽徽调和湖北汉调;弹戏,则来自北方的梆子腔;惟有灯戏才是*地道的四川乡土音乐。五种声腔,五个源头,兼收并蓄,融汇贯通,趋向于地方化和民间化,成为川剧艺术的突出特点,能够在四川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的沃土中生根、开花、结果。
毕竟辉煌已成为过去,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红火了几个世纪的川剧艺术,受当代多元的冲击,显出了薄西山的颓势,各演出团体更是在自身的生存运作上举步维艰。那些省、市级国营川剧团,按他们自已的话讲:不演不亏,越演越亏。排练演出吧,售出的戏票不足以抵销各项费用开支,要想凭借演出经营来解决团里数十、上百人的生存之需,纯属“天方夜谭”,只能依靠出钱养着,逢年过节拉出来充充门面、应应景罢了。但是,对于那些纯民间的川剧戏班子来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的生死存亡完接近全得由演出市场所决定。
数年前,万国兵老师从国营川剧团退了休,如今做起私营的“望江川剧团”的班主(老板)。
出于对川剧艺术的热爱,在妻子女儿的鼎力支持下,倾其家中积蓄,于年前“盘下”(即收购)了该剧团,经营一月有余。说起这一月来的艰辛,万老师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每有二百多观众看戏,像春节这些天,每人收三元钱(带茶一碗),除去其中属于剧场的一元茶钱,剩下六百多元,正好是当天各项费用之和(全团二十几号人的工资和场租水电、化妆品消耗等),若是时观众少些,只好倒贴了。他说:想赚钱别搞川剧,只因这辈子与川剧结了缘,钱拿来做啥?做点自已喜欢的事情,虽然难些,心里头却是衡坦荡的。
据我所知,万老师执掌“望江”之前,已不知易手过多少位班主了,短则二、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会有新旧班主的更迭。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改作:“铁打的剧团,流水的班主。”舞台还是这座舞台,甚至演员还是这群演员,只是老板換了。记得住我楼下的川剧爱好者焉大爷,曾与他人合伙入主过“望江”,开张那天还请我为“镇台”仪式拍过照哩!但终因持续的收不抵支,*初的万丈豪情化为后来的唏嘘哀叹,不得不“拆漂”(即退出)。好在会有如万国兵老师一样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将他们心目中视为神圣的川剧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那天,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万老师对戏班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像做父亲的对自已儿女的未来是寄予着厚望。他自言自语道:“开春了,气候转暖,观众会多起来的”!
如果说一个民间戏班无论班主怎样換,还能在一处一地长期驻扎生存下去,应该是相当不容易的事;那么,那些在实力上根本不能与“三大班子”相比肩的小戏班子,要想从有限的川剧市场中“分一杯羹”,不得不跑江湖似的(好像赶着大蓬车队的吉普赛人),靠不停地流动去寻觅属于自已的观众群:市井茶铺,乡村庙会,甚至民间举办红白喜事等,都成为了他们的临时舞台,这类的小戏班子被同行们称之为“火把戏班”。
所谓“火把戏班”,应该有两重含义:
其一:历民间川剧戏班根据自身条件划分为三六九等,实力雄厚的可以有象样的舞台(比如过去的“悦来”,如今的“望江”等)、齐备的道具和光鲜的服装行头,演出阵容也够威风气派;而一般小戏班子则显得寒酸得多,他们四海为家,凡事因陋简,虽不至用油灯、火把作演出照明(没准儿也用过),在硬件和软件(演员的名头和演出经验等)配备上,同那些大戏班相比自然是天上人间,因此,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戏班子以土哩巴叽的“火把”冠之,确也恰如其份。
其二:民间川剧戏班的生存,遵循所谓的“三自”原则:即(演员)自由组合,(班主)自负盈亏,(戏班与戏班之间)自由竞争,一句话,自生自灭。当然,是生是灭,*终都由演出市场所决定。一般小戏班子往往以城镇边缘、尤其是广大农村作为自已的活动空间,受历自然经济的影响,一年中演出市场也有“旺”“淡”之分:温暖适宜的气候,传统节期间,乡村农闲时,人们有功夫有心情看戏,属“旺”季,届时戏班组成也多,演员的收入尚可;遇严寒酷暑,或农事吃紧,演出市场进入了“淡”季,戏班经营入不敷出,许多戏班只好打烊,演员们要么回家“赋闲”,以待下一个“旺”季的来临,要么另谋生路。这种受外界因素制约而“旺”聚 “淡”散的现象,好比是火把的明灭,成为大多数小戏班子的运作规律,所以,这些戏班被称为“火把戏班”,演员上戏又叫作“唱火把”,多少还有些嘲弄的意味。
不过,“火把”戏班也在残酷的竞争中淌出了一条自已的生存之道:
比如,一个戏班要想在某地呆上一年,365天里均得演365出戏(大幕戏可几天演一出,折子戏则要演2至3折),对于非专业水准的“火把”班子来说有些勉为其难,如果将己经演过的剧目原封不动地搬上戏台,叫作“炒陈饭”,观众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这条应该做到“剧目要变”,即不断推出新戏以吸引观众,既便再上曾经演过(或别的戏班演过)的戏,名称都不能重复(如《双花配》又可叫《粉河湾》,《钓金龟》又可叫《判双钉》等),凭着演员的演出经验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在不违背原剧宗旨的基础上对剧情进行新的演绎,同一出戏不会有相同的翻板。第二条叫作“演员要换”。大凡“火把”戏班的人员配备不会超过二十人,其中真能上得了台面的演员不过三五个,但观众也有喜新厌旧心理,如果戏台上主唱的是那几付老面孔,久必要生厌,要想稳住观众群,得“新陈代谢”,吸纳一些新演员,甚至偶尔花重金请个把“名角”扎场子(临时演上一、二场),行內人称“请味精”。别说是“火把”戏班了,连“望江”这类大戏班子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万国兵老师从温江川剧团请来他的“师兄弟”肖方云,专演自已*辣手的保留剧目《巴九寨》。这《巴九寨》是川剧剧目中有名的袍哥戏,风格诙谐幽默,尤其是其中的“展言子儿”(说话时带出一些风趣的谚语、歇后语)功夫,充分表现出四川方言的语言特。据说该剧没有剧本,全凭言传身教和临场即兴发挥而流传下来。肖方云老师真是得了该剧的真传,将个角演绎得栩栩如生,精采的台词从他中连珠炮似地喷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还有一条叫作“剧团要转” 。借用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戏班子要想生存,要着眼于未来,不断开劈新的演出市场,别等着演“死了”才去虑换场子,所以感觉差不多时得派出人去“跑台儿”(即联系新的演出场地),让戏班在运动中争取更多的观众。我曾经开车带着我的朋友、“蓉艺川剧团”的班主王亮,从什邡洛水前往金堂赵镇联系新的演出场地,亲身经历过戏班子跑台儿换台儿的整个过程。
认识王亮还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那年他刚满二十岁,己经在后来成为岳父大人的李官禄组建的“成都市蓉艺川剧团”唱了好几年的生角戏了。后来年事渐高的李官禄老师退居 “二线”,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交到了女婿王亮和女儿李琪英的手中。那在“望江”邂逅了前来会朋友的王亮,我与他已是好几年未曾谋面,有一种故人久别重逢的感觉,一阵热烈的寒暄问候之后,得知他的戏班正在广汉金轮镇的包公庙里唱台儿(即搭台演出),他特意叮嘱我抽时间前去“捧场”。
从成都去金约有五十余公里的路途,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金灿灿的阳光照着初春的川西原,田野间一片新绿,早播的油菜籽迫不及待地绽出了星星点点黄的花蕾。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曾形容过:川西原虽无秋高气爽之辉煌,却有春光明媚之灿烂。每年从正月间到三月的清明,象白云一样飘浮在农舍林盘的是梨花和李花,象朝霞一样簇拥在地头天边的是桃花,而油莱花更象一张金黄的地毯覆盖着整个川西大地,微风吹过,阵阵清香引来了蜂忙蝶舞,游人如织,尽皆沉醉于纵横阡陌之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川剧演出按传统称呼叫作唱“春台戏”,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深受父老乡亲们的欢迎。当我到达金轮镇的时候,演出还未开始,包公庙院坝里己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了,粗约估计,少说也有千把观众,庙门外还不断涌来如潮的人流,与时下城市中戏剧舞台冷清寥落的情景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令我好一阵感慨!
近几年中,王亮的戏班虽也是有聚有散,但“蓉艺川剧团”的大旗始终不倒。此次来金轮镇唱“春台”,剧团成员大多是些新面孔,但我也能从中认出了李官禄老师和他的老伴,还有王亮的夫人李琪英,和他们的已经快要长大的三个女儿:娜娜、莎莎和婷婷。李老师快七十岁高龄了,依然还在唱戏,仅管将剧团的经营权传给了下一代,作为川剧人,必须保持时常地活在剧情之中,生命才有意义,因此是离不开戏台的,更何况剧团在艰难时刻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剧团也离不开他。这不,连他的三个小孙女也能在戏台上扮演角、串串“吼板儿”(即跑龙套,或叫作 “当差儿”)什么的。
谁说他们不是一个兴旺的川剧“世家”呢?风雨飘摇中的川剧事业似乎后继有人。
王亮李琪英夫妇的三个千金中,娜娜十六岁了,初中后无心读书,做父毌的怕她混迹于社会学坏,将她带在身边,帮助料理一些戏班杂务,戏票,演出需要时也上台串串“吼板儿”;莎莎快满十四岁,与九岁的小妹婷婷都还在上学,在家由外婆照管,遇期便跟随父毌在戏班住上一阵。这些孩子都是伴着川剧的锣鼓声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下对川剧和川剧人的生活有不同于他人的特殊的感受,按常规他(她)们后走上川剧之路顺理成章,过去不少川剧人,尤其是民间川剧演员,命运大多如此。当孩子们还是幼童时,被大人安排在剧情中扮演些小角,他(她)们一方面觉得“好玩”,另一方面在幼稚的心灵上多少可以满足一点面对同龄人时的小小的虚荣。不过,娜娜已经不小了,仅管现在有些无奈地被拴在了父母身边,作为新新人类,会有自己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和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未来的梦想。
在包公庙戏台的幕后,我与化好了妆、正搭拉着脸儿等待上戏的娜娜聊了起来,从她那里了解些戏班的近况,并随意地问她是不是也准备学唱戏,将来好续接家族的戏剧事业呢?谁知娜娜竟用了一种宣言般的吻、不思索地回答我:“打死也不学唱戏”!语气斩钉截铁令闻者愕然。
这天散戏后王亮一家盛情挽留我共进晚歺,饭桌上却不见娜娜和莎莎两姊妹,我询问一直依偎在母亲身旁的小婷婷:姐姐们去哪里了?她告诉我,被新认识的小伙伴们带到镇上的网吧“聊天”去了。
有一次去德阳探望正在“旌阳影剧院”唱台儿的王亮戏班,正赶上农历端午节,按照传统,他们演出了古装大幕戏《白蛇传》的本。据说端午节上演《白蛇传》是能够除秽的,与民间用艾蒿、菖蒲等草药熬水给小孩子洗澡,生疮痍,大人们喝雄黄酒去病避毒,具有同样的功效。
演出结束后的晚饭是端午节的团圆饭,由班主王亮夫妇“宴请”全体演职人员及随行家小(时戏班中人都是以“家”为单位自行开伙)。管服装道具兼串“吼板儿”的大娃子担任掌勺师傅,有卤鸡板鸭、盐蛋皮蛋、四季豆扁豆、红苋菜、粽子和香水鱼……,在剧场侧的院坝中摆起了三大桌。虽然没有雄黄酒,正好打开我捎去的瓶庄老窖,戏班上下二十几号人热热闹闹、心满意足地边吃边聊起来。酒过三巡,大家的谈锋从—些逸闻趣事、生活琐碎自然而然地转到明天将要演出的《白蛇传》第二本上,吃喝间又开始了即兴排练,并时不时在对剧情的理解和把握上展开激烈争论,甚至还会因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搞得个面红耳赤。
一般来说,那些吃饭的“专业”剧团或“望江”类的有固定演出场所的大戏班,上一出新戏前得进行专门的排练,要求演员对剧情有熟练把握,经“彩排”通过后才能正式演出。“火把”戏班不同了,演出地点的不稳定和演员频繁流动,生活和工作无规律可循,不允许事事按部班,太强了,因此,上新戏前大家只能挤时间找空隙凑一凑:饭桌上、麻将桌上、化妆台前……,都可能成为排练场所,叫作“、生产两不误”;剧情不熟练没关系,还可以一边说戏一边演出,甚至专门有人躲在帷幕后为前台演出的演员提醒台词,所以演员们也都练了一身临场应变的功夫。再则,历川剧艺术划分为不同流派,比如以成都为中心的 “川西坝派”,以南充为中心的 “川北河派”,以资中、资阳为中心的 “资阳河派”,以重庆为中心的 “下川东派”等等,各个流派都有自已辣手的剧目,既便同一剧目,流派间在表演技艺上又都各不相同。更何况“火把”戏班的演员来自于各个地区,分别受到不同流派的影响,演出前对剧目不做协调统一,这戏演不下去。记得正月初九包拯包大人的生那天,王亮戏班在金轮包公庙里演出包公戏《四下河南》,据说该戏有多个本子,演出套路各异,只好在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协调,于是,有了前台一边演着、后台一边练着(旋排旋演)的情形。排练时的争论是正常的,但戏班里跑龙套的老演员尹红与唱旦角的刘佐香却因各持已见在后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戏”:尹红是个火爆脾气、急子人,言语中时有顶撞;刘佐香又是戏班里的当家花旦,难流露出凌人盛气,几句话不中听两人便吵闹起来,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声音一个比一个大,骂出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生活中舞台上能够想得到骂得出的丑话脏话全都用上了。后来骂已经不解气,更加之以拳脚。先是尹红要去掀翻刘佐香夫妇搭在后台的床铺,刘佐香当然不依,便上前抓扯,尹红毕竟年纪大些,手脚上显然落了下风,情急中竟拾起半截砖头砸向刘佐香,所幸不曾击中……。这场因说戏而导致的“战争”当然只局限于后台,前台的戏依然演着,铿锵的锣鼓声会盖过了烦扰。在大家的规劝下,几分钟内风波逐渐息,尹红和刘佐香照样上台演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很快便融入了剧情。
《四下河南》讲的是被恶霸与官府勾结逼死了丈夫的寡妇赵田氏,领着一对儿女从四川历尽艰辛“四下河南”开封府,找包青天申冤雪仇的故事。其中赵田氏由刘佐香饰演,一个苦命而倔强的女形象被她演绎得维妙维肖,真情所至,无论低唱浅吟,抑或呼天地,字字捣人肺腑,声声摧人泪下,搅得台上台下一片呜咽之声。这种演员与观众真情互动的情形,在所谓 “专业”剧团的演出中恐怕是比较少见了。如果说那些吃饭的“专业”川剧演员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熟练的演唱,能够在表演中以技动人的话,那么,这些“在野”的民间川剧艺人,将自己的身世感受融入剧情,以真实、质朴、自然的表演奉献于观众,是能够以情感人的。
民间川剧演员们很努力,喜爱川剧艺术的观众也很捧场,但整个戏剧市场急剧萎缩却是谁也无迴避的现实,能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硬撑起民间戏班的大旗不倒,无疑是做了一桩天大的“善事”。像万国兵、王亮……以及许许多多有理想有追求的川剧人,他们的努力未必換得来川剧艺术的复兴。
…………
那一年的夏季尤其酷热难当,由白玉清师傅组伙的“安岳川剧团”正在成都郊区的白家茶铺唱台儿。号为“剧团”,从班主、演员到敲锣打鼓的共十三人,小得不能再小了,这么个阵容,照样上演传统大幕戏《白蛇传》。这天我和一位朋友下午准二时来到了这里,正好是常规的开演时间。演员们己经化好妆候在后台,开场锣鼓敲了一遍又一遍。但一直待到二时半钟还不见演员出场,我有些纳闷:等什么呢?环顾四周,台上锣鼓虽敲得热闹,但台下百多方米的堂子里,算上我和我的同伴,共才二十位观众。难怪!寻思中,那个反串饰演“青蛇”的小伙子赵兵走上了前台,向着观众席一抱拳,然后道:“各位老辈子,对不住了……”!意思是观众太少,收到的看戏钱不足以支付演出的费用(“火把”戏班演员的收入通常按演出场次支付,不演则没有),要么大家再凑些,要么不演了。
一个戏班里演员还是要分主次的,水高的饰重要角,收入也高出其他。所演《白蛇传》中以饰白娘子、许仙、海和尚的为主要演员,按时下行情,一次不低于十五元币,三个十五是四十五元。可仅二十位观众,每位交三元钱,其中五角为茶铺老板的茶叶钱,剩下二元五角才是戏班的收入。二十个二元五角也五十元,除去几元钱的戏台照明等杂项开支,既便够上了三位主要演员的薪水,戏班的其他人岂不是只能喝西北风?再瞧瞧台下这些观众,大多是七老八十的婆婆爷爷们,他(她)们虽然对川剧艺术的热爱痴心不改,但都不是经济上宽裕的主,如何能够承担这份本不应该承担的追加费用呢?
僵持的场面令人难堪,台上台下近五分钟几无声息。眼见着大家都对结局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赵兵终于又出现在台前,他按捺不住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感谢吴金贵老师帮补了不足的费用,的演出马上开始,不好意思让各位等久了”。——吴金贵老先生,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数出了四十五元钱,解决了主要演员的出场费用。
开场锣鼓又一次敲响,的戏终于开演了。
但明天呢?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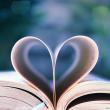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