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啼笑因缘 情感小说 张恨水 新华正版
“通俗文学大师人”张恨水之作,富家子弟与民女子、部长千金、江湖侠女的爱情纠葛。
¥ 27.55 5.6折 ¥ 49 全新
库存3件
作者张恨水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38554
出版时间2019-0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440页
字数400千字
定价49元
货号xhwx_1201893394
上书时间2022-12-3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啼笑因缘是“通俗文学大师人”张恨水之作,富家子弟与民女子、部长千金、江湖侠女的爱情纠葛。啼笑因缘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时代特,流传广泛,意义深远。张恨水的文字清新纯朴,行云流水,自有一番风格。啼笑因缘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人物真实鲜明,饱满立体。
目录:
序
李浩然题词 蝶恋花 并序
一九三○年严独鹤序
一九三○年作者自序
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第二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
第三回 颠倒神思书中藏倩影 缠绵情话林外步朝曦
第四回 邂逅在穷途分金续命 相思成断梦把卷凝眸
第五回 颊有残脂风流嫌著迹 手加约指心事证无言
第六回 无意过香巢伤心致疾 多情证佛果俯首谈经
第七回 值得忘忧心头天上曲 未遗憾局外画中人
第八回 谢舞有深心请看绣履 行歌增别恨拨断离弦
第九回 星野送归车风前搔鬓 歌场寻俗客雾里看花
第十回 狼子攀龙贪财翻妙舌 兰闺藏凤炫富蓄机心
第十一回 竹战只攻心全局善败 钱魔能作祟彻夜无眠
第十二回 比翼羡莺俦还珠却惠 舍身探虎穴鸣鼓怀威
第十三回 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
第十四回 早课欲疏重来怀旧雨 晚游堪乐小聚比秋星
第十五回 柳岸感沧桑翩鸿掉影 桐荫听夜雨落木惊寒
第十六回 托迹权门姑为蜂蝶使 寻盟旧地喜是布衣交
第十七回 裂券飞蚨绝交还大笑 挥鞭当药忍痛且长歌
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 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
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楼作别 模糊留血影山寺锄奸
第二十回 辗转一封书红丝误系 奔波数行泪玉趾空劳
第二十一回 艳舞媚华筵名姝遁世 寒宵飞弹雨魔窟逃生
第二十二回 绝地有逢时形骸终隔 圆场念逝者啼笑皆非
一九三○年作者《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
啼笑因缘续集
一九三三年续集作者自序
回 雪地忍衣单热衷送客 山楼苦境寂小病留踪
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归谒老父 庄谐并作小宴闹冰人
第三回 种玉来迟解铃甘谢罪 留香去久击案誓忘情
第四回 借鉴怯潜威悄藏艳迹 移花弥缺憾愤起起茵
第五回 金屋蓄痴花别具妙计 玉人作赝鼎激走情俦
第六回 借箸论孤军良朋下拜 解衣示旧创侠女重来
第七回 伏枥起雄心倾家购弹 登楼记旧事惊梦投怀
第八回 辛苦四年经终成泡影 因缘千里合同拜高堂
第九回 尚有人缘高朋来旧邸 真无我相急症损残花
第十回 壮士不还高歌倾别酒 故人何在热血洒边关
内容简介: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拥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啼笑因缘讲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江南富家子弟樊家树进京,与天桥大鼓书女艺人沈凤喜一见钟情,倾心相爱。军阀刘将军看中沈凤喜,逼她为妾。沈凤喜在其威逼利诱下屈从。书中穿插樊家树与民侠女关秀姑、北洋长千金何丽娜的情感纠葛。
作者简介:
作者张恨水是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张心远,1895年5月18生于江西广信。他是中国章回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目前的“章回小说大家”。
精彩内容:
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已失去那“首善之区”四个字的尊称。但是这里留下许多的建筑,和很久的,依然值得留恋。尤其是气候之佳,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三百六十,除了少数子刮风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气。论到下雨,街道泥泞,房屋霉湿,久不能出门一步,是南方人苦恼的一件事。北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这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场雨,一雨之后,马上晴,云净天空,尘土不扬,满城的空气,格外新鲜。北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尽管小,院子必定大,“天井”二字,是不通用的。因为家家院子大,到处有树木。你在雨雾之后,到西山去向下一看旧京,楼台宫阙,都半藏半隐,夹在绿树丛里,觉得北方下雨是可欢迎的了。南方怕雨,怕的是黄梅天气。由旧历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几乎天天是雨。可是北呢,依然是天晴,而且这边的温度低,那个时候,刚刚是海棠开后,杨柳浓时,正是时代。不喜游历的人,此时也未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园了。因为如此,别处的人,都等到四月里,北各处的树木绿遍了,然后前来游览。在这个时候,有个很会游历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游历来了。
这是北京未改北的前三年,约莫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个很精致的上房里。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条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绒球一般,一串一串,在黄的叶丛里下垂着。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这位青年樊家树,靠住了一根红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把站在花上的蜜蜂,甩了开去,又飞转来,很是有趣。他手上拿了一本打开而又卷起来的书,却背了手放在身后。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振动的声音,嗡嗡直响。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家树觉得很适意,老是站了不动。这时,过来一个听差对他道:“表少爷!是礼拜,怎么你一个人在家里?”家树道:“北京的名胜,我都玩遍了。你家大爷、奶昨天下午要我到西山去,我是前天去过的,不愿去,所以留下来了。刘福,你能不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刘福笑道:“我们大爷要去西山,是有规矩的,礼拜六下午去,礼拜一早上回来。这一次你不去,下次他还是邀你。这是外国人这样办的,不懂我们大爷怎么也学上了。其实,到了礼拜六、礼拜,戏园子里名角儿露了,电影院也换片子,正是好玩。”家树道:“我们在上海租界上住惯了那洋房子,觉得没有中国房子雅致。这样好的院子,你瞧,红窗户配着白纱窗,对着这满架的花,像图画一样,在家里看看书也不坏。”刘福道:“我知道表少爷是爱玩风景的。天桥有个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树道:“天桥不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吗?”刘福道:“不,那里四围是水,中间有花有亭子,还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清唱。”家树道:“我怎样从没听到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刘福笑道:“我决不能冤你。那里也有花棚,也有树木,我爱去。”家树听他说得这样好,便道:“在家里也很无聊,你给我雇一辆车,我马上去。现在去,还来得及吗?”刘福道:“来得及。那里有茶馆,有饭馆,渴了饿了,都有地方休息。”说时,他走出大门,给樊家树雇了一辆人力车,让他一人上天桥去。
樊家树常出去游览,都是这里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游玩一番,比较的痛快,也不嫌寂寞,坐着车子直向天桥而去。到了那里,车子停住,四围乱哄哄地,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在自己面前,一路是三四家木板支的高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给了车钱,走过去一看,门楼边牵牵连连,摆了许多摊子。以自己面前而论,一个大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黑块中放了两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大概是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又一个摊子,是地放了一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皮的死蛇,盘满在锅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家树皱了一皱眉头,转过身去一看,却是几条土巷,巷子两边,全是芦棚。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出名的估衣街了。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巷上,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铜铁器。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店,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片黑泥浆,流着蓝的水,臭气熏人。家树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之胜,当然不在这里。又回转身来,走上大街,去问一个警察。警察告诉他,由此往南,路西便是水心亭。
北京城是个四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人家的住房,也是四方的四合院。所以到此的人,无论老少,都知道四方,谈起来不论上下左右,只论东西南北。当下家树听了警察的话,向前直走,将许多芦棚地摊走完,便是一片旷野之地。马路的西边有一道水沟,虽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沟那边,稀稀的有几棵丈来长的柳树。再由沟这边到沟那边,不能过去。南北两头,有两架板木桥,桥头上有个小芦棚子,那里摆了一张小桌,两个警察守住。过去的人,都在桥这边掏四个铜子,买一张小红纸进去。这样子,是买票了。家树到了此地,不能不去看看,也掏了四个子买票过桥。到了桥那边,地上挖了一些水坑,里面种了水芋之属,并没有花园。过了水坑,有五六处大芦棚,里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个棚子里都有一台杂耍。所幸在座的人,还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气味。穿过这些芦棚,又过一道水沟,这里倒有一所浅塘,里面新出了些荷叶。荷塘那边,有一片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绿树,树下一个倭瓜架子,牵着一些瓜豆蔓子。那木屋是用蓝漆漆的,垂着两副湘帘,顺了风,远远的听到一阵管弦丝竹之声。心想:这地方多少还有点意思,且过去看看。
家树顺着一条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开,对了先农坛红墙,一丛古柏,屋子里摆了几十副座头,正北有一座矮台,上面正有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里坐着,依次唱大鼓书。家树本想坐下休息片刻,无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满了,于是折转身走回来。所谓“水心亭”,不过如此。这种风景,似乎也不值留恋。先是由东边进来的,这且由西边出去——过去却见一排都是茶棚。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解的,有摔跤的,有弄技的,有说相声的。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也围住一圈人。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会俱乐部。北方一个土墩,围了一圈人,笑声烈。家树走上前一看,只见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块破蓝布,脏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蓝布下一张小桌子,有三四个小孩子围着打锣鼓拉胡琴,蓝布一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黑汉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长衫,拦腰虚束了一根草绳,头上戴了一个烟卷纸盒子制的帽子,嘴上也挂了一挂黑胡须。其实不过四五十根马尾,他走到桌子边一瞪眼,看的人叫好。他一伸手摘下胡子道:“我还没唱,怎么样叫起好来?胡琴赶来了,我来不及说话。”说着马上挂起胡子又唱起来。大家看见,自是一阵笑。
家树在这里站着看了好一会儿,觉得有些乏,回头一看,有一家茶馆,倒还干净,踏了进去,找个座位坐下。那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条,上面大书一行字:“每位水钱一枚。”家树觉得很便宜,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过的茶馆了。走过来一个伙计,送一把白瓷壶在桌上,问道:“先生带了叶子没有?”家树答:“没有。”伙计道:“给你沏钱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龙井?”这北京人喝茶叶,不是论分两,乃是论包的。一包茶叶,大概有一钱重。常是论几个铜子一包,又简称几百一包。一百是一个铜板,茶不分名目,窨过的茶叶,加上茉莉花,名为香片。不曾窨过,不加花的,统名之为“龙井”。家树虽然是浙江人,来此多,很知道这层缘故。当时答应了“龙井”两个字,因道:“你们水钱只要一个铜子,怎样倒花了四个铜子茶叶给人喝?”伙计笑道:“你是南边人,不明白。你自己带叶子来,我们只要一枚。你要是吃我们的茶叶,我们还只收一个子儿水钱,那非老娘不可了。”家树听他这话,笑道:“要是客人都带叶子来,你们全只收一个子儿水钱,岂不要大赔钱?”伙计听了,将手向后方院子里一指,笑道:“你瞧!我们这儿是不靠水的。”
家树向后院看去,那里有两个木架子,插着许多样武器,胡乱摆了一些石礅石锁,还有一副千斤担,院子里另外有重屋子,有一群人在那里品茗闲谈。屋子门上,写了一副横额贴在那里,乃是“以武会友”。在这个时候,有人走了出来,取架子上的武器,在院子里练练。家树知道了,这是一班武术家的俱乐部。家树在学校里,本有一个武术教员教练武术,向来对此感到有些趣味,现在遇到这样的俱乐部,有不少的武术可以参观,很是欢喜。索将座位挪了一挪,靠近后院的扶栏,先是看见有几个壮年人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刀棍,后走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横腰系了一根大板带,板带上挂了烟荷包小褡裢,下面是青布裤,裹腿布系靠了膝盖,远远的一摸胳膊,精神抖擞。走近来,见他长长的脸,一个高鼻子,嘴上只微微留几根须。他一走到院子里,将袖子一阵卷,先站稳了脚步,一手提着一只石锁,颠了几颠,然后向空中一举,举起来之后,望下一落,一落之后,又望上一举。看那石锁,大概有七八十斤一只,两只一百几十斤。这向上一举,还不怎样出奇,只见他双手向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起,那石锁飞了出去,直冲过屋脊。家树看见,先自一惊,不料那石锁刚过屋脊,照着那老人的头顶,直落下来,老人脚步动也不曾一动,只把头微微向左一偏,那石锁稳稳落在他右肩上。同时,他把左手的石锁抛出,也把左肩来承住。家树看了,不由暗地称奇。看那老人,倒行所无事,轻轻地将两只石锁向地下一扔,在场的一班少年,于是吆喝了一阵,还有两个叫好的。老人见人家称赞他,只是微微一笑。
这时,有一个壮年汉子,坐在那千斤担的木杠上笑道:“大叔,你很高兴,玩一玩大家伙吧。”老人道:“你先玩着给我瞧瞧。”那汉子果然一转身双手拿了木杠,将千斤担拿起,慢慢提起,齐了双肩,咬着牙,脸红了。他赶紧弯腰,将担子放下,笑道:“乏了,更是不成。”老人道:“瞧我的吧。”走上前,先了手,将担子提着了腹,顿了一顿,反着手向上一举,了下颏,又顿了一顿,两手伸直,高举过顶。这担子两头是两个大石盘,仿佛像两片石磨,木杠有茶杯来粗细,插在石盘的中心。一个石磨,至少也有二百斤重,加上安在木杠的两头,更是吃力。这一举起来,有五六百斤气力,才可以对付。家树不由自主的拍着桌子叫了一声:“好!”
那老人听到这边的叫好声,放下千斤担,看看家树,见他穿了一件蓝湖绉夹袍,在大襟上挂了一个自来水笔的笔插。白净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边圆框眼镜,头上的头发虽然分齐,却又卷起有些蓬乱,这分明是个贵族式的大学生,何以会到此地来?不又看家树两眼。家树以为人家是要招呼他,站起来笑脸相迎。那老人笑道:“先生,你也爱这个吗?”家树笑道:“爱是爱,可没有这种力气。这个千斤担,亏你举得起。贵庚过了五十吗?”那老人微笑道:“五十几?——望来生了!”家树道:“这样说过六十了。六十岁的人,有这样大力气,真是少见!贵姓是……”那人说是姓关。家树便斟了一杯茶,和他坐下来谈话,才知道他名关寿峰,是山东人,在京以做外科大夫为生。便问家树姓名,怎样会到这种茶馆里来,家树告诉了他姓名,又道:“家住在杭州。因为要到北京来大学,现在补功课。住在东四三条胡同表兄家里。”寿峰道:“樊先生,这很巧,我们还是街坊啦!我也住在那胡同里,你是多少号门牌?”家树道:“我表兄姓陶。”寿峰道:“是那红门陶宅吗?那是大宅门啦,听说他们老爷太太都在外洋。”家树道:“是,那是我舅舅。他是一个领事,带我舅母去了。我的表兄陶伯和,现在也在有差事。不过家里还可过,也不算什么大宅门。你府上在哪里?”寿峰哈哈大笑道:“我们这种人家,哪里去谈‘府上’啦?我住的地方,是个大杂院。你是南方人,大概不明白什么叫大杂院。这是说一家院子里,住上十几家人家,做什么的都有。你想,这样的地方,哪里安得上‘府上’两个字?”家树道:“那也不要紧,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我也很喜欢谈武术的,既然同住在一个胡同,过过去奉看大叔。”
寿峰听他这样称呼,站了起来,伸着手将头发一顿乱搔,然后抱着拳连拱几下,说道:“我的先生,你是怎样称呼啊?我真不敢当。你要是不嫌弃,哪我去拜访你去。”又道:“说到练把式,你要爱听,那有的是……”说时,一拍肚腰带道:“可千万别这样称呼。”家树道:“你老人家,不过少几个钱,不能穿好的,吃好的,办不起大事,难道为了穷,把年岁都丢了不成?我今年只二十岁,你老人家有六十多岁,大我四十岁,跟着你老人家同行叫一句大叔,那不算客气。”寿峰将桌子一拍,回头对在座喝茶的人道:“这位先生爽快,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少爷们。”家树也觉着这老头子很爽直,又和他谈了一阵,因已落西山,给了茶钱回家。
到了陶家,那个听差刘福进来伺候茶水,便问道:“表少爷,水心亭好不好?”家树道:“水心亭倒也罢了,不过我在小茶馆里认识了一个练武的老人家谈得很好。我想和他学点本事,也许他明后天要来见我。”刘福道:“唉!表少爷,你初到此地来,不懂这里的情形。天桥这地方,九流三教,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怎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家树道:“那要什么紧!天桥那地方,我看虽是下等社会人多,不能说那里没有好人,这老头子人极爽快,说话很懂情理。”刘福微笑道:“走江湖的人,有个不会说话的吗?”家树道:“你没有看见那人,你哪里知道那人的好坏?我知道,你们要看见坐汽车带马弁的,那才是好人。”刘福不敢多事辩驳,只得笑着去了。
到了次上午,这里的主人陶伯和夫妇,已经由西山回来。陶伯和在上房休息了一会,赶着上衙门。陶太太又因为上午有个约会,出门去了。家树一个人在家里,也觉得很是无聊,心想既然约会了那个老头子要去看看他,不如趁无事,了却这一句话,管他是好是坏,不可失信于他,得他说我瞧不起人。昨天关寿峰也曾说到,他家住在这胡同东,一个破门楼子里,门有两棵槐树,是很容易找的。于是随身带了些零碎钱,出门而去。
走到胡同东,果然有这样一个所在。他知道北京的规矩,无论人家大门是否开着,先要敲门才能进去的。因为门上并没有什么铁环之类,只啪啪的将门敲了两下。这时出来一个姑娘,约莫有十八九岁,挽了辫子在后面梳着一字横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刘海,一张圆圆的脸儿,穿了一身的青布衣服,衬着手脸倒还白净,头发上拖了一根红线,手上拿了一块白十字布,走将出来。她见家树穿得这样华丽,便问道:“你找谁?这里是大杂院,不是住宅。”家树道:“我知道是大杂院,我是来找一个姓关的,不知道在家没有?”那姑娘对家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我姓关,先生你姓樊吗?”家树道:“对极了。那关大叔……”姑娘连忙接住道:“是我父亲。他昨天晚上一回来提起了。现在家里,请进来坐。”说着便在前面引导,引到一所南屋子门叫道:“爸爸快来,那位樊先生来了。”寿峰一推门出来了,连连拱手道:“哎哟!这还了得,实在没有地方可坐。”家树笑道:“不要紧的。我昨天已经说了,大家不要拘形迹。”关寿峰听了,便只好将客向里引。
家树一看屋子里面,正了一幅关羽神像的画,一张旧神桌,摆了一副洋铁五供,壁上随挂弓箭刀棍,还有两张獾子皮。下边一路壁上,挂了许多一束一束的干药草,还有两个干葫芦。靠西又一张四方旧木桌,摆了许多碗罐,下面紧靠放了一个泥炉子。靠东边陈设了一张铺位,被褥虽是布的,却还洁净。东边一间房,挂了一个红布门帘子,那红也半成灰了。这样子,父女二人,是这两间屋了。寿峰让家树坐在铺上,姑娘进屋去捧了一把茶壶出来。笑道:“真是不巧,炉子灭了,到对过小茶馆里找水去。”家树道:“不必费事了。”寿峰笑道:“贵人下降贱地,难道茶都不肯喝一?”家树道:“不是那样说,我们交朋友,并不在乎吃喝,只要彼此相处得来,喝茶不喝茶,那是没有关系的。不客气一句话,要找吃找喝,我不会到这大杂院里来了。没有水,不必张罗了。”寿峰道:“也好,不必张罗了。”
这样一来,那姑娘捧了一把茶壶,倒弄得进退两难。她究竟觉得人家来了,一杯茶水都没有,太不成话,还是到小茶馆里沏了一壶水来了。找了一阵子,找出一只茶杯,一只小饭碗,斟了茶放在桌上,然后轻轻地对家树道:“请喝茶!”自进那西边屋里去了。寿峰笑道:“这茶可不必喝了。我们这里,不但没有自来水,连甜井水都没有的。这是苦井的水,可带些咸味。”姑娘在屋子里答道:“不,这是在胡同上茶馆里沏来的,是自来水呢。”寿峰笑道:“是自来水也不成。我们这茶叶太坏呢!”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家树已经捧起茶杯喝了一,笑道:“人要到哪里说哪里话,遇到喝咸水的时候,自然要喝咸水。在喝甜水的时候,练练咸水也好。像关大叔是没有遇到机会罢了,若是早生五十年,这样大的本领,不要说做官,是到镖局里走镖,也可顾全衣食。像我们后生,一点能力没有,靠着祖上留下几个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没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咸水的心安。”说到这里,只听见扑通一下响,寿峰伸开大手掌,只在桌上一拍,把桌上的茶碗都溅倒了。昂头一笑道:“痛快死我了。我的小兄弟!我没遇到人说我说得这样中肯的。秀姑!你把我那钱袋拿来,我要请这位樊先生去喝两盅,攀这么一个好朋友。”姑娘在屋子里答应了一声,便拿出一个蓝布小袋来,笑道:“你可别请人家樊先生上那山东二荤铺,我这里接来做活的一块钱,你也带了去。”寿峰笑道:“樊先生你听,连我闺女都愿意请你,你千万别客气。”家树笑道:“好,我叨扰了。”
当下关寿峰将钱袋向身上一揣,引家树出门而去。走到胡同,有一家小店,是窄小的门面,进门是煤灶,煤灶上放了一大锅,热气腾腾,一望里面,像一条黑巷。寿峰向里一指道:“这是山东人开的二荤铺,只一点面条馒头的,我闺女怕我请你上这儿哩。”家树点了头笑笑。
上了大街,寿峰找了一家四川小饭馆,二人一同进去。落座之后,寿峰先道:“先来一斤花雕。”又对家树道:“南方菜我不懂,请你要。多了吃不下,也不必,可是少了不够吃。为客气,心里不痛快,也没意思。”家树因这人脾气是豪爽的,果然照他的话办。一会酒菜上来,各人面前放着一只小酒杯,寿峰道:“樊先生!你会喝不会喝?会喝,敬你三大杯。不会喝敬你一杯。可是要说实话。”家树道:“三大杯可以奉陪。”寿峰道:“好,大家尽量喝。我要客气,是个老混账。”家树笑着,陪他先喝了三大杯。
老头子喝了几杯酒,一高兴,无话不谈。他自道年壮的时候,在外当了十几年的胡匪,因为被官兵追剿,妇人和两个儿子都被杀死了。自己只带得这个女儿秀姑,逃到北京来,洗手不干,专做好人。自己当年做强盗,未曾杀过一个人,还落个家败人亡。杀人的事,更是不能干,所以在北京改做外科医生,做救人的事,以补自己的过。秀姑是两岁到北京来的,现在有二十一岁,自己洗手快二十年了。好在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上座之际,楼上无人,让寿峰谈了一个痛快。话谈完了,他那一张脸成了家里供的关神像了。
家树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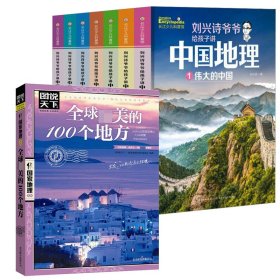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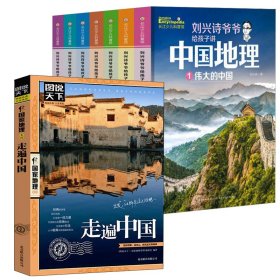


![灰姑娘(精) 绘本 [美]玛西娅·布朗改写/图 新华正版](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afdbecbe/233f0936fe9e7c65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