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物集(精)9787540787394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25.78 5.7折 ¥ 45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唐棣
出版社漓江
ISBN9787540787394
出版时间2019-1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5元
货号30785334
上书时间2024-11-2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第一辑
蒌草
羊角
紫藤
茑萝
莴苣
屎瓜
红顶儿
一圈树
狸木考
第二辑
饥饿旅人
捕蛇少年
丢魂的人
捞尸的人
养羊的人
造字的人
铸钟的人
说书的人
拉电线的人
开大车的人
不存在的人
治不好的人
锔瓷器的人
水母保佑的人
以驴会友的人
走在矶上的人
死于雨中的人
使锯弓子的人
第三辑
吃苦
搽香
草田
瓮葬
石桥
龙泉寺
石榴河
尼龙袜
一把梳
蚊香药片
方形风筝
第四辑
土狗
树猴
蚱蜢
灰鹅
灯鱼
知了猴
蝲蝲蛄
露水鸟
第五辑
茶疼
各饼
上味
吉子
第六辑
四兄弟
两姊妹
死亡四则
附录一
创作手记
附录二
风物小解
内容摘要
作者唐棣,少小离家,忆起家乡风物人事,打算赶在它们在脑子里消失之前,以文字记录下来。很多离家在外的游子极力书写乡愁,而支撑唐棣写下这些的,肯定不是一份单纯的乡愁而已。
作者的现实是,从小在采煤沉降区长大,地面塌陷,地面涌水这些外人觉得神奇的事见得多了,作者是到后来才回想起小时候天天怕水把家淹了,放学回去找不到家。当故乡真的被大水淹没,作者的情感一
时没了渊源,不安和紧张更加强烈。而他现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仍想继续说点什么。这些年感受尤其明显,楼房逐渐覆盖了乡村,形同一种比大水更猛的淹没。
故乡在哪里?每次遇上那些有个地方储存情感、
激活记忆的人都让作者特别羡慕,这也是他想说的原
因之一。
作者就是在寻找这个地方的旅途中,完成了这样一本失物之书。
主编推荐
精彩内容
蒌草最早,马州地面上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泥潭、水洼
地。时间久了,地下水渗出地缝儿,几乎一眨眼就冒出来了那么多面积不小的水塘。
我追忆故乡就是从水塘边蒌草疯长时节开始的。
大片大片的水塘里滋长最多的就是这种草了。在我还不认得这种草的时候,就知道只要它一出现,就表示此地“快了”——即使现在还只是湿潮没有水,也很快就会涌上水来。小学时学习古诗“蒌蒿满地芦芽短”,老师说的这种草,好像就是我当年在水塘边见得最多的蒌草。
这蒌草也叫“芦蒿”“藜”“艾蒿”,喜温湿,生于阪隰,而以沼泽尤佳。走河坝子的人经常见到野蒿子,绿叶红蔓,一股淡香。
野蒿子和蒌草其实是两种草,混着长成了一大片一大片,好多时候是看不大出来的,也不怪它们!等我长大一
点才知它们的生长期挨着,也都很短,话说“三月藜,四月蒿。五月藜蒿当柴烧”。每年三月过后,蒿子茂盛,五月一到,满地枯黄。
当然,书上也记载着另一种名贵的蒌草,是春秋时的君子草。
如《诗经》里写:“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又写:“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文中的“蒿”“蒌”,我以为指的都是水塘边的蒌草。难怪村里人拿着镰刀出门,问他们干什么去,都说去割蒿子喂猪。其实割回来的,大多是蒌草。
后来读了点书,又发现“蒌”和“蘩”可以作为祭祀
神灵的祭品,“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采蘩是不是采蒌草?留下疑问给好奇的人吧。
其实,萎草、马羚菜、蕨等这些野菜,在我妈看来完全不值一记。平时,我写东西她完全不参与意见。唯独在这方面,一下子见多识广起来。她看着我,摆了摆手,说:“草就是草。东西还能变?”我想到早几年吃过的蒌草还是一味药。隐约记得好像看过《本草纲目》称“采其根茎”,可败毒去火。第一次煎药,入口的味道不仅是苦,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第二天,问大夫能不能换一种吃法。大夫看着我,笑说,你当这是吃菜呢!
一个朋友知道我这段经历后,有一天非开车载我去到一个极偏僻的小馆子,神秘兮兮地,点名要让我尝一尝镇店名菜“腊肉蒌草”。
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药,一会儿又是菜。你说,蒌草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复杂!
羊角羊角长在后山一溜儿坡下面,春夏之交正是它们闹得欢的时候。女孩们被惹得兴趣高涨——它像山羊角似的竖起来,扯一枝插在头发上,真是俏皮又好看。
“羊角”是我们的叫法,外面的人叫杜鹃、马樱花、
山石榴,一些书里还讲到它在朝鲜就叫“金达莱”,知道这些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在马州人古老的知识系统里,名字就是个代号,什么东西有趣最重要,直到今天还是“羊角、羊角”地叫着,不管不顾,理直气壮。
这也是我记忆里羊犄角般地“顶”起的五色缤纷的那一部分——白的、红的、蓝的、粉的、紫的,复色、条纹和斑点的都有。查了查杜鹃品种有九百余种,但说故乡的野羊角吧。
马州人除自家田地,屋舍前后庭的空地会被他们辟成田,按节气撒种青菜。我家当年没种菜,辟成的田地,圈起了篱笆,养鸡养鸭。
周围是山,山也不高,山脚和山腰之间是田。从这座矮矮的后山走上去不远,眼前铺展出一条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山腰了——我家曾在在那儿有块田。儿时,我妈在那儿种过菜,不时扛锄下地,挑水浇菜,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的两边,到了季节,尽是野羊角匍匐着。印象里它们把路边的水沟占满了,好多好多,开得极盛。那些羊角是玫红色的。
我妈在远处田里种菜,我一个小孩无聊,只能摘几枝路边的羊角。手上的野羊角,不管好不好看,首先是好玩——那时就这么觉得,可以当“零食”是后来长大了一些才知道。有人告诉我以后,我玩完了,就把红瓣儿在嘴里含着,先酸后甜。
除田里的活儿、家务,马州妇女一般上山割蕨,这是她们在那个年代里最基本的工作。后山的蕨菜是之前各户人家里最常见的生火燃料。人们每天磨好镰刀,背一枝竹杠,杠上缠着绳索,几人相伴,就这么谈笑着,进了山去。听老邻居说当时都是这边割,那边不忘在山里寻看有没有野果,带回去给孩子。那些割蕨的妇女沿山路而归,过了河,我们这些小孩子早早就在河边等着了。(P3-7)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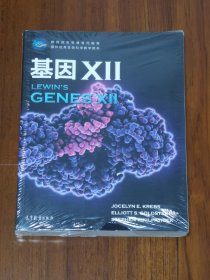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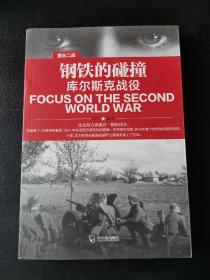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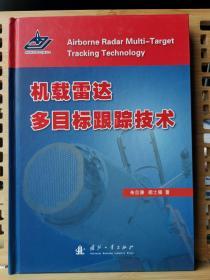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