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9787221184443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57.18 5.8折 ¥ 98 全新
库存4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日)蛭田圭|译者:孟凡礼
出版社贵州人民
ISBN9787221184443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2193684
上书时间2024-11-02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蛭田圭丹麦奥胡斯大学奥胡斯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兼AIAS-COFUND研究员。
译者简介:孟凡礼
1980年生。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代表译作有:《论自由》、《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合译)等。
目录
第1章 引论 001
第2章 “眼中钉” 015
敌意 017
汉娜·阿伦特的生平 018
以赛亚·伯林的生平 021
对话犹太复国主义 023
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 038
纽约的“内战” 055
俄国革命研讨会 071
“生前是,死后也是” 075
第3章 自由 079
术语及区分 084
伯林的自由理论 088
阿伦特的自由理论 106
消极自由、政治自由与个性 132
结论 138
第4章 非人性 141
定义极权主义 146
集中营社会:阿伦特论极权主义 153
极权的心理:伯林论极权主义 173
结论 198
第5章 邪恶与审判 201
艾希曼神话 206
伯林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初看 211
程序上的反对 215
实质上的反对 233
结论 260
第6章 自由之岛 263
伯林的英国 268
争辩英国帝国主义 277
阿伦特的美国 291
争辩革命精神:美国1968 299
自由和/或民族主义:匈牙利1956 303
结论 321
第7章 结论 325
致谢 337
附录 343
缩略词表 347
注释 353
索引 449
内容摘要
本书首次全面介绍了20世纪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的深刻分歧如何继续为政治理论和哲学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以赛亚·伯林(1909—1997)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他们在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尽管他们作为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经历有重叠之处,但伯林非常不喜欢阿伦特,说她代表了“我最厌恶的一切”,阿伦特则以冷漠和怀疑的态度回对伯林的敌意。《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以生动的风格写成,充满了戏剧性、悲剧性和激情,首次讲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并展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如何继续为今天的政治思想提供重要教训。利用大量新的档案材料,蛭田圭追溯了阿伦特和伯林的冲突,从他们在战时纽约的第一次见面,到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扩大的思想鸿沟,对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他们在1967年的会议上最终错过彼此接触的机会,以及伯林在阿伦特死后对她的持续敌意。蛭田圭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研究了同时将阿伦特和伯林联系在一起并造成分裂的关键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性质、邪恶和大屠杀、人类主体和道德责任、犹太复国主义、美国民主、英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革命。但是,最重要的是,阿伦特与伯林在一个关乎人的条件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自由意味着什么?
主编推荐
1.同样是犹太裔,同样都是客居他乡,为何伯林对阿伦特有着“终生的仇恨”? 谁憎恨谁,为什么?有很多很好的细节;蛭田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伯林和阿伦特的冲突。
2.蛭田本书的目的是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冲突——从专业、人格、政治几个角度理解——并阐述他们各自的政治理论方法存在的一些差异。书的调子是周密而平静的;书写之清晰令人佩服;蛭田无疑提供了一个公正而详细的年表,梳理了阿伦特/伯林的相遇以及伯林的各种敌意表现。
3.蛭田本书还考察了伯林和阿伦特各自选择的国家跟他们思考的关系,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精彩内容
引论几年前,我把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叫到一起……这次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条顿范、太黑格尔化了。阿伦特则把伯林的风趣误认为轻浮,觉得他不够严肃。
——阿瑟·小施莱辛格[1]1991年,美国哲学家诺曼·奥利弗·布朗写信给他的朋友、从前的导师以赛亚·伯林,[2]赞许地提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恐惧共和国》的书。[3]这本书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复兴党(Ba?athParty)的开创性研究,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卡夫卡式”世界与其据称的20世纪前身相比较。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这本书借鉴了一些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包括伯林的《自由四论》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4]伯林对这一对举颇为不悦。他回信给布朗,“我想那(《恐惧共和国》)是关于伊拉克恐怖的故事,这个就不说了。但让我深感不快的是,我的名字竟和汉娜·阿伦特小姐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告诉我,你真的明白阿伦特小姐跟我的某些根本区别吗——否则我们怎么继续交往?”[5]伯林在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表达出了对阿伦特的强烈厌恶,其实这种恶感由来已久。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当时这两位思想家在二战时的纽约经介绍会面。我们对这次会面所知甚少,但他们的观点肯定不同,双方给彼此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至少可以说,大约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当两位思想家在哈佛大学再次说话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安排这次会面的政治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他俩的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6]他们的道路在此后15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再次交叉,伯林继续在英国建立他耀眼的学术生涯,阿伦特则在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如果从社会关系、文化或思想等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不仅有各种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学术联系人和合作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他试图说服伯林认识到阿伦特工作的重要性。这位牛津哲学家从未被说服。相反,由于他对现象学哲学传统的深深怀疑,伯林将阿伦特的理论著作如《人的条件》(中国大陆版译为《人的境况》)斥为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联想”。[7]他的蔑视随着1963年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出版而演变成终生的憎恶。伯林极力地赞同广泛的指控,即阿伦特傲慢地指责大屠杀的受害者,她提出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关于恶的解释。
奇怪的是,尽管伯林对阿伦特及其著作不屑一顾,他还是继续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略读——她的书籍和文章,包括被忽视的作品,如《拉赫尔·瓦尔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也包括她的主要作品《人的条件》《论革命》。[8]然而,他读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对阿伦特作品的评价是正确的。后来伯林将他深思熟虑的观点总结如下:阿伦特“没有提出任何论点,没有严肃的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证据。”[9]此外,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从未因她的死或随后的时间流逝而减弱。在上面引用的1991年给布朗的信中,伯林形容阿伦特“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她死后”。他继续说:“她真的是我最厌恶的东西。”[10]阿伦特意识到伯林对她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多次抗议伯林对阿伦特的贬斥,以至于她和伯林的友谊因此被“毁掉”了。[11]与此同时,阿伦特本人也从未对伯林的敌意做出过回应。首先,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并且以此而自豪,尤其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她吸引了许多满怀怒气的批评家。她不可能回应所有人,在她看来,伯林并不是特别重要或值得回应的那一个。她知道伯林在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地位和关系,但她认为伯林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12]这部分是因为阿伦特认为德国哲学理所当然地优于英美哲学。尽管她尊重霍布斯,但她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哲学沙漠,认为罗素、摩尔等人发起的分析运动没有什么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两位主人公的偏见是对称的:一如伯林无法欣赏德国现象学,阿伦特也无法欣赏英国经验主义。不过阿伦特认为伯林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尤其是在俄国思想史这个主题上。她有时在课堂上使用伯林的作品;[13]她幸存的个人藏书里有一本伯林的处女作《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以及他的四篇论文。[14]然而,这表明阿伦特似乎唯一仔细读过的伯林作品是他给FrancoVenturi《革命的根源》写的导言。事实上,正是作为这篇导言的作者,伯林在阿伦特出版的著作中(而且是在脚注)唯一地出现了一次。[15]对她来说,伯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思想史家,也是她所谓的“犹太当权派”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员。伯林对她的敌意被她对伯林的冷漠和偶尔的怀疑所抵消。
不过事情不止于此。他们是同时代人,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伯林出生于1909年。他们属于20世纪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故事彼此重叠。[16]阿伦特和伯林分别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和波罗的海犹太家庭,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都经历了反犹太主义。两人都开始关注20世纪30年代欧洲迫在眉睫的危机,都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放弃充满希望的纯哲学职业,并在此后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理解极权主义的根源,遏制其增长并防止其死灰复燃。他们都有朋友和亲戚被他们后来致力于研究的极权主义政权谋杀或处死。此外,他们自己都曾在刚兴起的极权主义世界生活过,因此能够做一些类似于人类学家所说的“参与式观察”的事情:通过实际生活在所要研究的社会中来收集材料。众所周知,少年以赛亚·伯林惊恐地目睹了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他后来1945—1946年回到苏联在英国大使馆工作之前,伯林“反复做着被逮捕的噩梦”,并考虑过被捕后自杀的可能性。[17]就阿伦特而言,她被逮捕并在纳粹化的德国接受了八天的审讯,随后在被占领的法国的拘留营被拘留了五周(在那里她也考虑过自杀),然后移民到美国写《极权主义的起源》。压迫、统治、非人性和政治的颠倒,既是他们的生活主题,也是他们的思想主题;自由、人性和政治也是如此。
※?※?※本研究的两个目标是:追踪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的历史形象和他们之间不幸关系的发展,并让他们的思想发生对话。前一个目标是历史和传记性质的;后一个是理论性质的。前者涉及以下问题:阿伦特和伯林在何时何地会面,以及在这些会面中发生了什么?
两人的个人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以及阿伦特反过来对他的冷漠和怀疑,是如何步步升级的?除了实际会面之外,他们还有哪些互动?
这些问题值得一问,不仅因为它们是20世纪思想、文学和文化史的一个迷人部分。它们值得一问,还因为在阿伦特和伯林的生活和著作中,个人、政治和思想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严肃地认为,对于他们两人来说,一个基本事实是:政治理论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或有报酬的劳动,还是韦伯意义上的天职,他们每个人都过着政治思想家的生活,体现了独特的理论观点。[18]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深切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紧迫问题,试图对他们居住的“现实世界”施加影响,尽管方式不同。正如我将要展示的那样,这种生活和思维模式有其自身的缺点,因此并不明显优于今天已经成为规范的更超然和制度化的政治理论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怀念那个时代,那时政治理论家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因为他们的“想法确实有后果”。[19]这项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方面,涉及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将我们的两位主角既联系又分别开来。联系在于:它们是阿伦特和伯林思想的中心;分歧在于:这两位思想家对它们的回答是相互冲突的。这些核心问题可以正式和扼要地表述如下:对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被剥夺自由,被剥夺人性是什么感觉?[20]最恶劣形式的不自由和非人性的社会,即极权主义,其核心特征是什么,这是如何典型地出现的?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抵抗或对抗极权主义邪恶的明显失败,比如当一个人被迫与国家支持的大规模谋杀者合作时?
如果我们想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自由,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政体?
阿伦特和伯林对这些问题有时重叠有时冲突的思考将在第3—6章中讨论。这些章节是按主题组织的,尽管每个章节都笼统地对应着某个时间阶段。第3章,主题是关于“自由”,时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已成为完全成熟的政治思想家,并提出了他们对立的自由理论,各自被他们对“人的条件”的对立观点所支撑。第4章“非人性”,涵盖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并追溯了两位主人公一生与极权主义的接触。它主要考察了两种不同的著作:他们对极权政治和社会的战时和战后分析;他们后来试图根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现实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新考察。第5章“邪恶与审判”,重点是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伯林对它的评论。由于我们两位主人公的争论与他们在核心道德和政治概念上的分歧有关,如责任、判断、权力和行为主体,本章也涵盖了讨论这些概念的相关作品。第6章“自由之岛”更深入地探讨了两位思想家的中后期作品,梳理出他们对理想政体的不同看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了他们对一系列现实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对立观点,包括英国自由主义的现在和帝国主义的过去、动荡的60年代的美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在结论(第7章)中,我简要重申了我的主要论点,并考虑了它们对当今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影响。
虽然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故事有很多曲折,但它的主干很简单,可以提纲挈领地表述如下。首先,阿伦特和伯林之间理论分歧的核心在于对“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whatitmeanstobehuman)有着不同观点(第3章)。正如米勒和达格尔所说,如果当代政治理论的特点是拒绝“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如“人的条件”),认为这与“发现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在社会中并安排他们的共同事务”无关,那么阿伦特和伯林都属于更早的时代,当时政治理论还不那么“肤浅”。[21]其次,两位思想家对自由和人性的分歧源于他们对极权主义的不同观点。尽管两人都认为极权主义是非人性和不自由的终极形式,但他们的理论却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彼此竞争的模式:阿伦特的纳粹模式和伯林的“多数派”(Bolsheviks)模式(第4章)。这些分歧——一方面是对自由和人性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对极权主义的不自由和非人性的分歧——在许多问题上引发了进一步的分歧。其中包括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抵抗的可能性(第5章),以及理想政体的形式,在这种政体中,男男女女都有体面的机会过自由而充实的生活(第6章)。阿伦特和伯林的经历和生活故事为所有这些主要的比较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尽管他们的想法不能简化为他们的传记。因此,在第2章中讲述的历史传记故事意在为后面提供信息,本书后面将集中于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分歧。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阿伦特-伯林冲突各个方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理论的)的著作。不过,不用说,它建立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这些文献从更具体的角度阐明了冲突。虽然每一个这样的贡献都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讨论(通常在注释中),但在这一导论性章节中需要强调的是,相关文献的稀缺和出现时间的较晚。诚然,那些了解阿伦特和/或伯林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写他们的冲突;[22]然而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著作只是最近才出现。[23]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伯林与他“最厌恶”的女人保持距离的决心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4]正如那些研究过他未发表的论文的人所知,伯林对阿伦特和她的著作有很多话要说,但他几乎从未在出版物上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因为伯林非常讨厌她,以至于不愿意“与(她)建立任何关系”,哪怕是敌意关系。[25]诚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条规则有一个例外:他在1991年发表了关于阿伦特的实质性评论,作为他回答拉明·贾汉贝格鲁采访的一部分。[26]然而,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眼中钉”保持公开沉默。[27]结果,直到1997年他去世后,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评论才开始见诸报端。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的授权传记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8]尽管如此,它给出的仍是一幅不完整的画面,引发学者们一些有见地但基本上是推测性的评论。[29]伯林对阿伦特的作品和人格的完整评论的一个公平样本直到2004—2015年才出现,当时亨利·哈代、珍妮弗·霍尔姆斯和马克·波特尔出版了他的四卷精选信件。[30]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伯林冲突,尤其是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直到最近一直是一个基本上被忽视的话题;以及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试图讲述这场冲突的全部故事。
最后,我想再说几句,从一开始就说明这本书不是关于什么的。首先,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这项研究既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它调动了两个学科的方法论工具。一方面,它仔细考察了阿伦特和伯林的生平,并重构了相关的语境,以阐明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及其比较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它经常抽象地讨论他们的思想,撇开了这些思想的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背景。怀疑论者可能会说,这两种方法的并列必然是不连贯的。他们可能会说,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完全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在将二者应用于研究对象之前,必须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在广义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方法的选择应该遵循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不是相反。这项研究需要哲学和历史的方法。借用一位最近的哲学史家的话来说,抱怨像我这样的学术研究“既不恰当地具有哲学意义,也不恰当地具有历史意义,就像抱怨一座桥既不在一边也不在另一边”。[31]话虽如此,我将不在一般和抽象的层面上详述方法论问题,因为目前的研究不是对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辩论的贡献。布丁好不好只有吃了才知道。以下几章展示了我的研究发现;读完这本书后,每个读者可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是不是成功了。
第二,这项研究不是为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中的任何一个辩护。相反,这是一本不偏不倚的书。不用说,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阿伦特-伯林冲突保持中立或试图保持中立。相反,这意味着我根据两位思想家各自的优点来评估他们的个人论点,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知道这很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失望。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暂且不说伯林,阿伦特仍然是一个高度分裂的人物,赢得一些人的盲目忠诚,同时激起其他人的强烈敌意。前者希望看到的是在批评面前对他们主人的坚定不移的辩护;后者,希望的则是对他们敌人的整体打击。这本书对双方都没用。正如我希望在接下来所展示的那样,阿伦特和伯林都做对了很多事情,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尽管方式不同。将两者并列的目的不是决定哪一方“赢了”,因为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不是体育比赛、选美比赛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游戏。更确切地说,重点是更好地欣赏阿伦特和伯林的思想,互相对照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样每个理论家所做的默认假设和隐藏的偏见就可以被梳理出来并受到批判性的审查。
如果这听起来闪烁其词,如果我被要求“坦白”我的偏好和偏见,我唯一能实地说的是:我知道我同时偏爱着阿伦特和伯林。我知道我的思想形成与我对这两个人的著作难以抑制的兴趣是分不开的,我的观点也是在与他们持续的批判性接触中从根本上形成的。阿伦特和伯林同样是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
然而,这两个英雄不幸地无法相处。下一章讲述了这个失败的故事。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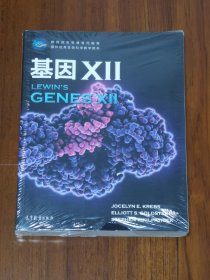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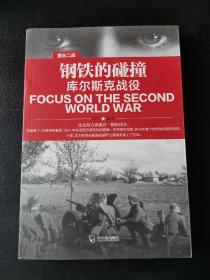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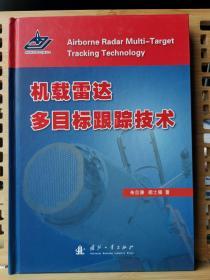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