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费曼丛书:走近费曼丛书:别逗了,费曼先生9787571000189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39 5.7折 ¥ 68 全新
库存3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R.P.费曼
出版社湖南科技
ISBN9787571000189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30659909
上书时间2024-07-30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别逗了,费曼先生》是费曼zui具盛名的自传。费曼无疑是20世纪仅次于爱因斯坦的zui受爱戴的物理学家,他的粉丝每一个都鼎鼎大名:比尔·盖茨、乔布斯、维尔切克……当你读这本书的时,一定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彻底折服于这位极具智慧、特立独行、不惧权威、惊世骇俗的科学顽童。
?杨振宁先生建议孩子们读科学家传记,那么,《别逗了,费曼先生》毋庸置疑是首选之作。费曼卓越的学习法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拥有永不停止的创造力?什么才是人生中zui值得珍视的?
?费曼说他的父亲对他有很大影响,引导他如何观察和理解世界。《别逗了,费曼先生》不是教你如何培养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基因恐怕很关键),但会教你如何把乐观、有趣、自信、对生活永远充满好奇的品质传递给孩子。
《别逗了,费曼先生》适合每一个人,尤其当我们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孩子,忘记了对世界的好奇和期待,忘记了专注和兴趣带来的欢愉,忘记了什么是炽热的爱的时刻。
目录
第1部分 从法罗克维到麻省理工学院
他动动脑袋瓜子就能修好收音机!
菜豆
谁偷了门?
拉丁语还是意大利语?
总想逃避
米特普拉斯特公司的首席化学家
第2部分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岁月
“别逗了,费曼先生!”
我————!
猫地图?
魔鬼头脑
搅和油漆
别具一格的工具箱
测心术
业余科学家
第3部分 费曼,炸弹和军队
嘶嘶的信管
考验猎犬
从低处看洛斯阿拉莫斯
撬锁贼碰到了撬锁贼
山姆大叔不要你了!
第4部分 从康奈尔大学到加州工学院,接触巴西
讲派头的教授
有问题吗?
我要我的一块钱!
你就这样问她们?
幸运数字
又是这个美国人!
什么话都会说
照您吩咐的,老大!
盛情难承
第5部分 一个物理学家的世界
你解迪拉克方程吗?
百分之七的答案
十三次
“鸡母牛,鸡母牛!”
但那是艺术吗?
电是火吗?
书好书坏,看看封面
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
把文化带给物理学家
巴黎见分晓
另类状态
野狐禅科学
内容摘要
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对原子弹发展贡献卓绝。《别逗了,费曼先生》费曼zui为著名的自传,书中的这些故事,是科学怪才理查德·费曼和拉尔夫·莱顿高高兴兴打鼓的七年之间,零散而随意地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的一辈子,竟然能发生这么多奇妙而发疯的事情:在大学宿舍里愚弄同学、观察蚂蚁、模仿猎犬嗅气味、不可思议的计算能力、撬开了装着原子弹保密文件的九个保险柜、在酒吧的厕所里跟人打架、看裸体舞表演、在巴西打桑巴鼓、学日语的尴尬、画儿画得相当不错、愚弄精神病医生、破译玛雅天文学古本,等等。这些令人发笑的故事,表现的是费曼坦率诚实的品格、自由的精神和创造性的思维。作为他生活轴心的物理学研究,其实是这个大玩家用全部的好奇心和热情来玩的一个玩具。
精彩内容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在家里搞了个实验室。它由一个旧木头包装箱构成,我在里头加了搁板。我有个加热器,我平时把肥油放里边做炸薯条。我还有个蓄电池和一个电灯排。
为了做这个电灯排,我上小杂货店,弄了些插座,用螺丝钉固定在木座上,然后用电铃线把它们串起来。通过把开关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串联的和并联的——我知道我能够得到不同的电压。但我没意识到灯泡儿的电阻决定于它的温度,因此我计算的结果和这个电路弄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但不妨事儿的,灯泡儿串联起来的时候,都半亮着,它们都发发发发发光,很漂亮——棒!
我在系统里装了保险丝,所以哪儿一短路,保险丝就烧了。现在我必须弄到比我家里的保险丝弱一点的那种,我就自己造保险丝,方法是把锡纸包在一段儿烧坏了的保险丝上。我在保险丝的那头安了个五瓦的灯泡儿;保险丝烧了的时候,总在给蓄电池充电的点滴式充电器出来的电,会把灯泡儿点亮。灯泡儿在配电盘上,在一片褐色的糖果纸后面(后面的灯一亮,糖果纸就发红)——因此,如果哪儿出了娄子,我就会看配电盘,撑不住劲的保险丝那儿就会有一个大红点儿。好玩儿哦!
我喜欢玩儿收音机。我先是从商店里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在夜里,我在床上将睡未睡的时候,用耳机听。父母晚上出去要很晚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来我房间,把耳机拿开——担心我在睡着的时候,别有什么玩意儿在我脑袋里闹腾。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我发明了一个防盗铃,一个简单的傻玩意儿:那不过是一个大电池,用电线连着一个铃儿。我房间的门一开,门就把电线推到电池上接通了电路,那铃就响了。
有天晚上,我妈妈和爸爸夜出回来,蹑手蹑脚的没一点儿声音,怕吵着孩子啊,开了我房间的门,好拿开耳机。突然之间,那个巨大的铃儿震天价地响起来——乓乓乓乓乓!!!我大叫着从床上跳了下来,“管用啊!管用啊!”我有个福特线圈——从一辆汽车上卸下来的打火线圈——我把打火端弄在我的配电盘上头。我打算在打火端装个RathenonRH电子管,里头是氩气,火花会在真空里产生紫色的亮光——那可真叫棒!
有一天,我正在玩那个福特线圈,用火花在纸上打窟窿,把纸给点着了。我很快就拿不住那纸了,因为快烧到我手指了,我就把它扔在装满报纸的字纸篓里。你知道,报纸烧得很快,在屋子里,火苗儿显得挺大。我关了门,那样我妈妈就发现不了我房间里起火了——她跟朋友在客厅里打桥牌呢,我从近旁抓了一本杂志,盖在字纸篓上想把火闷死。
火灭了之后,我拿开杂志,但现在房间里都是烟。字纸篓还是烫得没法儿动,我就用钳子把拖它过房间,把它弄到窗户外散烟。
可是外面刮着小风儿,又把火吹着了,而现在我也够不到那本杂志了。所以我又从窗口把字纸篓拖了回来,好去拿杂志。我注意到窗户上有帘子——非常危险啊!
还好,我拿到了杂志,又把火扑灭了,这次我抓着杂志不放,我把字纸篓里发红的火炭抖落到两、三层底下的街上。然后,我出了屋子,随手把门带上,对我妈妈说,“我去玩儿了,”烟慢慢从窗子里冒着。
我还用电动机干了一些事情,还为我买的一个光电池造了一个放大器;当我把手放在这个电池前面的时候,这个光电池能把一个铃儿弄响。我想做的事很多,但没能都做到,因为我妈总不让我在家呆着。但我常常在家里,摆弄我的实验室。
我从清仓大甩卖那儿买了几个收音机。我没什么钱,但东西不贵——都是旧收音机,坏了的。我买来,想修好。毛病通常不大——一眼就看到有电线松了,线圈断了,或者有些地方没缠紧——因此,我还真能让几个收音机响起来。有一晚上,我从一台收音机里听到了在得克萨斯州韦科(Waco)市的“韦科广播电台”——这可太刺激了!
在我的实验室里,用的还是这同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我听到了施奈克忒底(Schenectady)市的一家叫WGA的电台。现在,我们这些小孩子——我的两个堂兄弟、我妹妹,还有邻居家的小孩儿——都在楼下听收音机,听一个叫“伊诺犯罪俱乐部”的节目——伊诺泡腾盐赞助的——就这玩意儿!我发现,在楼上我的实验室里,我能提早一小时听到在纽约播出的这个WGA的节目!因此,我知道什么事儿将会发生,然后,当我们大家都在楼下围着收音机坐成一圈儿听“伊诺犯罪俱乐部”的时候,我会说,“你们大家知道,我们好久没听到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我敢打赌,他会来,来挽回局势。”两分钟后,嘀嗒,他来了!大家果然欢呼雀跃,我还预言了另外几件事。于是他们才意识到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门道——不知怎么,我必定知道这个门道。因此,我也就爽快地承认了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在楼上提前一小时听这个节目。
很自然,你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这一个钟头,他们是等不得了。他们都到楼上,在我的实验室里,守着这台叽叽嘎嘎的收音机守上半个钟头,听施奈克忒底市的“伊诺犯罪俱乐部”。
那时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那是我爷爷留给他的孩子们的,这些孩子也没有很多钱搬到别处去住。那是个很大的木头房子。我在房子外边把电线拉得到处都是,在每个房间里都装了插座,这样我总能听那台在楼上的收音机。我还有一个喇叭——不是一个完整的喇叭,没有喇叭口儿。
有一天,我戴着耳机,我把耳机连到喇叭上,我发现了一点儿东西:我把手指头放在喇叭里,而我从耳机里能听到这个。我用指甲刮喇叭,而我能从耳机里听到这刮擦声。因此,我发现,喇叭能有耳机那样的作用,而且你甚至不需要电池。在学校里,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我就把这个喇叭和耳机演示了一番。我不知道这就是电话,但我想这就是贝尔当初用的电话。
因此,我现在有了一个麦克风,我可以从楼上向楼下、从楼下向楼上广播了,用的是我在清仓大甩卖那里买来的放大器。那时,我妹妹琼(她比我小九岁)一定也有两、三岁了,电台上有个叫唐叔叔的家伙,她喜欢听他的节目。他唱些“好孩子”之类的小儿歌,还念父母们寄去的卡片,说“住在弗莱特市布什大街25号的玛丽什么什么的这个星期六过生日。”一天,我堂弟弗兰西斯和我把琼安顿坐下来,说有一个特别节目,她应该听听。然后,我们跑到楼上,开始广播:“我是唐叔叔。我们认识一个名叫琼的可爱的小女孩儿,她住在新百老汇。她快过生日了——不是今天,而是哪天哪天。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我们唱了一首儿歌,然后我们播放音乐:“嘀哆哩嘀,嘟哆噜嘟;嘀哆嘀哆哩,嘟哆噜嘟嘟……。”我们把这一整套节目弄完了,然后下了楼:“怎么样?你喜欢这节目吗?”“很好哦,”她说,“可你们为什么用嘴巴弄音乐呀?”有一天,我接了一个电话:“先生,您是理查德?费曼吧?”“是。”“我这儿是家旅馆。我们有台收音机出了毛病,想修修。我们知道您或许能帮点儿忙。”“可我不过是个小孩儿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是啊,这个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您还是来一趟吧。”那家旅馆是我姑妈开的,但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到了那儿——他们到现在还讲这故事呢——带着一把螺丝刀,插在后裤袋里。哈,我很小,什么螺丝刀在我后裤袋里看起来都挺大。
我跟收音机忙活上了,想把它修好。它什么毛病,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旅馆里还有个打杂儿的,或许是他注意到了,或许是我先看见了,可变电阻上的一个旋钮,就是用来调节音量的那玩意儿,松了,所以拉不动轴了。他到一边去锉了个什么东西,然后装好了,事儿就办妥了。
我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机,完全没声儿。这个容易:插头插得不对。修理的东西越来越复杂了,我的本事也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到了。我在纽约买了个毫安表,把它改造成了个伏特计,上面有不同的刻度,方法是用经过我计算过的合适长度的上好铜线。它不很精确,但还是足够好的,能测准那些收音机的不同接点是不是正常。
大家雇我干活儿,主要原因是大萧条。他们拿不出钱修收音机,他们听说这个小孩儿钱少也愿意干。于是我就爬到房顶上修天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问题越来越难,我就得到了一系列的教训。最终我干的活儿是把直流电收音机改为交流电的,要想把嘈杂声从系统里去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做得也不很好。我不该弄不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弄。
有个活儿干得实在轰动。那时我在为一个搞印刷的工作。有个人,认识那个搞印刷的,知道我在找修理收音机的活儿,于是他就派了个伙计到印刷所来找我。那家伙明显地穷,那汽车快报废了——我们就到了他家,在城里的穷人区。在路上,我说,“收音机什么毛病啊?”他说,“我开了它,它就出噪音,过了一阵子,那噪音就停了,一切正常了,但是我不喜欢开始时的那个动静。”我心里想:“见鬼!要是他没钱,他就该暂且忍一忍那点儿噪音。”在去他家的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唠叨,“你明白收音机,是吧?你怎么明白收音机的——你还是个小孩儿嘛!”他一路上都在拿我开涮,我心里想,“这人什么毛病?一点儿噪音,有什么要紧的。”但等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把收音机打开。一点儿噪音?我的天啊!怪不得这可怜的家伙受不了。这东西开始咆哮加上哆嗦——哇啊哇啊啊啊啊啊——声音大得不得了,接着,它安顿下来,运行正常。我就想:“这是怎么了啊?”我开始来回踱步,想辙,我想到,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子管发热的次序不对——就是说,放大器全热了,电子管准备好了要工作,可是电子管没有得到什么输入,或者说有某种逆着电路走的输入,或者说在开始的部分(射频部分)有毛病了,因此它才产生了这么大的噪音,是在拾起什么东西。当射频电路最终运行起来的时候,栅极电压得到了调整,一切也就正常了。
那家伙就问我:“你磨蹭什么啊,你是来修收音机的,可你光在这里走来走去的!”我说,“我在想辙哪!”接着我在心里说,“好吧,把电子管拿出来,把机器里的次序来个大颠倒。”(那年头儿的许多收音机,在不同的地方用的是相同的电子管——我想是212安的那种——兴许也是214安的。因此我把电子管都改了,再把收音机打开,它安静得像只小绵羊:它等着热起来,然后运行完美——噪音没了。
当一个人对你瞧不上眼的时候,而你接着就做出了像这种真能挽回面子的事儿,那他们通常对你就百分之百地另眼相看了。他又给我弄了一些活儿,逢人就说我是个多么了不得的大天才,说,“他动动脑袋瓜子就能修好收音机!”一个小孩子,停下来想了一阵子,就能琢磨出怎么个弄法——思想,这个东西,能用来修理收音机——他压根儿没想到这事儿是可能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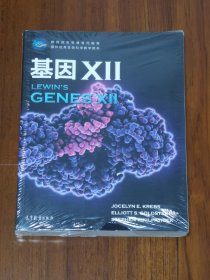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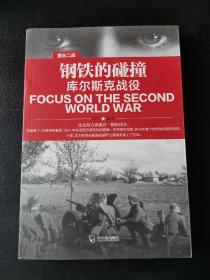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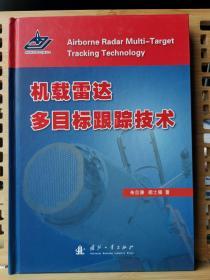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