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贤9787521219210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54.7 7.3折 ¥ 75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孙见喜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19210
出版时间2022-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5元
货号31558505
上书时间2024-07-29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孙见喜,原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孔子学会顾问,出版有各类著作二十余种,主要有:小说集《望月婆罗门》,散文集《小河涨水》《浔阳夜月》《跪拜胡杨》《西部的咏叹》等,以及《孙见喜评论集》《蕉皮论语》《回顾与前瞻:中华文化百年流变》《贾平凹传》等。其长篇小说《山匪》荣获2009年陕西省首届“柳青文学奖”。
目录
第一章 草庙沟 /001
第二章 苦胆湾 /023
第三章 油坊里 /035
第四章 太岁宫 /053
第五章 染坊里洋布衬衫 /098
第六章 金陵寺 /153
第七章 流岭槽 /194
第八章 崂峪庙 /246
第九章 商县城 /285
第十章 州河滩 /328
第十一章 小挎院 /378
第十二章 葫芦豹 /415
内容摘要
小说开始于一个没有女性的家庭——被称为孙老者的乡贤,他和他的四个儿子一个长工六个男人的故事,小说终结时孙家只剩下五个媳妇和三个幼子……小说以河南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八个月、二虎守长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为时代背景,以陕鄂豫三省交界的东秦岭地域风情为舞台,书写了民国十三年到二十一年约八年的战乱年代,这位乡贤老者依靠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内力管理一方乡域的成效与艰难。
精彩内容
第一章 草庙沟
事情出在草面庙有人说:就是这女人的一泡尿惹出了两条人命!
女人名叫十八娃,是州川里远近闻名的俏媳妇儿。她凭什么招惹这么大的事端?凭她那三寸半的小脚?凭她玉簪般的十个指头?凭她妈给她存放了六个年头的八幅子罗裙?凭她打贩挑的老实疙瘩的父亲?凭她新婚八个月怀孕已半年的笨身子?
她没有招惹人命案的本事。
那是秋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老贩挑送女儿十八娃回婆家。
婆家在苦胆湾,娘家在乱石窖,从乱石窖到苦胆湾顺草庙沟下行二十里,再翻马鞍桥的岭就到了。从民国初年起,老杆子陈贵生称霸东秦岭商县州川到流岭槽山阳县一带,说是为了保境安民,就剿灭或收编了南北二山的草寇匪帮,加之地方行政延用清制,所以商路集市大体还算安宁;老贩挑父女一路下来钻乌梢林翻石耙浪过鬼游谷,也没遇上地痞逛山狼虫虎豹。只是过槲叶林的时候,女儿两次说要尿尿,父亲说我娃忍一会儿到庙上了着。
他主要是想着庙上有人烟。
所谓的庙,是一处山神野庙,地处沟头岭底,乃清朝乾嘉两朝举国修庙高潮时所建。只是后来因了一桩乱伦事件坏了名声,从此绝了香火,院墙倾圮檐廊坍塌,成了游狗走兽的栖身处,或樵夫猎户偶然的歇脚之地。那桩让沟里人蒙羞的事件,也是因了某位父亲送女儿回婆家的。说是父女俩在半路上淋了暴雨衣裳湿透,俩人就到这庙里脱了衣裳拧水,见了女儿的白身子,为父的忍不住就把女儿的“活”给做了。送到婆家,吃饭时女儿给父亲捞了一碗面条,父亲操起筷子一搅,面条下边是一把青草,为父的就啥都明白了。他把面条吃了,也把青草吃了,回来路过此庙进去就上吊了。由此,这庙就叫作了草面庙,这沟就叫了草庙沟。也由此,沟里人在州川里名声就不大好,比如十八娃她娘家妈,从十六岁生到二十五岁满共才成了一个娃,人就传说她娘家妈的胎宫是二皮子、老贩挑的蛋丸是乱黄子。不管怎么说,老贩挑都不懈怠了炕上的耕作。婆娘九年怀了十一胎,前六胎都是三个月就流了,接下来“四六风”走了五胎,老贩挑实在没了法儿,找有面情的人携了“四色礼”,下州川来请“陈八卦”——陈福吉上乱石窖来给他禳镇禳镇,陈八卦一听是进草庙沟竟说啥也不去。有人给老贩挑出主意叫换剪刀,就是生娃时剪一次脐带埋一把剪刀,结果还是不行……还得求陈八卦。
是老贩挑亲自去的。那时候陈八卦正在五圣师庙里炼丹修道,但他是出家不离家,他父兄们又经营着打油坊,衙门里每月要从这儿买走五担油,所以生意场上括尽地利人和之便。老贩挑肩背褡裢在油坊外转了几个来回,就是寻不着正门。问一个伙计指一个门,几个伙计说的都不同,进去了要么是豆饼房,要么是旧油槽。老贩挑就坐在大核桃树下吃旱烟,心想人说这“陈八卦”住的是四坡五脊歇山转角楼,怎么不见转角也不见楼呀?可他一袋烟未毕来了一顶兜子,二人抬的,晃儿晃儿进了一间茅庵。老贩挑就觉得有些怪,紧追几步尾随进去。抬兜子的兜夫朝他跺了一脚唬他出去,他看兜子上下来一个穿道袍的先生长了个粪笼大的头,乌油发亮的长发在脑巴盖上绾了个碗大的髻,髻根别一支拇指粗的象牙簪子,又有两根乌黑缎带缚髻而垂;此人平端着一顶皂色斜坡额玉道冠,目不旁视,气象高古,老贩挑立时眼圈就热了,立时就“扑通”一声跪下。
在州川一带,陈福吉的足智多谋人所共知,又是推演周易八卦的高手,所以人称陈八卦。陈八卦无视老贩挑的屈跪之礼,径自前行。穿麻鞋的兜夫在他屁股上轻轻蹬了一脚,老贩挑感觉出了这种许可性的暗示,就紧巴紧地跟了进去。说是茅庵,其实拐弯抹角地通着正堂。油坊里这四坡五脊歇山转角楼原本就没有像样的门楼,更没有拴马桩石狮子大门二门照壁之类。陈八卦在正堂坐定,下人双手接了皂色额玉道冠。他端眼看着下人把皂色额玉道冠正放在红油板柜上、银镜插屏旁的白瓷帽筒上,才眯了眼,沉沉地问:“啥事?”老贩挑听到的是山谷里滚木头的声音,他耳朵里轰轰隆隆直响。还是那个麻鞋兜夫凑到耳边告诉他:“叫你说事哩。”老贩挑赶紧从褡裢里掏出银锞子——就是贩挑行里说的“打柱头”,又是跪地一个撞头磕,然后双手呈上去。麻鞋接了,老贩挑眼看着那颗从南阳府挣来的银锞子,白光光地映在了插屏镜里,就哀哀乞乞地说:“我婆娘怀胎十一回没落下一个娃娃。”又啰里啰唆反反复复地述说着每一胎“娃娃”的来龙去脉。麻鞋兜夫先不耐烦,就给太师椅上眯眼静坐的陈八卦递话:“是要娃哩!”陈八卦半天没有声音,老贩挑跪着不是,起来也不是。偏门里进来一个围着蓝花肚兜的厨娘,她手端黑漆托盘,麻麻利利地过来把托盘里的两只蒸馍一碟蒜泥放在陈八卦旁边的堂桌上。泼过油的蒜泥散发出浓重的香味儿,陈八卦优雅地蘸着蒜泥很仔细地吃着蒸馍。麻鞋看着陈八卦把一口蒸馍咽下,就及时给跪着的人传话:“问你要男娃还是女娃?”老贩挑赶紧说:“男娃女娃都是娃,能落住就行能落住就行!”说着又连连磕头。山谷里滚木头的声音又响了,他看见陈八卦的喉结在松皮下滑动,一种苍老的声音发出来:“老坟,知道吗?回去给老坟里埋一块十八斤重的石头。在州河里寻去,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行,背回去要小心,不要碰破了,碰破了娃娃就四体不齐。”当老贩挑在祖坟里埋下一块十八斤白石头的第十个月,炕上哇的一声,婆娘下裆里掉下个女娃娃,白白胖胖的女娃娃,十个指头蛋儿上圆兜兜儿着十个“斗纹”,真真的福星啊!于是,花儿叶儿的名字也不要了,老贩挑只管“十八斤娃十八斤娃”地叫着,后来“十八娃”就成了女儿的正名。及长,看着女儿满屋里跑,老贩挑仿佛又闻到了那油泼蒜泥的香味儿。这女儿也见风就长,要模样儿有模样儿,要心灵有心灵,眼睛像画上的,鼻子像粉涂的,小嘴是一颗草莓骨朵儿,六岁上就显出了银盘大脸、如葱纤指。人说这女娃巧啊,给人家绣的枕头顶子,牡丹瓣儿像立起来了,石榴籽儿也透出水光。人家女娃六岁缠足,老贩挑四岁半就扶着十八娃上了脚架子。缠脚的一套工具是他在州川里定制的,缠脚架、缠脚凳、绞板、一丝子布;人家女娃缠脚哭天喊地、满地爬滚,她却一声不吭,娘说这娃的脚像柿饼,捏个啥样儿是啥样儿。后来,娘在石瓮沟给认了个干妈,那瞎眼婆自己是天足就不叫再给十八娃缠脚,可称奇的是,她脚不缠了骨头却没再长……老贩挑的光景虽苦却不穷。乱石窖那地方,鸡尻子地打不了几升粮,沟沟岔岔的人家,祖祖辈辈靠以割生漆编竹器打贩挑为生。要靠打贩挑挣银子就得跑远路,豫西、川东、鄂北、晋南,都有东秦岭挑帮的老商户,打贩挑的口传四句话:“要担黄表四川有,河南药材马山口,潞盐山西运城走,要贩皮货走西口。”老贩挑十六岁走南阳担水烟,住过社旗县的山陕会馆,也在龙驹寨的船帮会馆耍过女人;二十岁开始入川,在三原县八个铜锅子(铜板)买四斤棉花,挑到四川万县卖十六个铜锅子;他开始挑八十斤,后来挑一百,梁力最好的几年能挑到百五。走一趟两个月,回来一觉睡上十天半月,在婆娘身上蹭一下就种着了一粒胎。往四川贩棉花的,一趟回来可挣二百个铜锅子,那时候二百个铜锅子能换四个银元,一个银元在荒春上能买三斗小麦。草庙沟的贩挑行里,春里入一趟四川,秋里下一回河南就算强手了,可他十冬腊月还要跑一趟湖北郧西,担木蜡、担香表、担灯笼罩子,全是年节时货,这一趟的进项,足够使他的婆娘女子娃过个阔阔绰绰的春节了。
这个十八娃,老贩挑百日里给她上“元吉楼”取了长命锁,过周岁又在银匠炉子上取了带铃铛的银牌银项圈,还有帽子上的银佛爷,耳掐子上的银坠子……为了承谢给他生了娃娃的婆娘,老贩挑也给自家女人定制了银簪子、疙瘩针,还有时兴的银纽丝手镯。为了这个媳妇这个娃,他老贩挑一根扁担溜九州,从十六岁挑到四十五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十六年里,三十年里,他自个儿或一家人的日子,就凭的是肩上这根桑木扁担!
这扁担是爷留给他的。父亲死得早,没有享用这根扁担的福分。这原本是一截百龄桑树阳面的膘质部分,被爷用大板锯解开了,看得清那断面上数十层的年轮线。爷把它裁成八尺长三指厚五指宽的毛坯,然后将这毛坯材料斜靠墙根,请力拔山的沟里后生弓了腰,以臂力、腰力、踵力,三力合一冲这材料做千百次的闪晃,这叫“压桥”;之后选用不炸不折者上杠“定桥”。这是在露天,选四块老砖,两块相叠,将定过桥的坯料架其上,下边用文火烘烤着;烤软了由四位壮汉抬一碌碡,压负正中,成月牙之形。如此静置半年或一年,经风霜冰冻、经烈日暴晒。经此磨砺,这扁担钢质的体魄、绵韧的性格就形成了。然后是繁琐的成形过程,先用寸刨刮,瓷片刮;再用青石磨、细沙磨;而后打蜡、上釉。上釉最要耐得心性,那是三斤五斤的药籽油,在敞口的撑锅里熬得沸了,将刮削成形过、硬质处理过、软纱抛光过、散发着浓烈气味的、色黄如蜡的扁担,横架于炭火盆上,以狐皮蘸沸油,将这扁担反复做通体拭擦;擦而烤,烤而擦,沸油,扁担,火,油烟腾腾,木质咝咝,眼见着它成了活物:红了,亮了,透出肉肉的圆润。之后,这根上过釉的扁担被爷们郑重其事地用麻布缠裹了,又慎慎地架到阁楼上去,任那油气慢慢渗透木质,渗透了就叫熟化了,熟化了就能防潮防腐,就横在肩上若面条,竖在屋角如钢板,贼来了能当大刀长矛,唱臭臭花鼓了当当地敲着能当梆子使!
老贩挑忘不了这根扁担开光的那一天。当时他还是十来岁的碎娃子,看着爷在沟沿子上焚起香案,看着五服长老一齐跪下磕头,看着一刀黄表在瓦炉燃烧、三炷柏籽香烈烈扑鼻,爷的口里就念念有词。然后,扁担从楼上被请了下来,一寸一寸地绽开麻布,看着这红透了熟透了的神品仙物,一位大汉就在当场上列了虎势:他挺胸鼓腹腿扎马步,他脚下穿着苎麻拧成的“踢倒山”麻鞋,一丝子布的白裹缠直扎到膝盖下;他双手撑直了枣木头荆木杆的搭柱,有人给他肩上戴了新麝毛的围子,有人在地上用朱砂画了两个“十”字,这大汉用双脚踩了,然后收腹运气,这时就有两位老者,将这刚打了木蜡的扁担放在了他的肩上,两个挑选来的半大小子十指交叉,猛地揪悬于扁担两端!大汉双膝一弓,倏地弹起,强大的筋肉之力,过腹经胸传输肩胛,那二百斤的负荷即刻使上翘的弧形变成坦平的一字!如此,一人挑二人,在山场上闪晃着、旋转着、舞蹈着,这原始的长途运输工具,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注进了铁质的坚硬!
草庙沟的挑夫们经常是集群而行,他们人手一杆搭柱,这个支撑扁担以便行路换肩歇脚的器械,其上端做成元宝形便于搁置扁担体,倘逢着强人,那元宝形的搭柱头便是锤击的重型武器,而搭柱扎地的那一头又正是一柄钢锥!他们出一趟远门,至少要带三板子麻鞋,一板子麻鞋十双,穿破了的也只能挂在路边树上,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后来人如果鞋子坏了,可从路边捡破鞋修补,如果谁把穿坏的鞋子扔到沟里,就被同行视为无德。贩挑行里有一句行话:“不留烂鞋的人无后。”从东秦岭商县出蓝关古道入秦川的贩挑们,麻鞋缠子裹脚腿,这是形象特点,他们不穿袜子,只用裹脚布,逢溪涉水那么哗哩哗啦就过去了,所谓:“三十里崂峪走一天,四十里猫沟一袋烟,七十里会峪脚不干!”再难的山路鸟道,再多的溪涧沟河,惟有麻鞋缠子裹脚可以对付,除此而外,布鞋皮鞋木鞋铁鞋统统不管用。所谓缠子就是裹腿布,勒紧小腿长途跋涉不肿脚,腿肚子上不出“蚯蚓蔓子”。因此关中道里的人一见贩挑队过来就说:“看人别看腿,看腿商州鬼。”受辱也罢,挨骂也罢,贩挑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沿途顺便捎些小杂货走州过县就赚钱,南盐北醋西辣子,河南人爱吃豆芽子。
他们行走在老河口的官路上,攀登在东秦岭的山阴道,贩挑们闪着软溜溜的扁担,统一着扁担的方向和姿势,就合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桑木扁担两头翘,宁挑担子不坐轿;谁家女子脸儿白,随我回到乱石窖;乱石窖里石头多,砌个圈儿来做窝;窝里下了两颗蛋,孵出一对庄稼汉,庄稼汉,怕婆娘,一根扁担走南阳,南阳有个寺坡子,住了一窝姑姑子……却说老贩挑护送着女儿十八娃继续在草庙沟里行走。出了槲叶林是苇子岔,女儿还说想尿尿。爹望一眼这沟道儿两边密密麻麻的苇子,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依旧说:“到庙上了着。”女儿十八岁了,为父的也六十又二。多亏一辈子打贩挑,练就一副好腿脚,乱石窖一路下来,挑着担儿,又过坎涉涧的,还得搀扶着女儿。女儿虽有六个月的身孕,却腰身不笨腿脚不肿,只是路走长了气喘。女儿拄着竹杖,肩上背了娘的蓝花包袱,包袱里有一件娘给的八幅子罗裙,罗裙里裹着一对老派的蒜薹形银手镯。银手镯是成婚的时候夫家给取的,八幅子罗裙隐藏着娘给一个人的承诺。这罗裙虽说放置得久了,可娘说黑来上了炕穿着舒坦。州川人没有睡觉穿裤衩子的习惯。
为父的还挑着他的桑木扁担。只是没有分量。一斗黄豆装在麻布袋里,他把它拴在扁担中间,然后一只肘子压了扁担前半部,后半截就高高地翘着,黄豆布袋就多一半搁在他的后肩上。是娘执意要给十八娃拿上这黄豆的,她说这黄豆做成钱钱饭补胎顶好。
此前,夫家派了兜夫来抬,被老贩挑打发回去了。说是让怀孕的女儿坐兜子他不放心。所谓的兜子,就是两根竹竿中间绑了一个布兜子,布兜子下拴一块踏板子,被抬的人坐在上边,说软不软说硬不硬闪闪晃晃,看着堂皇坐着趔趄。再说老贩挑也不放心那两个冒失鬼:一个是扛活的海鱼儿,一个是名叫镢头的小叔子老三。
这州川里的老亲家,正是方圆有名的孙老者。孙老者,孙法海,光绪年间在县衙里执过水火棍,识得几条大清律,有点小脾气却做事还公正。“反正”后,民国初,地方行政沿用晚清旧制,官吏、衙役依袭陈规。地处东秦岭的商县仍然作为直隶州之所在,行政机构设了三班八房。三班是快班、壮班、皂班;快、壮二班专司缉盗剿匪传唤诉讼,皂班主管牢狱;各班设正、副、代、小四个班头,分别按里甲划片兼收田赋催办承差各有一份额外收入。班头俗称贯爷,通常人叫大贯爷、二贯爷、三贯爷、四贯爷;每个贯爷管八十名专职差役,另有百十人的临时伙计供随时差遣。八房即户房、工房、柬房、南北刑房、兵房、礼房、官吏房及仓房,每房工事十一人,月薪俸八块银元;每房有房头三人,人称大案爷、二案爷、三案爷,每位案爷手下有无薪俸的雇员和学徒八十人。全县十六里,户房收八个里的田赋,其余房各收一里田赋,田赋是肥差,户房不能独吞。三班贯爷从田赋上拿的只是“催收”钱,而八房案爷才是田赋的专管者。八房案爷工役的薪水,每逢年节由案爷将各项陋规收入列单集中分配。
民国初建,延聘晚清旧人,孙法海被聘为快班大贯爷,水火棍只偶尔用来杖责种烟贩毒之人,而出门办案则执佩腰刀,肩挎一只布袋,布袋里装二升麸皮,麸皮里埋着铁绳,铁绳埋在麸皮里一是不锈二是不响。那时候逮住人犯,就一条铁绳拴了脖子由差役牵着,这一是防逃二是示众。民国初年兵乱政浊,八年里平均一个县知事坐官九个半月。因看不惯官府腐恶,又不忍残害乡里,孙法海就辞职归田,归田了却不种田,他被推为下州川里长,前清时叫里正,入了民国一度叫里长;曾一度不堪匪患罢里回村,又被推为甲脚,后来又改叫保长。
民国初期的几年,基层政权承袭晚清设里甲制度,后来在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了《地方保安团条例》,规定县知事任保安团总监督,每户出一人,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五甲为一保,分设牌、甲、保长,团设团总,这种组织架构的经费就地筹集,地方治安就由他们负责。再后来,县知事改叫县长,里长改叫保长,甲脚改叫乡约。
孙法海在乡里行走办事,给人合辙解疙瘩,正直公道,在州川颇有名望,不到五十岁就被人称作孙老者。他的信条是“见姻缘说合,见冤家说散”。他靠执水火棍的俸禄和当大贯爷的积蓄,置有一面坡地几亩水田,圈里养有两头黄牛一头母猪,在场房边又开了一间染坊,小日子虽不宽裕,却也荒春上不借粮,红白大事不背债。孙老者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火镰、二儿子锛子、三儿子镢头、四儿子杆杖。四个儿子就像家织机上的老粗布,疙疙瘩瘩不平整却还结实好用。孙老者再说也是住过衙门的,“反正”后又成民国人士,加之他幼年读过私塾,知孔孟,通文墨,所以内心深处有对儿子们的另一番寄意,他给四个儿子取的官号依次就叫:承礼、取仁、兴让、文谦。
十八娃嫁的是老大承礼,可承礼的大名始终没有叫响,六尺高的汉子了人们还是火镰火镰地叫。可十八娃听不惯人们喊丈夫火镰,为此还跟人红过脸,这样孙老者就跟村里人打招呼说,娃有了媳妇,今后不准再叫小名了,还请人给刻了一方印章:承礼。承礼一副好脾气,父亲多在外少在里,他就掌着这个家。要紧的是这座染坊,他的主要精力是经营着染布的生意。
老二就是取仁,小名锛子。锛子在私塾上到十二岁,被父亲送到洛南县景村镇,去给山西运城程掌柜的“裕源堂”熬相公。所谓熬相公就是当学徒,三年以里学徒也只是个名分,实际上是店里的勤杂工、老板的用人。早起开门、扫地、挂幌子;晚上睡觉支凳子、睡铺柜;三年熬满,成了正式店员叫把式,吃穿去过就有了三十块银元的年薪;能独当一面处理业务了姓张叫张师、姓李叫李师;一般的“师”都是秤杆子耍出来的,收货发货老秤新秤搞得你客户眼花缭乱,什么货是死价活秤,什么货是死秤活价,耍滑了也就成“师”了。这家商号主营药材,兼做皮毛,暗中走贩私盐。老二一到店里就叫着“取仁”的大号,“锛子”的小名就被人忘掉了。取仁脑筋灵光,冬天了他给掌柜的被窝里早早放了暖壶,夏天了他早早在掌柜的卧室里点了艾绳,又开了撑窗往外赶蚊子,地上还洒了薄荷水;早晨,总是他先拎走掌柜的尿壶,晚上过账,又总是他一遍遍地给掌柜的添茶续水……三年之后,程掌柜教四个相公娃打算盘,又是取仁最先通过了“九归壳廊子”,为了训练珠算的准确和速度,过一些时日程掌柜就把四个相公娃招在一起“斗盘子”,或“四马投夜”,或是“五鬼闹街”,每次都是取仁得第一。其他相公还在背着口诀练习“一女进三宫”“二小抬香桌”,取仁却进到更为复杂的“七郎打擂”“八仙请寿”等算法上去。到了十六岁,取仁就能双手同时拨打两张算盘子,报账的舌头没有他盘子上的指头快,以至后来“斗盘子”,取仁敢向程掌柜挑战。程掌柜何许人也?他盘子上的功夫在景村一条街上无人能敌,他左手打着“凤凰门前一树杏”,右手打着“三人哭活紫荆树”,口里念的却是“李三娘担水”,每逢二月初八算盘会,程掌柜同时与三人对阵打擂,常常是观者如堵,热闹得跟唱大戏一样。到了十七岁上,取仁开始学中药、认皮毛,每临早晚,他都到药库闻着浓浓的药香,面对千种百样的药材,背诵“麻黄桂枝解表药,薄荷牛蒡主辛凉,三黄芦根能泻火,附子肉桂祛寒逆……”;二十岁上,程掌柜教他读老书,给他讲诸子百家,又讲解历史朝代,哪一朝谁坐了多少年,从周秦汉唐直到宣统都要他背诵;二十二岁,程掌柜教他学书法,送他一册赵孟书的《唐狄梁公碑》,让他日每临帖习字,又给他讲这碑文的作者范仲淹是“宋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知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而书写这碑文的是“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赵孟”。
因为处事机灵、记性好,取仁不但字临得像模像样,还把字帖上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且在与客户言及生意萧条时,还时不时地用上几句:“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就一时深得程掌柜的器重,派他去收款,派他去进货,派他去扎账等等,他一时被人称为二掌柜的。逢着夏夜月高风清,程掌柜过目了账房递上的簿子,竹躺椅上一靠,品着自家配制的凉茶,吹一曲洞箫,或是哀怨悱恻的《孔子哭颜回》,或是清丽妙曼的《小霓裳》,取仁就陶醉在人生最甜美的时刻。程掌柜要教他也学上一曲半律,他摸索了许久,终觉十个指头做不了这活,就说我脑子里这条窍道不通。可程掌柜说,商人要传代,非得浸上儒气,否则一代兴盛一代败亡,终逃不脱暴富奸商不久长的宿命。只有一个独生女的程掌柜,已把取仁和裕源堂的前途合在一起考虑了。但取仁似乎对医药学术更有兴趣,他怀里常揣着一本自己手抄的《汤头歌》,时不时地默诵几则方剂。当然,依据裕源堂的商势,程掌柜嘱他多留意中药丸散。取仁牢记程掌柜一句话:“商人有商人的道德,你煤油里掺水,火柴盒里架桥,扯布尺子斜量,只能是奸商小贩,永远发不了大财。”入裕源堂十四年后,二十六岁的取仁出落成一位英俊文雅的儒商。
镢头老三的大名叫兴让,这是一个四肢发达、脑子简单的角色。一面坡的旱地和州河边的水田,全靠他和海鱼儿耕作。给牛割草是他的事,给猪垫圈是他的事,跑贼背娃送干粮敬神上香出工役全是他的事。海鱼儿是只出力气不拿事,紧急关头他总是火镰哥火镰哥地扯嗓子直喊老大。
可是火镰哥自娶了十八娃,似乎终日心事重重,他给海鱼儿说他老做噩梦,总觉着有人要谋他的命。染坊里收的石榴叶子石榴皮、橡碗子、乌叶子、景村捎回的黑矾,他做的成本账一塌糊涂,为此他挨了孙老者几顿责斥。镢头老三心善,看大哥愁眉不展的样子,几次给他说:“地里的事有我哩,嘴上吃的有我哩,大哥你只一心务好染坊,我们仨的大事还靠你染坊上哩!”他说的大事是婚姻。其实,杆杖老四还是个青皮后生,说是派他赶三六九日打儿窝的集,可他尻子后头总串系着州川里的几个闲人,孙老者说他苦汉不像苦汉逛山不像逛山,有一阵子,他竟对枪产生了兴趣,收集的弹壳炮铜子儿在窗台上摆了一行。
娘死得早,坟上的树都一人高了。也有人张罗着给孙老者办个后,陈八卦甚至串说他去察看一位寡妇,但被老者笑拒了。他说还有三个儿子都光着棍儿,我年近六旬了也没那份心思。
相关推荐
-

乡贤9787521219210
全新广州
¥ 47.04
-

乡贤9787521219210
全新廊坊
¥ 39.38
-

乡贤 9787521219210
全新广州
¥ 40.44
-

乡贤(精装)9787521219210
全新北京
¥ 35.00
-

正版 乡贤 孙见喜 9787521219210
全新天津
¥ 29.57
-

正版现货新书 乡贤 9787521219210 孙见喜著
全新北京
¥ 44.21
-

乡贤 9787521219210 孙见喜 作家出版社
全新北京
¥ 39.30
-

全新正版 乡贤 孙见喜 9787521219210 作家出版社
全新北京
¥ 45.73
-

新华正版 乡贤 孙见喜 9787521219210 作家出版社
全新北京
¥ 38.28
-

保正版!乡贤9787521219210作家出版社孙见喜
全新天津
¥ 30.74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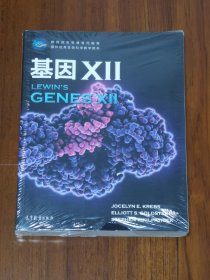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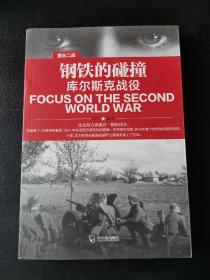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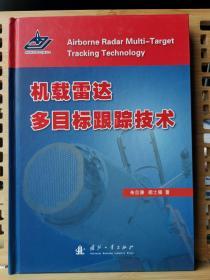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