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避之路(精)/格雷厄姆·格林文集9787532784578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55.36 7.4折 ¥ 75 全新
库存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84578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5元
货号30924886
上书时间2024-07-29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的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二十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亦是英国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
目录
无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作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对另一些作家来说,探险般的生活却是对枯燥写作的逃避。格雷厄姆?格林显然属于后者。这也正是这本自传的来由。他个性的魔咒使他无法停下寻找危险的脚步——显然,无趣、单调、安宁的生活比死亡的阴影要更可怕。毫无疑问,格雷是个勇敢的人,而且有自己的正义准则;他一次次的逃避之路不单单是猎奇的冒险,而且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战斗。他能在并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看到一个普通人遭受的政治苦难,不论他所属的阵营与党派,而且能感同身受并愿意冒个人危险为他们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他能看穿当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掌权的那一个个政治强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华美说辞与主义理想,看清他们给现实国度中的个体带来的真实痛苦,并且不畏恐吓,以笔为剑,抨击强者,声援弱者。从这个角度看,这位逃避自我的文人却颇有几分云游骑士的侠肝义胆。 \\\\\\\\\\\\\\\"
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第六章马来亚是我数次逃避中的第一次。
1951年,马来亚上空笼罩着一片道德争议的阴云–到底有多严重,我到了印度支那后才明白。对于英国人来说,战争背离正常,就像情感背离一样。对于法国人来说,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就像通奸一样。“Laviesportive(译注:法语,意思是“体育的生活;运动的生活”等。)”–这就是一位法国指挥官在西贡南部三角洲一艘小型登陆艇上对我描绘他的生活时说的话,他在一条条狭窄的水道里追杀越盟(译注:VietMinh,1941-1951年间的抗日抗法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及其武装部队的非正式名称。)游击队,两岸的迫击炮火力很容易击中他的小艇。
人说话要公正。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个地理问题。马来亚比较靠近赤道;这里几乎每天下雨,因而总是雾气蒙蒙;疲惫不堪、劳累过度的人们因此而更加精疲力竭,紧急法令时期所产生的工作鲜有人过问:管理劳工的人员太少,种植园主太少。除种属于马来亚公务员的种植园主和官员之外,这里多数人干活都抱着临时观点: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已经登上回家的小船。如果紧急法令时期结束(就像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那样,政府不正式称之为战争),宽松政策就会较快出笼。但是,战争(名符其实地说,应该这样称它)毫无快要结束的迹象。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在激烈争论朝鲜战争是继续还是结束,马来亚那场被人遗忘的战争半死不活地拖着。每天零零星星都有人员死伤:1950年的前十一个月有四百平民惨遭杀害,一个游击队营地被摧毁,三个游击队员被枪杀,六人逃跑。战争就像迷雾:它渗透一切;它消耗精力;它含糊不清。它当然不是laviesportive。
在马来亚所有平民中,橡胶种植园主的处境最危险。共产党突击队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从经济上毁坏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不值得维系的地区,而马来亚的财富主要是锡和橡胶。与橡胶园相比,锡矿相对比较容易守护,因此共产党突击队的主要袭击目标就是橡胶种植园主。那么谁是橡胶种植园主呢?
去马来亚之前我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从一份不同情的马来亚状况的报刊那里偶然获得的,这份报刊隶属一帮资本主义大企业冷酷无情的掌门人,他们从不妥协,对当地劳工实行消极剥削,在当地俱乐部里一杯接一杯地喝stengah(译注:马来语,意思是“一半”,但此处指一种用一半威士忌酒一半苏打水再加冰块合成的饮料。),也许还用萨默塞特?毛姆的方式,相互换妻做爱。但是,在马来亚居住不久,我了解到根本就没有种植园主这回事–只有X君或者Y君。
以X君为例。他与妻子生活在一栋两层小楼里,四周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住;夜间,小楼周围的场地用探照灯照亮,远至第一排树。他年纪五十多岁,曾经是日本人的囚徒,原本应该渴望比较轻松、比较富裕的晚年生活。他是个优秀的狩猎人,作为一名渔猎法执法官,原本应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因为大象与共产党一样,必须与之斗争,他的种植园里有一片特拉法尔加广场大小的地方遭受大象蹂躏,就好像被炸弹炸过似的–没有一棵树木直立着)。
但是,他的余生与他渴望的生活截然不同–如果有人能把这种没完没了的无法避免的暴力称作生活的话。他没有助手,因为几个月前他的助手被谋杀在种植园里,而他却无法再雇佣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最靠近的村庄每隔半小时打一次电话过来,以确保电话线没被割断。有一次,他离开家宅仅一英里便遭到伏击,不过他开枪射击杀出一条血路,还救出几个受伤的同伴。在我来此暂住前不久,共产党曾来过种植园,向园里采集橡胶树液的工人询问他的动向(他的助手生前曾不明智地在固定的时间按固定的顺序巡视种植园的几片作业区)。当他到铁丝网以外活动时(要是去几百码以外的种植园办公室就好了),他手臂上挂着一支斯特恩式轻机枪(译注:英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武器。),臀部别着一把自动手枪,皮带上拴着两个手榴弹。他是一个英勇无比、精力充沛的男子汉,既具有冒险精神又和蔼可亲,他不会考虑退休生活–他一生都在前线,他的前景不是安宁而是死亡,最近似安宁的生活就是偶尔去一次相对安全、官僚化了的首都吉隆坡。
如果早餐时他不喝咖啡而是喝一杯白兰地和干姜水,那么你几乎不用惊讶。“酒后之勇,”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按下防备不严实的小型装甲汽车的起动按钮,出发去巡视种植园,或者慢慢转过死角,驶上通向村庄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说不定哪一天,从对面丛林里,斯特恩式轻机枪几乎肯定会开火。在村里,与中国店主一起喝一杯不加冰的啤酒;中国店主立场暧昧,店里四周点着中国蜡烛,摆放着一箱箱茶叶;店主买下X君的廉价橡胶,充当他的钱庄(当场支付一万马来元)–也许会把他的行动报告给游击队。随后,在军官下榻的客栈里喝上一两杯红杜松子酒,之后,便驾车沿着孤寂的两英里长的道路回种植园,在那片丛林围墙前面的拐弯处放慢车速,十秒钟神经极度紧张,随后是橡胶园不堪一击的防卫体系,在那里,死亡照样可能发生,但是在那里你至少能够看清子弹来自单调的灰色军服之间。一天早晨,我和他晚一个小时回家,他的妻子既生气又爱怜,焦急等候着汽车的引擎声响,直至他安全回到铁丝网围墙里边。那天晚上,广播里报道又有三个种植园主遭到谋杀。
或者以B君为例。他是另一位平民,在紧急法令情况下干着他和平时期的工作。他不是种植园主,而是一条重要铁路枢纽的交通主管,在这里,东海岸铁路与吉隆坡-新加坡铁路相衔接:他是个熊腰虎背的男子汉,读书的品味让人意想不到,在人际关系方面相当敏感(他的所有助手都是印度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完美无缺的耐心。他的外貌像个军士长,但行为却像个医生。
东海岸铁路终止于彭亨州(译注:Panhang,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州名。)。日本人毁坏了这条铁路的延伸段,而B君管辖的这一段铁路正在重新铺设–他们对此事的感情相当复杂,因为要维持现存铁路的安全运行已经不可能了。南新加坡线路上的夜间邮政列车已经完全放弃;东海岸铁路线上,八台机车已经无法正常使用,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货车不能正常使用。一年之中,整个铁路系统发生了四十九起火车脱轨事故。至于种植园主中的伤亡人数,伤亡率这么高,多数军队觉得很难维系他们的士气。每节车厢里的铁路告示用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中文表达:告示:恐怖主义一旦铁路两侧发生交火建议旅客们趴在车厢地板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离开火车一月份,我与B君一起在火车上度过好几天。他的住宅前面一百码开外就是无法避开的丛林;带刺的铁丝网、警察哨位、一种受约束的感觉。随后,雨季来临,二十五年来降雨量最大。因此,除强盗土匪外,又增添了洪水、冲溃、塌方等问题。人们会有一种老天不公的感觉,就像纳粹德国空袭伦敦期间,在自己的民防区内发生一起严重事故时的感觉,另外,暴力袭击就是持续不断,没完没了。人们觉得上帝应当每次只给每人制造一个麻烦。
下面是“两个盟军”–共产党和自然灾害–两天的作孽时间表。自然灾害打头阵:星期五,上午十点。新加坡方向的南线铁路发生一起塌方。不过,发自吉隆坡的早班邮政车刚好已经通过,所以自然灾害不得不再次采取行动。下午两点。南线又发生两起塌方。这时,救险火车载着一队士兵出发,试图去清理铁道,为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开辟道路。
整个晚上,我能听见电话铃不时作响–这使我想起种植园主的住宅。星期六凌晨一点,发电厂遭水淹,于是就停电。凌晨两点一刻,共产党走出丛林,使救险火车出轨。凌晨四点,通往铁路枢纽的陆路完全被切断,东海岸铁路被洪水冲断。早餐时刻,供水中断–在倾盆大雨中,这可是一桩令人不爽的怪事。甚至四分之一英里外的车站也必须靠蹚水抵达。北边又发生一起塌方事故。
傍晚,我们蹚水前往车站,借着烛光坐在小吃部里,与此同时,各种信息纷至沓来。甚至铁路信号匣也只能用油灯昏暗照明;人影消失在长长月台的黑暗之中,整个朦胧的车站和它潮湿的场地有一种奇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仿佛电还没有运用。傍晚六点,南边发生一起冲溃,北边又发生一起塌方。晚上八点三刻,一列东海岸列车脱轨–这次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共产党干的。必须动员小镇上所有的劳力,借着油灯的光亮,给货车车厢装载道砟,但是有足够的劳力,足够的道砟,足够的货车车厢吗?这位个子高大耐心十足的男子汉不时放轻脚步走回到他的酒杯跟前,对着雨天、寒冷和敌人放声大笑,平静地等待下一份灾难电报。人们常常谈起士兵与平民,但是没有比B君更好的士兵了。这场战役与在丛林中跋涉搜寻一样非常危险,他的军队遭到洪水以及突击队的埋伏,他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一样,得到部下的爱戴。因此,我在吉隆坡经常发现自己在思考:如果政府官员像这些人–X君和B君–那样工作该有多好!不过,在没有危险的地方,你也许找不到勇气,而且爱戴也许也是战时的产物。
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外几乎无人明白。它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参战人员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人,在丛林中参战的少量马来亚人中,较大一部分人是印度尼西亚恐怖分子。我访问过吉兰州(注:Kelantan,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州名。),在这个州里,马来亚人占绝大多数,去那里就像到访异国他乡。这里平静安宁:你可以不带武器随意走动;公路上不需要护送车队;四周有一种幸福美满的气氛;人们的服饰比较艳丽;甚至太阳也似乎更加灿烂,因为丛林几乎已经渐渐远去。我已经多么厌倦那片昏暗敌意的绿色围墙:丛林不再是中立的了!
我们英国人的良知可以很清晰–我们不会在违背马来亚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控制他们;我们与他们一起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中国追随者,这是一场更加重大的战争,远不止报界使用“土匪”一词的含义。土匪不可能像这些人那样年复一年在艰苦的丛林中幸存下来:几千名土匪不可能坚持与几十万武装马来亚警察、两万五千名英国、廓尔喀(译注:Gurkha,西方国家对尼泊尔人的统称。)和马来亚军队作战。这些人是共产主义突击队,按俄国师的编制组建,有他们的政治机构,他们的教育机构,他们的政治委员,他们不知疲倦勤奋努力的情报机构。没人知道他们的总司令部在那里–也许在某个城市里,新加坡,吉隆坡,甚至在古老、相对安宁的马六甲城–但是,它的领导人却是路人皆知的。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人英勇战斗,曾行进在伦敦胜利大游行的队伍之中。
你必须在马来亚丛林中至少生活过几天才能理解它的艰难困苦和单调乏味。它比缅甸的丛林稠密得多,它妨碍行动,在丛林中一小时还走不到一英里。林中的能见度有时只有二十英尺。几乎每天大雨如注灌浇丛林,这使得无数山岗陡峭溜滑的山坡极难攀登。人们的身上没有一刻是干燥的,夜晚也没有一刻是安宁的–各种昆虫难听嘈杂的叫声不时打扰着初到乍来者和他的美梦。行军时暂时停下歇一歇,你就能看见许多蚂蝗朝你的靴子爬去–细火柴杆似的虫子,伸屈着身子在一片片潮湿的叶子上盲目地蠕动,稍后如果在你的衣服上找到开口处,它们就会膨胀成一条条肥肥的灰色鼻涕虫。还有那种永远不会散去的丛林恶臭–腐烂植物发出的浓重气味。这种气味会黏在你的衣服上久久不散。当你走出丛林时,你的朋友们会躲避你,直至你沐浴更衣。
在马来亚作战的英国部队很多–皇家燧发枪团、皇家海军陆战队、伍斯特郡军团、奥尔巴尼公爵团,仅举几个为例–如果列举我所在的廓尔喀步枪团为例,那只是因为他们非常好客,允许我随他们一起在彭亨州进行一次最小规模的作战行动。然而,敌人的确区分廓尔喀步枪团和它的其他对手。一份缴获的情报显示,敌人相当不公正地鄙视马来亚团,说英国军队非常勇敢,但非常喧闹–很远就能听见英国军队来了–不过,廓尔喀步枪团非常凶猛而且非常安静。
廓尔喀步枪团是一支雇佣军。这支部队的职业就是消灭它正式的敌人,也许因为它有一份真正的职业,所以它特别驯服。廓尔喀步枪团没有女人的麻烦–他们把一种妻子儿女的幸福家庭生活随军带到驻地。廓尔喀士兵领取薪酬,作为回报,他们对英国军官绝对忠诚,他们的长官报以爱兵如子,这在其他任何部队都是没有的。英国兵团的军官们抱怨说,他们在廓尔喀步枪团的同事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士兵,他们的士兵是他们的激情。
廓尔喀巡逻兵行动靠罗盘不靠道路。他们按直线运动。皇家空军轰炸了某个地区,据悉二百名共产党突击队员在那些特殊地图方块内的某个地方来回乱窜。一个由十四名士兵组成的廓尔喀排在一名英国军官的带领下,被认为足以完成侦察任务。巡逻队从营地直径出发,穿过炊事区,穿过狭窄的橡胶林区,进入热带密林。我们的目的地是这片丛林另一边的主干道,离开我们仅九英里,但是我们走了两天半,过了两夜才到达那里。我们出发比较晚,五小时行军后,我们就开始宿营。当确定我们方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丛林中穿行了三英里多。面前是重重叠叠漫无尽头的五百英尺高的山岗,溜滑的红土山坡几乎成四十五度斜角。廓尔喀士兵即便试图借助树枝攀登,但有时也难免滑倒,他们丛林靴的橡胶鞋底在烂泥和树叶黏液里无法支撑。
经验证明这种靠罗盘走陡峭山间小路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像英国军队那样沿着小路巡逻,你可以避开最难攀登的山岗(在这一地区,山岗有时高达两千英尺),也永远不必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但是,当你在巡逻的那一条小路上寻找敌人踪迹时,你是在拿全体将士的性命冒险。廓尔喀兵团的战术意味着,在一天时间之内,在寻找敌人踪迹的时候,你穿越了许多条小路;一根刚折断的竹子,竹液还是湿的,这也许是唯一的敌情。
四点半停止行军,给部队时间在天黑以前安营扎寨。首先选好几处哨位,然后用kukris(译注:印度廓尔喀人用的阔头弯刀。)(那种神奇的多用途武器)砍伐树枝,每两人搭建一间棚屋,一张铺地防湿布撑开遮在棚顶上,以防夜间下雨;另一张防湿布铺在用树枝和树叶建成的卧床上;在用砍刀开辟出一片空地架设无线电收发机,收发机的天线被投掷到一百英尺的高处。夜幕开始降临,这时kukri成了开罐器。在一只大约9x4x3英寸的罐头里装着廓尔喀士兵们的口粮–米饭、葡萄干、咖喱粉、茶叶、糖以及一盏小酒精灯和固体燃料,用以烹调。黑夜中,那一盏盏酒精灯微弱的火焰就像保育院里的夜明灯。我的同伴奇尔斯少校直挺着身子倾听,但不是在听共产党的动静。他低声说,“我总在倾听一种鸟 –黄昏和黎明都在听。听,那声音就是!像铃声。你听见了吗?”除了丛林营地的噪杂声,我啥也没听见。早晨六点,少校站在我们卧床边夜间暴雨造成的新泥浆里。“就在那里!你听见了吗?”他低声说。“像铃声!”经过一天半强行军和艰难攀爬,除发现两处被遗弃的营地外,一无所得。我们在离开出发地九英里的地方走出丛林–在作战指挥室的地图上可以添上两个纽扣,仅此而已;除一枚空炮弹壳外,甚至没有空袭的迹象,还有一处塌方,那也许是大雨造成的;例行的巡逻,常见的蚂蝗,常遇的疲劳,还有常闻的恶臭。
不过,我们可以沐浴和更衣,而共产党军队始终生活在他们潮湿的绿色樊笼里。
因此,为了提振士气,他们讲课,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用胶版誊写机印刷《列宁新闻》和《红星报》,召开自我批评会。与不知悔改的恐怖主义相比,显得多么奇特幼稚!人们可以用缴获的文件勾画出这种生活的景象:人们获悉李庆“不太卫生”,阿蔡“具有友善的团队精神”,刘奔有点懒惰,学习拖沓,“行为不太讨人喜欢”(他有时“担心形势”,他的同志们认为他“相当不成熟”)。
对待爱情,他们既严格又同情(丛林军队中有许多妇女)。从缴获的《列宁新闻》中,人们了解到未婚男女同志禁止呆在一起,除非获得高一级长官的特准。“我们不禁止任何人做爱。但是,这种性爱必须是符合规定的。一旦爱情确立,当事人应该向组织报告此事和确切情况。此事必须经过组织调查,然后根据组织决定通知双方。”下面是事先确定的讨论题:1.共产党人的爱情为什么是一种严肃的本能?
2.什么是正确的爱情观?
3.目前我们这个地区是否还存在少数几种不正确的恋爱观?
4.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5.原因是什么?
6.我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什么?
7.我们如何克服不正确的恋爱观?如何对待不正确的爱情?
想到这些问题是用漂亮的正楷从右到左的倒着书写出来,人们心中就会感到非常奇怪,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看来,自从两千多年前诗人枚乘用毛笔作诗以来,这种书法几乎没有变化,下面是枚乘写的爱情诗(埃兹拉?庞德[译注:Ezra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牗。
纤纤出素手……人们一想到这场缓慢耗时令人生厌的马来亚冲突,就会想起这首诗歌,多么不可思议的对比!有位巡逻兵发现了一个孤身一人的游击队员,他显然沉浸在一种文学练习之中–他必须从用胶版誊写机印刷的一些句子中发现并纠正错误。一个种植园主与他的妻子驾车前往吉隆坡俱乐部出席一次苏格兰晚宴,晚宴菜单是“苏格兰肉汤、迪河鲑鱼、羊肉杂碎布丁、土豆泥、碎萝卜、迪内高地特色菜、糖豌豆、烤土豆、巴尔莫勒尔圣代。”当消息传来他们两岁的女儿被华人共党分子近距离平射致死时,他们不是刚好在吃羊肉杂碎布丁那道菜吗?“党解决了爱情问题。”\\\\\\\\\\\\\\\"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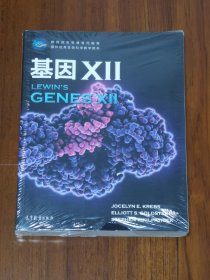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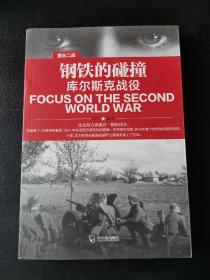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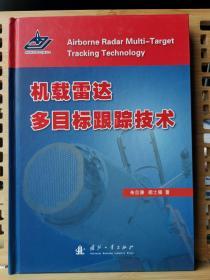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