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伽门农的女儿(精)9787229158224
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33.53 6.7折 ¥ 49.8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阿尔巴尼亚)伊斯玛伊尔·卡达莱|责编:秦琥|译者:孙丽娜
出版社重庆
ISBN9787229158224
出版时间2021-09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49.8元
货号31234871
上书时间2024-07-2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伊斯玛伊尔·卡达莱(IsmailKadare),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936年卡达莱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诺卡斯特。1954年他以诗集《青春的热忱》初登文坛,此后创作了《群山为何沉思》《山鹰高高飞翔》《六十年代》等,在诗坛独领风骚。1963年,他的首部小说《亡军的将领》问世,在法国名声大振。之后创作了《雨鼓》《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阿伽门农的女儿》《金字塔》等代表作。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共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著名文学奖,包括2005年的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2009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2015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奖、2019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卡达莱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译者简介:孙丽娜,长春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目录
长城
致盲敕令
阿伽门农的女儿
内容摘要
《阿伽门农的女儿》一书包含三个中篇小说,分别是《长城》《致盲敕令》及《阿伽门农的女儿》。本书讨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统治。
《长城》围绕对峙在长城两侧的一位明朝官员和一个蒙古士兵展开,最终征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却无法突破明朝的薄弱防线,文中以长城为分水岭,记录了不同地区之间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交流,长城也成为见证死亡的碑铭。
《致盲敕令》的背景是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改革,描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家族在帝国政治下的悲哀命运,详细写出了专制政体的运作模式。 《阿伽门农的女儿》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的阿尔巴尼亚,借助两则希腊神话,展现现实生活中主人公和一位高官女儿的爱情的失落和国家机器的残忍,讨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
全书情节循环往复,有如迷宫般精巧别致,是一部充满荒诞与隐喻的黑色寓言。
精彩内容
长城LaGrandeMuraille宋督察
蛮夷迟早都会回来的。我的副将叹息着说道。我猜他此刻一定正在望着远方,那里可以看见蛮夷们的马匹。
至于我,我正在思考的事情是,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无论是它那一个个的小镇,还是那些大城市,或是它的都城——虽然那里的人的确要比乡下人知道得更多——当游牧民族穿过长城的时候(甚至那些作为官方代表团穿过长城的游牧民族),你在哪里都找不到一个人不去评论说,蛮夷迟早都会回来的。同时,他们还会发出一声叹息,这样的叹息通常是在感慨一些你认为最后会带着欢喜的悲伤去回顾的事情。
这里的一切几十年来都像墓地一样安静。但那没有阻止我们帝国的子民去想象一场无休无止的残酷战争,长城这面是一方,北边的游牧民族是另外一方,双方永远都是挥着长矛彼此拼命厮杀,有时还会用上硅石,眼睛被挖出来,头发被扯下来。
但是当你想到人们不仅会用英勇的虚假光环来粉饰长城,还会把它其余的部分——它的结构、它的高度——想象得与它真正的样子完全不同,你就不会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他们不会自己去看看,尽管长城有的地方建造得的确很高——确实,有时它高得如果你从它的顶端向下看,就像从我们此刻站着的地方往下看,你会感到晕得厉害——但沿着它一直那么走下去,你会看到它大部分都亟待修护,那副惨淡的样子真是可惜。它已经被废弃得太久了,墙上的砖石一直被当地的居民窃取;城墙本身也有坍塌;现在几乎看不出墙头那种凹凸起伏的线条,在有的地段,它只是名义上的长城罢了,只是几块石头的结构散落在那里,就像无人知晓什么原因建造的工程剩下的残骸。如今它就是这般模样,就像一条蛇在稀泥中游走,以至于在长城蜿蜒到戈壁滩的边缘地带时,你根本无法看清它——它很快就被吞噬掉了。
副将的眼睛一片茫然,就像某些需要一直盯着远处的眼睛一样。
还没等他开口问我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便对他说:“我们在等一个命令。”显然,与游牧部落使团谈判的结果会决定命令的内容——如果能做出什么这类决定的话。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等待命令的到来,直到避暑时节结束的时候,皇帝和大臣们应该都回到都城了。秋风吹来,然后是冬天里夹着雪花的冷雨,可是仍然没有什么决定传达到我们这里。
就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命令,更像是某种回响,总是在所有人已经不再去想它的时候突然到来。我把它称为一种回响,是因为早在宫里的信使来到我们这里之前,我们就从一些村民那里了解到了政府的决定,那些村民居住在防御工事沿线的村庄或帐篷里。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村舍迁到附近山上的洞穴里,每次听到消息他们都会这么做。他们总是能极其神秘地得到消息,甚至比我们接到马上开始修复长城工事的通知还要早。
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种明智的迁移,因为逃到山里,且不说其他形式的一些痛苦,至少他们可以免受官家的折磨。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直从长城的城墙上拿走砖石去搭建自己的屋舍和院子,他们非常清楚,总归得将砖石送回来重建长城。
他们告诉我,这种事情几百年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像用来织成围巾的缕缕毛线——会被拆掉重新织成毛衣,然后又被拆掉织成另一条围巾,周而复始——城墙上的大石块已经在村民的屋舍和长城之间这么周转过很多次了。在有的地方,你甚至能看到烟灰的痕迹。游客和外国使团可能会被它们引发各种遐想,却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些痕迹不是什么英勇刀剑的铿锵印记,只不过是灶台的烟火留下的炭灰,多少年来,某间无名屋舍的主人一直在这里烹煮他那寡淡无味的稀饭。
所以,当我们今天下午听说村民们已经搬离了他们的住处,我们就猜到,整个中国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要重建长城的消息。
虽然这标志着紧张局势的升级,但修复工作并不能加速战争的爆发。与武装冲突不同,重建工作时时发生,以至于长城很容易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重建。总的来说,它说不上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长城,不过是无数次接替性的修补罢了。人们竟然假装长城在一开始出现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在旧城墙上加以修补,也不过是对之前的城墙,或是更古老的城墙进行了重制而已。甚至有人提出,起初最早的城墙建立在国家的中心,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修补之后,它逐渐离边界越来越近,在那里,就像一棵树终于被移植到了合适的土壤中,它长成了巨大的样子,以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感到害怕。人们无法想象没有了蛮夷的长城,他们甚至认为正是蛮夷的出现才促成了长城的修建,或者说,也许正是在边境兴建长城,才招致了蛮夷的出现。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蛮夷使团的到来,然后又看着他们离开,我们也许也会像为数不多的那些人一样,认为这种紧张局面(就像之前发生的大多数事件一样)的出现缘于这个国家内部,甚至国家中心,频频出现的纷争。只要了解无数谎言中的一个真相,那种沾沾自喜的满足便会让我们将漫长的夜晚用来构想各种各样的假设,去猜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还有宫廷中正在筹划的种种阴谋。这些策划如此机密而错综复杂,以至于即使是谋划者恐怕也很难解释清楚;这些策划也有可能源自猜忌,它们如此有力,以致人们说它们可以在黄昏时分将妇人的镜子击碎,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蛮夷就在我们脚下来了又走。我们仍然能回想起他们宽松外套上彩饰的镶边,还有他们马蹄的嗒嗒声——不会忘记我副将说的那句“蛮夷迟早会回来的”,还有他的叹息、他那空洞的眼神。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至少假装有那么些许的疑惑,但是这次,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不管冬日的夜晚多么无聊,我们总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时间,除了关注蛮夷的到来,断然不会去编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国家的焦虑。
来自北方的一种隐隐不安正在我们心中升起。这个国家日趋紧张的局势,如今看来并非源于一种外部威胁是否真的存在。正在日渐明朗的是,从现在起,唯一的问题是战争是否真的存在。
第一批石匠已经到了,但是大多数还在路上。有人说路上还有四万人,还有人说要比这还多。这绝对是最近几百年来最重要的修复工程了。
更听得,悲鸣雁度空阔。昨天,去北边的荒地检查时,我突然想起了这行诗句,可惜作者的名字却想不起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空旷的恐惧是让我最感到不安的地方。他们说,如今蛮夷只有一位首领,他正在试图建立统一的国家。目前,我们对于那位首领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跛子。那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知道他跛脚。
最近几天以来,蛮夷一直在薄雾中出现,像是一群群的寒鸦,过一会儿又消失不见。很明显,他们也在关注着这里的修复工作。没有了长城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何生存下去,我敢肯定,对他们而言,长城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它一定深深地困扰着他们,就像北方的空旷困扰我们一样。
蛮夷勇士库特卢克我接到的命令,是骑着马不停地疾驰,要一直监视着它,无休止地做同样的事情,石头上面的石头,石头下面的石头,石头左面的石头,石头右面的石头,以及所有的石灰缝,可是不论我来回飞驰过多少次,那些石头都没有变化,一直都是那样,就像那该死的风雪,总是与那次一样。
狗年年尾的时候,我们纵贯西伯利亚追击托克塔米,当时我们的可汗帖木儿告诉我们:“将士们,一定要坚持住,因为它只不过是风雪而已,不过是发威的母狼逞逞能罢了,你只要等上一会儿,它就会变得柔和湿润。”可是这支石头军队却危害更大,它不会脱落也不能融化,它挡住了我的去路,真不明白可汗为什么不下令向那破石堆进攻毁掉它,就像在怵布卡巴德,我们用手按住巴雅茨德·亚德姆苏丹,当时可汗对我们说了这么一句话:“荣耀属于你们这些征服雷霆的人,纵使你们还未曾掌控整个天庭,但那迟早会实现的。”后来,虎年的时候,我们在阿克什赫把所有的战俘活埋,所有人都紧抱双膝,就像在母亲子宫中的姿势一样。当时,可汗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是无辜的,如洽特什巫师所坚信的,那么大地母亲,她的子宫比任何女人的子宫都要丰饶,会给他们第二次生命。”哦!那些日子多好,但我们的可汗再也没有发来命令,让我们把一切夷为平地,而且首领们聚集在库里台大会上时,也不过七嘴八舌地尽是废话,竟然声称那些人们称作小镇的地方不过是些棺材,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小心,绝对不可进入,因为一旦进去就再也无法出来,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是可汗还是没有发来进攻的命令,一直以来,我所接到的一遍又一遍的命令就像那可恶的砖石:“勇士,继续观望!”宋督察
长城整个西北沿线的修复工作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每周都会有成批的石匠到达,他们所在省份(朝廷的各个地区争相以最大的规模向长城地带输送劳役)赠送的五彩旗帜和条幅耀眼地招摇着,但是在哪里都看不到军队的调动。蛮夷的侦察员还是像往常一样在远处疾驰而过,但是随着冬天的到来,雾气更加厚重,很多时候我们无清晰地将他们辨认出来,看不出是马还是骑手,以致有时候他们不像是骑着马的将士,倒像是来自什么地方战场上残缺的肢体,被狂风驱赶着成群地飞过。
眼下发生的事情让人很难理解。一开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军事演习,每个阵营都在试图通过对另一方的蔑视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但是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当中包含了极其不合常理的因素。我非常肯定,这是长城地区与京城之间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脱节。我之前还以为它们是牢不可破地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我在京城当差时有这样的想法,在那之前,当我还是西藏偏远山区的一名小吏时,也是如此考虑的。我当时总是觉得,它们之间互相牵扯,就像人们说到的月亮与潮汐的关系。来到这里之后,我所了解的是,虽然长城无法移动到京城那里——换句话说,它可以将它朝自己的方向吸引,或者也可以将它推向更远的方向——京城却没有力量来改变长城。它顶多能试图移动一下,就像苍蝇试图避开蜘蛛网,或是来到近前以便依偎在它的胸膛,像一个害怕得抖个不停的人,仅此而已。
在我看来,长城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恰恰可以解释过去两百年里中国都城的迁移——它向中国南部迁移,到了南京,尽可能远地离开长城,然后它又迁回北方,迁到尽可能靠近长城的地方,北京,这里第三次充当起中国都城的角色。
最近几天我绞尽脑汁地想找到一个更加确切的解释,来弄清楚近来发生的一切。有时候我以为这种摇摆——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直接受到与都城距离的影响。比起要用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的都城,较近的都城发出的命令可以更加容易地撤回——都城过远的话,撤销命令的第二辆马车要么没有追上第一辆,要么因为速度过快或是信使过于焦急而翻了,或是第一辆马车出了事故,或者它们都出了事故,等等。
昨天晚上,我们闲聊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轻松聊天的一种方式,经常是在花了一些功夫将其他人的看法隐去后才开始,因此尤为可贵),我的副将断言,如果不只是都城而是中国本身想要迁移,长城绝不会有一寸的移动。“另外,”他又随口说了一句,“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的确,我们两个都一下子想到了,自从长城建成以来,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不止一次地扩张出自己的边界,把长城撇在一边,没有任何意义地将它丢弃在灰色的荒原中,与此同时,中国也以同样的次数缩回到自己的边界之内。
我记得,有个姑姑小时候曾把手镯戴在手臂上。等她渐渐变得丰满的时候,那个手镯还是留在手臂的原处,已经快要被埋在她手臂的肉里了。这件事让我想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长城一会儿勒紧它,一会儿又放松。到了近些年,它看起来大小正好。至于将来,谁能说得准呢?每次我看到我的姑姑,都想起她手镯的故事,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到好奇。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去想,如果手镯没有被及时取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还有,极端的是,我竟然能听到它在她死后还叮当地响个不停,甚至一直松垮地挂在她骨架的手腕处……我双手拢住头部,感觉有些尴尬,竟然想象中国正在随着她手腕上琐碎的装饰一起烂掉。
夜空中看不到星星,但是月光明亮,让你有种很强的慵懒之意,以至于你会以为明天一早所有人都将放下所有的活动——那些蛮夷,那些鸟儿,甚至举国都会平躺着不动,疲惫不堪,如尸体一般并排摆放着,死气沉沉的,就像此刻我俩的样子。
我们最终知道了蛮夷统帅的名字:他叫帖木儿,人们称他为跛子帖木儿。据说他曾经发起了对奥斯曼帝国恐怖的战争,在俘获他们的国王——被人称为雷霆王——之后,拉着他游行,从大草原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很显然,不久前他已经计划对我们用兵。如今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重建长城的命令,还有这眼前的平静,我们都不知所措地称之为“谜题”,不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无法理解国内的工作部署。在他对付土耳其的时候,这个一条腿的恐怖分子没有构成一点威胁,可如今……昨晚返回的信使带来了让人不安的消息。在我们王朝的西部边界地区,就对着我们这边的长城,离它不到一千英尺的地方,蛮夷已经建起了一种瞭望塔,不是用砖石砌成的,而是由割下的人头垒成。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并不算高——也就两人来高——从军事的角度看,它对我们的长城也算不上什么威胁,但是那些头颅透出的恐怖,要比一百个要塞还有威慑力。虽然召集了士兵和石匠,将那堆头骨的事情向他们做了解释,告诉他们,那与我们的长城相比,还不如稻草人有效果(乌鸦还是围着它到处乱飞,这就是比喻本身要表明的意思),可是每个人,包括士兵在内,都感觉有阵阵阴风从身边吹过。“我从来没往京城寄过这么多的信件。”信使拍着他那皮革鞍囊说道。他说,大多数的书信都是军官的妻子写的,写给她们的闺中好友,诉说在这里让人难以忍受的头痛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就是想让好友帮忙,看看能否将她们的丈夫调往其他职位。
信使还说,那堆头骨散布的可怕气氛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它一出现,就让长城的威力大大减少,之前信使曾经向神灵祈求,希望长城的修复工作在这种恰当的时机下能尽早完成。
信使讲的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沮丧。虽然不愿承认,但我们知道,今后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长城损毁的部位、城墙上的裂缝,还有那些修补过却仍不牢固的地方。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出那堆头骨的样子。信使刚刚离开,我的副将就对我说了一句古语:“鸡蛋碰石头——不堪一击。”这句话中每个字的一笔一画我们都清清楚楚,这还多亏启蒙老师的戒尺——如今这法子早已经过时了。这样看来,那些头骨不过是为了对抗长城所选择的一种武器罢了。
边界附近还是没有军队的调动。一场严重的地震毁掉了所有的东西,唯独没有长城,早就听说它能应付地震的袭扰。上一次余震之后,周围笼罩的死寂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正在进行的重建工作给我的印象是,一点也不仔细,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地震前的一天,我们右面那个充当瞭望塔的建筑又坍塌了,在这之前它已经塌过两次。这让我想到,对于朝廷的不忠已经侵蚀到这座威严的宫殿了。我的副将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以来都坚信,都城的人纵情酒色,已经深陷歌舞升平之中,哪还有人去想蛮夷和前线的存在。就在昨天,他对我说,他之前听人说起有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镜子——它比男人的阳物大上两倍。女人们在做爱之前把它们带入自己的卧室,能起到催情的效果。
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除了几个侦察的骑兵时不时地疾驰而过,长城的另一边似乎也没有任何动静,再有就是,我们偶尔会看到小股破衣烂衫的突厥兵士。突厥人第一次出现是快到夏末的时候,我们的哨兵仓皇报告。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大概是作战部队,乔装成溃散的突厥兵,后来我们从混入其中的线人那里接到报告,原来那些人实际上是帖木儿在怵布卡巴德击溃的那些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残余势力。他们已经沿着边境线游荡了好些时日了。他们中多数是老兵,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们的思绪就会回到那片遥远的故土,那片土地上有他们为之奋斗的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他们也许还会想起他们的巴雅塞特苏丹,他的记忆会跟着他们踏过草原,就像一道冷漠的闪电。
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想要加入长城的修复工程;在右面那个瞭望塔接连倒塌多次之后,其中一人更是十分坚持,实际上他已经私下见过我,用蹩脚的汉语告诉我,他曾经在很远的一个地方见到过一座桥,在它的一个桥墩上镶着一个人。他用手指着眼睛,发誓他的确见过这样的场景,他甚至向我要了一块纸板,说他可以在上面画出那座桥的样子。那不过是一座小桥,他说,但是为了防止它倒塌,就得为它提供祭品。那么,这么宏伟的长城要想屹立不倒,怎么能没有类似的东西呢?
几天之后,他又来见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详细地画了一张那座桥的草图。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上下颠倒地画图时,他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我不知道,”他答道,“也许是因为这是它从水中看上去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前天晚上我在梦中见到的就是这样,是上下颠倒的。”他离开之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他那奇怪的草图。我盯着它看了好一阵子,感觉我都快看到那座桥开始颤动了。要么就是因为那个突厥人之前告诉我,那座桥在水中的倒影要比桥本身还让他记忆深刻?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那是从水中看事物的角度——那个突厥人说过,这种观点与常人的想法完全背离,或者说那种所谓的人类的观点。是那片水域需要将人镶在桥上来祭祀(至少,传说是这样)——就是说,将一个人处死。
那天晚上稍晚一点的时候,月光斜斜地照在城墙上,时不时地显现出人影的形状。“该死的突厥人!”我暗暗地骂了一句,心想一定是他在我的脑袋里搅起这么恐怖的影像。我突然想到,那座上下颠倒的桥,也许正是此时这月光下的世界中善与恶在不断涌现的一个缩影。极有可能的是,朝廷之间的确就是在用那样的方式传递消息——那信号早在几百年前或是几千年前在宣称,他们派出的使团即将带着他们用黑蜡封好的信件到来。
蛮夷勇士库特卢克首领们已经聚集在忽里勒台,帖木儿可汗的命令已经抵达。“千万不要冒险越界到另一边,”上面写道,“因为那样你们将万劫不复。”可是越不让我去,我反倒越想跨过去看看那里的城镇和那里的女人,听说她们在锃亮的镜子中能变成两个人,除了一层他们称之为丝绸的薄纱什么都不穿,女人的快乐夹缝比蜂蜜还要甜美,可这些该死的石头堆不让我过去,它阻碍着我,压抑着我,真想用短剑将它刺上几下,虽然我也清楚,铁器对它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两天前的地震它都能经得起。当颤动的大地和那石墙在彼此较量的时候,我在震动中高呼:“你是唯一能让它倒下的!”可最终还是没有什么作用,城墙胜出了,它让地震偃旗息鼓。望着地震最后的几下抽搐,我流下了泪水,就像一头被人砍断喉咙的公牛,直到,唉,我看到它没了气息,老天啊,我是那么伤心,就像那次在别特-帕克-达拉平地上我对统帅阿巴嘎说的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大喊几声。”他对我说:“这片草原叫别特-帕克-达拉,是饥饿的草原,如果你体会不到自己的饥饿,就会感受别人的饥饿,那么策马前进吧,孩子!”那就是他们告诉我的:草原的儿子,策马向前,什么时候都不要停下来,可如今这堆石头让我无法前进,它挡住了我的去路,它与我的战马赤膊对峙,它的骨子里都在嘶喊,我感到自己正在被它拉进阴森的灰泥中,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它正在把我的脸变成灰白色,正在让我融化,将我漂白,啊……宋督察
日子还是这么一天天无聊地过着,就好像被突然切换到了晚年。我们还没有从周末遭受的地震中恢复过来。
他的两轮战车停在我们的瞭望塔前,他说:“我来自教坊司二十二号。”从那时起,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或者说是某种极其类似的感觉。我问他那个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真的想为长城修复工程中的军士和匠人们演奏几首曲子或是唱上几段,他高声大笑了几声。“我们部里的人很多年不做那种事情了!”他接下来对我们说的更是令人惊骇,以至于我的副将一度打断他,哀伤地向他询问:“那都是真的吗,还是你在开玩笑?”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当然听说过,朝廷中的一些部、署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名号,可是职能早已完全改变了——但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听说为皇帝提供增强性能力的药,竟然成了水军要员的主要工作,而舰队却掌握在宫中大太监的手里,唉,没人知道这些人的脑袋都在想什么。他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你知道现在铜矿和铸造厂归谁管吗?这些天谁在操控外务决策?谁在掌控朝廷事务?”对于他的倾听者流露出的慌乱,他下巴一沉,带着沾沾自喜的满足。他在那儿自问自答,就像将啃了很久的骨头扔向饥饿的野狗。他压低声音,向我们道出了实情,如今负责阉割太监和特务工作的是内阁。他根本没给我们时间喘息,继续透露说,最近,皇宫里的太监集团掌握了不可名状的权力。他认为,那些人不久将完全控制朝廷,中国也许再也不会被称作天朝上国了,或是中央之国,倒是可以轻易地成为阉人的天朝。
他狂笑了几声,然后脸一沉。“你们不妨也笑一笑,”他说,“可是你们不知道,一旦清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恐怖。”没有一丝笑意,更谈不上大笑,我们的脸色变得像焦油一样黑。他还在那里继续说着,每句话都带着一句“你们不妨也笑一笑,可是……”,在他看来,我们笑了也不会意识到随即到来的灾难。因为我们不知道,男子气概的丧失会使一个男人的权力欲增大十倍,等等。
夜晚悄悄地到来了,他这次喝得更多,尤其是快结束时,那种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的快感还有那种来自京城的骄傲,怂恿他向我们泄露了更多可怕的秘密。也许他说得太多了,可是每一句都很有分量,从中你能感觉到,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当今的局势。当我们开始议论来自北方的威胁时,他又像之前一样轻蔑地大笑起来。“和蛮夷开战?你们怎么这么天真?我可怜的、亲爱的吃公家饭的兄弟们,你们竟然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长城的重建工程?开不开战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那是与蛮夷签订的第一份秘密协约中的一个而已!你们为什么那么看着我,眼神像鳕鱼一样呆滞?是,就是呀,长城的修复工程只是蛮夷所提要求中的一个而已。”“不,不会的!”我的副将伤心地说,一下子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我们的这位客人从容不迫地继续说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游牧部落的侵袭,但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事情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呀,”他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的确,很久以来,中国都很惧怕蛮夷,而且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理由惧怕他们。但是也有一些时候,蛮夷是害怕中国的。如今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候。蛮夷惧怕天朝。那就是他们坚决要求重修长城的原因。”“可那多疯狂!”我的副将说,“害怕一个国家,却让它加固边防,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老天!”我们的客人喊了一句,“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让我把话说完……你们那么瞪大眼珠子盯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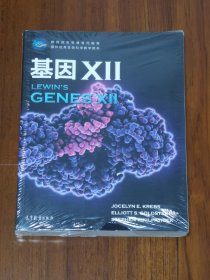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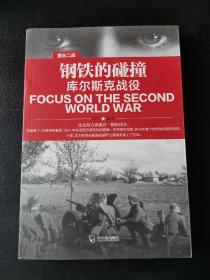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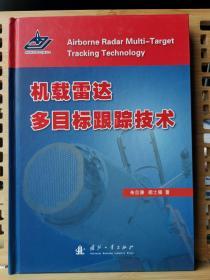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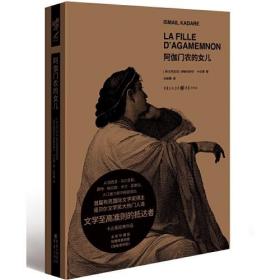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